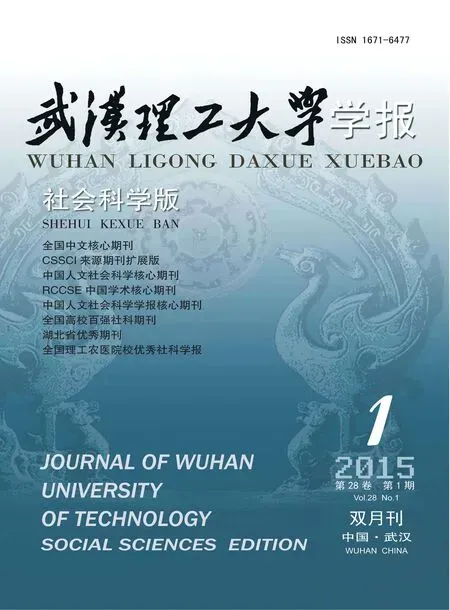“观看”与“倾听”:西方的两种深层审美范式∗
郭玉生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观看”与“倾听”:西方的两种深层审美范式∗
郭玉生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在西方文化中,视觉能力和观看行为在对理性认知和审美观照方面被认为具有超越其他感官的优越性。然而“观看”的审美范式表现出来的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具有等级制特征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对个性、差异性、多样性的压抑与专制。相反,通过“倾听”的审美范式,人能够领悟存在的真理,即世界是一个包容与接纳万有的整全,物质与精神、自然性与神圣性彼此交融地存在着。
观看;倾听;审美范式
观看是人生存的基本形态之一。人与其文化和世界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视觉和观看来实现的。在人的各种感官中,人的观看方式对于使用语言、进行思想分析以及认识世界都有重要作用。观看所给予的效果,不只是一种图像式的描绘,而且能够引起人类整个肉体和心灵上同步而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不只是局限于肉体和生理的欲望层次,而且也激荡起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对于人类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艺术的表征机制塑造了人的“上帝之眼”,摄影塑造了人的“科学之眼”,平面影视图像则塑造了人的“欲望之眼”,而“好奇之眼”则是后现代的文化机制决定的,它不要求我们的眼睛去看到上帝的绝对、科学的真理、无意识的欲望,它只要求我们的眼睛永不停歇地随着主体身份的不断变化而“游目”。由此可见,无论何种“观看方式”都已戴上了无形的“文化眼镜”,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一系列的文化机制所制约。
最初,西方文化并不是一种视觉文化,而是一种听觉文化。古希腊社会最初是为听觉文化所主导的。例如,尼采从音乐的精神之中引出了古典希腊文化的核心发明——悲剧。在荷马笔下的贵族群里,听觉是头等重要的。[1]213西方文化中视觉的优先地位最初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初叶的希腊。赫拉克利特就宣称:“眼睛是比耳朵更为确实的依据。”[2]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标志着古希腊文化从听觉优先向视觉优先转移。视觉为先的原则由此开始统治了西方文化,到当代以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的时代更是达到了它的顶点。视觉能力和观看行为在对理性认知和审美观照方面被认为具有超越其他感官的优越性。视觉在其他感官中的首要地位而形成的感官等级制和视觉在思想中的核心功能所确立的视觉中心主义,也使它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对传统进行反思和重构的关键所在。例如,麦克卢汉在《理解传媒》等一系列的著作中指出西方人一直生活在视觉至上的时代,以延续性和同质性为其特点,一切井然有序。相反,听觉世界是同时态的电子世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但听觉文化的优势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它不再居高临下颁布法令,而是加深我们对他人和自然的关怀;比如它意味着理解、含蓄、接纳、开放和宽容,等等。“观看”与“倾听”因而被看作一种态度,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一种行动及行为的方式。
在古希腊传统中,知识和理性是寓于“看的视觉空间”。古希腊语中的“知道”实际上就是“看”的意思。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真理就是被去蔽之物,明了、清晰、显著就是能被清楚看到的对象。受此影响,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洞口的“太阳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之光,到启蒙运动的“Enlightenment”,西方每个历史阶段的思维方式几乎都假定了“视觉”的普遍有效,都和“光的隐喻”密切相关。
由此出发,西方古典美学把美和艺术首先作为一个知识的对象来认识的,表现出对于理性分析获得的知识的无尚崇拜精神。审美总是使人从日常生活中超拔出来、抽身出来,观感、吟哦、思虑、怀想,审美的境界总是被领会为比世俗生活更高、更纯粹、更富有精神性和崇高价值的境界,因而审美一直被看成是一种人生意义的领会和价值的追思的活动。柏拉图认为人开始凭借感官对个别的有形体的美的事物的认识,逐渐上升,最后豁然贯通凝神观照美本身这种真实本体,从而进入最高的生活境界:“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3]在柏拉图看来,美的理念是感性事物之所以美的根本原因,人通过感官能够感受到美,那也是因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它在下世之前,曾观照过美的理念。由此感性事物引起了人的灵魂对美的理念的回忆。亚里士多德同样把理性的知识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较之其它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4]因此,亚里士多德判断文学艺术的最后标准仍然是知识。他认为文学艺术比历史更有必然性或普遍性,它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使人获得求知欲的满足。某些东西实际上看上去会使人感到不快,例如难看的动物和尸体,但惟妙惟肖地模仿这些东西的画像却能引起人的快感。这原因就在于人们在观看画像的时候,可以一边看画,一边在求知,推断每一画像是何物,从而获得快感。由此可见,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快感源于求知活动,文学艺术通过生动可感的具体形象给人以真理,所以文学艺术具有自身的存在价值。
中世纪审美文化主要表现为基督教审美文化,在基督教信仰中,可见世界乃是不可见的上帝的产物,因此,万事万物都深藏着上帝那难以察觉的意图,都是那难以觉察的意义之象征。这样,人们的眼光不会停留在事物本身,而总是要探询它隐喻的深意,即所谓事物的深度意义。中世纪美学家认可绘画的存在,这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图像虽然不可能直接达到对上帝本身的认识,但是它们可以对人们认识基督教的终极真理发挥启迪作用。在中世纪的教堂建筑及绘画中,注重对光与色彩的运用。根据基督教教义,上帝是绝对的存在,它意味着无限与永恒。感性的物质媒介无论具有怎样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都不足以显现上帝的灵性与完满,但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难以理解的神启。由于在所有的感性媒介中,光是物性因素中最轻微的,因此基督教经常把“光”当作上帝的隐喻与象征。同样,彩画玻璃要想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只有在受到光的照射下才有可能。色彩被基督教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比如,金黄色象征上帝,红色象征上帝的爱,紫色象征上帝的服色,绿色象征希望,蓝色象征天国之色,彩虹象征上帝的灵光四射,等等。对“光”与“色彩”的格外关注是基督教审美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是其对西方审美文化的卓越贡献。
作为近代美学的代表人物的黑格尔指出:“一切艺术的目的都在于把永恒的神性和绝对真理显现于现实世界的现象和形状,把它展现于我们的观照,展现于我们的情感和思想。”[5]黑格尔的观点显示了在西方近代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潮中,衡量艺术最高价值的标准是看它能否给人提供普遍性的真理,艺术品的感性形式并不具有独立性,它的价值是使普遍性的真理在想象力和直觉面前历历可辨。可以认为,黑格尔把艺术看作绝对精神的一种自我观照方式,由此建构的“观看”的审美范式超拔于人的感官享乐或自然欲望而受到理性文化的制约和支配。因此,福柯提出,视觉性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话语谱系和知识型的一个重要层面,它涉及现代权力与话语的共生关系。根据福柯的观点,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充满了暴力、专横、封闭、控制、隔离、排斥、压抑的历史,知识和权力都是权力的共生体,而凝视、注视在权力技术中具有重要地位,从而产生了“看”与“被看”的现代权力形式。凝视、注视是伴随着权力运作的观看方式。观者被“权力”通过“看”赋予主体地位,而被观者则沦为“看”的对象,丧失主体地位,成为异化之“物”。这种“看”与“被看”的权力形式的运作是通过诸多复杂的规则来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例如所谓真与伪、善与恶、理性与疯癫、正常与反常、科学与非科学等一系列的区分和对立。通过这些区分和对立,形成了某种排斥、压抑和控制的权力运行机制,有些观看方式是可以被接纳的,有些则必须排斥。真的、善的、理性的、正常的和科学的是被认可和接纳的,而其对立的范畴则是要加以排斥的,这便构成了认知型的视觉话语。
这样一来,现代社会确立了很多审美的、科学的、理性的观看原则,这些原则制约着每个人如何去看,也决定了他看到什么,或者说要看什么,对所看之物给予怎样的褒贬评价等等。例如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涉足绘画、电影等视觉艺术的分析,发现女性受男性目光的束缚和影响,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女权主义“凝视”理论。女权主义认为,女性经常以消极被动的方式迎合男性的目光,希望被男人喜欢和欣赏的意识取代了她的自我意识,从而失却了自身独特的体验和言说方式。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劳拉·穆尔维1975年发表的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是当代电影研究和女权主义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该文认为,好莱坞电影的一个特点是把女性的外貌编码成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色情形象,而且这种编码方式遵循“男性凝视”的原则[6]206。男性的凝视控制和约束女性,女性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被置于被观看和被展示的位置上,只是一种证明男性强大的对象和工具。穆尔维指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供投射了男性欲望的被看对象——女性身体,电影(也包括其他媒介形式)必然会选择以视觉快感为轴心的方式来安排。“女人作为影像,是为了男人——观看的主动控制者的视线和享受而展示的”[6]215,“电影为女人的被看开辟了通往奇观本身的途径。电影的编码利用作为控制时间维度的电影(剪辑、叙事)和作为控制空间维度的电影(距离的变化、剪辑)之间的张力,创造了一种目光、一个世界和一个对象,因而制造了一个按欲望剪裁的幻觉。”[6]219-220这样,通过凝视机制,女性将男性的观念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内化,由“自为的人”异化为“为他的存在”。
因而可以断言,“观看”的审美范式表现出来的就是等级制的单一世界的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对个性、差异性、多样性的压抑与专制。所以卡西尔提出:“人不能狂妄自负地听从自己。他必须使自己沉默,以便倾听一个更高和更真的声音。”[7]倾听的拉丁文一词是obaudire,其含义是以恭敬和理解的态度听取他者的声音。通过倾听,人可以进入某种不同的东西,尊重它而不仅仅是支配它。因而在倾听的审美范式中,人能够领悟存在的真理,即世界是一个接纳和包容万有的整全,物质与精神、自然性与神圣性彼此交融地存在着。真正的人类文明要求对神秘性和外在世界的特殊性的维持,需要一种对神秘事物的热情。由此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埃克哈特尤其推崇听:“听的力量,远远要比看的力量更为宝贵,因为,人们通过听所获得的知识,胜于通过看所获得的,通过听,人们更加得以生活在智慧之中。……去听,更多的是向内,而看,则更多的是向外,至少就看这个活动原本的含义是这样。因此,在永生之中,我们的福乐,依靠听,远胜过依靠看。因为,听那永恒的道,那是在我里面,而看,却是离我而去;在听的时候,我是在接受,而在看的时候,我却是在做事。可是,我们的福乐却并不有赖于我们所做的事,而在于我们从上帝那里的领受。”[8]观看是主体的主动投射,是对于差异和他者的暴力支配和占有;倾听则是人的承受,它从四面八方感受到万物的声息。所以浪漫主义美学与偏爱光和视觉的启蒙主义美学恰恰相反,它已经转向了黑夜和听觉。
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的重要思想家,他第一次明确而严格地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他认为,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所说的都不过是某种“存在者”,而不是“存在”,造成这种“存在”被存在者所遮蔽的原因,是肇始于古希腊哲学的认知方式,即以直观的“看”为特征的研究世界方法,所以他的哲学并不是再去研究“存在者”,而是要去追问“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强调世界从来不是立于我们面前让我们观看的对象,真理是让存在者自由敞开地是其所是的无蔽状态。所以真正的艺术并不以塑造美的形象为最终目的,它是存在者之无蔽存在的揭示和自由展开的“真理”。然而现代人由于受到技术时代的理性逻辑的控制,精于算计和各种功利性活动,已经忘却了自己的本真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强调人诗意地栖居,从而虔诚地聆听神性的启示,以自己充满劳绩的自由创造,繁荣我们的大地,丰富我们的世界。海德格尔将诗理解为诸神的命名和万物本质的命名,认为存在之为存在乃是在语言表达关系中确立起来的,故而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语言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是诗,诗人则是人的这个栖居地的守护人。诗的本性是倾听本源性语言沉默的、无声的、孤寂的“道说”,并使这无声的、沉默的、孤寂的“道说”发声地说出。“作诗(Dichten)意为跟随着道说(nach-sagen),也即随着道说那孤寂之精神向诗人说出的悦耳之声。在成为表达(Aussprechen)意义上的道说(Sagen)之前,在最漫长的时间内,作诗只不过是一种倾听(Hören)。孤寂首先把这种倾听收集到它的悦耳之声中,籍此,这悦耳之声便响彻了它在其中获得回响的那种道说。……观看和道说之语言就成了跟随着道说的语言,即成了诗(Dichtung)”[9]这即是说,诗是随着源初语言的“道说”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倾听。倾听什么?倾听源初语言沉默的、无声的、孤寂的“道说”,也即诗歌倾听作为原诗的语言的“说”。这种作为原诗的语言的“道说”是一首“纯粹的诗”,它是所有写出来的诗的本源或源泉。海德格尔认为,思在本源上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思维和推理,思乃诗的近邻。所以,西方思想界长久地把思与理性关联起来恰恰把人引向了歧途,按照这种被规定为理性的思,人们也就把思与诗绝对地对立起来了。海德格尔则强调思在本源上跟随着存在之无蔽显身的方式,进而言之,思是倾听“存在”的召唤,其特征体现为一种本源性的体验,是对人的本真存在的一种回忆、忆念和应答,是一种追思。因而诗人写作的诗文并非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对本真存在的倾听,是对所倾听到的声音的记录。
在海德格尔的语言分析中,正是这种听-说的关系,构成了交谈,交谈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支撑交谈者存在的东西。与海德格尔的这种本体论语言观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颇有影响的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巴赫金和海德格尔一样,也是从生存的角度来思考语言的。他认为,对话不但是语言(话语)的本质,也是思想的本质。对话必然会构成一种双方或多方的言说和倾听关系。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对话就是希望被听到,希望被人理解,得到从其他立场上作出的应答。人的生存的最低条件是两种不同的声音的对话,对话就是反对独白,反对意义的专制和垄断,就是话语和思想的多元化,就是差异的原则。在巴赫金看来,这正是语言的本性所在,同时又是一切伟大的艺术或审美活动的存在条件,进而言之,这也是人存在的本质。同样,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传统,也倡导“听觉优于视觉”。在伽达默尔看来,诗的语言不但有东西要说,而且有人要听,不但有提问,而且有应答。这就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而对话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他的看法很明白:“必须准备好使某种东西对我们述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词语变成为联结:它把一个人的存在和另一个人的存在联系起来了。无论何时,只要通过我们彼此述说,只要我们确实进入和别人的真正对话,这种联结就会发生。”[10]因而自我与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沟通的可能性,人们对文本的解读实际上就是自我与他人的对话,而只有通过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我们才能倾听他者向我们说的话:“因此,只有当解释者倾听文本、让文本坚持它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真正向文本开放时,解释学的对话才能开始。”[11]伽达默尔强调,包括审美理解在内的一切理解的基本模式都是对话和应答,对话和应答首先要求倾听,即使那种所谓审美上的“逗留性”的观看和觉察并不简单地就是对纯粹所看事物的观看,而是具有对话性的理解活动。
“观看”与“倾听”的深层审美范式可在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说明。生态学的文化概念旨在揭示文化并不仅仅限于人类和人类的创造,它同样与其他物种和整个自然领域密切相关。具体来说,生态学的文化概念视文化为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互补的象征关系,一个对话交流的过程,强调人应由“自我意识”向“生态意识”转变。自然与人之间的最直接的生态联系表现为光线或者说观察者的视线。因而华莱士·史蒂文斯把视觉看成一种人与自然的联系方式,但是这种视觉方式又困扰着他。视觉将事物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让它们各就其位,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视觉方式及其体现的思维模式在斯蒂文斯许多早期诗歌中有所展现。例如《山谷的蜡烛》就表现了通过视觉方式建立人与自然之间联系而失败的主题:“我的蜡烛孤独地燃烧在无尽山谷。/广阔夜晚巨大的光线在它上面聚集,/直到有风吹来。/然后广阔夜晚的光线,/聚集在影像上面,/直到有风吹来。”(张曙光译)这首诗表面上写孤独的自我勇敢而悲壮地去照明这个非人的宇宙,展现人的精神似乎坚不可摧。但是在诗中,蜡烛被风吹灭了,随之消失的是它所映照的一切。因此,在视觉方式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无论人作出了多么惊心动魄的努力,在宇宙规律之中都显得渺小而不值一提,而且在时间的冲刷中,将变得无影无踪,从而启示人们对于大自然应该进行由“观看”到“倾听”的生态模式或者说生态联系的转换。“观看”关注持续的、持久的存在,相反“倾听”关注飞掠的、转瞬即逝的、偶然事件式的存在。“观看”肯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别、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别,导致对于差异和他者的暴力支配和占有;而“倾听”则需要人沉浸于人周围的环境,取消人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区分,承认了更高意义的存在。把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重心由视觉方式转移到听觉方式,意味着人对大自然理解、开放、关怀的加深,人由此意识到自己的界限所在。因而在《山谷的蜡烛》中,当人通过视觉方式与自然建立联系时,所感到的是巨大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焦虑。而《雪人》则通过听觉方式与自然建立联系,由此听风者处于人与自然的互动生成关系中:“必须怀有冬日的心境,/方能领略眼前的万树一片冰晶雪白;/只有经受长久的严寒,/才会欣赏松枝银装素裹/在夕阳中闪烁的光采;/寒风啸啸,落叶嘶嘶,/冬天的强音声震天外;/苍茫大地响起同一的奏鸣,/雪上的聆听者把悲情全都抛开;/自身虚无才能审视不存在的虚无,/自身不存在方可洞察虚无的存在。”(吕志鲁译)在这首有名的诗歌中,听觉成为人在世界中重获“家园”感的新感知方式。冬季被史蒂文斯认为是最容易体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季节,听风的人在对冬季声音的感觉中,与自然相互交融,回到原初生命源头大地之上,领悟到了宇宙的真谛。
德国当代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指出:“尽管我们有所有这些充足的理由,告别视觉至上来呼吁一种听觉文化,防止反过来作一面倒的归顺,亦殊有必要。转向听觉文化,我们总是联想到一些希望,希望把主体-客体的思想方法,把自我主体化与他人这对孪生兄弟抛诸脑后,而追求达成参预的结构,追求共生,追求人类和世界的生态整合。”[1]220“观看”与“倾听”作为西方两种深层审美范式,昭示着人固然应该重视自己的意志和空间,但更应该尊重他者为自己设定的界限和空间。人不是世界的主人,只是作为世界的守护者而存在于这一大地上。于其中他观看着、聆听着、感受着和参与着存在的生成,这就是所谓的“诗意地栖居”。
[1]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 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2]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M].楚 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3.
[3]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15.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
[5]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34.
[6]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M]∥张红军.电影与新方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7]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 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6-17.
[8]埃克哈特.埃克哈特大师文集[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00.
[9]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9.
[10]Gadamer,H-G.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106.
[11]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1.
(责任编辑 文 格)
“Viewing”and“Listening”:Two Kinds of Deeper Aesthetic Paradigms in Western Culture
GUO Yu-s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Heilongjiang,China)
In Western culture,visual power and viewing behavior are considered superior to other sense organs.But aesthetic paradigm of“viewing”shows the thinking model based on duality-opposition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ed system,and then to a great degree becomes constraining and autocratic to individuality,difference and variety.On the contrary,from aesthetic paradigm of“listening”,people can grasp truth of“being”that the world is the whole which contains and adopts universal,and then matter and spirit,naturality and holiness which are blending with each other.
viewing;listening;aesthetic paradigm
B83-0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1.005
2014-08-06
郭玉生(1973-),男,山东省汶上县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美学、西方文论及西方文化研究。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ZW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