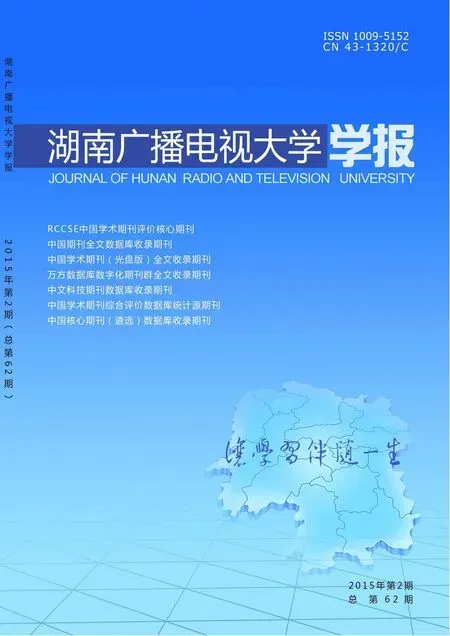张天翼与马克·吐温讽刺小说之对比
杨 巍
(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永川 402160)
一、引言
作为近现代中西方现实主义创作的杰出代表,马克·吐温和张天翼在讽刺小说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马克·吐温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杰出的幽默、讽刺小说家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继承前辈幽默作家的写作特色和技巧,通过巧妙地融合幽默与讽刺,深刻揭露、批判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陋现象。因其卓越的幽默讽刺艺术不仅在本国当时的文坛独树一帜,而且对后来的美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美国文学界的林肯”。张天翼则是中国现代著名讽刺家、儿童文学家,他摆脱了当时文坛流行感伤主义情调和“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以轻快、幽默、泼辣的讽刺笔调,描绘社会各阶层的斗争和生活,揭露现实,有力地鞭挞着三十年代中国社会一处处阴暗、龌龊的角落,被称为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领域里的“双璧”之一(另一位是老舍),而196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更是把他称作是“最有才华的小说家”。
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善于从最平常的生活现象中挖掘新意(即从习以为常中发现艺术),表现出各自独立的批判意识。他们以针砭时弊为重心,作品语言明快洗炼、泼辣风趣,具有明显的幽默特色,同时又具有哀怨的特征,让读者笑过之后心情倍感沉重。当然,两人在讽刺小说创作上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本文拟从结构安排、情节叙述、人物刻画和思想高度四个方面作一番比较。
二、结构安排:完整区别于片段
作为一篇文章的骨架,结构安排决不单单是个艺术技巧问题,它实质上是作家的思想认识在创作方法上的反映,和作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理解有密切关系。[1]马克·吐温集西方现代主义之大成,其“典范之作”的小说明显体现了现代小说完整性的美学原则;而张天翼为满足反映“五四”时期急剧变动中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小说结构上更敢于打破“边界”的限制,体现出了更多的自由和自主。
马克·吐温善于进行宏大、复杂的结构设计,他常常通过导入或必要的交代,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做足准备,然后在结尾处作出总结性的处理,与开头呼应。如小说《牛肉公案的真相》中,开头是“我想尽可能简单概括地向国内陈述一下我跟这件事的关系……这件不幸的事情起源是这样的……”而结尾是“关于那份舆论纷纷的伟大的牛肉契约案,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此。”[2]首尾呼应,读后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而且,他还会运用铺垫、伏笔来制造悬念,使小说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如《一百万磅的钞票》中的“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只有一张用掉和注销了;其余一张始终保存在银行的金库里。”[3]《三万元的遗产》中的“排字工人把提尔贝利的讣告送上备用架去的时候,偏巧又把字盘搞乱了。”[3]P125等等,无不体现他在这方面圆熟的技巧。此外,有时文中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内容也是作家精心安排的下文的引线,如《狗的自述》中,男主人和他的朋友们在实验室称赞“我”的“英勇行为”时的东拉西扯,实际上也在层层铺垫、步步设伏。难怪有人说,马克·吐温的小说一开始便布下陷阱,装好诱饵,利用戏剧性的情节使人感到非读下去不可。正是由于谋篇布局严谨,马克·吐温的小说结构匀称,大多有着发生、发展和高潮,以及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可谓做到了滴水不漏。
张天翼的小说结构以“经济”为原则,他既不注重事件本身,也无意于生活的自然流程,而是聚焦于一些非常态的、具有强烈戏剧性的瞬间。他仿佛从人物性格发展的长河中取下一段,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一个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廓大给我们看。[4]由于大量的省略,他的小说显得紧凑、灵活,而又简洁明快,寥寥几笔便能写活整个人物,以个性化的神情和心态折射出灵魂深处的东西。如《呈报》不仅省掉了对于人物、事件的一般性的交代或罗列,也没有对故事作琐细的描写或铺陈,只把重心放在人物的动作与情绪上,却可以帮助读者领略社会的黑暗,窥见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又如《脊背与奶子》,文章并没有先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等,而是以人们的传闻开头,直接聚焦到主人公任三嫂身上,并引出故事。由于笔墨干净,有着流水似的畅快,作品一下子就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使人欲罢不能。不仅如此,为使主题更加鲜明,重点更加突出,张天翼还喜欢跳跃,喜欢省略。如《包氏父子》中,他通过使焦点不断地在老包与小包之间变换,且时不时地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跳跃,于无意中形成对比,既同时刻画出老包的愚昧、软弱和小包的蛮横、不成器等性格特征,又从另一个方面深化了主题。类似的还有《华威先生》等速写三篇,仅仅通过设置三个会场等浮光掠影的精选生活片段,集中笔墨让华威自己作充分表演,掌声、演说、踏铃,就鲜明地刻画出这个小官吏形象,从而达到了讽刺的目的。难怪有人说张天翼写出来的是“速写”体小说,甚至连他也承认自己的小说“没有故事性”。可尽管张天翼没有描绘出历史生活的全貌,但在跳宕畅肆的外部形式中,狄更斯式提炼特征的技法却蕴含着严谨整饬,浑厚结实的内在逻辑。
显然,相对于马克·吐温小说结构上细密的针脚,以及突兀、强烈的结尾,张天翼更擅长采用凌而不乱、散而有聚、分中寓合的结构特点来调动读者主体的思维与想象力去完成作品的艺术创造。他喜欢留给读者很多“艺术空白”,让他们自由地补充,因而作品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尽管有人评价他有时太过“活跃”和“敏捷”,显得步声急切、焦躁,难得从容,且因少了一种揣摩和品味的心境而妨碍了深沉,但这也只是他攫取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他那生硬而强劲的笔触从故事的几个“点”上匆匆跳过,恰恰使得叙述中充满顿挫跌宕,耐人寻味。
三、情节叙述:离奇区别于平淡
众所周知,情节是表现主题思想和展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马克·吐温直接继承了西部“幽默文学”的手法,大量运用夸张、荒诞等手法,使得小说情节极富戏剧性;而张天翼受“五四”时期进步读书界“世界图景决不混沌”思潮的影响,加上剧烈的政治斗争、社会阶级斗争似乎“澄清”了生活,使生活内容变得简明而易于把握,其小说情节似乎更偏向于以凸显社会图景本身的清晰性为目的。
马克·吐温的故事情节有着奇特、曲折和巧妙等典型特征。小说往往开篇便是大肆铺垫、渲染,使读者按照常理做出如此这般的推想,然而情节发展却多与此相悖,出现一个荒诞不经、违反生活逻辑的“意外”结局。如《他是否还在人间》中,作者通过描写原本默默无闻、作品备受冷落的画家装死并让同伴吹捧“生前”作品,最后大获成功,以前后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名气比画作本身更重要。又如《竞选州长》中,原本占优的“我”遭遇无奇不有、层出不穷的污蔑、栽赃、恐吓和迫害等卑劣手段,最终意外地在竞选中败下阵来,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民主选举”的内幕和所谓“民主政治”本质。有时,为揭露和讽喻某些丑恶的社会生活现象,马克·吐温甚至不惜采用闹剧、恶作剧、极度夸张、废话连篇的过火手法。如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一只追逐甲虫的狗跑进了庄严肃穆的教堂,让里面的人啼笑皆非,强烈的反差让读者立刻感觉到教会的荒谬可笑。又如《罗马大神殿维纳斯神像的故事》中,艺术家的一件完美作品本来无人问津,被斧头砍得支离破碎之后反倒价值连城,借此讽刺了所谓的艺术品不过是某些人装点门面的货色,其艺术性的高低本来就无足轻重。跌宕起伏的情节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局大大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理解创造力和阅读兴趣,使他们的心灵深处会产生一种游戏般的快乐和美的感受。当然,马克·吐温小说中超出常理、脱离生活常轨的“奇”并非游戏之作,这种“意外”的偶然中往往包含着必然,怪诞虚构的外形中更隐藏着真实的内核。
张天翼的小说虽然少有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却善于以几无陪衬拖带的粗线条勾勒,精准到位地抓住矛盾冲突的激变和情节发展的关节点,从而造成故事发展的陡势。他往往创造性地将人物置于一个个平凡、简单而真实的情境中,让人物自说自话,自我表现,通过凡人小事透出人物灵魂深处的种种波澜。如《皮带》中,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刻画了一个穷窘落魄而又灵魂猥琐的小知识分子的处境和精神状态:邓炳生是一个醉心于升官的人物,当他几经周折终于挂上了梦寐以求的“斜皮带”时,幻想又瞬即破灭,只得趴在“斜皮带”前伤心地哭泣。又如《善女人》中,长生奶奶看似一个虔信佛教的女人,可她的“善”也只是嘴上说说,实际上却通过菩提庵的老师太把钱拿去放高利贷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并且逼走媳妇,逼得儿子逃亡。类似的还有《讲理》,孩子在别人杂货店门口拉屎的太太反而振振有辞;《度量》中,坐洋车的先生庆幸自己被车夫摔了以后可以不付车资,等等。这些事件本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了的,作者凭借自己灵敏的嗅觉,从社会各个角落巧妙取材并经过加工,才引人注意。可以说寓深刻、丰富的内涵于平淡、朴实的叙事之中,张天翼有其自己的特点,显示了他的短篇的平淡美。[5]当然,他的小说情节平淡而不平庸,很好地避免了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且,他所展现的生活事件和刻画的人物,恰恰因为真实、自然、亲切,使得读者身临其境,大大缩短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他常让人物用庄严的口气叙述琐屑荒唐的小事,让听众感到若有其事,“使人明白在那种庄严的态度中原来也隐藏着嬉笑”。虽然有人评论他的小说多的是“生活”,少的是“风致”,但他却能在平淡、直白的文字叙述中找到艺术上真正有力的支点,以丰富的内涵深入人心。
不可否认,一名作家独有的叙述方式和习惯的形成,不仅跟当时的历史变革、时代发展需求密切相关,而且还深受其生活经历、兴趣爱好和艺术修养等因素的影响。或许不同的读者各有偏好,但小说中的生活容量与思想容量并不见得受影响。只要作家能感受到生活的真实节奏,以及他从事创作时的心理节奏,由此融会并形成作品的内在节奏,就能为读者奉献出经典的作品来。
四、人物刻画:和谐区别于别扭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特定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由于作品的讽刺性往往是主客观在这一区域内相遇的结果,每个讽刺作家都有其特殊的“道德敏感区”。相对于马克·吐温以温和、宽厚的方式融幽默和讽刺为一体,在轻松嬉笑的外表下隐藏着严肃的社会批判,张天翼的讽刺手法更加锋利泼辣,显得冷峭且毫不留情,甚至令人反感、别扭。
作为一名改良主义者,马克·吐温在心理刻画方面较为注重整个变化过程,他笔下人物的心理动态往往具有流动性,尽管偶尔会有曲折,但总的来看,前后浑然一体。如《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原本较为诚实的理查兹夫妇,自从收到金币,他们渐渐有了想法而睡不着觉。接着他们开始编故事,妄想把金币据为己有。最后,他们良心上的不安消失,甚至开始“盘算如何处理这笔钱”,贪婪无耻的本性开始原形毕露。又如《三万元的遗产》中的福斯脱夫妇,对三万元遗产怀有强烈欲望并且信心满满的他们开始用它来“投资”,一笔又一笔地赚钱并终于成为巨富。离奇的幻想代替了现实,直至两人完全失去了理智。马克·吐温的幽默虚虚实实,真假难辨,难怪有人曾对马克·吐温做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幽默流动在全书字里行间,不断地涌现和更新,给人丰富的感受,如同血液的循环流动,既不炫耀也不喧嚣。”[6]而且,马克·吐温的小说语言委婉、圆滑,多寓于诙谐、幽默的谈笑风生之中,很少有词意浅陋的批评和谩骂。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描写一个孩子因傻头傻脑地连续背三千节“圣经”而用脑过度成了白痴,夸张、幽默的背后既讽刺了宗教的虚伪,也讽刺了宗教对人的毒害。又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当吉姆说:“但是,哈克,这些国王都是些地道的坏蛋,他们就是这么种东西,是一帮坏蛋。”哈克却回答:“对呀,我也就是这个意思。照我看,所有的国王差不多都是坏蛋。”[7]更是巧妙地借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之口道出南方种植园主虚伪凶残的本质,也暗示了封建奴隶制注定要灭亡的命运。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幽默句子、段落和情节很自然地串成了喜剧,而将幽默串在一起的正是讽刺的主题。
张天翼则“很少凝神思考,只对人物的种种丑相,极尽描写,他挖掘的是恶。”[4]P39他笔下很少有“完人”,常常通过某一本质特征“廓大”了的不成比例或不协调的畸人来施以讽刺。如短篇《皮带》以邓炳生视作荣华富贵象征的军官斜皮带为焦点,通过描写他因靠山亲戚调走而被上司裁减后的心理活动,讽刺的利刃直达人物的灵魂:“再看一遍,再看一遍,也是这样;又再看一遍,又再看一遍,还是这样。炳生先生的眼睛花起来。一切在打旋,在跳动。挂在衣架上的斜皮带飞了起来,飞在半空,忽然裂成粉碎。灰布衣和军帽变成一团黑东西,上面有两只放光的眼睛……炳生把脑袋倒在衣架前面的一张椅上吸泣着。”[8]而且,为了突出讽刺对象的可笑可鄙,张天翼还注意捕捉一些让人反感、甚至厌恶的独特嗜好和癖性。一方面,他喜欢利用粗话和脏话揭示了骂人者或被骂者那丑陋的内心隐秘,如《脊背与奶子》里任三嫂大骂调戏她的长太爷:“畜牲!老狗!强盗!杂种!痞子!任剥皮……”[9]《团圆》里大根动不动就来一句口头禅“操你妹子的哥哥”[10]等等。另一方面,他还喜欢反复描写一些秽物和不雅动作,如在《我的太太》女人“手在鼻子上那么一撮,一条黄色的鼻涕在手指上挂着——像皮带似的扭了几扭,叭儿一声就给甩到了墙上。那罐饭在冒着热气。”[10]如《温柔制造者》中,“男的想着,搔着脑袋——头发里落下些灰白色的雪片。”“鼻孔里还有一根毛长到了外面,也不去剪一剪。”女的“腮巴上糊着橙黄色的粉”[10]诸种对丑陋的渲染固然令人感到不安且反感,似乎在“故意的以丑恶的东西来做骇人听闻的刺激的工具”。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污秽描写使得讽刺效果大大加强。
讽刺笔锋的差异恰好反映出两位作家立足点的不同。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马克·吐温的理想没有也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且他的讽刺也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而张天翼则由于旨在促成社会变革,会有意地摄取那些丑恶的、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漫画化,甚至“挖心”,就是为了让读者从那些真实可信的讽刺中窥见社会的“人生相”,促成其毁灭。
五、思想高度:世人区别于国人
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和张天翼的小说都是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教训,因而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不过,由于相较于二十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有着更强的普遍性,再加上马克·吐温人生经历更为丰富,多次前往欧洲,他的小说在观照社会的广度上无疑更胜张天翼一筹。
首先,马克·吐温极富人道主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讽刺的对象没有明显的侧重,往往是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结合自己的观察,从社会这个广阔的背景中去选取。在他的笔下,报界的编辑记者、政府机构的官僚、普通小人物,几乎涉及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只要发现不正常、不公平的现象,他都敢于去揭露、去批判。因为关注的人物类型更多,马克·吐温不仅能更全面地展现出一幅富于个性的世界图景,而且还可以更灵活地选择切入点,游刃有余而又尽可能地避免了单调、雷同之感。以同样描写惨无人道的种族歧视这一主题为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重在反映反蓄奴制度,而《傻瓜威尔逊》则强调了“身份危机”。其次,从涵盖的地域范围来看,马克·吐温的小说突破了本国的局限,具有明显的世界性和普遍性。虽然美国人占了他笔下人物典型的绝大部分,如《竞选州长》、《镀金时代》和《卡拉韦拉斯县驰名的跳蛙》等,但以外国人为题材的作品也很不少。如《冉·达克》,写的是法国历史女英雄的故事,不仅向忘恩负义的国王、出卖英雄的贵族和僧侣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更反映了自己坚持正义的思想;《一百万英镑》通过小办事员的种种“历险”嘲弄了金钱在资产阶级社会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作用,刻画了不同人物在金钱面前的种种丑态;而《高尔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则写到了中国民工的悲惨遭遇,不仅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表达了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同情。即便是在以美国社会为描写对象时,他也常常是以小见大,含沙射影,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持有的讽刺批判态度。其真实意图不在于揭露美国社会的弊端,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问题。他的小说,不仅仅是美国的,更是世界的。
张天翼的文化背景和教养则相对较为单纯,他缺少仅仅属于自己的对世界的把握和解释,更缺少以世界作为整体的哲学思考。由于他以自己的讽刺小说“尽了当前的任务……文学是战斗的!”主要将着眼点聚焦在近百年来在半殖民地土壤中,以服务于革命斗争为宗旨。尽管他塑造了各个阶层不同类型的众多的人物形象,但描绘的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中的生活图景,着重刻画的是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丑态:一是虚伪、凶狠、狡诈的地主、官僚,如《脊背与奶子》中的长太爷,《笑》中的九爷和《一个题材》里的小说家翰少爷等等;二是势利、庸俗、动摇的小公务员、小知识分子、小市民,如《宿命论与算命论》里的舒可济,《友谊》里的苏以宁,《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等等;三是愚昧、不幸的城乡劳动人民,如《小帐》中的学徒伙计,《小彼得》中的工友们,《包氏父子》中的门房老包等等。[11]他在最切近的生活中攫取小说材料,似乎无暇前瞻也无暇反顾,是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当前”对于他的艺术,几乎是一切。[12]而且,尽管张天翼的讽刺熔政治、道德、风俗和人性为一炉,他揭露和曝光的也不外乎中国人身上较为普遍的问题。他常常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笔下的这些人物,讽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黑暗社会的暴露和国民性的批判上。他在敏感地追踪着一切老和新的丑恶的基础上,用犀利的笔锋剖析人物的劣根性,意在通过揭示国民弱点来暴露问题,达到揭露和疗救的目的。因此,纵然他凭借冷峭的手法深刻揭露了现实社会弊病的同时,却仅仅关注到现实社会灰暗的一角,没能像马克·吐温那样描绘出一个富于个性的世界图景。他的小说是中国的,不是世界的。
当然,偏重于广度或深度只能说明马克·吐温和张天翼的文学创作焦点不同,这不仅受制于他们各自的审美意趣和创作理念,更与特定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密切相关。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表面上评价孰优孰劣,毕竟只要能够发挥独一无二的社会功能,并对读者大众产生积极影响,就可算作是成功的作品。从这个层面上讲,只能说两人各具千秋,却难作高下之分。
六、结语
马克·吐温和张天翼分别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度,接受完全不同的思想教育,有着不尽相同的信仰,这难免导致他们在观察社会、评价事物的角度和着眼点上的差异。不过,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始终坚持探求社会文化心理的创作理念,以手中的笔来描绘各自当时的社会现实,使自己的作品跟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紧紧相联。而且,由于两人都深谙写作的要领,懂得如何产出伟大的小说作品,无论是反映社会问题的角度、文章的组织形式,或是语言风格的生成等等,都可以说把近现代小说带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他们的笑声中包含着对生活真理的思考,留下的一座座丰碑既体现了他们的价值,也造就了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不可替代性。
[1]张西元.略谈马克·吐温的小说创作艺术[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81,(2):41.
[2]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小说选[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5:221.
[3]朱树飏.马克吐温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40.
[4]吴福辉.锋利·新鲜·夸张——试论张天翼讽刺小说的人物及其描写艺术[J].文学评论,1980,(5):36-37.
[5]张巍,论张天翼小说的讽刺艺术[J].辽宁师专学报(社科版),2007,(2):34-36.
[6]刘建中.论马克·吐温和契诃夫的幽默[J].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3):110-113.
[7]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M].伊犁:伊犁人民出版社,1984:207.
[8]张天翼.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上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125.
[9]张天翼.张天翼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66-94.
[10]沈承宽.张天翼文集(第2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211-229.
[11]王付根.论张天翼讽刺小说中的人物及艺术手法[J].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87,(4):76-81.
[12]赵园.论张天翼小说[J].文艺研究,198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