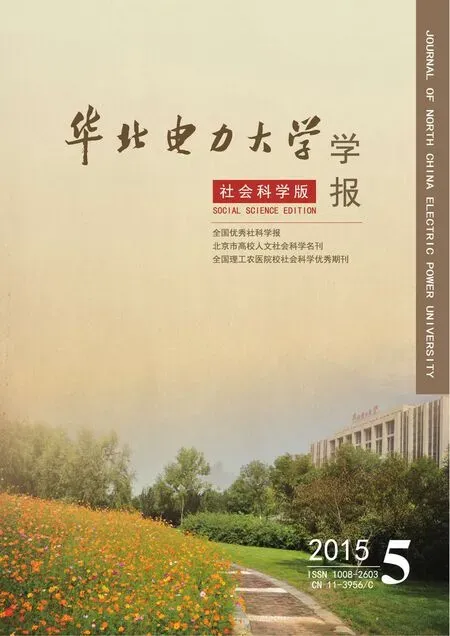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建设文化强国的哲学思考
金庆昕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37)
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建设文化强国的哲学思考
金庆昕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37)
全球经济、政治、文化逐步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但也带来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面对机遇与挑战,加强我党的应变能力、执政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课题就凸现出来了。本文试从全球化的涵义、全球化对我党发展的双重影响及我党的应对策略等几方面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面对全球化进程,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之路。
全球化;文化建设;哲学思考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但也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风险。面对多变的形势,我们党能不能在“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世界发展大潮中,浪遏飞舟,“弄潮儿向涛头立”,关系到执政党应变能力和领导权威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大课题,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
一、全球化的涵义
全球化问题使我们再一次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我们不无惊讶地看到,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全球化问题作出了精辟预见和深刻论证。虽然他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术语,但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词句,而是把握其精神,那么,他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历史意义的分析,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其灭亡的历史过程揭示,对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的强调,仍给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全球化问题以宝贵的启示。
什么是全球化?目前对这一概念没有统一的理解。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它的最本质,最一般的意思,应是指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让我们来看《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论述。马克思在那里写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促使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1]273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和获取利润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因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276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可以使我们把握全球化概念的如下几个本质规定:
第一,全球化是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现在才出的,而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因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所谓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全球化趋势从现象上看也是“古已有之”,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后才形成的,因而也只有把它置于大工业之中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它的含义。
第二,全球化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是“世界性”,即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世界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世界历史”思想具有一致性。这个思想是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冲破了地域的壁垒,把各个民族都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之中。这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是成为世界历史”。[3]291对全球化概念也可作同样的理解,它实际表达了自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各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这一事实或者“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趋势。
第三,全球化发进程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逐步一体化过程。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主要是个经济范畴,因为它主要指贸易、资本、金融和现代化生产的国际化趋势,指国与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所以,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这个观点似乎停留在对事物根源和现象的分析上,缺少理论的彻底性,在我们看来,全球化首先导源于经济上的必然性这一事实,并不构成全球化就是经济“单一化”的理由。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的过程。“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276所以,全球化的内容和走向决不可能仅仅限于经济这一方面。虽然它起因于经济,并且在一段时间和一定程度上主要表现为经济,但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也必然逐步加强。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日益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86
二、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资本主义的烙印,体现西方的游戏规则,传播美式的政治理念,价值原则,集中反映在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真理性,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依据。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的源泉。
但同时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令前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种崭新的实践已经在某些方面改变了马恩的某些设想,表明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某些个别结论的局限性,使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遇到许多理论上的挑战。例如,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任何商品和货币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没有,更不用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尽管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判断,然而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它既要与全球化相适应又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政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相结合时,仍然遇到了众多的新课题。
再比如,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它在产生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着惊人的两极分化: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生活在集中了81%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占据了82%的出口市场、58%的外国投资、91%的新技术利用和74%的电话线路的国家。8亿人忍受着饥饿,8000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超过2.6亿人不能上学,第三世界国家外债总额达2.5万亿美元。“有钱能使鬼推魔”的现象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比比皆是。这种现实与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生产的社会化具有一种“革命的本性”,它要求占有也社会化的论断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帝国主义似乎还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最高阶段”,相反显示出它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人们对马恩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产生一种动摇、疑虑或底气不足的心态。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民主观等理论都提出了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中的新现象正在同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某些观念发生着碰撞,正在同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着碰撞,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需做出一种新的理论回答。
第二,从政治体制改革看,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为我党健全体制、调整权力、拓展参与、扩大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条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正视一个现实,即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主义的改革中的深层矛盾更容易集中暴露出来,并日益显示出解决这些矛盾的艰巨性。如: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企关系、银企关系保留着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一旦参加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竞争,便暴露出它在体制、结构、机制上的脆弱。目前,国有企业一只脚已踏入市场经济,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企业领导者一方面要扮演追求经济利益的经营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要扮演追求一方平安的小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这种政府与企业的角色错位使得大批国企难以摆脱困难、轻装上阵、投入国际竞争。而传统的银行与企业、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使得银行商业化的进程缓慢,难以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由于目前的国际竞争在许多地方的不公平性,而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尚未完成由农业化进入工业化之时,又遇到了知识经济的挑战,面临着现代化的双重压力,显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使得政府在如何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问题上承担着更多的压力和责任,出现不同程度的治理危机,其改革的成本和代价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昂贵的多。
第三,开放性是全球化的根本属性和根本要求,它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一些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也多为发达国家所控制,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动权也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这样,发达国家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这种不公平的经济秩序中受益较少,相反地是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主权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德国经济学家汉斯·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合写的《全球化陷井》一书中说:“跨国公司的投资取向,足以左右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一些金融机构逼迫一些国家的政府就范,使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对于中国来说,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后,随着市场准入的扩大、关税的削减、非关税措施的取消,外国产品、服务和投资有可能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那些成本高、技术水平低、经营管理落后的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包括三个方面:质量的挑战,数量的挑战,价格的挑战。由此而来的是对农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提出的严峻挑战。
第四,全球化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进步,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方兴未艾的数字宠儿却也让世界增添了新的数字鸿沟。因为尽管信息网络技术普及非常快,但世界仍然存在上网与否、拥有和不拥有信息技术的分别;况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信息制作和传播方面的主动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国家边界形同虚设,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如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来传播、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搞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妄图“西化”“分化”我们,进行文化渗透。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电子银行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给计算机犯罪提供了机会。金融系统的网络化,使金融在自由、快速运行中处于高风险之中,常遇电子黑客的攻击。同时,对军事领域和国家安全,也构成了挑战。此外,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还造成了自由化思潮的骚扰,政治文化的冲突,文化强势的压力,民族认同的消解等问题,从而对我国政治秩序、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五,全球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带来了巨大冲击。别有用心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思想文化的渗透活动,更是利用经济全球化过程试图影响和控制别人思想的直接活动,这种活动将在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失衡的基础上愈演愈烈。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流行的“全球文化同质论”,就反映了这种现实。“同质论”认为,全球化将弱化具有不同特性的民族文化,代之以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共同文化即全球文化;而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里,全球市场化普及的实际是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各民族国家将同质化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因此,“同质化”也就是“西化”。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论证了今后不同文明体系的人们之间,思想的交互影响甚至冲突在所难免。
三、全球化的对策
全球化把我国的发展纳入了世界的轨道,对我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面对全球化进程,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之路。
西方学者汤因比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引领世界文明的地位将为东方的新文明所替代。对西方文明的未来,汤因比是悲观的、不抱希望的。汤因比认为:由于物欲的泛滥,无节制的经济发展,西方文化已经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尖锐的分裂、对立、甚至是战争状态,西方文明来日无多。汤因比问道:“谁将继承这些遗产呢?不会是苏联或日本。因为这两个强国已如此西方化了,他们也得了西方先天固有的毛病。他们在这场竞赛中已经被淘汰了,而黑非洲和印度也已被淘汰了。非洲人正全神贯注地处理许多地方性的问题,在印度次大陆,则由于宗教和语言方面的冲突,处于分裂的状态。”“我们必须向东亚的社会去找西方的继承人。这个社会既要能对付西方留下来的遗产,又要能对付农业社会固有的问题。简言之,要找到一个能为人类历史打开新的一页的社会。作为西方的潜在继承人,最具备经得起审查的资格的就是中国。”“中国历史的进程是周期性地一起一伏的。但中国比之西方却更成功地解决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它多少世纪来能成功地把千百万人民团结在一起,在国内有比较稳定的和平和井然的秩序;它也曾成功地吸收了像佛教这样外来的意识形态,从而丰富了土生的文明。”
近30年的岁月进一步证明了汤因比的远见卓识,用伊斯兰伟大的思想家班纳的话说:西方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却没有给人类的精神带来丝毫光明。是的,在世纪之交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文明中的物质与精神的大背反,看到是物质丰裕的国度里到处潜伏的社会危机、精神危机。新世纪伊始,抗议全球化、反工业化、反资本主义的抗议浪潮再次打破了西方社会的平静。中国能如汤因比所预言那样成为西方的继承者,继续引领人类走向未来吗?当年汤因比提到了西方文明继承者需要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解决自身源于农业社会的问题,即发展技术、生产力,发展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同时又要解决西方工业化、现代化遗留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的新的道路。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正在努力跟上世界的步伐。以向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学习为主要取向和特征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当说,传统性很强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农业社会发展迟缓的问题,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却正在遭遇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没有解决的文化矛盾与问题。西方的老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的新问题。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对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文化矛盾的超越和解决,而中国超越西方现代化中的文化矛盾的道路,必然建立在对西方已有现代化经验教训的总结的基础上,也必然要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健康和有益文化因素加以总结和发扬。如果说,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向西方现代化学习,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那么,建设文化强国则是中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尝试。具有时代感,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的中国文化将决定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中国能否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做出新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的文化建设,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3.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49-550.
[3] (英)汤因比.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J].思潮,1974(9).
(责任编辑:杜红琴)
The Philosophy on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 Globalization
JIN Qing-xi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China)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global integration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provides valuabl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on one side, meanwhile, it also brings challenges. Faced with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ow to enhance our Party′s resilience and improve the governing and risk-resistance ability are catch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globalization, twin influences brought by globalization on our Party′s development, and our Party′s coping strategy, this paper is will give unique solution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ruling position of our Party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glob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is a must.
globaliza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2015-07-29
金庆昕,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后。
G120
A
1008-2603(2015)05-0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