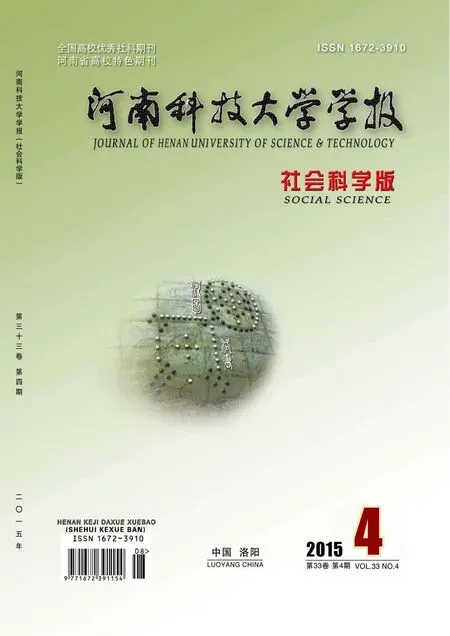《文选》哀伤诗中的哀伤情感流变
摘 要: 《文选》诗体“哀伤”类所选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品。由于历史时代和审美意识的影响,哀伤意象大量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创作之中,但是由于每个朝代的写作背景又有所不同,这种哀伤所具有的特质也不尽相同。建安时期的哀伤带着慷慨进取的功业之心,正始名士所产生的则是无望的悲哀,两晋时期又出现从哀叹社会向哀叹人生的变化,至南北朝时期哀伤情绪逐渐淡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5)04-0047-05
DOI:10.15926/j.chki.hkdsk.2015.04.009
收稿日期: 2014-12-19
作者简介: 邹朝斌(1990—),男,湖南邵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先唐文学研究。
一、《文选》哀伤诗作品概说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中收录从周至南朝梁共130余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文选》流传甚广,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文人学者不在少数,故从隋唐间的曹宪开始就形成了专门研究《文选》这部书的“《文选》学”。此书的产生对我国诗歌创作以及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选》的编纂遵循着“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1]4的原则,在《文选》所归纳的37类文体中,诗体下的“哀伤”类共收录9 家13篇作品,即嵇康《忧愤诗》、曹植《七哀诗》、王粲《七哀诗》2首、张载《七哀诗》2首、潘岳《悼亡诗》3首、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颜延之《拜陵庙作》、谢緿《同谢咨议铜爵台》、任窻《出郡传舍哭范仆射》。与诗体中的哀伤类相同,《文选》赋体下也收有“哀伤”类作品共5家7篇,除司马相如《长门赋》为西汉作品,其余6篇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可见,《文选》诗体、赋体哀伤类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进一步考查发现,《文选》诗体其他类别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包含哀伤情感的作品。诸如“祖饯”“挽歌”等,从类目名称就能感受到或多或少的哀伤之情;又如“咏怀”“咏史”“行旅”“赠答”等类别中也有大量诗作关涉哀伤主题。胡大雷先生《文选诗研究》第14章所述,“祖饯类收曹植《送应氏》二首”,“咏史类收王粲《咏史》与曹植《三良》”,“咏怀类有欧阳建《临终诗》”;“杂拟类有江淹所作《潘黄门述哀》” [2]245-246,作者均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然,《文选》诗体中表现出哀伤之情的作品不仅仅于此,据笔者粗略统计,除开哀伤类作品所收与胡大雷先生所述这些作品,《文选》诗体中其他关于哀伤主题的诗作大部分产生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毋庸置疑。
二、魏晋南北朝哀伤思潮
《文选》的选文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 [1]3。从其所选蕴含哀伤情感的诗歌大部分集中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即这一时期已产生了大量哀伤主题的诗歌。同时代钟嵘《诗品序》所言:“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3]在钟嵘总结的以诗歌“感荡心灵”的种种情景中,除“扬蛾入宠,再盼倾国”之外,其余都多多少少有哀伤的情感在其中。大量哀怨悲伤的情感不仅仅存在于诗歌当中,其他诸如赋、文等文学体裁也不例外,以至于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4]。把“流连哀思”作为成文的一个标准,表明这个时期以悲为美的感伤主义文学已成主流。再从这段时期与文学密切相关的音乐这一艺术体裁来看,嵇康《琴赋序》有云:“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 [1]332-333可见在音乐上亦存在着相同的现象。这说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都存在着非常多表现生离死别和生命迁逝的哀伤情感,而且形成了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和感伤主义的文学潮流。
究其原因,从历时性的回溯来看,无论在文学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中,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并发展着一种悲哀文学传统。正如钱钟书所言:“孟、荀泛论德慧心志,(司)马迁始以此专论文词之才,遂成惯论。撰述每出于?傺困穷,抒情言志尤甚,汉以来之所共谈。” [5]魏晋时期出现这种哀伤文学潮流也是不足为奇的。而从共时性的诗歌作品对比来看,这种现象与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而在社会背景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中的感伤特质也有着一个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方面。
三、《文选》哀伤诗的哀伤特质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离乱的时代,近400年时间里历经了七个朝代,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是以无数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伴随这段历史的是无尽的战乱和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 [6]208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儒家的礼教变得僵化而导致人们的思想活跃,桎梏世人已久的汉代经学濒临崩溃,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体生命的价值,开始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这个时期“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6]208。这个混乱痛苦却带来了“人的觉醒”的时代,诞生了一批个人主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文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战乱、别离、失意、失恋、病痛甚至死亡这些客体作用于生活中的文人主体之时,主体便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些负面东西所带来的结果——哀伤之情油然而生。在众多负面的历史现实和个人情感作用之下,感伤意象大量进入文人的创作之中,由此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文选》诗体中才出现了众多重视创作主体个人情感抒发的哀伤主题之作。具体来看,《文选》诗作跨度几百年,从建安到正始,再历经两晋到南朝末年,每个时代的写作背景不同,因而这种哀伤所具有的特质也不尽相同。
(一)建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东汉中晚期就已经初露端倪。那时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当时宦官外戚干预朝政,政局黑暗无边,士人晋身之路被阻塞,在这种痛苦的人生体验中才产生了《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1]588的深思和“所欲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1]541的生命迁逝感。
建安时期的大离乱、大死丧使得士人对社会人生有着更为深重的哀伤感。士人们亲历亲闻战乱和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带给人民的苦难,他们一边饱尝时代的痛苦,一边哀伤地思索着社会和人生,于是产生了一种怅惘悲哀的情感。但这种情感是哀而不悲观,士人们对社会和人生抱有一种慷慨积极的进取精神的,他们的作品中贯穿着“壮志与悲慨纠结的情怀”。 [7]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形成了这个时期格调沉着、风力遒劲的建安文学。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建安时期“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8]61。他们的作品中虽有许多类似“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9]350的深沉悲凉感,更多的却是“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芳” [10]这样积极进取的功业之心,这种以哀伤为宗却追求慷慨激昂的审美趣味成为建安文学中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关于曹植《七哀诗》吕向题解曰:“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 [1]428由此观之,七哀是一种哀伤到极致的表现。曹植写这首诗的缘由,吕向认为是“为汉末征役别离妇人哀叹” [1]428。从历史背景来看,汉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征夫徭役之事极为常见,丈夫出征久不归,妇人独栖哀怨叹息是再正常不过的。但从诗中内容也可发现另一种可能。诗后半部分“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1]428古代文学中有着臣对君以妾自比的传统,而曹植有着强烈的功业之心,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1]154。这首诗似乎表达了曹植想努力靠近朝政建功立业却郁郁不得志的无奈与幽怨。因为魏文帝即位后,曹植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到孤立冷落。《三国志·陈思王传》载:“常自愤怒,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 [11]339-341在这种情况下,以妾自比期待入君怀的写法也是自然而然的。
王粲《七哀诗》共3首,《文选》诗体“哀伤”类所收前两首在内容上有连续性。李周翰称其“哀汉乱也” [1]428。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年十七,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 [11]353第1首就是王粲在远赴荆州路上的所见所感,诗中把“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1]429的凄惨景象与妇人弃子的场景相结合,哀伤之感深沉厚重。第2首是他在荆州不受重用之时抒发的羁旅思乡之情。“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不甚重也。” [11]354所以他在此种抑郁不得志之时在诗中抒发忧愁幽思之感,这在他同时期所作《登楼赋》中也有所体现。
综上而言,建安时期的文人虽然时刻感叹着社会悲苦混乱、时间流逝生命无依,哀伤忧虑充盈于他们的生活之中,但是对人生的去向还是有着较为理性的思考和积极的追求。“他们真正的终极关怀,只能建立在伦理价值生命观上,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思想,是他们真正的归依”。 [12]所以这个时期的文人在哀伤喟叹之余还是会奋发向上坚韧追求以求实现个人价值的。
(二)正始时期
从建安到正始,社会上延续着混乱黑暗的格局,封建统治者严酷的言论控制使得文士朝不保夕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怀着满腔的忧愤悲哀寻找发泄的途径。与建安文人积极的功业之心不同,险恶的世事消减了正始士人政治参与的热情,他们以超俗怪诞的举动抗议世俗社会及躲避祸乱。阮籍就能很好地代表这种状况。《晋书》说:“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13]1360
士人们开始怀疑日益僵化的名与名教的价值,此时盛行的玄学包括神仙思想开始影响到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他们的建功立业之心。反映到文学上便是《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8]9尽管正始士人避开世事谈玄论道求仙问药,但他们终究脱离不了那个动荡不安政治黑暗的时代,“游仙诗人的浪漫主义,和丧乱、挽歌诗人的感伤主义一样,也是悲剧性的。感伤主义哀生叹死沉溺于丧痛,诚然可泣;而浪漫主义幻想永生、神往仙界,明知虚妄而拒不醒悟,岂不是埋藏着更深刻的悲哀” [14]。从这一点上看,正始文学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哀伤悲叹的悲剧色彩。
嵇康的《忧愤诗》就很能代表这个时期的哀伤文学特色。面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嵇康有着难以平息的不满和愤懑,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1]802,发表过离经叛道、菲薄“圣人”的言论,还得罪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钟会借机称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皇帝听信谗言,使嵇康身陷囹圄,最后置之于死地。此诗为嵇康被诬入狱后所作,当时他还未料到自己已经大限将至,在诗末还抒发了“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1]428的隐居愿望,殊不知他的这种愿望在离乱黑暗的时代与自身嫉恶如仇的性格之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的,最后只能以一曲《广陵散》来结束自己对整个社会人生绵绵无尽的哀伤忧愁。可以说嵇康对自身无法逃避和超越的现实命运痛苦的哀叹正是这个时期的文人断绝功业之心后更为沉重哀伤的代表。
(三)两晋时期
两晋诗歌依然充斥着大量哀伤的情感。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使得社会依旧动荡不安。一些士人逐渐形成了重门第而轻功名的浮华不实风气,特别是西晋中后期的上层社会,重清谈废务实,“风俗淫僻,耻尚失所” [13]136,而中下层的寒素族士人若想追求功名,就不得不以名教的规范来塑造自己,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个人价值。西晋文学的一个变化就是不太关注政治局势和社会忧患,而更多地关注文人自身,抒发一己的哀伤之情,反映在《文选》诗体“哀伤”类作品的选录上,就是哀伤类诗作明显分为为社会人生而哀与为某人的死亡而哀两类,而在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之前根本没有收录为某人死亡而哀的诗作。究其原因,胡大雷先生见解深刻:“西晋以前的知识分子对死亡这个问题,其个体意识、自我意识在诗歌中还是不强烈的;在诗歌中,个体死亡问题还未真正从人生、社会的大问题中彻底独立出来”。 [2]243
东晋王朝偏安江南,文人的乱离之感虽然有游山玩水抑或谈玄之风来消释,但是心中那种对生命与人生的隐痛哀伤也是如影随形的。此时依然有郭璞多慷慨之词的游仙之作,也有陶渊明的悲伤慨叹孤独凄凉。
张载《七哀诗》2首不知作于何时。据《晋书》载:“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 [13]1518从两诗的内容来看,与世道混乱世事变迁有关。第1首李周翰注云“哀人事迁化” [1]429。诗中世道丧乱、汉皇陵的沧桑变化,从而引起诗人的悲怆哀伤之感。第2首写秋日林中所见所感,亦能品出其哀痛。
潘岳《悼亡诗》3首是为其亡妻所作。《晋书》载“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 [1]1507潘岳的哀伤之作感人至深,可谓是深情至哀的典范之作,3首《悼亡诗》中细腻、凄恻、婉转的悲美情调正代表了他哀诔作品的特点。陈祚明曰:“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 [15]正是倾注了作者至深之情,而未能有语不佳者,亦能感人至深。
(四)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社会基本延续了魏晋的动荡不安。南朝政权更迭频繁,宋、齐、梁、陈四朝均只存在了几十年时间,北朝少数民族纷起建立政权。这个时期的文人很多都经历过王朝更易,有的甚至经历过被俘扣押。这样的时代变迁与人生沧桑虽然使整个南北朝都弥漫着感伤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潮。而且这种情感反映到文学上多见于模拟魏晋诗歌的作品中,在众多描写现实社会人生的作品中却少见哀伤情绪的蔓延。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世俗化的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心理和审美趣味。在俗化的社会中,人们似乎发现寻欢作乐远比苦苦思索哀叹人生来得轻松实在,此时社会上充斥着的是艳情、新声。文学上表现为风格绮靡艳丽内容单薄空虚的宫体诗盛行于世。感伤情绪稀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佛教的蓬勃兴旺。佛教指引文人们忘记了现世的痛苦和恐惧,而去追求冥冥之中的彼岸世界。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文学中哀伤情绪的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化的表述,而不是像魏晋时期因社会和人生的困苦而发出的真挚感伤情绪,因而才出现了诸如江淹《恨赋》、《别赋》这种总结式的作品,把对人生社会的哀伤抽象化、概念化,却不见作者自身具体的哀伤之情。
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为悼念亡友刘义真所作。据《宋书》记载,谢灵运与庐陵王刘义真交情甚好,义真还曾言“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 [16]。然而义真在政权斗争中失败,谢灵运因徐羡谗言而被排挤出京,后得以昭雪,在还朝途中经过庐陵王墓乃作此诗。诗中表现出对庐陵王之死的沉重哀痛。此外谢灵运还作有《庐陵王诔》。
颜延之《拜陵庙作》为应制之作,与诗体哀伤类其他诗作的艺术成就相比逊色不少。李善注称“自元嘉来,每正月舆驾必谒宁陵” [1]433,刘良注“延之从文帝拜高祖陵” [1]433。颜延之的庙堂应制之作甚多,此诗亦是,歌功颂德在所难免,哀伤的情绪也被大大冲淡了。
谢緿《同谢咨议铜爵台》乃和其侄谢琨所作。曹操死前《遗令》中说让婢妾、伎人于“月朝十五日,辄向帐作伎” [1]434,诗歌内容就是据此而来。此诗主要内容虽然是咏史,但还是可以看出其对生命无常的感叹和自悲自怜的哀伤之情。
任窻《出郡传舍哭范仆射》为悼念亡友范云所作。二人均为“竟陵八友”成员,交游甚久,有诗云“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 [9]1963,足见其情谊深厚。诗中“将乖不忍别,欲以遣离情,不忍一辰意,千龄万恨生” [1]435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离愁别绪了,而是对生死之别的千哀万恨,感人至深。
四、余论
由《文选》诗体“哀伤”类的作品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了大量哀痛社会人生的诗作,以此为依据可知当时存在着悲美的审美心理和感伤主义文学思潮。但细观《文选》所选各个朝代哀伤类诗作的写作背景,可知其中的哀伤情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一个发展的轨迹。建安时期的哀伤带着慷慨进取的功业之心,正始名士则用以怪诞之举抗议世俗社会、躲避祸乱而产生的悲哀无望取代功业之心,两晋时期又出现了从哀叹社会向哀叹人生的变化,至南北朝时期哀伤情绪逐渐淡化而出现将哀伤抽象化、概念化的总结式作品。
《文选》“哀伤”类诗歌对唐代感物而哀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从隋唐间的曹宪开始就形成了“《文选》学”,至盛唐时代,《文选》成为士子的必读经典。《文选》诗体“哀伤”类作品对唐诗的影响可分两个方面:从文本上看,唐诗中有诸多语句直接借鉴或化用《文选》诗体“哀伤”类诗作。如沈?期《古歌》中“绣户徘徊明月光” [17]出于曹植《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1]428,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无鱼良可哀” [18]出于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脆促良可哀” [1]433,等等。从情感上看,诸多唐诗在描写社会动乱、个人失意之时所抒发的哀伤情感都可见《文选》诗体“哀伤”诗作的影子。比如白居易随感遇而写的感伤诗中,除讽谕教化的功用外,所体现出的悲哀伤感也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哀伤情感一脉相承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使文人们创作了大量的哀伤诗作,这种写作背景也与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物感说”在此时走向成熟密切相关。“物感”是指审美主体对客观现实所产生的感受,物感于心而生情,“物感”是创作主体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起点。从先秦时期《礼记·乐记》以心物交感多样性的角度来论述音乐的本源开始,“物感说”在文学艺术领域一直存在和发展着,而且对中国的文论和诗论影响深远。在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背景下,“物感说”中的“物”从社会事物向自然景物变化;“感”从集体情感向个人情感变化,这在《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著作中都有诸多阐发。在《文选》诗体“哀伤”类所选诗作中也有所体现,上文已论及。
《文选》哀伤诗中的哀伤情感,可以看作“物感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体现,这与日本传统的“物哀”精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本“物哀”的审美理念有着久远的历史,“物哀”一词始于本居宣长(公元1730—1801年)对《源氏物语》的评论。叶渭渠先生在《日本文学思潮史》中,将物哀解释为“‘物’是客观的存在,‘哀’是主观的感情,两者调和为一,达到心物合一” [19]。“物哀”不单指悲哀的情感,也包括人生中赞赏、亲爱、共鸣、同情、可怜等情感体验。“物感说”与“物哀”精神在文学审美上的共同点是都强调现实客体对创作主体的作用,而且在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下这种作用的情感表现都不过度。二者的主要差异是“物感说”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之上,“物哀”则是建立在直观感受上的,且受佛教影响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