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英译的主体性
天津师范大学 张智中
汉诗英译的主体性
天津师范大学 张智中
诗不可译或难译,只有以创补失,才能译出原诗的情趣和意象。诗歌的可译论,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当译者缺乏创造性之时,诗歌就是在翻译中流失的东西;当译者充分发挥其创造性之时,诗歌便是通过翻译和译者而获得的东西。因此,创造性是诗歌翻译的生命。另一方面,如果译者的创造性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断送诗歌翻译的生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当是诗歌译者应该牢记的座右铭。
汉诗英译;主体性;创造性;创造性的限度
一、引言
诗歌不可译论者认为,诗是内容和形式,或情趣和意象的统一体;诗是不可译的,因为诗的情趣和内容不能用另一种语言形式来表达;由于两种语言、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同一意象造成的情趣、引起的联想也不尽相同,所以诗作为内容和形式、情趣和意象的统一体,是不可译的。同时,诗歌可译论者认为,诗不可译论者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译诗不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诗的情趣和意象;但诗不可译论者的错误,是认为译诗一点也不能传达原诗的情趣和意象。有了以创补失论,诗歌就不再是不可译的了;并且,只有以创补失,才能译出原诗的情趣和意象。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诗歌翻译更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说诗歌可译,其实是指诗歌在妥协基础之上的可译。有了以创补失论,妥协的程度变小了,诗歌的可译度也就增大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所创大于所失,译诗或可胜过原诗。诗歌的可译论,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二、汉诗英译:谁是合格的译者?
格拉汉姆(A. C. Graham)说:“我们不能把翻译工作留给中国人,因为翻译最好是译成译者自己的语言,而不是从他自己的语言译出来”(丛滋杭 2007: 148)。但是,一些中国的学者如许渊冲等,却持相反观点:汉诗英译只能由中国人来做,因为外国人的汉语水平有限,往往理解失误,而且英文表达有时也不怎么高明。
例如,王昌龄《出塞二首》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一句,Bynner译作The moon goes back to the time of Qin, the wall to the time of Han. Bynner不谙“互文”现象,把明月看作是秦代的明月,把边关咬定为汉朝的边关。许渊冲则译成The moon still shines on mountain passes as of yore, 为后一句“万里长征人未还”(How many guardsmen of the Great Wall are no more!)做了很好的铺垫。两行译诗连起来读,就可触摸到悠远的历史感以及诗人忧世伤时的情怀: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边关还是那个边关。可是,这不断重复着的边关战火和无数热血男儿尸骨遍野的悲剧,何时会有个了结呢?
杜牧的《金谷园》是一首吊古伤今之作。其中,“落花犹似坠楼人”,诗人的这一联想不仅使绿珠的“坠楼”跟花的凋零在外观上具有可比性,而且揭示了绿珠的命运跟落花有相似之处。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寄托诗人对绿珠的深切同情。Giles 将这一结句译作Petals, like nymphs from balconies, come tumbling to the ground。 Giles没有确切把握作者写这一句诗的真实用意,当然就难以传达原作吊古伤今的意蕴了。这样翻译不仅皮相,而且会使英语读者觉得一头雾水:为什么把落花比作精灵或美少女,从阳台上掉下来呢?(丛滋杭 2008: 93-94)
可见,Bynner也好,Giles也好,在理解不到位的情况下,翻译自然也就不会到位,译诗也就不会令人满意。汉诗英译,一如其他类型的翻译,仍然是理解占据第一位置。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究竟该由西方人士还是中国译者来完成,实乃不可一概而论。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应该由英美人士来做,因为他们英语的语感和语言功底,毕竟比中国人要高出许多。然而,日本人小畑薰良(Shigeyoshi Obata)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 Bernhard),英语和汉语均非他们的母语,两人却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方面孜孜以求,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此二译者,对于那些执着于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中国学者或译家来说,岂不是一种很好的鞭策与鼓励?
总之,汉诗英译,谁是合格的译者?答案不是一定的。“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中国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林语堂 1995: 154)精于汉诗英译的林语堂,一方面鼓励中国人从事汉译英,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项工作的艰难性。
三、译者的创造性
高健说:“等值等效说比较更适合于以资料、事实为主的科技翻译,而不太适用于语言本身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学翻译;换句话说,它更适合于整个翻译阶程中较低层次的翻译(在这类翻译中一切似乎都已有其现成的译法),而不太适合于较高层次的翻译(其中一切几乎全无定法,而必须重新创造)。”(丛滋杭 2007: 59-60)这就意味着,翻译若只求语言层面的等值等效,那只是较低层次的翻译,译文求得信、达即可,译者也只是译匠而已。只有当翻译进入审美层面,译文方可望达而至雅,此时的翻译才称得上是较高层次的翻译,译者才具备译家的资格。
其实,任何翻译,无论如何讲究忠实和拘泥于原文,都不可能在语言层次上与原文完全相同。就诗歌翻译,或汉诗英译而言,情况自然更是如此。朱光潜说:“诗不但不能翻译,而且不能用另一套语言去解释。诗本身就是它的唯一的最恰当的解释。翻译或改作,如果仍是诗,也必另是一首诗,不能代替原作。”(孙玉石2007: 136)思果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诗不能译,译就是毁灭。译者只能再创造,把一首诗用另外一种文字重新写出来。音调、韵律、辞藻是诗的性命,一经翻译,就烟消云散了。只有另创音调、韵律、辞藻;不过这已经不是翻译,而是创造。”(丛滋杭 2007: 153)
这些论述都强调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诗歌不能被翻译,诗歌只能被创造,或者被重新(二度)创造。“综观中外翻译史,创造性叛逆的翻译就是活生生的翻译史。创造性叛逆就像色谱一样是一个连续体,不同的译作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不同位置。它们没有绝对之分,只有程度之别。”(董明 2006: 186)就汉诗英译而言,重点应该在于原诗美感和诗性的再现。另外,译者的创造性,往往通向译者的译诗风格。
(一)汉诗英译:美感和诗性的再现
诗歌之所以引人入胜,乃在于潜藏于文字之下的审美内涵,而非其文字表层的基本信息。因此,汉诗英译所关注的,应是原诗内在美感和诗性的再现,而不仅仅是表层文字的转换。如果译者只将汉诗的基本信息译出,而置原诗的审美信息于不顾的话,译诗必将是失败的。
就汉诗而言,“诗蕴蓄着多种意思,读者也可以做多种理解。诗的内涵表现了无限伸张的弹性”(孙玉石 2007: 10)。言少意多,正是汉语诗歌的一大特点。“翻译的动态性充分体现在其灵活性中,翻译在无奈的情况下,把含蓄的转变为直白的,缩短了符号与所指的距离,达致理解的清晰化,同时也破坏了源语文本原本的审美距离,……在文学作品里,话语信息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所传递出的附属信息更为重要”(孙艺风 2004: 58)。所谓“附属信息”,这里可理解为附属在语言文字之上的审美信息。正是汉诗英译中原诗审美信息——而不是基本信息——的传译,才给译者以巨大的再创造空间。
约翰·德纳姆说:“翻译诗不单是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从一种语言里的诗译成另一种语言里的诗。”(丛滋杭 2008: 148)因此,译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其最终的译诗,必须是“诗”。即是说,译诗必须具有诗性,而且要具有充沛的诗性,至少与原诗一样的诗性。换言之,诗性,应该是汉诗英译的重点所在。
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要深入体会原作的审美经验。“由于英汉语在审美价值、表现方式、语域应用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翻译时这些美学要素多有磨蚀。译者应该运用译语最恰切的表达手段来再现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词序、语法、结构等语言细节,但必须对原文总的语言特点,如修辞手段、谋篇布局、效果氛围等进行全盘考虑,然后把原文重新组合成合适的译文。整个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审美过程,译者要考虑译者的自身条件、翻译规范和读者接受等多种因素,把原文的审美价值最大限度地转化到译文中去,使译文读者真正地体会到原文的审美价值。”(严晓江 2008: 169)本来,汉诗诗性浓郁,如诗;英诗诗性淡薄,如文。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若译者不注重汉诗美感和诗性的再现,则译诗必将流于浅淡寡味。“一个知道用审美眼光看待一切的人,不分高低,都是高质量的人。”(曹文轩 2003: 505)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说:一个知道用审美眼光看待汉语诗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高质量的译者。
(二)汉诗英译的创造性
就汉英诗歌而言,两者在语言上的差别,巨大昭然。此时,若译者试图“忠实”地传递意义,就会事与愿违。因此,汉诗英译者应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王佐良说:“每一首好的译诗不仅是好的翻译,也是好的创作。”(廖七一 2006: 53)这就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意识。著名翻译家蒂里特(Tyrwitt)说:“翻译贵在发幽掘微,穷其毫末。在选词与琢句方面,要译出其文;在性格与风格方面,要译出其人;在褒贬与爱憎方面,要译出其情;在神韵与语感方面,要译出其声。”(严晓江 2008: 178)郭沫若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谢天振 2007: 72)
其实,翻译诗歌的过程,一如诗歌的写作过程。诗歌写作的过程,便是十分艰苦的体现创造性劳动的过程。那么,译诗又何尝不相类似?“译诗不是复制原文,而是创作相似的文本,是‘种子移植’(transplanting the seed),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给译诗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活力”(丛滋杭 2007: 152)。文学性越强,语言留给人们的阐释空间就越大。毫无疑问,汉诗的文学性极强,读者或译者的阐释空间也就极大。那么,译者的主体性,便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
另外,“在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域里,翻译还应该为译入语注入新鲜的文体风格。在此意义上,轻度的违反规范不仅可以容忍,反倒可能受到鼓励。一般而言,这样的违规行为并非译者有意而为,而是由于在源文本已经出现了违背规范的情形,在文学作品里较常见,所谓‘陌生化’便是有意识的违规之举”(孙艺风 2004: 190)。所以,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在语言方面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语言学家维尼弗来德·诺俄特尼认为,诗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技巧本质上就是对语言的潜在属性的一种开拓和发展”(沈天鸿 2005: 14)。那么,汉诗英译者们所使用的语言技巧,本质上就应该是对英语语言的潜在属性的一种开拓和发展。例如宋人杨万里的《小池》及其英译: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A Pond The fountain eyes quietly treasure the tender streams, The tree shadows reflecting in water love the sunny softness; The young lotus blooms just shoot their sharp buds, On which dragonflies have already settled their tender kisses.
(廖昌胤 译)
将“泉眼”直译为fountain eyes, 大佳!这正是丰富译入语、开发译入语语言潜力的手段之一。可以想见,汉词“泉眼”在诞生之初,当具有“陌生化”之效果。而随着该词的频繁使用,便失去了“陌生”之感。此处直译为fountain eyes, 却不为英语搭配所常见,便保留了“泉眼”当初的“陌生化”效果。再如树才《莲花》一诗中的两行及其英译:
我只是在学习遗忘—— 好让偌大的宇宙不被肉眼瞥见。 I’m merely learning to forget— Let that huge universe be unseen by eyes of flesh.
(Denis Mair 译)
“肉眼”一般英文作naked eyes, 译文以eyes of flesh出之,于是生动新鲜,令读者眼睛一亮。英语语言的潜力,得以开发。“译文语言运用上的融合创新有一个典型的标志:译作中的若干词句会作为名言警句流传开来,继承下去,成为后人的翻译典范,或者进入译入语言系统,成为新的创作源泉”(王宏印 2002: 5)。
朱光潜认为:“读诗就是再做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如此,没有创造就不能有欣赏。”(孙玉石 2007: 9)我们可以说:诗歌阅读的创造性,通向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因此,巴斯奈特说:“诗歌不是在翻译中流失的东西,诗歌是我们通过翻译和翻译者而获得的东西。”(廖七一 2006: 117-118)当译者缺乏创造性之时,诗歌就是在翻译中流失的东西;当译者充分发挥其创造性之时,诗歌便是通过翻译和翻译者而获得的东西。
综观古今中外翻译史,凡一流的译文,都出自一流译家之手;而一流的译家,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与创造性。“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每一篇译作都蕴含着译者智慧的结晶,是创造性的产物,自然也就融合了译者自身的审美志趣、价值取向和个人爱好,而这正是翻译的魅力所在。”(黄中习 2005: 121)其实,有人把翻译比喻成演奏,我们觉得这倒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同一首乐曲,同一首歌,由不同的演奏家来演奏或由不同的歌唱家来歌唱,其风格自然有别——甚至还可能千差万别。那么,真的可以有那么大的差别,而不需要什么约束了吗?答曰:否。唯一的束缚,大概也就是所演奏的乐曲或所唱的歌的意境。只要能把乐曲或歌曲的意境表现得酣畅淋漓,他就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演奏家或歌唱家,无论其风格如何。同一首乐曲,由不同的演奏者来演奏,趣味不同,这是自然的事情;同一首乐曲,由不同的乐器来演奏,其风格也有差异。这里,如果我们把演奏者比喻成了翻译者,那么,不同的乐器,正是通向不同翻译策略之下的不同译文。译者的创造性,还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变通上。例如王维的《相思》及其三种英译: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英译一: Love Seeds Red berries grow in southern land. How many load in spring the trees? Gather them till full is your hand; They would revive fond memories.
(许渊冲 译) 英译二: The Love Pea This scarlet pea is from the southern land, Where e’ven in autumn with fresh sprigs it grows. I would that you pick as many as you can— For fond remembrance nothing is like those!
(王宝童 译) 英译三: Missing the Loved One Red beans grow in the south. In autumn they appear on a few branches. Pick some. They wake the solitary heart.
(Tony Barnstone, Willis Barnstone & Xu Haixin 译)
在“春来发几枝”中,“春来”一作“秋来”。英译一采用“春来”而译之(in spring);英译二和英译三却采取后者而译之(in autumn)。英译一的译者许渊冲,此一译诗,虽然未做变通,但他处之“春”,仍有变通手段的运用。如王维《鸟鸣涧》一诗及许氏英译: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Sweet laurel blooms fall unenjoyed; Vague hills dissolve into night void. The moonrise startles birds to sing; Their twitter fills the dale with spring.
(许渊冲 译)
“桂花落”说明时间是秋天,而“春山”、“春涧”又明示时间是春天。显然,原诗存在时间上的矛盾。在许译中,spring的涵义不是“春天”,而是“春意”,这样就巧妙地解决了诗歌在时间上的矛盾问题。
不过,汉诗英译的创造性,或者译者的创造性,不是随心所欲或无限制的。译者的创造性,是在忠实性基础之上的创造性。换言之,忠实性和创造性在对立的同时,必须取得统一。如果译者一味坚持忠实性而忽略创造性,就会导致硬译或死译;如果译者只注重创造性而脱离忠实性,就会带来胡译和乱译。这即是说,在发挥译者创造性之时,译者应该译而有度,收放自然。例如《木兰辞》中的八句及其英译:
朝辞爷娘去, 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 暮宿黑山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And then before the sun began his journey steep She kissed her parents in their troubled sleep, Caressing them with fingers soft and light, She quietly passed from their conscious sight, And mounting horse she with her comrades rode Into the night to meet what fate forebode; And as her secret not a comrade knew, Her fears soon vanished as the morning dew, That day they galloped westward fast and far, Nor paused until they saw the evening star, Then by the Yellow River’s rushing flood They stopped to rest and cool their fevered blood. The turbid stream swept on the swirl and foam Dispelling Muh-Lan’s dreams of friends and home; Muh-Lan! Muh-Lan! She heard her mother cry— The waters roared and thundered in reply! Muh-Lan! Muh-Lan! She heard her father sigh— The river surged in angry billows by! The second night they reach the River Black, And on the range which feeds it, bivouac; Muh-Lan! Muh-Lan! She heard her father pray— While on the ridge the Tartars’ horses neigh; Muh-Lan! Muh-Lan! Her mother’s lips let fall! The Tartars’ camp sends forth a bugle call!
(Charles Budd 译)
“《木兰辞》中的八句,译者竟添枝加叶地铺叙为24行17句。……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原辞,就可以立即发现译者的文辞虽然华美,但已经脱离了原文的语义限制,信笔臆造,而且不符合汉民族的行为习惯。这可能是为特定读者(如儿童)讲述故事而做的权宜性改写,碍难称为译诗”(刘宓庆 2005: 26-27)。
四、小结
在强调汉诗英译的主体性或译者的创造性的同时,译者也该有所节制;否则,如果译者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则无疑会断送诗歌翻译的生命。译者的创造性,是在忠实性基础之上的创造性。换言之,忠实性和创造性在对立的同时,必须取得统一。如果译者一味坚持忠实性而忽略创造性,就会导致硬译或死译;如果译者只注重创造性而脱离忠实性,就会带来胡译和乱译。这即是说,在发挥译者创造性之时,译者应该译而有度,收放自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当是诗歌译者应该牢记的座右铭。
曹文轩. 2003. 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丛滋杭. 2007.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丛滋杭. 2008. 中西方诗学的碰撞[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董 明. 2006. 翻译: 创造性叛逆[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黄中习. 2005. 中华对联研究与英译初探[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廖七一. 2006.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林语堂. 1995. 林语堂自传[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刘宓庆. 2005. 翻译美学导论(修订本)[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沈天鸿. 2005. 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30讲[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孙艺风. 2004. 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孙玉石. 2007. 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宏印. 2002. 参古定法,望今制奇——探询文学翻译批评的评判标准[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3): 1-5.
谢天振. 2007. 译介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严晓江. 2008.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侯 健)
通讯地址: 300387 天津市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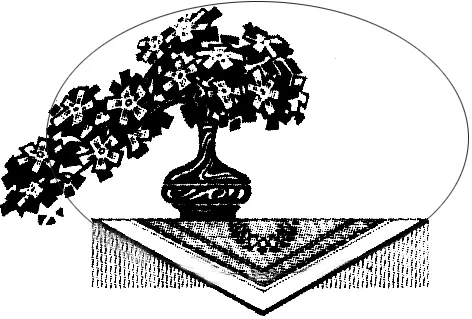
本文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诗英译美学研究”(项目批准号: 13FYY007)和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副文本的中国古典诗歌国外英译新论研究”(项目批准号: 13BYY035)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H059
A
2095-5723(2015)01-0078-06
2015-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