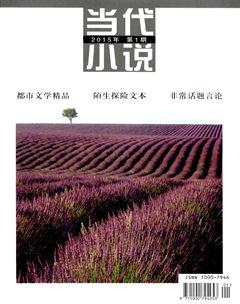回忆录
尹群
在我所有的亲戚当中,算起来我大舅是出息最大发的一个,一辈子做官,从公社武装部干事做起,一路做上去,最后做到县政协副主席。亲戚们不知道政协副主席是个多大的官,但听说跟副县长是平级之后,就连走路的架势都牛了起来。每逢聚到一起,说上一阵庄稼长势,展望一下未来,抱怨几句物价忒不像话,再骂上几句狗日的村干部,之后必然会谈论到我大舅,谈论我大舅的时候,是那种钦佩的口吻,眼神中充满了崇拜。说人家我大舅这辈子,那可真是!亲戚们崇拜我大舅,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我大舅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得非常明白。我的大表弟在外乡,三十几岁已经快要当上了书记;我的二表弟在县交通局当办公室主任,虽然官不算大,但实惠,管着全局上下的吃喝拉撒;我的表妹先是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后来调到县妇联,当了副主任。应该说我大舅的几个孩子如今都混得有头有脸,前程似锦。比起其他亲戚家那些没能走出庄稼院的孩子来,怎么说呢,简直是天上地下之别。所以亲戚们对我大舅佩服得五体投地。前几年大舅退休之后,大会小会都不参加了,闲起来了,有点落寞。大舅一贯是个上进心强的人,不想虚度光阴,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得发挥点余热,为政协工作再立新功,于是花了一年多时间,写了部回忆录,据说有可能成为县志办编县志的文史资料,载入史册也说不定。我猜我大舅写回忆录,附庸风雅是一个方面,多半还是冲着这个来的。听说我舞文弄墨,发表过几篇小说,打电话让我帮他修改润色。大舅一面交给我手稿,一面嘱咐说,记住,没出版之前,不能给任何人看。更不能遗失。大舅的口气,是上级对下属的口气。跟在机关里说话那样,冷冰冰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大舅平时跟我们说话就是这样。不过大舅随后又补了一句,说他最信得过我。而且带着一丝诡谲的笑意。这句话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赶紧点头说舅您放心吧。并且还恭维大舅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谢谢您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大舅说你少扯没用的(后来我发现,这句话原来是大舅的一句口头禅)。稿子在大舅手里抖抖的,他再一次郑重地看了我一眼,好像交给我的是一份“鸡毛信”。
从小亲戚们对大舅的崇拜便影响了我,让我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想到我有个当官的大舅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浑身增添了一股无穷的力量。虽然在我面对我大舅的时候没有亲切只有畏惧。长大之后,跟大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我姥爷的生日酒桌上,面对自己家里人,大舅也改不了官腔,还要一本正经地讲上半天开场白,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从全县讲到全公社,最后讲到我们家族,讲到姥爷的生日,大伙端了半天酒杯,端得胳膊酸,最后在大舅对我姥爷的祝福声中,连干三杯。然后,大舅把筷子放在饭碗上,又讲起来。我发现,大舅不动筷,桌上的人谁也不动筷。
下面,还是说说我大舅的回忆录吧。
一
首先,关于他当初婚恋的记述。那时我虽然尚小,是个正念小学的孩子,但关于大舅的婚事,也算亲历,大舅结婚时我还吃过喜糖,后来还经常听母亲说过。在三十多年后大舅的回忆录里,大舅的记述十分简要: 一九七一年,我从沈阳部队某部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我原来所在的红旗公社武装部当干事。不久经人介绍,与红旗小学的一名民办女教师处了对象。后来,因为那名民办女教师的哥哥出了事,犯了法,强奸杀人,我怕影响日后的前程,就提出与其分手。后又经人介绍,与公社革委会主任宋百川的女儿订婚,并于一九七二年冬季结婚。婚后夫妻相敬如宾,至今已经走过三十六个春秋。
而据我所知,事情的原委并非如此简单。大舅转业后处的第一个对象确实是红旗小学的一名民办老师,这个人叫高红。当介绍人介绍高红是个民办老师的时候,大舅有些犹豫了,大舅想找的是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对象,但是在见到高红之后,大舅的想法改变了,对高红有没有正式工作似乎并不那么在意了,大舅被高红的漂亮打动了。那段时间,大舅天天吃过晚饭之后便去找高红,两个人一起出去溜达。在部队呆了几年的大舅,思想已经明显有别于一般的农村青年。那应该是秋天了,新学期刚开学,高红白天很忙。披着金色的晚霞,慢慢慢慢走在学校旁边的庄稼地边上,大舅双手插在裤兜里,高红呢则是随手掐一片草叶在手里揪着,揪着,不停地揪着,把一片草叶揪成碎屑,再随手掐片草叶揪。揪到最后,纤白的手指都染绿了。庄稼成熟的气息扑面而来,人们的目光追逐着他俩的身影,望着望着忽地就不见了。离学校不远是红旗大队的果园,果园很大,有两个小学操场那么大,樱桃树,李子树,沙果树,林木茂盛。树下的空地上,种着白菜萝卜。果园的四周用柳树条夹的障子,当年的柳条,如今已经长成了碗口粗的柳树,枝条纷披,把个果园遮挡得严严实实风雨不透。隐蔽的地方,被小孩子已经扒开了豁口。晚霞照在果园里,树枝上的沙果金黄明亮。原来,大舅和高红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被孩子们扒开的豁口处,大舅就拽着高红钻进果园去了。
若是后来没有宋兵的出现,大舅跟高红就要结婚了。就在那年的八月,公社新调来个革委会主任,就是大舅提到的宋百川,那年宋主任的女儿宋兵刚好高中毕业,被宋主任安排在公社文化站上班。文化站跟武装部离不远,没隔几步路,这样每天大舅都能看见宋兵。应该说,我大舅年轻的时候,长得确实是一表人才。再加上每天穿着一身草绿军装,雄赳赳气昂昂的,人就更是英姿勃发。许多年轻的女孩子见了都忍不住多看一眼。宋兵长得算一般人,但是穿戴好,打扮得比别人时髦,也比一般的女孩子大方,不那么扭扭捏捏,敢说敢做,宋兵看上了大舅,每天总往武装部跑。一来二去,大舅就动了心思。其实,就高红跟宋兵两个人比,宋兵长得远没有高红漂亮,但大舅最后选择了宋兵,放弃了高红,大舅主要是从自己的前程上考虑的。这一点,任谁都能看得出来。问题是,大舅提出跟高红分手的时候,没有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反而说是因为高红,因为高红的家族里面出了个强奸杀人犯。当高红哭着对大舅说,她已经有了大舅的孩子的时候,大舅一脸的惊诧和无辜。甚至认为高红是在讹诈他。还有,大舅说他跟宋兵婚后夫妻感情很好,相敬如宾,也是溢美之词。事实上,大舅当初根本就没有看上宋兵的长相,所以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随着大舅步步高升,作为当官的大舅,在外面不可能没有别的女人。为此,宋兵跟大舅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硝烟不断。起初,因为宋兵父亲的关系,大舅还能服从宋兵管束。后来宋兵的父亲出事,下台了,大舅就无所顾忌了,一干仗干脆借口外出开会,多少天不回家。吵到后来,人也老了,儿女也大了,不那么吵了。宋兵也认了,睁一眼闭一眼。我大舅妈宋兵最后总结了,说女人哪,要想婚姻家庭幸福,千万别找当官的。
当我就这段史实求证大舅时,大舅挠着稀疏的白发,浑浊的眼睛空洞地望向远处,似乎陷入了对那段往事的回忆。我试探着问大舅,你跟高红以后再也没来往吗?大舅说,说真的,踹了高红他心里别提多难受啦。有多少个夜晚都睡不着觉,起来跑到那个果园里去坐着。当了领导之后,他也试图替高红办点事,比如帮高红转正,来弥补一下,可是高红一直恨他,不理他。也不用他帮忙。再说宋兵对他看得也特别紧。高红后来怎么样?大舅叹口气,摇摇头:她工作干得不好,破罐子破摔,后来干脆不干了,嫁到很远的地方。那地方我后来去过,公共汽车一天只有一趟。
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广大“知青”开始一批一批地返城。“知青”们为了早日返城,不惜一切代价,给领导干部送礼。那时候送礼,可不像现在这样直接往你兜里塞钱,那时候就是送条烟送两瓶酒,过年扛块猪肉柈子,一般能舍得送块表,比如上海表,很少。“上海表”贵不说,主要是不好买。但知青们有办法,想方设法淘弄到。那时公社一把手姓石,石主任,此人贪酒好色。群众都知道,他听说哪个地方有好看的妇女,他就去哪个地方检查工作检查得勤。反过来,大伙看见石主任往哪个地方检查工作检查得勤,就猜想哪个地方肯定出了好看的女人。他包的生产队,稍微有点姿色的妇女,基本上常用的手段,是先找你的毛病,让你怕他。怕得了不得,他让你干啥你会立马干啥。人们发现,石主任开始找哪个女人的毛病了,十有八九是看上了哪个女人。大舅经常跟石主任下乡包队,对于石主任的这个嗜好,大舅是再了解不过了。但大舅却从不往外说石主任的这些馊事。所以石主任走到哪儿都愿意领着大舅。大舅当时已是公社“组委”,就是组织委员,在公社几十名干部当中,组织委员一职是相当重要的。“组委”的下一步,就可以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后来石主任出事了,强奸女知青。县里下来调查取证,详细了解事情原委,自然要找跟石主任过从甚密的人。我大舅从始至终都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石主任也一口咬定女知青是诬陷。那女知青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结果此事不了了之。石主任安然无恙,没多久大舅就被提拔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关于当年石主任强奸女知青一事,大舅的回忆录里有比较详尽的记述(此时石主任已年逾古稀,前列腺弄得他裤裆里总是一股臊烘烘的味)。那个哈尔滨女知青也姓石,叫石文娟,长得白净,苗条,嘴也甜(女知青们大多嘴都甜),为了回城的事去找石主任。石文娟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石字,您年纪大,您是长辈。所以石文娟一张嘴没管石主任叫主任,叫石叔。叫得又亲切,又深情。石主任浑身僵硬。石文娟说她的母亲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准备提前退休,按政策她可以回城接替她母亲的工作。再者母亲有病,身边也确实需要人照顾,希望石叔能考虑她眼前的困难,让她第一批返城。石文娟说她母亲病的时候说得很详细,还掏出雪白的手绢轻轻在眼睛上沾了沾。石主任正襟危坐,板着面孔,拒腐蚀永不沾的样子,发黄的手指间夹着根烟卷,眯着的眼睛透过淡淡的烟雾,盯着面前这个跟他同姓的女知青。石文娟以为石主任在认真听她陈述理由,说完了就等着听石主任的意见。可是石主任依然正襟危坐,用警察审视犯人的眼光盯着石文娟,似乎是在分析石文娟说的话里有没有谎言。石文娟脸忽地热了,像火烧云,石主任的眼前犹如忽然绽放了一朵鲜花。石文娟等了半天也没有得到一句答复。石主任到最后只是出口长气,说好,很好。然后往窗外望了望,不远的球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石主任粗大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站起来,一面拍一拍裤子上的烟灰,一面说今天他有事,告诉石文娟明天再来谈。这件事,他须跟其他领导商量。第二天是周末。石文娟走出门外忽然想起来,就回头怯怯地问石主任,明天是周末,您不休吗?石主任说,休什么?不休。背着手走了。第二天,公社院子里静悄悄的,走廊里也是静悄悄的,都放假了嘛。石文娟抱着一线希望,壮着胆子再去敲石主任办公室的门。一敲,石主任果然在。石文娟心里一热。觉得石主任虽然面上冷,却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接待群众。石文娟进了门,石主任盯着她,并不让座,而是上下打量石文娟的身材。还让石文娟转过身去,看石文娟的后面。石文娟手足无措。石主任的办公桌上,放一杯水,冒着热气,石主任用下巴示意石文娟坐那儿。石文娟怯生生地坐下。石主任又用下巴示意石文娟喝水,石文娟迟疑着端起水杯,端了半天,才敢啜一小口。又是半天,才又啜了一小口。石主任看着石文娟喝水,问石文娟今年多大了,有对象没有。顿了顿,话锋一转,语气冰冷:有人反映,你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过不满言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积极,时常泡病号,回家呆着。一呆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这回事吗?石文娟心惊肉跳地站起来,石主任的大手按住了她瘦削的肩膀。石主任的办公室里有个套间,套间里有床。石主任站在套间里面命令石文娟,你还愣着干什么?进来!石主任强拉石文娟进套间的时候,石文娟还挣扎着喊了几声“石叔”。
大舅在回忆录里对石文娟的遭遇表现了应有的同情。说到此事,大舅埋怨石文娟年轻没经验,一点证据没留下就去告领导强奸,不是闲扯吗?所以当初大舅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石文娟铁定是被石主任强奸了,但石文娟一点胜算都没有,当然不能向着她说话了。多年以后,当了领导的大舅,曾经接待过几回当年的哈尔滨知青故地重游,大舅还没忘向他们打听过石文娟的情况。
三
在回忆录里,我大舅带着十分自豪的口吻说他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乡镇(八十年代中期公社改为乡镇)一把手。而且一当就是十几年。他所在的乡镇,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他本人也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成为县里树立的典型。那个年代“现场会”是比较多的,诸如“抗旱打井现场会”、“玉米一埯双株现场会”、“秸秆还田现场会”、“小流域治理现场会”、“植树造林现场会”等等,各种名目的现场会,多数在他当“一把手”的那个乡里开。如果有上面下来检查参观之类的事,县里也把这些检查团参观团往我大舅那个乡上领。参加工作之后我大舅赶上的运动也算不少了,比如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九七六年的批判“四人帮”、一九八九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我大舅没有一样不是表现积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从来都走在别人的前面。用我大舅的话说,交上一张令上级满意的答卷(这段记述,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上学,那时候特别听老师的话,每当老师布置个什么任务,我们都是积极并且超额完成,为的就是听到老师的一句表扬,当个模范标兵啥的)。大舅为了证明他这段记述的真实性,还举了不少具体的事例。比如有一年,上面忽然刮起一阵风,号召大力发展养殖业,各个乡镇都下达了具体指标,到时上级不听汇报,要实地检查落实情况,完不成任务的,拿一把手是问。要求各乡镇把这项任务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为此,全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养牛养羊养猪养鸡运动。我大舅召开全乡干部大会,下死命令,每个农户必须养蛋鸡多少白鹅多少,黄牛多少仔猪多少。有困难的家庭,乡政府给予贷款扶持。应该说,大舅所在的乡拥有广阔的草原,具有发展养殖业的良好条件。后来,全县三级干部现场会就在我大舅那个乡召开,大舅在大会上作了经验报告。三级干部们还参观了下面一个村屯的养殖情况,挨家挨户看。结果令人满意。家家圈里有猪,栏里有牛,鹅满坡,鸡满架。当时很多人对我大舅的工作魄力都伸出大拇指,认为大舅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不愧是样板。大舅在群众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大舅说,提起他的名字没有不知道的。
大舅的记述只写到这里,不知情的,当然以为我大舅工作能力强,有魄力,有事业心,是个一心为民的好干部。事实上,这背后的故事我大舅并没有全部讲出来。讲出来的话,我大舅的高大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我大舅那个被参观的村,任务之所以完成得那么好,是因为我大舅事先就跟那个村的干部下了死命令,每家每户到时必须有物在。若有一户完不成指标,罚款不说,村支书回家抱孩子。村支书当然不敢怠慢,谁能拿自己的乌纱帽当儿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还是我大舅有经验,给他提了醒。我大舅说,活人能让尿憋死?发动群众。村支书说发动群众?没懂。我大舅骂了一句粗话(在乡下当干部,说话文绉绉的不行,得骂人,这样才有魄力),干脆明白地告诉他,发动群众的意思,就是上亲戚朋友家去借,什么没有就借什么,借牛借羊,借鸡借鹅。结果一夜之间就全借回来了。不幸的是,那年入冬,一场瘟疫,鸡死了,猪没了。事后,那个村的村民提起此事,气愤难平,暗地里把我大舅和那些乡村干部骂了个狗血喷头。
四
说起来,小时候我们很少上大舅家串门。母亲也不让我们去。上二舅家上老舅家去的时候比较多,可能是因为二舅和老舅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比较贫困的农村家庭,没什么差距吧。大舅家就不同了。大舅当官,有钱有势,住的是红砖房,吃的穿的都比我们好多了。特别是我大舅妈宋兵,架子大,根本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宋兵眼睛细长,嘴唇精薄,皮肤白净,衣裳总是带着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她家的收音机,缝纫机,后来的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等,几乎所有的家具上面,都苫着一块雪白的白布罩,里屋的门上撂着半截白门帘,上面绣了一朵一朵的梅花。宋兵爱干净,从她的眼神就能看出来,她嫌我们穿戴破烂,不讲卫生。宋兵有时也把她家孩子们穿过的衣裳送给我们,也给我们水果吃,但是从来没留我们在她家吃过饭。不是怕吃,是不愿看我们那狼吞虎咽的吃相。当然,大舅家两个人上班,挣现钱,生活条件好是正常的。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大舅家送礼的人又多,大舅家吃不了,用不尽,就再送给亲戚们。我们家年年都能吃到大舅家送来的鸡呀鱼的。大舅知道我父亲爱喝酒,所以给我父亲另外再拿几瓶酒,都是好酒。有一年,大舅家的大表弟,被大舅打发给我父亲送来两瓶酒,我父亲一看是“茅台”,感动得不得了,说这不叫我喝瞎了吗?叫我大表弟拿回去。我大表弟说,他家柜子里,好烟好酒有的是。本来他爸要给我父亲多拿两瓶,拿四瓶,被宋兵抢回去了(那时我大表弟才十多岁)。我母亲看着我父亲撇下嘴。我父亲暗暗扯一下我母亲的袖子。父亲在别人面前经常夸耀说“茅台”怎么怎么好喝,大概是以为别人不知道他喝过“茅台”呢,说比“一元糠麸”(就是当地的小烧,一元钱一斤)好喝多啦!也比“青泉”(我们县酒厂生产的瓶装白酒,一般过年过节串个门,拎两瓶“青泉”白酒就觉得不错不错了)好喝。喝多少都不上头。要不是借我大舅的光,这辈子,见都别想见到“茅台”长个啥模样。因此在我们家的亲戚当中,只有我父亲对我大舅恭敬得不行。我大舅一来,我父亲倾其所有招待。换成我二舅我老舅,顶多是一盘鸡蛋炒韭菜,豆腐蘸大酱。我母亲就说我父亲是势利眼。我父亲眼一瞪,你吃人家多少,穿人家多少?你吃他们多少,穿他们多少?能一样吗?母亲没话说了。大舅和宋兵就不用说了,连大舅家的孩子都骑“凤凰”自行车,戴“上海”牌手表。
大舅家北墙上挂的一排相镜子里,有很多大舅在全国各地的留影。天安门前照的,黄山迎客松下照的,杭州西湖上照的,黄浦江边照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照的,新疆吐鲁番葡萄架下照的,蒙古包旁照的,布达拉宫前照的,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照的,漠河北极村照的……大舅跟那时候的许多干部一样,以参观学习的名义去过全国很多地方。究竟到过多少个地方他自己也说不清。只要有人说起个地方,大舅就能把那个地方的名胜古迹说出个一二来。这一点,尤其令没出过门的父亲母亲羡慕得不行。
然而,在大舅的回忆录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清正廉明的清官形象。用大舅自己的话概括,一生为官,两袖清风。下乡包队在农户家吃饭,从不白吃,每顿饭都要扔下两角钱和四两粮票。
五
看过大舅的回忆录,笔调像过去的“讲用稿”,诸如上述不实之处更是比比皆是。我一时不知该怎样跟大舅谈自己的看法。闷了几天,大舅先忍不住了,放下架子,电话里虚心地问我咋样,我敷衍说挺好。并且口气夸张地说没想到大舅还如此有文才!大舅看出我说的不是真话,并且带有调侃的味道,骂我,少给我扯没用的!你没看?我说哪敢。从头至尾,一字不落。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不过……这样吧,我再给你找两本书看看。我于是找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我国当代大文豪巴金的《随想录》,抱给大舅看。我没敢直接说大舅在回忆录里文过饰非。像大舅这样的干部,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那样一种说话做事的行为方式,不太喜欢别人提出相左的意见。在大舅读书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大舅有无思想上的变化,期待着大舅有何感想跟我交流,但大舅却越来越沉默,常常面对摊开的书本发呆。后来大舅悄悄问我,这能是真的吗?他们真的会这么揭自己的老底?大舅满脸疑惑。
就在我努力帮助我大舅把他的这部回忆录(也可以说是自传)往真实客观的方面改的时候,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我猜多半是大舅正在修改的稿子被谁偷看了——结果引来了我们家族内部的一片反对之声,其中反对最强烈的,是我大舅那几个前途无量的孩子。他们本来就瞧不起我写小说,认为我做事不务实,从来不管我叫表哥,叫我“尹大作家”,这回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我幼稚,理想主义,缺乏起码的政治头脑云云。背后说我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的大表弟媳妇说话直接,指着鼻子问我,你到底啥意思?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你怎么净给老爷子出馊主意?他老糊涂了你也糊涂了?陈芝麻烂谷子的,把那些破事都抖搂出来让人家说三道四,你叫我们这帮当儿女的脸往哪儿搁?我支吾说回忆录本来就是这样一种写法嘛。大表弟媳妇嘴一撇,说没听说过。这老爷子也是,消停地呆一会儿多好,写哪辈子回忆录呢!我没法跟她解释。我的大舅妈宋兵本来跟我大舅的感情并不太好,夫妻关系长期不睦这我是知道的。没想到连她也不同意我把大舅那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写进回忆录里。看起来,关键时刻人家还是维护丈夫的名誉。宋兵不拿好眼神看我,你大舅啥时候得罪你了,你这么坑他?我说没有没有。这怎么能是坑他呢,我这完全是为了大舅好啊!宋兵哼一声,为了你大舅好?我看你这是糟践你大舅呢!我不死心,又委婉地询问其他亲属的意见,这里面包括我大舅的姐姐姐夫,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大舅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二舅和老舅,结果,他们没有一个赞成我的想法。我二舅和老舅还好,跟我感情较深,我从小就是跟在他们屁股后长大的,嘴上没说什么,我父亲就不那么客气了,一张嘴便骂我混账,猪脑子,说那么一写,把你大舅写成啥了?你大舅,那不仅是咱家族的荣耀,也是咱家乡的荣耀!你那么一写,那不光是给咱家族脸上抹黑,也是给咱家乡百姓的脸上抹黑!你看你写小说胡编乱造无关紧要,写回忆录,关系到你大舅的生前身后啊。那么些书,让你白念啦,狗屁不懂!我父亲吧,当了十来年的农民,因为念过书,脑子好使,是我大舅把他的身份由一个农民变成了我们当地小学的民办老师,后来又帮他转了正。所以父亲的认识和表达要远胜大表弟媳妇一筹。
就在我们家族内部因为大舅的回忆录究竟应该怎么修改闹得很不愉快的时候,大舅突然得了中风,半边身子不好使,说话也含混不清。亲戚们谁来看他,大舅都嘴唇哆嗦着掉眼泪。来一个掉一回眼泪,来一个掉一回眼泪。我知道大舅是怕死。其实人到了这个时候差不多都这样。眼看着大舅的回忆录就这么前功尽弃了,别人都幸灾乐祸,我却替大舅惋惜。
大约半年之久,大舅的病情有所好转,一天我去看他,趁屋里没别人,大舅示意我到他的枕头底下掏出张字条来让我看,字是大舅写的,虽然笔画歪歪扭扭,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大舅说他的回忆录不准备出版了,稿子送给我,可以当做我写小说的素材。我问大舅,他的形象在小说里应该怎么写,大舅含混地说,随便吧……我俯下身,紧紧握住大舅的一只冰凉的手。
如今大舅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而关于他的这部小说,我至今还迟迟没有谋划成篇。我始终捉摸不定,究竟怎样写才能让九泉下的大舅灵魂得到安宁呢?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