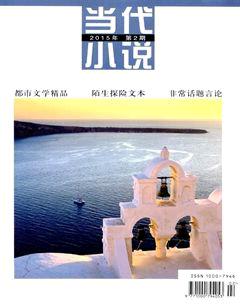小哥,你马上来电了
美桦
1
这些日子,喜旺盼爹回家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一个让人沮丧的问题,把喜旺的脑子塞得满满的,乱麻样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喜旺把希望寄托在爹身上,他相信爹一定能给出满意的答案。
爹在苦竹箐修水库,十天半个月才回乌地吉木一次。每次回来,爹都会变戏法一样,给他和弟弟一人变出颗糖或三两个花生,最不济也有几粒瓜子。除此之外,爹还会给他几个用来折三角板的香烟盒。爹不抽烟,但工地上抽烟的人多,经常可以捡到。烟盒折成三角板,往地上叭一拍,喜旺就会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里,收获更多的自信。
喜旺没有理由不高兴。爹一回来,妈妈乌黑的头发就会洗得干干净净,老远就能飘过一股雪花膏的香味。这还不说,妈妈还会做出好吃的。好像家里那几块腊肉,就专门为爹准备着。爹前脚才进门,妈妈就会生火煮腊肉,锅里再烀上半锅豆。吃饭前,妈妈把腊肉切成筷子这么厚,一咬嘴里就是一包油。油汪汪的豆汤里扔一把踩缸菜进去,那种特有的浓香,就会随着袅袅的炊烟弥散开来,馋得满寨子的人口水直流。
当然,也有让喜旺生气的时候。爹一回来,就有叔叔伯伯笑嘻嘻地用手揪喜旺的耳朵:
喜旺,你爹回来了,咬不咬你妈?
喜旺,你爹晚上和你妈打不打架?……
叔叔伯伯们每次笑呵呵地问到这样滑稽的问题,喜旺都是一脸的无辜。喜旺眨着眼睛,心想:胡说,爹怎么会打妈妈呢?问的次数多了,喜旺就会直冲冲地顶回去:
你爹和你妈才打架哩!
叔叔伯伯当然不会顾及喜旺的表情,在旁边嘎嘎嘎地笑,声音野鸭子一样嘹亮。
爹才从山丫口转下来,喜旺就看见了。那时候,喜旺正翘着屁股和他的同伴在河里筑水坝,浑身湿得像水獭。喜旺赶紧把目光收回来,用最快的速度洗了脸和脚,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岸上。和爹娘老子斗智斗勇,喜旺有着丰富的经验。河里水太凉,在河里玩水,是要挨骂的。喜旺非常害怕爹那双凌厉的眼睛,尽管他想早点见到爹,却不敢冒冒失失地回去。喜旺耐着性子,在河堤上吹着不成调的口哨,催促稀疏的阳光早一点把衣服烘干。喜旺心里早盘算好了,晚饭后用菜叶包上两片瘦肉,再折几个用新烟盒做的三角板,好好馋馋这帮还在河里给他打下手的跟屁虫。
可是,喜旺这一天却恰恰想错了。喜旺回到家,就被爹那双铁钳样的大手摁在凳子上。喜旺还没回过神来,就感到屁股火辣辣地疼。爹抡起一根竹片,叭叭落在他的屁股上。
疼不?爹粗着嗓门,吼。
喜旺嘴里嗞嗞抽着气。喜旺吃不准爹为啥打他,不敢轻易开口。
疼不疼?这一下,爹下手明显比刚才重了许多。
咝……不疼。爹的嗓门很高,但听得出来,爹的脸上一定还挂着笑。有了这种想法,喜旺咧着嘴,说。
真的不疼?喜旺的屁股上叭叭又挨了两下。
不疼。喜旺还是咬着牙。
喜旺像条鱼一样,不住地在凳子上扭动着身子,他只觉得辣乎乎的屁股很快就要暴裂开来。
院子里那两只母鸡蹑手蹑脚,伸长了脖子,小眼睛不安地眨着。弟弟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不停地擦着快要流到嘴里的鼻涕,脏兮兮的脸上写满了惊恐:哥,真的不疼?
不疼……爹,你多打几下才好!喜旺觉得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咧着嘴说。
什么?爹把喜旺从凳子上提下来,手里的竹片高高举起,没有再打下来。
你多打几下没个啥。以后去读书,那些屁孩欺负我,我就抗得住打了!喜旺强忍着没让泪水掉下来,笑着说。
爹一下怔住了。爹扔掉竹片,嘴唇动了动,把喜旺推一下,吼道:
小子,知道为啥打你不?
喜旺摇摇头。
爹那根擀面杖一样粗的食指,直戳戳地指着神龛那个纸盒,说:你得长记性,绝不能动里面的东西!
2
爹那根盛气凌人的食指,让喜旺无比的伤心。
爹太小看人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揍人,算什么好汉!喜旺懊恼地想,你以为我是三两岁的小屁孩,会稀罕你那些臭玩意儿?
喜旺知道,神龛上的宝贝盒子里装着雷管和导线。喜旺还知道炸药和导火绳放在另一个地方。家里就只有这么大块地盘,爹不把这些宝贝放在一起,为的就是怕孩子们捣蛋。这一点,爹不说喜旺也明白。对于这几件宝贝,喜旺有着清醒的认识。寨子里的表舅拿了雷管炸药去炸鱼,鱼没有捞上几条,把一只手给炸飞了。和表舅相比,喜旺的胳膊就是一根枯瘦的麻秆。喜旺不会这么蠢,拿自己麻秆一样的胳膊开玩笑。
客观地说,喜旺确实去翻动过了神龛上的纸盒。尽管喜旺认为做得天衣无缝,可是事实上根本就办不到。神龛太高,喜旺要拿上面的东西,得在饭桌上再搭上条凳子,然后踮着脚尖才能把那个盒子拿下来。
这就让爹看出了蹊跷。
爹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揍,把喜旺一肚子的话给打没了。喜旺要向爹讨教的问题,三叔不只一次给他解释过。对于三叔那一套理论,喜旺虽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但在频频点头的过程中,心里并不踏实。爹天天在外面,见的世面比三叔多,从爹那里得到的答案才准确。
整个下午,喜旺的屁股一直火辣辣地疼。喜旺不想搭理爹,他只能把那个秘密掺杂着委屈硬憋在心里。
第二天,喜旺睁开眼睛的时候,爹早就走了。
3
喜旺去翻动那只要命的盒子,秘密只有三叔知道。
三叔常常微睁着眼睛,肯定地说,喜旺是个有野心的家伙。
三叔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直不停地捋着下巴上并不多的几根胡须,神态异常安详。在喜旺的眼里,三叔就是智慧的化身。三叔满脑子都是学问,不管什么样的问题,在三叔那里都能找到答案。遗憾的是,三叔和喜旺这么大的时候从树上跌下来,昏睡七天后只能象蛇一样在地上爬行。三叔的眼睛常常严严地闭着,除非万不得已才会睁开。或坐或卧,三叔尽可能让身子保持不动。三叔说这样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最大限度地节约水和粮食。三叔说哪怕是少用一点光,对人类也是一种贡献。
三叔的智慧,就是在这样冥思苦想中提炼出来的。
喜旺去动那个盒子,不是为了雷管。喜旺要的是导线,那种红的绿的,用来引爆电雷管的导线。喜旺要用这些导线,做一件了不起的试验。对于喜旺的这一举动,三叔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证明他一直持赞成的态度。
爹是炮工,常年住在修水库的工地上。爹常常乐呵呵地说,他们不是修一般的水库。这个水库之所以不一般,是要用来发电的,以后这些地方就可以点上电灯了。爹笑声朗朗,每一个字都飞溅着亮晶晶的火花,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可是,这一天爹才说完这样的话,满屋里幸福的憧憬,很快就被喜旺粉碎了。
爹,以后是多久?
以后……以后就是以后嘛。
爹,以后到底是啥时候?
以后你就知道了,小孩子家操心个卵?!
不,我就要现在知道!
喜旺缠着爹的脖子,嘴巴凑在爹的耳边,热呼呼的气直往他脖子里灌。爹浑身让喜旺哈着热气的嘴巴拱得酥麻麻的,扭着脖子笑呵呵地揭开了谜底:
就你小子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少说得五年!
五年?
对。
还要五年呀……呜——!
喜旺哇的一声就哭起来。喜旺哭得很伤心,他很长时间没这么伤心过了。即使是挨了揍,喜旺也只是用哭声象征性地表示抗议,不会像今天这样投入。喜旺的哭声让一屋的人摸不着头脑,都在问:
喜旺,你怎么啦?
人家都六岁了,还要五年,不把人的头发胡子等白了才怪!呜——呜——!
轰的一声,屋子里的人全笑了。
4
电灯,对于喜旺来说并不陌生。爹和妈妈带他去晒场上看电影的时候见过。只是那阵子喜旺忙着凑热闹,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
喜旺的姑姑嫁到了城里。姑父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在县土产公司上班,家里非常殷实。临过春节的时候,爹带着喜旺到姑姑家,第一次见识了电灯的神奇。电线上结着个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一根细绳控制着,叭嗒一声,灯就亮了;再叭嗒一声,灯又灭了。电灯明晃晃地照着人的眼,让喜旺都看神了。喜旺指着电灯,对爹说:
爹,有电灯卖吗?
有。商店里大的小的都有。
爹,买个电灯回去嘛。
干啥?
有电灯,晚上脑袋就不会在床上桌子上碰起包了。
你小子,尽想美事。
买一个嘛。要不,小一点的也行。
你小子,大白天说梦话!
爹,我不要你买糖。你把钱省下来,买一个电灯嘛。
莫得电,有了电灯也不会亮。
电?
晓得不?要有电,电灯才会亮。
爹,你咋蠢哩,你不会买点电回去?……
喜旺仰着头,冲着爹直嚷嚷。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让爹恶狠狠地在额头上刮了一下。
旁边的姑姑和姑父都笑得弯下了腰。
电是啥东西,哪里才有卖呢?喜旺听得一头雾水。喜旺把注意力集中在电灯开关那根细绳上,希望从叭嗒叭嗒的响声中找到哪怕是一丁点的奥秘。遗憾的是,喜旺才拉了两下,手上就挨了一巴掌。
姑姑家大壮气冲冲地站在面前。大壮比喜旺小半岁,却比喜旺高出一个脑袋。大壮的脑袋让绒帽子捂得严严的,只留了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在外面。大壮手上也戴着绒手套,为了保持手上拍打的力度,大壮已经把右手的手套脱下来交给了左手。喜旺的手还没来得及缩回来,大壮又恶狠狠地在他的手上打了两下,一双尽是白眼仁的眼睛瞪着他:
干啥,不要钱呀?
钱?
用了电,你给钱!?
什么钱不钱的,喜旺实在听不懂城里表弟的意思。喜旺依依不舍地把手缩回来,老老实实地藏在自己的裤包里。喜旺早已把表弟划入了城里人,他只觉得表弟和尖酸刻薄的城里人一样吝啬,宁愿让这样的玩具在那儿闲着,也舍不得让他多玩一下。喜旺不明白那细绳和钱有啥关系,他心里一直琢磨着,等会儿趁大壮不注意的时候,再悄悄地拉几下。喜旺甚至还想,要是大壮还敢打他的手,他就想办法把那根细绳弄断。可是大壮早看穿了喜旺的伎俩,绒帽子下面那双警惕的眼睛防贼一样盯着他。直到第二天喜旺恋恋不舍地走出姑姑的家,他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喜旺心里无比的沮丧。尽管姑姑给他买了双胶鞋,往他兜里装了很多的爆米花,可是就为那只电灯,喜旺仍然非常懊恼。
臭电灯有啥了不起?我那些玩具,以后他小子别想摸一下!喜旺恨得牙根直痒痒,一路上缠着爹,向他讨教怎样才能有电。
对于这个高深的问题,爹费了老大的劲才让喜旺明白了个大概。虽然只是个简单的轮廓,却像春天里的一粒种子,牢牢地在喜旺的心里生了根。喜旺朝着大壮家的方向狠狠啐了一口,鼻子朝天直哼哼:
走着瞧,我要让你小子知道马王爷究竟长了几只角!
5
喜旺从姑姑家回来,就迫不及待把自己的想法跟三叔说了。对于喜旺的很多举措,三叔都很支持。三叔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不尝葡萄,咋知道葡萄甜不甜?
可是,这天三叔一直闭着眼睛,似睡非睡,什么话也不说。
三叔站不起来,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三叔常常用这样的话激励喜旺:有咱老侄在,这样的小事还用得着三叔的手?喜旺说的这件事,三叔过去并没有尝试过。能不能成功,他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
三叔和喜旺差不多大小的时候,最大的爱好是去掏鸟窝。三叔听瞎子爷爷说过,背上用雏鸟羽毛做成的翅膀,人就可以飞起来。三叔那时候天天做着飞起来的美梦。只要一有空,三叔就在墙头上瓦檐下田埂边树洞里下功夫。寨子里只要有鸟雀安身的地方,都让三叔那只乌黑的爪子翻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日子里,三叔的房间里到处是羽毛。一进他的房间,就会觉得尘埃里全是羽毛在飞舞。三叔的脑子里常常呈现出这样的场景,他扇着一只毛茸茸的大翅膀,呼呼啦啦从寨子上空飞过来飞过去。三叔最向往的,是到祖国的心脏北京天安门看看,到大海边看看,到最高的喜玛拉雅山看看。当然,三叔还想到非洲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看看,那些地方是不是真的是那么穷,要不要发扬点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他们送点水或偷点红薯什么的送过去。
遗憾的是,三叔还没把那只承载着他太多希望的翅膀做好,就在树上掏鸟窝的时候跌下来。其实,三叔在爬树的时候,嘴里还紧紧咬着一只吹了气的气球。事后三叔固执地认为,要不是那只气球,他就是有三条命都死了。至于那只气球后来落到了谁的手里,三叔没有过多地去计较。
要干成这件大事,喜旺作了充分的准备。要发电点上电灯,最起码的材料就是电线和灯泡。
这两件东西恰恰难不住喜旺。
喜旺家里有一把手电筒,喜旺悄悄把手电筒上的灯泡拧了下来。当然,这件事妈妈并不知道。那把电筒,在家里也跟宝贝似的。整个乌地吉木就只有三把,老队长家有一把,生产队会计家有一把。除此以外,就是他们家里有了。偶尔有客人来,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才会让客人用一用。遇上寨子里老人生病或是女人生孩子,得去请医生请产婆,才会借他们家的手电筒。毕竟队长和会计是领导,一般人不愿去给领导添乱。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家的手电筒才会在感激声中派上用场。
喜旺把盒子里的导线拿出来,把手电筒里的小灯泡拧下来。
那时正是春天,满世界萌动着春的气息。河边的草渐渐泛绿,岸上的柳树也吐出了嫩嫩的芽,可是河里的水还是刺骨的寒。喜旺挽起裤腿,卷起衣袖,嗞嗞抽着冷气,在小伙伴们的簇拥下,光着脚跳进冰冷的河水里。喜旺选了一个紧水口,把那根红色和绿色的导线插进哗哗直响的水里。
水哗哗地流走了,小灯泡却没有亮。
咋这么日怪?
几双贼亮的眼睛里满是疑惑。
春天的太阳就像一张薄薄的煎饼。风就有些狂。冷嗖嗖的风就像一个捣蛋鬼,不住地撩着喜旺单薄的衣裳,让他瑟瑟发抖。清鼻涕也一个劲地挤出来凑热闹,这就让喜旺不得不腾出手来擦掉这令人讨厌的东西。
几双手一起抢着帮忙,小伙伴们的衣服很快就湿了一大半,灯泡还是没亮。
喜旺把灯泡扯过来,举过头顶,睁大了眼睛对着太阳看。七八颗脑壳也挤过来,盯着喜旺手里的灯泡,齐刷刷地对太阳行注目礼。几只鸭子大概嫌水太凉,慢慢地踱到河边,好奇地朝喜旺他们伸长脖子。喜旺气不打一处来,顾不得揉一揉让太阳刺得胀痛的眼睛,抓起一块石头,照着鸭子就砸过去,吓得那几只呆鸭呷呷呷落荒而逃。
会不会是灯泡出问题了?
手电筒的灯泡坏了,爹会照着灯泡,屈着拇指和中指,轻轻弹几个脑瓜嘣,就亮了。喜旺学着爹的样子,对着小灯泡弹了几下,再放进水里,还是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时间一长,喜旺在河水里就站不住了,他只觉得自己的脚像踩在了一堆锋利的碎玻璃碴上。让喜旺特别伤心的是,手下那一帮跟屁虫的脸上都写满了失望。喜旺觉得这只该死的灯泡,把他的脸丢尽了。喜旺学着爹生气的样子,咧着嘴,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
日你妈,日你妈!
喜旺把手指弹疼了,才把小灯泡拿到水里去试。冰凉的河水,刀子一样割着喜旺的手和脚,让他差点忍不住跳起来。
该死的灯泡依然保持沉默。
有人从路上过,对着喜旺大声吼:
小杂种,这么冷的天,在河里捞个锤子,找你爹啊!?
喜旺挨了骂,并不急着从河里上来。可是,那人一句话却让他赶紧爬上岸来:再不上来,老子叫你妈来请你!
喜旺虽然知道这是威胁的话,还是很快就提脚上了岸。妈妈生起气来,也会抽他,但一般是用稻草或干透了的蒿秆一类,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重要的是妈妈一生气就会流眼泪,妈妈一流泪,喜旺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惹妈妈生气。
几绺头发贴在喜旺的头皮上,凛冽的风把他的鼻子吹得通红,嘴唇乌青,以至于两排还没有换整齐的牙齿,嗒嗒嗒地磕得异常清脆,一点也不听使唤。
6
喜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小灯泡重新安在手电筒上。喜旺一摁开关,一下就被吓坏了:
灯泡居然没亮!
喜旺很后悔。前一阵急着去河边,灯泡拧下来的时候,事先没有试一试。这只该死的灯泡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只有天老爷知道。
喜旺照着小灯泡弹了几下,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坏了!喜旺的心咚咚跳个不停。要是爹知道他干了这样的好事,弄不好又要挨揍的。
喜旺恶狠狠地把一把清鼻涕甩在地上,就像扔掉满脑子的烦恼。
这么大的水,该死的灯泡为啥不会亮?这么大的事,喜旺当然要向三叔讨教。
三叔闭着眼睛,静静地听了喜旺的叙述,幽幽地说:小哥,电线分阴阳两极。你小子把电线接错了!
阴阳?三叔说得很肯定,喜旺眼睛却瞪得大大的,他确实没听说过还有这么日怪的课题。
三叔眯缝着眼睛,叹了口气,说:笨啊,小哥。阴阳就是公母。世上凡事分阴阳,有男人就有女人,有公鸡就有母鸡,万事万物都是这样。阴阳不配,怎么会来电,小哥!?
你小子拴狗拴猫一样拴灯泡,会亮个卵?三叔的眼睛瞪得老大,眼眶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三叔恨铁不成钢地说:小哥,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还会搞个卵!你把灯泡拿过来,我接给你看……
三叔把手电筒里的电池和小灯泡拿出来,正极负极一接,小灯泡还是没有亮。三叔肯定地说:
灯泡坏了!
真的?
小哥,三叔啥时候骗过人?
喜旺愣了一下,接着就哈哈笑开了:
三叔,太好了!
喜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一把从三叔手里夺过小灯泡,一溜烟跑了。喜旺作了一个简单的推理,灯泡有问题,说明发电就有希望。
7
在喜旺眼里,三叔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三叔手巧,是寨子里最好的篾匠。只要把竹子砍回来,三叔就会坐起身子,一双巧手随着篾片翻飞,大到篮子筐子簸箕凉席,小到篾枕果盘苍蝇拍,很快就会呈现在主人面前,让人啧啧称奇。
三叔常常教导喜旺,失败是成功之母。喜旺当然不甘心失败,他想起了枕头下面藏着的压岁钱。数去数来,虽然还是只有一角六分钱,但每一分钱在喜旺眼里都闪烁着光芒。
妈妈收工回来,喜旺就缠着说:妈妈,哪天集上赶场?
妈妈说,你算嘛,七天一场,还有四天哩。
喜旺说,我要去!
妈妈瞪了喜旺一眼,说,去哪?
喜旺说,赶场!
妈妈说,干啥?
喜旺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玩。
妈妈说,这么远的路,得走大半天哩,有啥好玩的?
妈妈说的是大实话,乌地吉木离集镇还有二十里。平时里去赶场,都是爹和妈妈带着喜旺去,赶一趟集回来,腰也酸腿也疼,比干一天农活还累。喜旺摇着头,噘着嘴:不,就去!
馋,又想买东西吃了吧?!妈妈把喜旺头发上粘着的两根草屑拈出来,说,你爹回来了,让他带你去,好不好?
喜旺还是噘着嘴:不!
听话,妈妈这几天不得空。妈妈低下头,笑着说:以后,妈妈有空了带你去!
一听以后,喜旺的眼泪就委屈得叭嗒叭嗒掉下来了。
爹说的以后就是五年,喜旺哪里等得及呢?
8
这一天,喜旺突然从寨子里消失了。
妈妈发现这一重要变故是在下午。妈妈收工回来,就没有看到喜旺。那时候,妈妈忙着做晚饭,并没有留心喜旺。直到妈妈做好了饭,不见喜旺回来吃饭才急起来。往常只要妈妈一回家,喜旺就会嚷叫肚子饿,然后不停地催促她快一点。可是,这天妈妈从院子里叫到大门外,就是没有听见喜旺的声音。妈妈吓坏了,拖着长长的哭音,在寨子里跌来撞去:
喜旺,你在哪儿?
喜旺——,快点回来——吃饭——喽——!
空空的山谷里,妈妈单调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为了打消顾虑,妈妈还拿起一根长竹竿,在小河里,在水塘边,一边抽泣着,一边忐忑不安地搅着。
只有三叔微闭着双眼,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三叔一点也不担心,这么大的孩子,能到哪去?三叔知道,喜旺一定是到集镇上去了。三叔心里明白,喜旺就是喜旺,他认定的事情,一定会想方设法办到。
不过,三叔并没有把这事点破。三叔知道,和兄嫂一起过日子,寄人篱下,不该多嘴的话最好不说,特别是在这种时候更不能添乱。再说,喜旺走的时候既然不愿意告诉他,偷偷出去自然有他的道理。那毕竟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以喜旺的年龄,翻山越岭来回差不多得一天的工夫。要是三叔知道喜旺有这样的想法,也一定会劝他打消这样的念头。
事实证明三叔的判断是正确的。
喜旺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还在山丫口,喜旺就听到了妈妈的哭喊声。妈妈的哭喊声鞭子一样抽着静寂的山野,让喜旺感到头皮发麻。喜旺非常清楚偷偷去赶集的严重后果,他不敢贸然开口答应,轻手轻脚溜进院子。喜旺知道,在这个时候,找个地方先藏起来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在还没有找到藏身地方之前,喜旺赶紧把那两颗小灯泡塞进了墙缝里。尽管喜旺已经作好了挨揍的准备,可是两条腿还是因为害怕而微微颤抖。
没想到妈妈一见他,就紧紧地搂住他,从锅里拿出一颗红薯,递给喜旺。喜旺咬了一口,从兜里掏出一颗糖,说:
妈,你吃。
不要,你吃。
我吃了一颗的,这颗你吃。
不要,给你弟吃。
吃嘛。
给你弟吃。我问你,哪来的糖?
我……
哪来的?
集上……买的。
妈妈眼睛一亮,用指头在喜旺的额上刮了一下,说:
你呀你呀……
妈妈的脸上全是笑,眼泪却顺着她脸颊流下来。
9
两颗小灯泡,两颗糖,花去了喜旺的一毛钱。
虽然有些心疼,但喜旺觉得值。喜旺满脑子都是电灯璀璨的光。两只灯泡,喜旺早安排好了:一只挂在堂屋里,一只挂在房间里。当然,以后攒下了压岁钱,再去买两颗,给三叔房里装一个,厨房里装一个。
问题是喜旺弄成了个水獭,浑身湿漉漉的,那两只该死的灯泡还是不亮。
日怪?
天空中的流云悠悠从头顶上飘过,呜呜的风越过星星点点的柳树枝头,吹皱了小河。喜旺抓破了脑袋,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喜旺想不到办法,自然要求助于三叔。
三叔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一言不发。
空气因三叔的眼睛紧闭而显得凝重。过了好一会儿,三叔才说:小哥,你不会像上次拴狗样,把导线弄绞了吧?
看你说的。
分了阴极阳极?
是的。我还做了两个夹子,放上电池就会亮的。
之前你试过?
电池还在我身上装着哩,不信你试试。
这么日怪?
喜旺把电池和灯泡拿过来,当着三叔的面演示了一次。随着电灯泡忽闪忽闪的光,三叔的鼻息渐渐粗重起来。三叔破天荒地睁大了眼睛,说:
我跟你到河边看看。
喜旺在前面带路,三叔紧紧跟在他的后面。三叔就像一只短粗的四脚蛇,沙沙沙往锁定的目标爬过去。
三叔找了一处干燥的地方,坐起来。三叔看了一眼就把眼睛闭上了,然后,手就不停地捋起唇下不多的几根胡须:
你这点水算个屁,还不够鸟喝!
三叔,你……嫌水少了?
小哥,你是啥鸡巴脑壳?!
咋了?
水小了,马力不够!
三叔嘿嘿嘿地笑着。三叔的笑声划过春天的阳光,均匀地跌落在潺潺流淌的小河里。
三叔,马力……马力是啥?
喜旺望着三叔,希望能够从三叔的脸上找到答案。
我的小哥哎,你怎么什么都不懂?
嘿嘿……不懂。
小哥,马力,就是马的力气。
为啥要用马力?
没力气能发电?做梦吧,小哥!
三叔……得用多大的力?
少说得几十马力。
天,几十匹马的力量?
对。
那得多大的水呀?
那些电站,都筑了大坝的!
三叔,你说嘛,要筑多大的坝?
嘿嘿,这就要看你小哥的了。三叔用眼睛的余光瞟了喜旺一眼,说:
光埋着头砌坝不成。得使巧力,小哥!
三叔脑子活络。这一点,喜旺是深信不疑的。喜旺像捡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摇着三叔的肩膀:三叔,哪来的巧力?
晓得不,得用水车。
水车?
小哥,用水车增加转速,摩擦才能生电。笨蛋!
三叔嘎嘎嘎地笑着。
听三叔的话不会错。小哥,你马上就要来电了!
三叔说完,扭转身,刷刷刷飞快往回爬。
10
喜旺一头雾水,被三叔扔在河堤上,他只能看着咕咕的河水发呆。
要是爹在就好了,爹一定能想出办法来。问题是前次爹回来,一顿揍把这样的机会给揍没了。喜旺感到无比的懊恼。
几只鸭子在小河里偏头偏脑觅食,嘀嘀咕咕探讨一阵,然后扇扇翅膀,伸长脖子嘎嘎高叫起来。那时候,喜旺已经想好了办法:在小河里选了一个窄的地方,高高地筑上一道坝。喜旺不相信,这么大的水,还怕马力不够?
喜旺累得贼死。喜旺成天拖着条长长的清鼻涕,带着那帮小伙伴,在河里垒坝。喜旺已经给他们郑重承诺,有了电,给他们每家接一个电灯。每天,喜旺都在向三叔通报堤坝的进展情况:
三叔,河堤有半人高了。
三叔,河堤有一人高了。
三叔,河堤有一人半高了。
坝堤越垒越高,让河水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湖。那些日子,寨子里的鸭子都赶过来凑热闹,在喜旺打的坝塘里呷呷欢叫着,似乎在乐呵呵地问:
喜旺,这么高的坝,水的马力够吗?
这样的话,喜旺同样问过三叔。三叔笑眯眯的,一直不表态。喜旺的心思三叔当然知道。这小子贼精,他哪里是在通报情况,他是在暗中催他做水车呢。十天后,喜旺说:
三叔,那坝到处是缺口,浑身漏水,还往上垒不垒,你老人家发句话!
三叔笑了笑,眼睛总算眯开了一条缝:小哥,不能再垒了。屁做的话,沙垒的坝,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懂吗小哥?!
喜旺实在是不懂,眼睛看着三叔满是疑问。三叔不满地瞪了喜旺一眼:
要是坝垮下来,吃个卵!
三叔用竹片为喜旺做好了一个水车。三叔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那只灵巧的手像飞舞的竹片一样比划着,很快就让喜旺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水一冲下去,水车就会飞快地转起来,这一摩擦,就有电了!
这天晚上,喜旺把那架还在散发着竹子清香的水车放在枕头边。那两颗灯泡和一大把电线就压在他的枕头下面。喜旺美滋滋地想,明天晚上这屋里就可以点上电灯了,到时候不知道妈妈该是怎样的高兴。
11
吃了早饭,喜旺就邀约着寨子里的孩子忙活开了。
当然,他们得把准备工作做好。所干的这一切都是冒险行动,得避开大人,等大人上工以后才可能完成。因为把身上的衣服弄湿了,是要挨揍的。
喜旺拿着三叔做的水车,水车上绑着根导线,上面连着两颗灯泡。
七八个小伙伴有的拿棍子,有的扛着锄头,只等下面的喜旺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把坝堤掘开,让滔滔的洪水瞬间有充足的马力冲击水车,发出电来。
三叔事先当然知道喜旺要干这件大事。三叔就像一个胜券在握的将军,早就盼着他们胜利的消息。当然,三叔一般是不会和喜旺他们行动的。毕竟是大人了,他用不着这么冲动。
水面上一点也不平静。几条鱼儿也很激动,跳出水面打得水啪啪响,震得那单薄的堤坝摇摇欲坠。风似乎比往天更大一些,坝塘里的水被风荡起了层层涟漪。那群鸭子不敢过来凑热闹,远远地躲在一边,伸长了脖子朝这边张望。这些扁嘴的家伙,都生怕一不小心就把堤坝震垮了。
七八个孩子踩在摇摇晃晃的堤坝上。堤坝很高,他们都有一种居高临下如履薄冰的感觉。堤坝太单薄,两个孩子胆小,不得不退到堤坝的两岸等待命令。风吹起来很冷,喜旺蹲在堤坝下面尽可能缩着脖子,如一只冬眠的蛹。
喜旺做好了准备工作,可是还没有等他发出命令,喜旺听见三叔远远地在喊他,接着就发出了呜呜的哭声。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三叔你哭个毬?一会儿发了电,你笑还来不及哩!
喜旺心里多了几分厌恶。他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候,三叔的骨头会这么软。
喜旺毫不理会,抬起头让上面的同伴赶紧动手。事实上,喜旺的话音还没落,摇摇晃晃的堤坝就已经崩塌,那坝塘里的水轰就下来了。
在水帘中,喜旺感到头顶上山崩地裂的一声闷响,眼前一道金光闪过,一个潜意识告诉他:
来电了!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