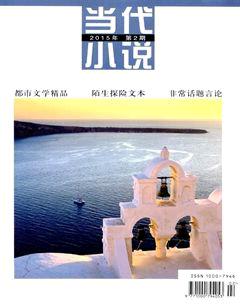哥哥
星子
第一次见到哥哥,是很久之前的一个夏天。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那个暑假非常无聊,四年级的圆锥体折磨着我,它们的面积让人无言以对,更别提体积了。李白依然每个学期都作诗,我都已经习惯了。
每天,我就这么坐在书桌边。直到有一天,爸爸忽然说:“带你回趟老家吧。”
妈妈也觉得,我应该回去看看奶奶、姑姑、姑父等等好多人。于是,我坐在爸爸的摩托车后座上走了。
摩托车在公路上驶了很久,公路两旁田野辽阔。摩托车驶过了集市,驶过了长长弯弯的田埂。水稻田里立着一排排小绿兵马俑。
爸爸停下车,带我走到两座稻草垛背后。我被拉进那扇屋门。在农村,似乎哪座屋子的哪扇门都可以直接进。门里头的东西虽然亲切,但是总体看上去还是有些不怀好意——满地的鸡屎,一坨叠着一坨,微风拂过,看不出如何下脚。猪在猪圈里拱着嘴,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狗和鸡们昂首阔步地扑过来。院子里很不好闻,但是奶奶、姑姑、姑父全都很热情地要我走进屋里去看看。我被他们拥着,被迫跨过门槛,走进里屋。里屋的桌边坐着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正在看书。
“来,进来呀。这个人就是你的哥哥。”
他们说。
姑姑在旁边催促着:“叫呀,叫妹妹。”
男孩站起身来,说:“妹妹。”
奶奶望着我,期待地说:“叫哥哥。”
“哥哥。”
他们便互相点头微笑了。大人们就是这样:有什么好秘密,他们总是不告诉你,你要等很久以后才知道。我有个这样的哥哥,他们就从来都没有说起过。
哥哥站起身,请大家坐下,给他们泡茶。他个子好高,比我高多了,眼睛很黑,眉毛很黑,鼻梁高高的,头发卷卷的。爸爸叫他“小三子”,并且和姑父一起解释说,因为他是我的三哥。
我装作不经意地听着,装作不经意地移到哥哥的桌前,随手翻开他的书。封面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物理》。
我呆住了。我默默地把书合上,感到一股深奥的陌生感从书里飘出来。
但哥哥走过来,朝我笑笑,递给我一杯茶,说:“我们进里屋去看电视吧。”
我赶忙点点头。
大人们的脸在呛人的烟雾里出没着。我和哥哥走进卧室,打开电视机。我坐在凉床上,看着哥哥站在电视机前,有模有样地调整电视机的两根天线,往这边摆弄摆弄,往那边摆弄摆弄。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上,黑白夹杂雪花的画面哗哗地掠过。每调到一个电视台,他就转过头来看一下我的脸,然后继续往下调。一直又调到了开头,我都是面无表情。
“都不好看吗?”他问。
“啊。”我才回过神来,原来哥哥是想让我说看哪个呀。我只好说:“我不知道……”
哥哥笑了笑,轻轻掩上门,让黑白电视机嗡嗡地发出声音。他坐了一会儿,站起身,在书橱里翻找出来什么,递给我,原来是五年级的教材。
“你爸爸说叫我找给你的。有点旧了。你还要吗?”
我接过他的书,翻开,书页上有哥哥的笔记,扉页上写着哥哥的名字。“要。”我说。
这时候门被推开,爸爸和另外几个男人叼着烟哈哈笑着走了进来,跟我们说话,有一个人非要把我抱到腿上,揽着我问我上学期考试的成绩单。可我实在不认识他。爸爸拍着哥哥的背,很大气地问他的人生规划。
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个人腿上跳下来,逃出那间屋子,走出大门。
我站在阳光下,看着那两个大稻草垛。一会儿,哥哥也出来了。他站在我身后,我转过脸去对他说:
“稻草好香。”
哥哥点点头,他的白衬衫发出阳光的气味,那气味仿佛阳光晒着一段干裂的香木头。他说:“去看看。”
我们走到稻草垛边上,我伸出手,抱着稻草垛,哥哥也伸出手,抱着另一边,然后我俩笑了,笑得很开心、很大声。因为稻草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胳膊太短了,手怎么也碰不到一起。
午饭,我只吃了一点点。因为如果想坐在那里吃得饱饱的,我就需要敬酒。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难题,我向来就排不好亲戚的辈分,什么姑姑、姑父、姥姥、小姨……大人们说已经教过我好几遍了,可是我一个也记不得。这可能是天生的。没办法,直到十七岁以前,我都一直因为这个被耻笑。
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一个男人一直鼓动我站起来端茶水给桌子上的每个人都敬一遍酒,还要说祝福语。姑姑又拼命地给我夹菜。我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妈,你别给她夹太多了。”哥哥忽然说。
我低着头,脸红到了耳朵根。吃了两口我就端着碗溜出来了。把还有剩菜的碗偷偷搁到厨房里,回到卧室,掩上门,觉得松了一口气。黑白电视机还在嗡嗡地响着。
自由快活好多。我躲在门缝边,偷偷地望他们怎么吃饭喝酒。门缝里,我看到了坐在爸爸身边的哥哥。
哥哥站起来,端着酒杯。
“给奶奶敬酒。”
“给二舅爷敬酒。”
“给三妈敬酒。”
“好!好!小三子要好好学习,初三了吧?要考上好高中!”
“好。”哥哥说。抿下一口酒。
哥哥是厉害的,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酒桌上。而我还不可以。哥哥会敬酒,也会讲敬酒时该说的话。而我,直到十七岁以前,敬酒时该说什么还说不全,捧起酒杯还是会脸红。
吃完饭,哥哥就向卧室走来,我赶紧从门缝那躲开。
“吃完了吗?”
“嗯。”
“吃饱了吗?”
“还可以。”
“我在厨房看到你的碗啦。”
“什……什么?”我感觉被发现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没再说什么,去外屋拿来一盒糖,递给我。我小心地拈起一颗糖,在手指间揪着糖纸。
“你读三年级?”
“嗯。”
“在哪个学校?在镇上的中心小学?”
“嗯。”
“你成绩那么好,老师一定很喜欢你吧?”
“还可以……”我想着,摇摇头,“一般一般。我成绩也不是特别好,老师就一般、一般地喜欢我。”
“同学呢?跟班里同学都玩得好吧?”
“还可以……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看你总是不出门,很少出来玩,就知道学习,四年级的课本学完了还要学五年级。”哥哥笑笑,揉了揉我的头发,“多出来转转。”
“好。”我说。
我们能这么相处、这么说话的时间好像总是很短暂,因为爸爸和姑父们找不到牌友打牌,又哈哈笑着走进卧室里来,爸爸进来就问:“小三子哇,让你把课本找给妹妹看,找了吗?”
“找了,给她了。”哥哥回答。爸爸饶有兴趣地看着那本五年级的英语书,指挥哥哥找一个塑料袋出来,把这些课本、试卷都装上。我悄悄地对哥哥使了一个手势(向门外指了指),哥哥会意地点点头。
我先走了出去,站在阳光下拍拍那个稻草垛。
一会儿,哥哥果然出来了。
我们俩就互相看着笑笑,满脸都是“一起嫌弃大人们”的表情。
“哎,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别跟别人说啊……”我想了好久,下了很大的决心,说。
“什么?”
“刚才,你不是问我跟班里的同学都玩得怎么样吗?”
“怎么啦?”
“有一个人,好像一直都不喜欢我。”
“是吗?谁?”
“我们的班长。”
“男生?女生?”哥哥笑。
“男生……”
“他是嫉妒你成绩好吧?”
“不知道。他一会儿对我很好,一会儿又对我很冷淡……有时候,收全班同学的作业的时候,都故意不收我的。不知道哪里惹到他了。”
“怎么这样啊。下次,你不要理他,把作业直接交给老师。”
我抬起头,看看哥哥的眼睛,又看看稻草垛。他笑了出来:“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干的。”
“会的……”我低声说,其实在心里想,下次我会告诉他,我有一个哥哥。
“你读几年级了?”我认真地问。
“初二。”
我也会读到初二的。但是,初二,对我来说,是个太遥远的名词了。小学毕业,我都感觉像经历了生离死别一样。
四年级还是到来了。每天早晨,我们依然像三年级一样,匆匆忙忙地在教室外面排队,匆匆忙忙地唱国歌。国歌之后,是“国旗下的朗诵”,大喇叭里响起了我们班长声情并茂的朗诵声。
朗诵完,全校师生鼓掌。班长从广播室里出来,走过我的身旁。
“这次是陈明,”班主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因为他的朗诵稿写得感染力比较强,排比句运用得较为熟练。没关系,下次,要争取把朗诵稿写得更好,参加‘国旗下的朗诵,好吗?”
我点点头。回到教室,同桌拉着我的手问:“晓月,这次怎么不是你?我们都以为会是你呢。”
“我的稿子写得不好。”我对她淡然一笑说。
“你不要紧吧?”
“不要紧。”开哪门子的玩笑!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么问我?
“这次你好像不在意呢?”同桌说,“记得三年级时,发生这样的事你都会觉得委屈呢……”
“是吗?”我说,“哎,暑假我回了趟老家呢!”
“好玩儿吗?你去看奶奶了?”
“嗯!还知道我有一个哥哥!是姑姑家的哥哥!”
“真的?多大了?”
“已经读初二了哦。”我骄傲地说。
“哇——好厉害……”同桌的脸上出现了羡慕的神情。我们俩很快就忘记了“国旗下的朗诵”这回事。
我和哥哥平时是不能见面的。
因为我住在小镇上,而哥哥住在老家,而且在另一个小镇里读中学。所以,我只能在放假的时候回老家,在看望奶奶、姑姑、姑父等等好多人的时候,“顺便”看看哥哥。
有一次,哥哥终于到我家来了。头天晚上我就听爸爸妈妈说“小三子”要来了。我偷偷地高兴着,努力表现得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哥哥来了,我在里屋听到了外屋的声音,哥哥停下自行车,走进外屋,和爸爸说话。我还假装很惊奇地问妈妈:“咦,外面是谁?”
“你三哥。”妈妈说,“过来找爸爸补习语文。”
我静静地写作业,等待着。写一会儿,我就望望窗外,蓝窗网上,淡淡的日光流转。爸爸和哥哥在外屋的话,我都听到了。哥哥要考高中了,二模语文考得不太好,过来找爸爸补习,这是很庄严的事情。
哥哥去上厕所的时候,妈妈问爸爸:“小三子的语文怎么样?”
“不是很好。”爸爸沉思着说,“不是很好。考重点高中恐怕有点困难。”
“比起晓月呢?”
“要差一点。”
“他们家的孩子能考上高中就不错了。一家人都不识字,小三子已经很努力了……”妈妈叹息着说,“好好给辅导吧。”
于是我很懂事,从不在爸爸妈妈面前打听哥哥的消息。
吃完晚饭,就该洗漱了。妈妈为哥哥准备了新的刷牙杯。趁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偷偷地为哥哥的牙刷挤好牙膏,倒上水,然后自己赶紧跑到大槐树底下去刷牙。我确信我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人看到。
哥哥走过来,端着刷牙杯,微笑着轻声说:“谢谢。”
我站在一旁,没有吭声,满嘴牙膏。
哥哥把牙刷伸进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不过,你挤得实在是太多了……”
第二天哥哥走的时候,只进来说了一句:“我要走了。”
“哦。”我低着头看英语课本。
哥哥把手里捏着的东西放到桌面上,松开手,原来是一个乒乓球。“买给你玩的。”他笑笑说。
我听着哥哥走了出去,他背上书包、推自行车的声音响在门外。我很想追上去,很想很想追上去,看看哥哥骑车远去的身影。但是爸爸妈妈在那里。我放下了这样的冲动。
当屋外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我走出门。
绿柳飘荡,夕阳西下。
放暑假了,我又长大了很多。
终于有一天,爸爸提出要回老家去看奶奶和姑姑了。我说:“我也要回去。”
坐着爸爸的摩托车,经过一段公路,经过集市和田埂,又到了那两座稻草垛后面。院子的门打开着,鸡屎依然一坨一坨,猪还在呜呜地叫着,我勇敢地走了进去。
姑姑说:“让晓月今晚住在这里吧。好不容易来一次,就别急着回去了。”
爸爸问我:“你要不要住在这里?”
“好啊。”我假装思考了一会儿,假装不在意地回答。我的表情是“都可以啦”。
晚上,和姑姑一起洗了澡。因为没有带换洗衣服,我只能换上姑姑的衣服。姑姑的衣服真的很土气,是那种土土的红褂子,又很大,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我咬牙把这件衣服套在身体上,很不高兴。姑姑却很喜欢的样子。
我和姑姑坐在凉床上,旁边还坐着一个邻家的小妹妹。她大声地嘲笑我说:“新娘子!你穿得像新娘子!”
正在这时,哥哥走了进来。
“啊!”我大叫一声,发出的简直是惨叫声,“你,你怎么进来了!你快出去……你快走开……”我带着哭腔嚷道。一边把脑袋埋在膝盖里,双手抱住膝盖,把整个自己蜷缩成一团。
哥哥出去后,我一直不停地问姑姑:“姑姑,我的衣服洗了吗?明天就干了吧?明天早晨我就能穿回自己的衣服了吧?”姑姑答应说就去帮我洗掉的时候,我才安心地睡去。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洗漱好,换上自己的衣服。爸爸也起来了。他伸伸懒腰,咳嗽两声,望望远方的山脉,说他今天有事情,一定要走。
那我怎么办?我问。
让你三哥过几天再送你回家吧。你可以跟他多学习,问问初中的课程都学啥,要怎么准备。
我心里轻飘飘的,表面上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于是乎这一天好像很快就过去了。我问哥哥,初中怎么样?难不难?哥哥笑着说,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我又问哥哥,高中怎么样?难不难?哥哥搔搔头说,这个嘛,我也不知道。
吃过午饭,姑姑让哥哥带着我散步。哥哥带我走了很远、很远,走到了一片很深很绿的草地。不远处,有一个宁静的湖。
我们在湖边坐了好一会儿,很久以后我还记得,那午后的阳光轻轻落下来的样子。
回去之后,我写了一会儿暑假作业。哥哥带着两个邻家的小弟弟玩儿。我也跑进去看他们,发现他们三个人正在盯着电视,很有滋有味地看呢。
“你们在看什么呀?”我问。
“《蓝色生死恋》!”两个邻家的小弟弟大声地喊道。
“《蓝色生死恋》?没有看过……”当时,我被爸爸妈妈管得很紧,电视剧除了《还珠格格》,不允许看其他的。
“里面有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哥哥说着,比了比我的肩膀。当时,我的头发很短,还不到“披肩”。
“哎——”两个邻家小弟弟开始装腔作势怪腔怪调地大叫起来,我弄明白他们并不是在嘲笑我之后,也跟着他们叫了几声:
“咦——长发披肩的姑娘……长发披肩的姑娘……”
我一边叫,一边偷偷地瞥了哥哥一眼,然后就觉得没趣味了。哥哥抱着胳膊,苦笑着一直摇头。
“哥哥今晚还要跟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约会呢!”起哄的小男孩嚷嚷得更起劲了。
“对!长得就像《蓝色生死恋》里面那个一样!”
我看了一眼电视屏幕,那确实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十分美丽的姑娘。
“是吗?”我转过头问哥哥。
哥哥很是无奈地回答道:
“是啊。”
“几点?”
“今晚七点钟。”
“在哪里?”
“湖边。”
我走出屋子,复习功课去了。听见哥哥对那两个小男孩说:“你们别吵啦。”然后他们就不再嚷嚷了。但我没有再回去。我静静地写了很久暑假作业,也想了很多、很多。
晚上七点钟终于到了。但是,哥哥却好像始终没有动身的打算。最后,我着急起来,催促他说:“哥哥,你快去。”
“去哪?”哥哥莫名其妙。
“你不是要和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约会吗?”
“哦……”哥哥刮了刮我的鼻子,“知道了,我就要去啦。”
可是他只是在那里看那本《物理》,昏黄的灯光照着他,他的侧脸愣愣的,好像看得入神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也拼命地给哥哥使眼色,可是,哥哥只是笑而不语。看看钟,已经过了七点半了。
哥哥怎么能这样?我觉得很困惑。看样子,哥哥是不去了,而我却担心起那个姑娘来。那个长发披肩的、美丽的姑娘,和哥哥约会的姑娘,一定是很善良、很守时的人。她肯定还在湖边等着,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哥哥为什么迟到了,尽管不知道为什么,她也一定还在湖边等着哥哥。我相信。
哥哥怎么能这样呢?
我决定,自己去告诉那个姑娘,把话说得委婉一些。我在心里打了好几遍草稿:“对不起,是你吗?不好意思,我哥哥临时突然有事,他今晚实在是来不了了,只好让我来告诉你……”
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个人走出门,向湖边走去。
我有点忘记路了。中午是跟着哥哥走的,没怎么记路。那些草地、田埂,还有分岔的小路,在夜里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样。我边走边鼓励自己,一定能找到的,那里的草地很深,连成片,一眼望去几里外都没有人家。若是走到了,我一定能认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那里的。只记得过了好久、好久,眼前出现了那片青草很深的原野。月光下,青草是深黑的。
我站在那里,呆住了。
夜风轻轻地吹过来,青草太长了,一吹就伏倒一片。风吹过青草的背面,一直吹到湖面上。没有人,没有灯光。没有一座屋顶。惟有一片深深的草地,惟有一个圆圆的粼粼的湖。
我拼命地跑着,边跑边四处张望,可是哪里都没有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我试着大声喊道:
“喂!喂!有人吗?”
只有我自己的回音。
不对……那个姑娘一定是被哥哥气走了。
怎么办呢?我不知道……那是一个长发披肩的、美丽的姑娘,是哥哥喜欢的姑娘啊。
我又喊了几声:
“喂!喂!”
没有声音回应我。我站在一片黑暗中。
不知过了多久,从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晓月!晓月!”
是回音吗?我愣了一下才明白,这是哥哥的声音啊。哥哥顺着声音,一路找到了我。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哥哥又是吃惊又是担心地看着我。
“我想找那个长发披肩的姑娘,告诉她不要着急,你很快就会来了。”我嘟起嘴说。
“找到了吗?”哥哥问。
“找到了。”
“她怎么说?”
“我跟她说,你今晚来不了了,明天晚上七点钟,你还会在这里等她。”
我和哥哥一起走回了家。
回家的路上,晚风飘荡,青草浮出淡淡的香气。
第二天黄昏,哥哥在里屋睡觉。我又悄悄地走出了门。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一个人去湖边走走了。那样的黄昏,刚好。脚底下踩过长长的青草和坑坑洼洼的路。
在湖边,金色的黄昏落在水面上,我蹲下来,想着很多事。
我想着很快就要回家了。很快就要去镇里的小学继续念书。我四年级了,马上就要五年级了,然后是毕业,念初中……初中完了还有高中……我想着那时候我问哥哥高中难不难,哥哥说他也不知道。我想着昨晚其实有多可怕,万一我迷路了,万一我……昨天夜里,哥哥房里的灯一直亮着。我想着和班长之间好像重归于好了,最起码他没再冷淡我了,我也不太在意他和我的竞争了。我想着高中的数学会有多难,想着哥哥昨晚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为什么……我哭了出来。
我哭了很久、很久,最后哥哥来了。
哥哥走到我的身边,我还在哭。
哥哥把我扶起来,轻轻地说:
“现在想回去吗?要是不害怕,我带你绕远一点的路,去看看牧场。”
我点点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快乐的事情了。
牧场很宽阔,牧草的气息清甜。有几头牛站在牧场上。哥哥喊道:
“阿俊!小游!你们还在放牛?”
那是几个放牛的男孩子,他们也过来了。我们就在牧场的草地上躺了下来。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月亮很美。老家天空的月亮,很黄,很大,悬在天边,就好像悬在我的眼睛边缘。
“晓月,不是会唱歌吗?给我们唱首歌吧!”
我站起身来,唱着: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唱着,唱着,我们跳起舞来,哥哥拉着我的手,我们旋转着跳舞。累了,又躺了下来,天已经渐渐地黑了。
哥哥躺着,他的侧脸那么好看。哥哥笑着说:
“我没有那个长发披肩的姑娘。”
“嗯?”
我说,没听清,哥哥你说什么?哥哥却怎么也不肯再说第二遍。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哥哥送我回小镇上的家。田野很绿,泥土很黄。
天空很蓝。
哥哥问我:“要不要乘三轮车回家?”
要知道,爸爸骑摩托车带我来,都要骑上一两个钟头呢。我晓得,应该乘三轮车的,大人们肯定会叫一辆三轮车。可是,我摇了摇头。
“我不乘三轮车。”我说,“乘三轮车会头晕。”
“晕车呀?”哥哥问我。
“嗯。”
“不乘车也好,我陪你走。”
从农村走回家要很久很久。我们要走很远、很远。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哥哥都没有说话。只有广阔的蓝天,像一块巨大的蓝手帕,起伏在我们的头顶上。
有时候,我们并排着走。有时候,哥哥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走了一会儿,路上驶过一辆三轮车。
“你坐不坐三轮车?”哥哥停下来,转过身问我。
“不坐。”
“看你好像有点累了。”
“会头晕的。”我说,“我晕车。”
我和哥哥继续往前走。天空像一块蓝色的固体,石头般地竖立在高而深远的地方。底下是一条布满金黄色的泥土的路。路上走着我和哥哥,是一个小人,和一个比小人大一点点的人。
“你看你,满脸的汗。”
哥哥的话音里带着歉意。
路过一个买冰棒的小摊,哥哥走上前去给我买了一支棒冰。
“你吃吗?”看哥哥只买了一支棒冰,我把棒冰又递给他。哥哥笑着摇摇头。
吃了棒冰,感觉好多了。我振作精神,继续往前走。我们走过了田埂,走到了集市上。货摊多起来,卖冰棒的小贩支着帐篷,摇着扇子。
哥哥又给我买了一支棒冰。
我递给哥哥吃,哥哥还是说,他不吃。
一辆三轮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哥哥问:“你累吗?想坐车吗?”
我轻轻地、坚决地摇摇头。
那一刻,我只想永远和哥哥走下去。
可是,我不忍心。我看到了哥哥脸上的汗,看到了他在喘气。我真的不忍心,那么远、那么远的路,哥哥已经很累了,又热、又渴。我的脚已经很痛了,我想哥哥的脚一定也磨破了,也很痛吧?
第三次,当一辆三轮车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问哥哥:
“你坐车吗?”
他摇摇头,说:“不坐。你晕车。”
“但是你累……”我说。
“就这么一直走着,陪你一起走回家。”
在集市和公路之间,要经过一段很细、很细的田埂,很不好走,田埂里还有水渠形成的淤泥。哥哥说要背我,我慌忙摇头说不要。可是哥哥还是背起我,走过了那段田埂。
到公路上,哥哥把我轻轻地放下来。
黄昏的时候,渐渐地走近小镇了。渐渐能听见小镇里的喧嚷声、汽车集散地的喇叭声。我们走过繁华的十字路口,走进通向我家的小巷。那一刻,我并不是很开心。
回到家的时候,爸爸看着我们一副狼狈的样子,很是吃惊。哥哥只说:“我送她回来。”
“你们是步行回来的?”爸爸不敢相信地问。我听见哥哥嗯了几声。
我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凉床上,脱下鞋,脱下袜子。我的脚趾头都磨破了,脚后跟也磨破了,流着血。
爸爸要给哥哥钱坐三轮车,可是哥哥怎么也不要,爸爸又说,那你骑我的车回家吧。
听见哥哥在外面推自行车的声音,我急忙冲了出去。哥哥已经跨上了自行车,他转过头,朝我微笑着,挥了挥手。然后,伴随着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他远去了。
哥哥好像是带着黄昏远去的。因为天空上那些晚霞在哥哥走之后,都轻轻地黯淡了。
我一直、一直站在那里。在此后的人生中,我的眼前总是会浮现出那天夕阳下,哥哥跨上自行车时的笑容。
我开始养头发,我要长成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
我读初中了。哥哥读高中了,离我的学校近了一些,便经常来找我。
哥哥来学校找我的时候,我总是很自豪。别人问我:“那个男生好帅啊,是谁啊?”
“我的哥哥呀。”我回答。
有一次,哥哥是和另外一个男同学一起来找我的。
那个男生看上去高高大大的样子。我站在哥哥身边,生疏地和那人打了一个招呼。
哥哥说:“放学了啊,带你去买点零食吃吧。你想吃什么?”
“海带丝!”我嚷了起来,“妈妈总是不让我吃。”
我吮着海带丝,听哥哥和那个男生说话。那个男生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转过头,看哥哥,不答话。
“你害怕?”哥哥笑笑,揉揉我的脑袋,“不要怕。”
“别怕。”那个男生也笑了,“我和你哥是好朋友,喂,你吃海带丝的样子很好笑。是几百年没有吃过了吗?”
“你养的头发呢?”哥哥揉完我的脑袋后,严肃地问,“你不是说要长成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吗?”
“妈妈说,不好梳头,没时间打理。叫我剪了……”
我又是委屈、又是心疼地回答。
没想到,哥哥和他的朋友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放下海带丝,看着他俩大笑的样子,心里想,不知道哥哥把我小时候的历史说成了什么样子。
那个男生临走之前总是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当时怎么也不肯回答他。
“我不知道。”我说。
“你就说说看嘛。”
我就是不回答。
那个男生走之后,哥哥和我一起回到家。
放下书包,烧了水。我坐在桌边,哥哥也坐在一旁。哥哥笑着问我:
“你怎么不回答他?”
“你那个蓝色的、长发披肩的姑娘呢?”我赌气说道。
“我都告诉你了,没有。”
我不再说话,哥哥也没说话。我一直在纸上写东西。
哥哥是来拿爸爸给他的语文资料的。临走时,我递给哥哥一封“信”。信里是一张“问卷”,就是我刚刚写的东西。
“这是什么?”
“你帮我给那个人就可以了。”我说。
纸上这么写着:
“你好!为什么你总是要问我,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难道你自己还不了解自己吗?那好,我给你写了十个问题,如果你都回答了,你也就会明白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下面,有我不用绞尽脑汁就想出来的十道问题。什么偏好啦、倾向啦,等等。
我以为自己聪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麻烦你交给他。”我一本正经地说。
“交给他啊。”哥哥还是笑着,“我说是什么,原来是写给他的啊。”
“嗯。”
“为什么不自己给他?”
“我又不认识他。”
“我看你们俩很熟嘛。再说,他家也住得很近啊,就在……”
“我不去。”
哥哥带着那个人的回信来,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
他的眉毛,依旧很黑。
那时候,我正坐在里屋的桌边复习功课。我已经念初二了,好像到处都是考试。每个学期都作诗的古人们又多了许多。在外屋,爸爸和哥哥在商量着考大学的事情。结果他们谈话的时间里,我一点儿功课都没做,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竖起耳朵上。
哥哥走了进来。
看到他的一瞬间,我几乎想哭。但我只是问他,最近怎么样?
哥哥说,很好。又从怀里递出一张纸说,你的回信。我展开信纸,不禁莞尔。还是几年前的那张纸,每个问题下面都颇认真地做了回答。不仅有回答,还有解释。只是笔迹都已经洇到纸里了,感觉很陈旧了。
“给他你的‘问卷的第二天,他就回信了。可我当时忘记带给你了。”
“哦。”
“我见到他了。”哥哥笑着说。
“见到他了?”
“他快结婚了。长得非常胖。”哥哥比划着说,“这么胖,显得好老啊。肚子这么大了。你还要不要写信给他?”
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我问哥哥,高中毕业的时候,会不会哭呢?
“不会。”哥哥摇摇头说,“为什么要哭?”
“因为同学都分开了呀。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都哭了呢。”
“没什么好哭的。”
“哥哥,你要考大学吗?”
“要考。”
“哥哥,你毕业之后,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哥哥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子。
再后来,再见到哥哥的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没问哥哥去哪里,我表现出一副不关心他的工作的样子。
我只是问:
“哥哥,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哭了吗?你哭了吗?”
“没哭。”哥哥还是笑了,“大学同学之间感情很淡的。没高中那么好的。”
“可是我高中文理科分班的时候都哭了呢。”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大家都很喜欢你吧?”
我摇摇头,真心地摇头,“不是……我成绩在高中很一般的,他们也不喜欢我,他们喜欢漂亮的女生,要不就是会说话的女生。我长得不漂亮,成绩不好,也不会说话。”
然后,我就在哥哥面前哭了。好像自己已经忍了很久、很久。
“别哭。”哥哥凝视着我的眼睛说,“等什么时候,我去你们学校看你。”
哥哥没有去我的学校看我。
等待大学通知书的那个暑假里,我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谈论哥哥的事情。
爸爸说:“小三子走了,去了南方,好像是浙江还是江苏的一个县,说要自己创业,要办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去年过年,就在那边结婚了,都没有回家。”
爸爸和妈妈一起摇头叹息。
我在里屋听着,觉得天都塌了下来。
哥哥再也没有联系我。
回到老家,我再也没有看见哥哥。
但我还是要到了哥哥的电话号码。有了自己的手机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哥哥的电话。可是,电话那头永远都是错误应答的忙音。
上大学之后,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自己的同乡会。聚会的时候,别人都在和身旁的新朋友颇为热闹地交谈,而我,总是在给那个号码发短信。
短信里都写了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惟一记得的是,那个号码从来没有回过我。
第二年的中秋之夜,同乡会里的一个男生邀请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去看月亮。我就去了。四个人,坐在草地上,吃着月饼。男生们喝着啤酒。那一天月亮在云里,天空中缥缈着城市的烟雾。云丝絮般遮挡着灰暗的月光,看不见一颗星星。
我站起身,想一个人走走。
走了一会儿,我感觉到身后有人。是那个男生,他一直跟着我,直到我在草地边停下脚步。
“你不是总是说,你没有哥哥吗?”那个男生说。
我没有说话。
“我做你的哥哥,好不好?”
面对着一块草坪,和草坪上方轻轻的一块黑暗,我快要落下泪来。我不知道该是点头还是摇头。我使劲地强忍着自己哭泣的声音。
哥哥,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陪我走了很远、很远的那个下午吗?哥哥,你在哪里?我做错了什么?哥哥,为什么,你现在离我那么遥远?
但我终究还是谈了恋爱,终究平静地分了手。
毕业的时候,家里对我的希望是考公务员。他们如此对我说:“读书就是为了考公务员呀。你真的不考?”
父母、亲戚,轮番劝说我考公务员。我听着他们的声音,想象着那些画面。
如果我考上公务员了,家里的亲戚们都会觉得“与有荣焉”,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就会说起我,谈论我的工作时,神情就好像他们非常懂得一样。他们会互相碰着酒杯,熟练地说着那些真诚的祝福的话。他们会叼着烟,悠闲得意地吐出一个又一个烟圈,把我叫过来,教育我说,你已经是公务员了,要注意以下几点……
如果我没有考上公务员,会怎样呢?他们会安慰我吗?还是背后用鄙夷的眼神谈论这件事?他们会用一种很别致的语气说:“还在北京念了几年书呢,最后还是没有考上公务员……”
突然感到一阵寒冷。我想起了哥哥,想起当初谈论哥哥南下创业时,爸爸妈妈失望的神情和语气。
某一天。我在旧相册里翻着。突然看到了一张照片。
是哥哥在桌边的留影。
他坐在那里,眼睛望向画面之外,眼神清澈。手旁是一本《物理》。
我看着那张旧照片。照片的边缘发黄,和相册内页粘住了。我小心地把它和相册内页分开,把照片托在手上。感觉他在望着我,仿佛跟我第一次见面。
发黑的桌子,上面有油腻的旧时黑迹。发黑的墙,粘贴着红联和福字。
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第一次与哥哥相见的那个夏天。那个在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暑假。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照片,照的就是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哥哥时的情景。
可我记得,那时候分明没有别人来照相。
我坐在窗边,拿着那张照片,想了整整一个黄昏。我不记得第一次见到哥哥是什么时候了。
毕业之后我去了一家公司工作。第二年,回到老家的时候,我见到了哥哥的孩子。
“哥哥没回来?”我问。
姑姑老了。她摇摇头,“哪能回来呢?”她说,“你哥哥太忙了。我才去看了他,他在那边实在是太忙了,没有空,要挣钱,不得回来。生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很像他。你看。”
那是一张很像、很像哥哥的小脸。我抱着他,他很可爱。我喂他糖吃,耐心地,一颗、一颗地喂,帮他擦干净脏兮兮涂满糖的小嘴。我一直抚摸着他的小脸,始终舍不得放手。我陪他玩,给他买饼干,告诉他每一块动物饼干的名称,告诉他每一片饼干后面的故事。他很开心,跟我念动物的名字,一直笑,还分不清河马和海豚。我陪他玩了很久、很久,他要到处跑,我就陪着他小步、小步地跑。
他的小脸,真像照片上年轻时候的哥哥。
那天,我走在路上,回我的小镇。
依然是那条很远的路。连接着田埂、集市和公路。路很长。很难走。田埂很泥泞,集市很吵闹。我出汗了,好热。汽车和卡车在路边驶过,空气中扬起黏糊糊的灰尘。
我走了很久。有一辆小三轮车来了,问我坐不坐车。
我上车了。很快,我就远离了那条充满灰尘的路。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