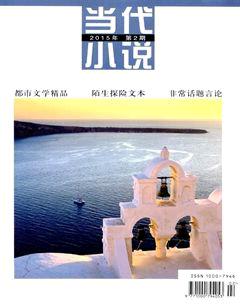你要去哪里
莫飞
她仰着头注视詹德的侧影,但詹德显然还没发现她在楼下。他的蓝色细条纹衬衣裹着肥胖的身体在缠绕着爬山虎的欧式铁扶栏间影影绰绰,浓密的黑发上盘旋几缕灰色的烟。他可能在不停晃动跷着二郎腿在抽烟,佳玛想。
他站了起来,一手搭在栏杆上,一手夹着烟,神情像四散的烟飘忽不定。佳玛看到一轮红日从他的后脑勺方向顺着高楼楼顶的避雷针滑落,詹德的脸顿时变得黯淡,缺乏生机。佳玛闭了闭眼,掂了一下手里刚买的芹菜,走过狭窄阴暗的楼道。芹菜的叶子挠在她的小腿肚上,她闻到芹菜的类似某种药物煎制过程中的溢出窗户的气味。佳玛皱了皱眉头,一些东西都可以慢慢暗示自己接受,譬如她吃不惯芹菜,但可以为詹德做。
她在厨房里做饭。攀爬着爬山虎的露天走廊连接厨房和卧室,走廊里养着一盆芦荟,一盆茂盛的吊兰,天晴的时候卧室里的藤椅会做客到走廊,花盆里常会积着詹德的好几个烟头。
佳玛看着滞留在走廊铁扶栏上的一抹余晖,爬山虎的绿色逐渐变得黯淡。詹德陷在另一端的卧室的藤椅里,盯着电脑屏幕,双手敲击着键盘的声音显示出一点生机,他的脑袋遮挡着屏幕,只露出一角的蓝光在闪着。佳玛拧亮了厨房的灯,走廊和卧室顿时都陷入了黑暗。她摆好了两菜一汤,站在门口朝黑暗里望去。
这一天是佳玛一个月中难得休息的一天。整整一天,詹德都坐立不安,从卧室走到厨房,在走廊上徘徊,看天上来来往往的云,时而趁佳玛不注意的时候盯着她的后背。这一切,佳玛都知道詹德在下一个决定,那个不可知的决定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自己一定会在什么时候一脚踩空掉下去。佳玛知道,自从詹德薄薄的嘴唇说话变得严谨和客气,懒散地躺在宽阔脸上的眉毛在不经意间拧紧,这都向佳玛在昭示着什么。
“刚才玩什么游戏,这么入迷?”吃晚饭的时候佳玛问詹德。
“没有玩游戏,在聊天。”詹德瞧了她一眼,“跟卫星在聊一些事。”
佳玛跟卫星见过几面,也知道詹德的这个朋友并不喜欢她。几次见面都是卫星抱着一箱啤酒来家里,30多岁,长得皱皱巴巴,闪婚了一次,又迅速离了。他喜欢在走廊上把腿架得老高,一边抽烟,一边盯着佳玛在厨房里忙碌。他的眼底总是装着许多忧虑,从来不去卧室里上卫生间,摇摇晃晃地下楼,找一个角落方便。有次佳玛下楼正好撞到,他慢慢悠悠地转过身来,拉上拉链。佳玛由此断定,这个人不太尊重女性。佳玛厂里的老板石阡子,见到女工走来,都是侧着身让捂着嘴哧哧发笑的女工先走。她相信卫星一直在帮詹德出主意,如何追求女人,以及如何摆脱同居一年多的她。
“你们天天在一间办公室,好像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佳玛一想到詹德跟卫星,一头熊跟一只瘦猴在一块儿咬耳朵,可是她的眼前却浮现了抱着熊胳膊的女人。
詹德的大腮帮停止了缓慢的咀嚼,又紧紧抿了一下嘴巴,好像要收回分散的严谨表情,以期恢复课堂上自信的神情来展开谈话。“人结交朋友,很大程度上是交流思想……思想的交流才是重要。”
他在嘲笑我没有思想。佳玛这样想,虽然她知道这样想不对,她在怄气,怄气会有种快感,感官上的享受,现在她想抓住詹德的只言片语大做文章。可是她知道,论夸大细节混淆思想这一点,她肯定是说不过詹德的。她像一只鼓鼓的气球,被扎了一下,满怀委屈又无可奈何地慢慢瘪掉。
“那么,昨天一个晚上,你都在跟他交流思想?”詹德一晚上都没有回家,也没有打来电话。佳玛这只软沓沓的气球好像乘着最后一口气折腾一下,“是在交流女人的思想?”
詹德撂下了筷子,显然是生气了。可他竟然什么也没说,在重新拿起筷子的一瞬间平息了自己的情绪。这在佳玛看来,他在酝酿一种更大的情绪。
“昨晚卫星的新交的女朋友请客,在他家喝多了。”他看到佳玛盯着他的嘴唇,好似期待他说,喝得不醒人事,电话忘记打了,这类带有愧疚和安慰性质的话。詹德的话在喉咙里翻滚了几下,又咽了下去。
“那个女人漂亮吗?”她不说,卫星的女人漂亮吗?但佳玛知道詹德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她不说,他将永远不知道她在无意中窥探到了他的秘密,在这个秘密之后的今天他所说的话对佳玛来说都是一种谎言,所有的动作都成了虚伪的姿态。
“还不赖。”
佳玛笑起来,詹德的用词让她心领神会。她不再有和詹德谈下去的欲望。
晚上,佳玛在台灯下赶一批手工活。詹德挨了过来,他把头蹭到她的头上,接着又用自己的厚手掌抚摸佳玛的头发。
“佳玛,没有人比你更勤劳了。”
她停止了飞针走线,聚精会神地听起来,甚至听得到詹德小心翼翼的呼吸声。
“我们厂里的女工个个都很勤劳……也和我一样,都希望嫁一个好男人。”佳玛侧过脸,定定地注视着詹德。
詹德显然被她的镇定的眼睛看得有些心虚,慌忙地把嘴凑了过去,吻了一下佳玛的眼睛。他曾经说她看人定定的眼神就像一头牦牛,犯傻劲。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他说,“其实再早些的时候就应该跟你说说了。”
“什么事?”她口气有些焦躁,“快说吧。”佳玛好像做好了义无反顾的准备。
“就是关于你想进厂办公室的事,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
她像绷紧的弦突然松弛下来,感到疲软。佳玛放下手中的活,无精打采地说:“都无所谓,只是一个月比待在车间多休息两天罢了。”
她好像又想到什么警醒起来,这难道是他想踢开我,用来安抚我的办法。
“你有什么关系可以这样做?”
“是托卫星的关系,他说他可以帮你。”
她试探地说:“那如果成功的话可要谢谢卫星……可是如果我做不好的话,说不定会被一脚踢出厂里,到时你可得养我了。”
“说什么傻话。”詹德明显勇气不足。
佳玛感到了詹德的退缩。她将整个身体使劲往詹德怀里挤,她明显感到容纳他的怀抱在往后退,她像挤进了一个泡沫之中,那些在阳光下转动的色彩,瞬间都会消失。
詹德也感觉到了她的执拗,用粗壮的手臂紧紧搂住她,想竭力转移她的注意力。
他们在沉默中拥抱了很久,直到詹德再也抵挡不住困意,低下了沉重的脑袋。
詹德已经睡着了,脸枕在自己的臂弯里,像一个无知的婴儿。佳玛灵巧的手正在给毛衣钉珠。毛衣柔软的触感让她想起曾经养过的两只羊。她把手摸到羊柔软温暖的肚子,接着把脸放到羊腹部。祖父说,羊是她的学费。父亲给羊脖子套了圈,拉到镇上,羊叫着。她啼哭着,看羊被拉进了赌馆。那个时候她恨透了父亲,站在赌馆门前咬牙切齿地等到半夜,拉着输得精光的父亲要钱上学。红了眼的父亲一脚把她踹到了泥沟里。她举着满是淤泥的双手像个木偶般躺在沟里,初春的月亮看着她。
詹德说得对。她有时就像一个犯了傻劲的牦牛,许多人告诉她,到了她这个年纪还去上什么学?何况她的基础那么差,能学到什么东西?她偏偏对学校充满了热爱,在成年有能力的时候去实现童年的梦想,这样有没有意义,佳玛没有考虑。她只想着父亲把她的羊牵走时,她绝望无助的心情,如今她用自己的能赚钱的能力去抚平这种无以平复的心情或者情绪。
她的眼睛发痛,可还是不想放下手里的针线。她有时不明白自己这样毫不懈怠地工作最后会换得什么。她想起两年前见到如今瘦得像竹竿上披了件旧外褂一样的祖父母,还在常年累月伺弄着跟他们同样贫瘠的山地。他们除了种地,已经没有了生活。可是她还年轻啊,要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吵吵闹闹的孩子。
佳玛被自己的想法搞得很伤感,一不小心就扎破了手。她赶紧将手指伸进嘴巴。她倒不是怕流血。鲜血沾到毛衣上,她干零活赚的钱都得赔给东家。她怀着气恼和绝望看了一眼詹德,他露着一张无辜的侧脸,沉沉地陷在自己的深度睡眠里。佳玛觉得从一开始被这张看似善良敦厚的脸而心甘情愿地骗了,其实这张宽阔的脸后隐藏着冷酷尖利的东西。
手指在黑暗里隐隐发痛,佳玛没有一点想睡的欲望。她听到了闹钟的嘀嗒声,越来越急迫地在她耳边响起,几乎是刺着她的耳膜进行的。她想着种种可能发生的灾难,先想到他要遗弃她,找了一个说话柔和、披着一肩长发的身材娇小的年轻女人。她想到了死,自己漂浮在河里,他站在河边护栏上看,就像家里的走廊里,每每当他站着凝望,她想着他在看她,可是每一次,他看向的只是屋宇之上的苍穹。这让她泄气、无助,一想到他把她当成对爱和恨完全无动于衷的人,让她觉得想发疯,想抓起枕头捂住他的脑袋,可最终佳玛在疲惫的思想行进中睡着了。
第二天佳玛起得很晚,她只能去上班途中买两个包子当早饭。詹德还在床上,他比她晚一个小时上班,即使去上班了,没课的时候也是在办公室里上网或者跟卫星聊天。
“我快来不及了,没做早饭,你一会儿自己买点吃的。”佳玛一边穿鞋一边对刚睁开眼的詹德说。
“你快来不及了吗?打个的去好了,别挤公交了,现在上班高峰。”詹德好像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下子从蒙昧状态苏醒过来,“那我等你回来,我有件事跟你说。”
佳玛看着床下的紫色的高跟皮鞋,她有些瑟缩,这双新鞋挤脚的隐痛在提醒她,她并不适合。她几乎想哭了,“我今天可能要加班到很晚。”
“没关系,我会等你的。”
佳玛觉得詹德的话像一个轻飘飘的幽灵一样跟着她穿过厨房,走到狭窄楼道,拼命地挤压她,又尾随她走到路上,像风一样从左耳窜到右耳,直到走到人群熙攘的公交车站台,这个幽灵好像才被更多的声音从她的耳边赶走。
公交车带走了佳玛。
佳玛暂时忘记了幽灵的事,车子里正在播报新闻。西部的哪个省的哪个市发生了两帮人的火拼,造成了十多个人伤亡;山西的一个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去山区旅游的一辆大巴坠入了悬崖。一早上,车子里的人听着新闻吃着包子咬着油条,喝豆浆的人得时刻注意着前方的玻璃,会精准地判断司机的下一个刹车在什么时候。乘客脸上安然自若的神情加重了佳玛的不安,她环顾了车内的气氛,她不用掏出手机看时间,就知道已经迟到了。她并不害怕迟到,是打卡器上发出“咔”的一声让她心里哆嗦,门卫保安慵懒和嘲笑的目光让她觉得浑身长满了刺。迟到早退会扣除一个月的全勤奖。佳玛工作的厂是个日资企业,要求缝纫工的针脚就像要求上班时间一样,不能差一分一秒。
上一次迟到是什么时候?佳玛心情灰败十分不愉快地回想。她不愿意这些回忆重新来到眼前,可是就像拨准的闹钟,到点就全然不顾主人慵懒的情绪,哇啦哇啦地叫开了。那时候才认识詹德两三周,他把她留宿在现在的那套有点奇特的居室里。可她喜欢啊,爱啊,全然都掩饰不住的兴奋。完全独立的属于詹德和她的小天地,一端通往卧室一端是厨房,她在这两端跑来跑去,感觉就像在云与云之间的穿梭。第二天,她被自己设定的闹钟惊醒,这是她住在厂区宿舍设定的时间,完全脱离了她住在詹德家的空间概念。她心里很急,可又有些害羞的样子慢慢地穿自己的衣服。詹德伸出粗壮的胳膊搂过她。她望着宽大的脸庞,门卫上的打卡器,同宿舍姐妹的嘲笑,逐渐在她的意识里淡去。她也在消融,在詹德的身边。她迟到了一个小时,门卫上曾向她献过殷勤的保安,一双遮在帽檐阴影下的眼睛像是要洞穿她还在胸口揣得热乎乎的秘密;收发报纸邮件老头抽着鼻子,像要从她的身上嗅出一丝放荡女人一夜未归的邪恶气味来。她慌慌张张地打完卡,像一只逃出猎人眼睛的兔子,可心里还不免得意,詹德早上答应过她,以后她上夜班,他会来接她。她一想到詹德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这厂区门口时,不自禁地哼起不着调的歌。连进车间时,女工人盯着她的目光好像都被这种快乐给屏蔽了。
她在厂区两个种满蔷薇的花坛挤出的一条鹅卵石的小道上急匆匆地走着。
“佳玛,你迟到了。”驻厂的日本经理石阡子离开十多米的地方让开了道。他的中文很流利,但怎么听都像嘴里含着块生硬的石头。
“对不起,石阡先生。”佳玛面带愧色地从石阡子身旁走过,但还是礼节性地向石阡子微微低了下头。
她的车间里充满了严谨和友好的气氛,但无论哪个人迟到了,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所有的女工都会从布料堆里抬起粉红的脸来,带着激动人心的神情,瞧着别人身上的被几分钟时间折磨着的神经在脸上出现的惶恐与不安。前面说的车间的严谨和友好的气氛一般出现在石阡子进来的时候,他常点头哈腰巡视车间,女工们总会向他还礼、巧笑和低头,悄悄议论这个男人的年龄,35或者37,也可能超40岁了。可是石阡子堆笑的脸和挺拔的个子,一丝不苟的头发总让女工们推翻自己的说法。她们在中饭的时候就会把头布摘下,头发散在肩上,摘下千篇一律的厂里边角料裁成的袖套,露出自己本色的衣服,她们热烈地期望平易近人、说话像嗑着石子一样的石阡子与她们坐在一起,还称他的声音“妙极了。”有时年轻一点的女工间会为了谁在勾引石阡子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只要石阡子一来,车间里又恢复了严谨和友好的气氛,只听得到电动缝纫机发出流利的咀嚼声。
佳玛趁着上厕所的时候去了一趟换衣间,查看手机,没有任何电话和消息。詹德以前都会给她发一条信息,以便她在午饭休息时间时看到。短信的开头,总是以各种让佳玛起初会脸红心跳的昵称开始的,宝贝、我的亲亲、我的小马儿。这样的问候短信,什么时候消失的,佳玛想不起来了。
佳玛缝纫机的位置前有扇不大的窗户,被修剪成球状的红叶石楠遮住了大部分的空间,隔着铁栅栏的行人和车辆便在枝叶中一闪而过,像一个微型的世界,一切来往有序,好像各人都有各人的步伐和梦想。她踩着缝纫机,像小心翼翼踩着的跳板。她想到,他睡觉的时候,她在干零活赚钱。他上班的时候,她在踩缝纫机,他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她还在踩缝纫机。他周末出去玩的时候,她还得踩缝纫机。一个月里,她只有两天可以休息。他有大把的时间出去跟别的女人搭讪约会,她连上个厕所都得看准时间。
她几乎气馁地想快些结束这样的关系。分手,不过是分手。离了他,我就不能活吗?
佳玛无数次地想到她和詹德的关系,以及今天晚上他将会向她提出分手的事。
詹德是成校的一名计算机老师,一周只有两三天有课。佳玛当初怀着美好的愿望,将几个月的工资交到了学校。她想感受一下坐在教室板凳上的感觉,以区别于多年坐在缝纫机板凳上的感觉。那种新鲜感和满足感还没有持续到一个月,詹德就挨近了她的身体。
她不知道詹德喜欢她什么。詹德说喜欢她的不聪明,太聪明的女人不好玩。
佳玛想起她曾经同居过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做倒卖服装生意的,样貌都像他倒卖的服装一样没有特色。他坐在她的对坐,跟她天南海北地聊,惹得她发笑,逗她勉勉强强一字一句咬着音说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在他要下车的时候,他看到她手里紧紧捏着包,问她:你要去哪里呢?她茫然地看了一眼窗外,又迅速抓起手里的包,跟着男人下了火车。他送她去上了缝纫班,半年多后她能完整地从裁剪到制作一个人完成。他带着她去地铁站、地下通道、天桥下卖衣服,没有摊位,衣服搭在胳膊上,跟着多看几眼的行人搭讪,将衣服硬塞给他们。他觉得她不够聪明,好几次都被客人将衣服扔到了地上,好几次被城管追得把手里的衣服全丢了。他们同居了一年多,她克服了刚从内陆出来浓重乡音的自卑感后便和他分了手。
第二个男人是在一家小餐馆认识的,戴着油腻的厨师帽,说着一口川普,炒得一手好川菜。可她常常因为他身上的油腻味而心生嫌隙,她知道她不爱他的。她其实不知道什么才是爱,像和厂里的大多数女工聊天一样,只说喜欢一个人,却很少有人说爱一个人。爱也许对她们来说太重大了,或许爱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可是几乎没有人不想拥有爱情,她们的爱情就像用锡纸小心地紧紧地和自己可怜的自尊心包裹在一起。
她和厨师不到一个月就分开了。男的总是嫌她太聪明,有着城里的人的娇贵和洁癖,不活络,在到处要钱的城市里他没有办法和她同甘共苦。
车间的工友来喊佳玛,通知去厂办公室一趟。
佳玛好大一会儿失神,看了看停止的缝纫机,又环顾了周围忙碌的景象。她真的能离开这个环境,她摇了摇头走出了车间。她曾经挣扎过,对生活的要求也少得可怜,可是未来真能脱不开这缝纫机?她在认识詹德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思考,工作疲乏得让她都无法怀念她所失去的东西,和正在失去的东西。
可现在她知道,她正在失去他。像一个沙漏一样,缓慢地,由她的这一端流向另一端。她清晰得几近痛苦,却毫无办法去挽回这一切。在休息日的前一天,佳玛跟采办员坐公交车去采买一批女员工的鞋,她就在市中心缓慢移动的车玻璃前看到詹德的,一个娇小的女人踩着尖细的高跟鞋,身体不稳当地挂在他的胳膊上。
那天,她买了一双平时不舍得买的皮鞋,新鞋夹得她脚痛。
如今,是不是连工作也一并失去。她突然想到今天早上自己无故迟到的事。前阵子不一直听说,厂里效益不怎么好,订单偏少,那就意味着员工可以少一些。
佳玛惊得背上一身汗。办公室里负责女工出勤和心理健康咨询的一个矮墩墩的女人,坐在窗口的办公桌上,用粗短的手指捧着一杯绿茶,她的嘴唇很厚,涂了很鲜艳的口红。
佳玛看了一眼女人的嘴唇,又看了一眼杯子,接着把目光移到了窗外。天阴沉沉地,办公室的留着渗水痕迹的墙壁像是响应梅雨季节的潮湿,此刻正散发出一股霉味裹挟住了她。佳玛在心底沉重地呼吸,带着听噩耗般的心情,等待鲜红的嘴唇慢慢喝完茶。
“佳玛,你们出来打工都不容易,特别像你还去过日本劳务派遣,知道一些工厂的纪律……你可不是第一次迟到了。”红嘴唇把杯子郑重地放到玻璃台面上,加重了口吻,“你去写一份检讨出来,到时挂在食堂前面的黑板报上。”
佳玛大舒一口气,她几乎欢天喜地感恩戴德地向红嘴唇鞠了一躬,“我会写好检讨,下次再也不迟到了。”
佳玛出办公室门的时候撞到了石阡子。
她在这个工厂工作的几年,石阡子总是对她投来关注的目光,就像詹德在黑鸦鸦的课堂上像发现了一颗星星一样,激动得让自己的眼睛闪闪发亮。
佳玛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美丽,可是几个同车间的大姐告诉她,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看中的美丽,那只是年轻,像花一样,折了就萎了。
佳玛偶尔怀念起自己溪水潺潺放牛牧羊的童年。那是在山脉和河流切断的内陆度过的。祖父母还在那里,他们的眼睛越来越接近尘土的颜色。父母打年轻时迁居小镇,堵了一个桥洞当家,在里面生了五个子女,像撒鱼苗一样将他们撒了出去,之后游于大海,陷进沼泽,或者固守日渐干涸的一潭死水全看孩子们的造化。佳玛是最小的孩子,祖父母领着长大,没读过几年书,一到了16岁,她就离开了他们。从内陆漂流到沿海城市,渐渐克服了自己口音和自卑心理。
可在一口流利普通话的詹德面前,她还是有强烈的自卑的。他像太阳,而她是露珠,一眨眼,就会被蒸发得无形。可詹德大多数时候是宽厚的,总是以一种怜悯的眼神听她讲到女工们十多人住在宿舍的状况。那种环境,她现在想起来也会觉得不舒服,所有的床铺上系着绳子,晾满了内衣内裤,一年四季潮湿着。有不喜欢晚上去上厕所的,就摆了几个痰盂,宿舍里永远都充斥着尿臊味和用电磁炉煮泡面的味道。
佳玛站在整齐的厂区,她往外墙剥落得像一个皮肤得了白癜风患者的宿舍楼望去,觉得心在打颤。
电铃的声音划破了宁静的厂区,女工人像两股潮水,一股涌向了宿舍楼,一股涌向了门口。天下起了雨,并不妨碍她们因为不加班而兴高采烈的样子,五颜六色的伞簇拥着像一条迅速涌动的河流,她们将奔向温暖的家里,孩子们会为母亲的提早归来而高兴,张开手臂要求抱抱。她们会撸起袖子,炒几个小菜,和爱人喝几杯黄酒,直到她们脸变成红彤彤的,爱人的眼变得炽热而深情。她们,在家里是扮演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佳玛看着彩色的河流奔向了各自的家,她站在空空荡荡的厂区。一把黑伞移动过来,是石阡子。
“佳玛有心事,来我办公室坐坐?”石阡子从伞底歪着脑袋,以探询的目光看着满腹心事的佳玛。
佳玛接过石阡子泡的绿茶,盯着墙壁上的一幅画。画上樱花盛开,一名穿和服的女子的背影站在成片的烂漫之下。
她感到,他在旁边观察她。
“佳玛觉得这画美吗?”石阡子看着佳玛沉浸到画里的脸。
“美……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樱花。”佳玛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樱花园,春风一拂,花飞如雪。这是詹德跟她描述过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带她去看过。当然,佳玛也从没要求过什么,她的眼里,堆满了小山一样高的手工活。
“有机会,我可以带你去看,樱花盛开。”石阡子说。
佳玛吃惊地从画上转到石阡子的脸上,怀疑这是自己看画的错觉。
她尴尬地笑笑,把手中的杯子放到茶几上,手竟然有些颤抖。
石阡子也跟着佳玛笑了。她不知道他为什么笑。
“你跟车间里的女工都相处得好吗?”
“很好,”佳玛说,“她们平常可爱议论你。”
“议论我什么?”
“有没有结婚的问题。”
“你说呢?”石阡子又微微笑地问佳玛。
“这个,我怎么可能知道。”佳玛朝窗外看了一下,雨下得很大。
“其实,我很眷恋我的家乡,背井离乡出来总是不容易……你看,在你们中国汉字里,家的笔画,那是个屋顶,下面是一家人,无论走多远,总是牵着一根中轴线。”
石阡子用手指蘸着茶水在玻璃茶几上缓慢地写了一个“家”字,他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带着思乡的一缕哀愁。
佳玛咬着嘴唇看了一眼字,又把目光移到别处。窗外的雨正拍打着几棵颤抖着的瘦竹,劈劈啪啪的声音。
她感到有点怕他,是除开身体危险的惧怕,而是他本身所具有的亲和力唤起了她身上的某部分的响应。这些东西在长年累月的机器前,过手的无数布料里,一次次无疾而终的恋爱中,她似乎一直把这种东西隐藏在内心深处。如今,她感到一种温暖,思乡的温暖,家乡那条溪流发出的声音在召唤,或者祖父坐在门槛前用烟管吐出的浓烈的烟味,此刻都萦绕她眼前,让她鼻子发酸。
她控制自己不让眼泪在石阡子面前流出来。佳玛不太明白,心底的像云团般愁绪是被一个异国人所牵引出来的。现在,他使她感到安全,虽然他曾经因多出几分对她的友好而让她深感不安。其实,很多时候,她都习惯于不友好的人。但她并没有觉得她要跟石阡子做朋友,就像跟卫星一样,表示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可她知道和他永远做不了朋友,更不可能跟他去日本看樱花。
“日本离我太远了。”佳玛知道自己的眼睛里一定含着泪,像窗外被打湿的竹子,晶亮晶亮的。
“我明白,明白……”石阡子注意到她情绪上的变化,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后背。“现在雨太大了,等雨停了,你再走。”
佳玛一无反顾地冲到雨幕中。
她一路奔跑着出了厂区。四周雨声打在绿化带里发出很大的响声,皮鞋在路面薄薄的一层积水里发出啪啪的声音,鞋里蓄满了水,湿透的衣服紧紧包裹着身体,眼睛里也积了水,她被水包围着。她拿起了公用电话亭的电话,想告诉詹德:她是爱他的,从他走上课堂的一刻。可是她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都没有硬币。
电话里发着嘟嘟的忙音。佳玛重又走回雨里。她想起十六岁那年,瘦弱的她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老家低矮的门框时,祖父在她的身后问她:“佳玛,你要去哪里呢?”
她扭着脖子回答祖父:“我不知道。”
责任编辑:李 菡
——石阡县全力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纪实
——石阡港——兼议石阡港对明清石阡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