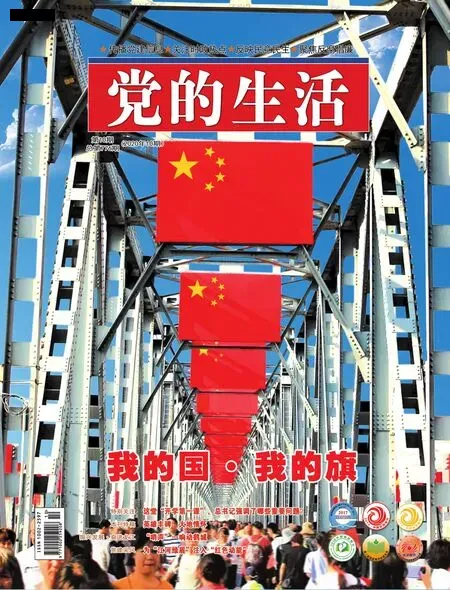爷爷的抗联交通站
□刘昱祥
爷爷的抗联交通站
□刘昱祥
每当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我就会想起英勇的东北抗日联军,想起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想起我的父亲刘运丰跟我讲的有关地下抗联交通站的往事……
九一八事变后,我的爷爷刘振铎根据开展地下抗日工作的需要,把家从周家窑搬到了庆城县城(现庆安县),在西马路茂世恒胡同租了一间房子住下。
听父亲说,那时家里常有“亲戚”来串门儿。每次来“亲戚”时,我爷爷总是让他到胡同去玩儿,并叮嘱他留意周围是否有陌生人出现。一旦发现异常情况,赶紧回来报信儿。每当这时,我奶奶或是坐在院子里做针线活儿,或是在院子里收拾、晾晒东西,或是忙着给“亲戚”做饭。而这些“亲戚”姓什么、叫什么,大人从不让孩子知道。
因为有的“亲戚”来过多次,和我爷爷的关系非常熟络,我父亲也就慢慢地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有的“亲戚”总是来去匆匆,即便不走,也是深居简出,好像睡觉都睁着眼睛。
来的次数略多一点儿的“亲戚”是于天放、朴吉松等人,有时给我父亲带些糖果,还跟他逗话儿闲聊。因为我父亲常在外面为他们把风(放哨),他们没事的时候也就给我父亲讲一些道理,借助他这个半大孩子的方便,帮他们跑跑腿儿、捎个口信儿或带点儿东西。
在我爷爷以及于天放、朴吉松等抗联干部的影响下,我父亲主动为抗联做一些具体工作。比如,借跟同学去庆城警察署玩耍之机,留心观察警察署的情况,或者带领抗联联络员去考察县公署、警察署、电话局、大烟馆的位置和附近的交通状况。
有几次,由于情况紧急,我爷爷就让我父亲到福合隆屯、徐万春屯、张大个子屯、八道岗以及铁力北关、小黑河等抗联经常活动的地方,给抗联送情报,或把情报藏在指定地点,再由抗联人员取走。当然,家里其他人也不时按照我爷爷的交代,去山上给抗联队伍送衣服、粮食、盐和药品。
1939年2月26日,在铁力城东北的张家湾河,抗联四支队支队长雷炎和政委郭铁坚接到我爷爷和我四爷送来的情报后,在那里打了一场硬仗。雷炎率领50多名抗联战士打死日伪军警30多人,缴获三挺轻机枪、五六十条大枪以及大量的弹药和食品。
由于我家在庆城的抗联交通站活动频繁,尽管小心谨慎,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次,我三爷爷在给山上的抗日联军送粮盐时,途中连人带物被特务抓住了。押送到哈尔滨后,因为我三爷爷拒不交代,被日本鬼子给折磨死了。
给抗联送粮盐是我爷爷让我三爷爷去的,出事后,我三奶奶一家因不明真相,一直怨恨我爷爷。更令人难过的是,我的大爷爷也因此对亲情、时世等失去希望而出了家。
我爷爷兄弟四个,突然间一死一出家,令他悲痛万分。但这些痛苦并没有改变我爷爷跟我四爷爷的抗日决心,而是更积极主动地参加与日寇的斗争。为了不让交通站暴露,1939年,全家先是搬到庆城东门外南下坎龙王庙屯,后又搬到东门外二里多地的石印局屯。


1940年,在我父亲16岁时,奶奶去世了。3岁的老姑不得不被送到三姑家,家中只剩下我爷爷和父亲相依为命。爷爷夏秋耪青、打短工,冬天上山伐木、烧炭,含辛茹苦地供我父亲上国民优级学校。因为长年在山里干活,爷爷与抗日队伍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随着来我家的人越来越多,我家的抗联交通站引起敌人的注意。警察署秘密撵走了对面屋的人家,把一个靠挑水卖钱做掩护名叫王青山的人派来监控我爷爷的行动,企图抓住来我家的抗联干部。
察觉到“王大哥”是特务,是在1943年的一天下午。那天,我父亲放学后去挑水,正赶上“王大哥”也去打水,他“亲热”地对我父亲说:“洋学生,能摇动这个辘轳把吗?我给你打吧。”正当他哈腰往水桶里倒水时,我父亲发现了他别在腰间的手枪,急急忙忙赶回家告诉了爷爷。
联想到刚刚发生的“福合隆事件”,爷爷立刻警觉起来。他让我父亲先离开家,之后自己再伺机脱身。按照爷爷的吩咐,我父亲随着招工的人来到三姑家所在地的圣浪火锯厂干活。
我父亲到圣浪后,爷爷便从石印局屯搬到了东门口附近,租了一户人家的北炕住下,以甩开特务的监视。即便格外小心,爷爷还是被警察抓去两次。在拷打逼问后,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再加上党组织安排了一位叫刘德丰的亲戚帮忙,我爷爷才得以保释。
爷爷出来后,立即来到圣浪找我父亲。爷儿俩又协助我的姑父周庆阳继续为抗联工作。
直到1947年,我父亲回家乡庆安参加土改工作,才知道当年“福合隆事件”的真相——1943年,朴吉松在庆城福合隆村活动时,曾派警卫员张廷贞、唐春生到庆城街内打探敌情。路上,二人遇到了曾拜过把兄弟、此时已当了特务的抗联逃兵姜贞。
姜贞拉张廷贞、唐春生到家里喝酒,同时指使他的老婆和大舅哥王青山到街里向山林警察队队长曹荣告了密。之后,庆城的鬼子、特务逮捕并诱降了张廷贞、唐春生,然后调集队伍,在叛徒的带领下乘车来到福合隆村抓住了朴吉松。
我父亲在上学途中,目睹了朴吉松的人头被悬挂在庆城警察署的大门上示众。
我父亲说,那个场景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
[编辑:王雪电子信箱:ddshwx@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