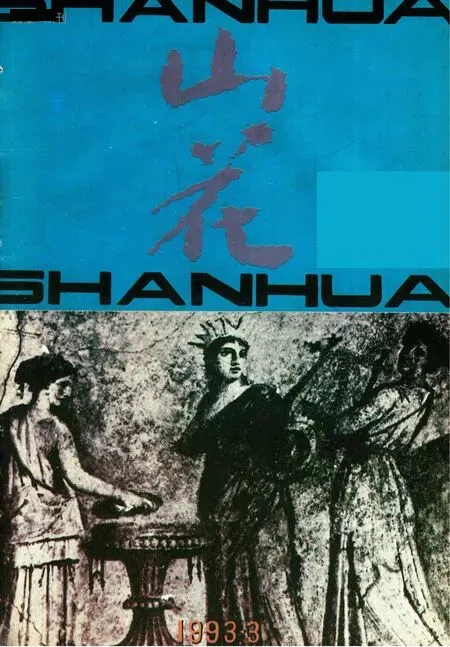在新历史小说视角下解析《翡翠旗袍》艺术特色
唐燕飞
在新历史小说视角下解析《翡翠旗袍》艺术特色
唐燕飞
新历史小说在叙事原则上强调艺术虚构;在叙事结构上打破以往历史叙事的模式,采用回忆、联想、闪回、蒙太奇等多种叙述手法,以个人化叙事代替宏大叙事;在叙事视角上更多地采用民间视角,以人性、文化等边缘化的视角取代正统视角。与传统历史小说多以主流人物或是历史文化名人为叙述主体不同,在新历史小说中,作为故事主角的往往是地主、匪徒、富商、妾侍等边缘化人物,小说展现的是这些人的男女情爱、婚丧嫁娶、家庭兴衰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的一面;构成新历史小说的叙事内容也往往并非来自正史典籍所载,而是普通人物的人生经历和自我体验。
黔北青年作家夏青的《翡翠旗袍》(发表于《莽原》2011年第5期)作为一部新历史小说,在具有新历史小说写作风格的同时,也表现了自身鲜明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民间视角
《翡翠旗袍》从民国10年(1922年)写到新中国2009年,作者不是重点去再现在这期间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而是以家族的兴衰沉浮和个人的命运遭际为描写重心,讲述祖母从出生到去世的一生的遭遇,其中有父母的反目、艰难的成长、家庭的败落,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生死相随的伴侣,以祖母亲手缝制的“翡翠旗袍”贯穿小说始终,将历史的叙事转化为凄美的人性悲歌和无奈的生存喟叹。
在这里,故事的主角变为了民间的普通男女,关于历史的内容也转变为家族记忆和个体体验,对历史的讲述不再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再现,历史在叙事中隐退为“背景”。小说从家族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沧桑变迁,来捕捉和描绘历史局部的影像,历史不再与宏大叙事有关,而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在故事中。
“旁观者”的叙事方式
由于在写作上强调个体的生命体验,新历史小说通常会以“我”这样一个叙述者的口吻来讲述故事。这个“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时隐时现,联结着当下与过去,体现着作者对历史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绪表达。
米歇尔·福柯认为,“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1]历史总是与历史的讲述者紧紧联系,历史的叙述是在当下与往昔的交错与沟通中完成的。新历史小说的时间背景具有不确定性,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常常会作一定程度的模糊化处理,有所取舍与省略,以此来重构历史时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如莫言《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就是新历史小说较为经典的一种叙事视角。《翡翠旗袍》也采用了这种他者叙事的视角。“我的祖母”“我的祖父”的叙事口吻,使叙事有了较大的自由度,“我”可以在不同时空穿插交错,在追溯和独白中从容地讲述整个故事。
《翡翠旗袍》的叙述者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他并不是事件的在场者,他演绎的是一段虚拟的、想象的历史,讲述的是祖母的人生故事。
语言的陌生化
《翡翠旗袍》的语言应该是经过作者精心锤炼的,简洁明朗,娓娓道来。此外,作者在表达上还刻意追求一种陌生化的表达效果。作家王安忆认为:“所谓陌生化,就是对常规常识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2]她所说的“陌生化”,指的是文本书写的一种创新,即语言在组合形式上打破常规,在事物描述和故事叙述上推陈出新,使那些被人们所习用、熟知的语言产生新的意义,从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其获得新鲜的阅读体验。且看《翡翠旗袍》中的一些描写:
“在祖母印象中,母亲的这扇房门一直关闭着,平时一团死寂,像一座空旷凄清的坟茔,只是偶尔响起的诵经声和从窗缝透出的檀香,多少为这房间沾染了一点人气。”
“一双明亮的眼神和天空中的阳光一样明媚,让独处深居的祖母眼前一亮,整个大厅顿时有了温度和色泽。”
“外曾祖母一如既往地沉默着,这沉默让外曾祖父的呼吸声失去平稳,如同出鞘的刀刃一样锋利。”
“祖母走在阳光普照的大街上,就像山林里滑出来的一阵笛声,清新,空灵,跳跃着,翔动着,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这些句子都是鲜活的生动的,作者敏锐地捕捉着对声色、光影、触觉和味道的感觉以及日常生活中那些细碎、琐屑的细节,并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运用比喻、通感、夸张等手法,从人物的内心入手,通过富有张力和表现力的语言,传达丰富的内蕴,与人物的感受、情绪、命运相结合,耐人寻味。
对人物对话表达方式的改造
在写作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是为了造成阅读间隔和停顿,而《翡翠旗袍》的作者为了达到表达的陌生和叙事的自如,在故事的书写中刻意省略了冒号和引号,取消了人物之间对话的引文标志,将叙述者的语言与人物的语言融合书写,让叙述变得灵活而简洁。这样,不仅使阅读变得流畅,而且使人物对话变得犹如心理活动,让读者得以更深入地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
“外曾祖父皱紧眉头,阴沉的脸色就像梧桐树身上暗褐的老树皮,说,你去哪里了?祖母远远站在桂花树的树荫里,不冷不热地看着外曾祖父不出声,那平静中透出的隔膜和坚决比她母亲更直白果断。外曾祖父被激怒了,他声色俱厉地训斥着祖母,仿佛是在教训一个砸坏了神像的孩子,说,和你说了多少遍了,没事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你看看你,哪有一点大户人家小姐的样子?你不怕人笑话我还要这张老脸呢!我们杜家的脸面,迟早要让你们母女给丢光。外曾祖父越说越激动,愤愤不平地转向一旁的秦巧夫妇,说,你们给我好好看牢她,她要是还不安分就给我带个信来,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翡翠旗袍》通篇都采用了这种对话描述方式,这种语用手段的使用使小说达到了一种流畅而耐人寻味的审美效果。
意象群的隐喻功能
在《翡翠旗袍》中,出现了旗袍、桂花树与梧桐树、镜子的碎片等意象。它们都和祖母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祖母感情经历和人生道路的见证物,也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
如文中多次出现的翡翠旗袍不仅是单纯的叙述对象,而且是有关人物命运的一种见证、象征和隐喻:
“祖母一生酷爱旗袍,……它勾勒出的身体曲线百转千回中又是那么凹凸分明的不屈不挠!”
“祖母喜欢旗袍并不是它能满足一个富家小姐鹤立鸡群的虚荣心和优越感,而是它的改良变革对那个时代产生的冲击,她冲破了加附在女性身上的樊篱,对女性的身心和个性都是一种解放。”
小说中,旗袍不仅是祖母钟爱的服装,而且也是祖母性格的象征。祖母的美丽端庄、祖母对自由的追求和在人生的苦难面前的坚韧不屈,正如这旗袍一样,让人爱慕、赞叹、欣赏。
桂花树和梧桐树则隐喻着祖母与林秋生的感情,他们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却又无法终身厮守,只能带着遗憾守望一生:
“两株桂花树已经开花,茂密的树叶间爆出一串串细碎的桂花,金黄的碎花吐露出深藏了一年的心事,祖母大口大口呼吸着这浓郁的幽香,浑身的毛孔都在这香气的刺激下扩张放大,如同经历了新陈代谢一样酣畅淋漓。”
“祖母和林秋生无语对视着,……就好像祖宅那两棵桂花树和梧桐树,在沉默中互相仰望,互相守候了一生一世。”
“袍身上用丝线绣着一株苍劲挺拔的梧桐树,裙摆上,是一株暗香偷渡的桂花树。两棵树伸展着手臂,相互守护,相互凝望,至死,也没有离弃,至死,也没有能拥抱在一起……”
“镜子的碎片”也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在祖母的掌心中赫然握着一小块镜子的碎片。正午的阳光在镜子碎片的边沿反射出一道寒光。”这块祖母打算用来为林秋生复仇的凶器,后来成为两人定情的信物,“被林秋生当宝贝一样珍藏着”,并成为林秋生最终留给母亲的一份珍贵回忆:“临终前,他托人给祖母带来一个朱红色的锦盒,四四方方的一小个,像我们今天用来装戒指的,朱红的缎面上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祖母打开锦盒,里面装着的是一块镜子的碎片,碎片上穿着一条细红绳。”“镜子的碎片”同时还从另一个角度对祖母的性格进行了补充诠释,小说中写道,外曾祖母认为祖母“就像那面完整光滑的镜子,一旦摔碎后,尽是尖锐而锋利的棱角”。
旗袍,桂花树与梧桐树,镜子的碎片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最大程度地丰满了祖母这一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翡翠旗袍》较好地体现了新历史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色,并在语言风格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可算是一部有特色的新历史小说。当然,小说也存在着一些瑕疵:
一是讲述故事中非叙事话语的介入:
如小说中赞美旗袍:“从来没有一种衣服可以如此生动地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气节”,评价外曾祖母:“她有博爱之心,又有小资产阶级苟且偷生的懦弱”。颂扬祖母:“这自由悠闲的生活养成祖母单纯随和的性格,也铸就了她独立而刚毅的个性,然而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年代,她的叛逆,她的坚韧,使得她和那个墨守成规的年代是那么水火不容。”感叹命运:“老天爷并不都是公正的,有时候,他更像一个刻薄恶毒的后妈。”
要知道,优秀的作家通常只是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地讲述故事,并不对人物或事件发表议论和评价。《翡翠旗袍》在叙事中那些带有情感倾向的非叙事话语的过多介入,反而会干预叙事,影响读者对文本的解读。这是应当避免的。
二是对名家作品的仿写:
《翡翠旗袍》中对旗袍的唯美描写和与将之与现代旗袍作比较的写法,从语言到风格上都与叶广苓的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极为相似。
将旗袍中作为重要道具出现在小说结尾,强化这一意象在整部小说中的作用,《翡翠旗袍》也与《梦也何曾到谢桥》异曲同工。
模仿也是创造的一种形式,这种对名家作品的模仿是作者善读的结果,但如能在模仿中有所突破,则能别具特色,独享风流。
三是地域文化特色的缺失:
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中,对地域文化的表现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地域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家创作时的聚散之地;一是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地域。[3]
而在《翡翠旗袍》中,虽然写到了祖母出生在黔北的一个小城里,但并没有对这片土地进行更多的描写,比如当地的民风民俗、风土人情等。作者在虚化了对时间的叙述的同时,似乎也淡化了对空间的描述,使这个故事的真实感和人文性相对削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58.
[2]王安忆.漂泊的语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3]陈继会.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36.
唐燕飞(1974— ),女,贵州遵义人,文学硕士,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黔北作家新世纪小说创作研究”(JD201421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