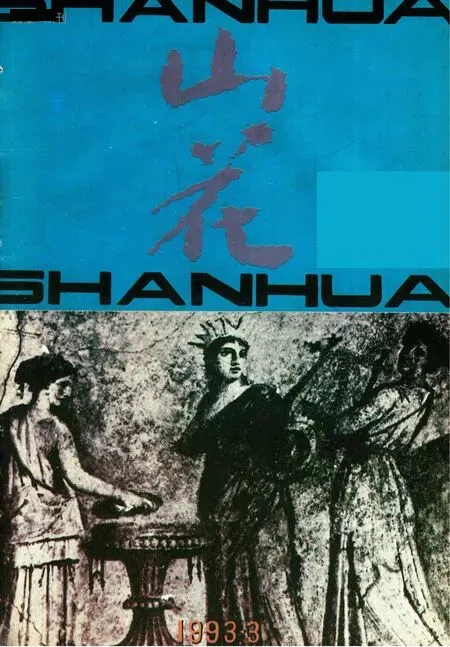蔷薇园(外四首)
桑克
蔷薇园
她在他们脸上看到许多恐惧,恐惧让他们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
——约翰·勒卡雷《史迈利的人马》
有人在但并不像风
掠过接骨木尚显稠密的
战阵或者把这战阵
据为己有借以抵御
各种庞杂的广播和市声
花曲柳只掩护尖兵
而不能保护军营的尾声
但是读者并不在乎
只要眼睛看不见就行了
看不见背后的虚空
蔷薇数量并不占优
同样不能妨碍她是
真正主人因为我的个人
命名权从柳园时期
就已开始散发
香味或者无味
并不计较但是声音却被
反复挑剔被电锯声或者
地下呼啸而过的地铁声
被游乐园噪声
追求寂静是有机的
讨论而不是非此即彼的
争论正如我想说的
其实是关于恐惧的问题
而不是蚂蚁的幸福
尽可能多地掩饰
自己的学识而对不慎
暴露的部分羞愧不已
并且暗下决心
决不透露柳园的奥秘
以激怒对方或使
对方嫉妒地靠着电梯
向你传递火焰的消息
决不硬碰硬或者
在微信为爱自拍
或者贪婪地享受
此时此刻的热闹之中
放风一般的宁静
把烟蒂的通缉令
藏起来而非为了卫生
想必你理解
关于风景的象征性之外仍然
存在温和的自然性
蔷薇的同时兴衰相当全面地
赐给你冷静
榆叶梅的机警
显得过于即兴
而不是深思熟虑和知情
好汉就吃眼前亏
中圈套就是对抗的报应
而漠视同样
不如虚风可靠
并且因为迟钝与时间间隔
而显得并非不知所措
而显得更加擅长变脸
然后是等待
是小心翼翼地做点儿什么
描摹风景或者
蔷薇园里看书
然后消逝无踪
从来没有出现过
如同手写的信
而不是打字的或者出现在
电脑或者手机屏幕之中的
称之为信的便条
被偶尔经过
头顶的航班尾烟
轻轻搅散而代以
垂泪与义务
并不明确悲伤
并不保证
保存秘密的真正意义
就能兑现组织的
嘴巴和木门
虚构从不卖书的书店
并且承认
自己的脆弱与不明真相
而且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预兆的真相
在雨的怜悯之中
嗅到柴油的
叛乱气息
而且充满只有北京
小剧场演出才有的
喜剧感
躲在树丛之中
把我当出土文物或者
饮罢雄黄酒而现形的
蛇精
反复拍照和扫描
反复咳嗽
反复提醒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随机的而且单纯
充满真正微笑的
灿烂笑容
没有一只蚊子
足以鉴别现在距离
盛夏还有一段时间
这不由使坏人
再次感到庆幸
纪念涅斯梅洛夫被带离哈尔滨六十九周年
轰鸣过后的风暴
化作白色的舰队
——涅斯梅洛夫《天空撒下鸟语……》
根本不能指望乌云。
根本不能指望寂静的乌云理解灰暗的石头
以及暗红色的星辰。
指望乌云势必引起冷漠而消瘦的
怀疑,而你远离人群的努力
正被毛瑟枪和镰刀拉进临时兵营
颤栗的回忆,恰如浪漫小说和纪录电影显示的——
的确没有一只松鼠愿意担任
招风耳的辩护人,担任掷弹筒的律师。
多么单纯的恐惧啊。
如果勋章能够弥补伤疤,那么就得把伤疤修整得
如同勋章一样的形式,连同代表星芒的金属尖刺,
绝对不差一毫一分。
就在黑夜之中,在坚硬的铁锤对面,
然后就是通向鄂木斯克的秘密旅行。
反复见识铁锚,反复见识严冬和湖水凝结的硬冰
如何还原愤怒波涛的树状条纹。
你的呵气抚摩下巴但是更像白色的套绳
羁縻简洁的传记,借以逃避接收
狐狸致敬的书信。噢,黄色的哈尔滨——
面包石和插图附近的诗,一个陌生的中国人
正在礼貌而狡黠地向你靠近。
你读巴黎杂志。为什么是古米廖夫和叶赛宁
而不是帕斯捷尔纳克和曼杰施塔姆——
老帕在同行面前究竟如何赞许遥远的你而小曼的转
运站和芦苇
离你即将抵达的格罗杰科夫又有多远?
必须应用问号了而句号正在闭拢
暗黑的嘴唇,弹簧,蛆虫正在大声朗读来自权威的声音,
犹如亚裔导游的木制棒球棒在格罗杰科夫低矮的
屋檐下
向正在办理通关手续的我宣读的戒律,
笑话,逸闻,口令,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奇妙——
你预言。你一语成谶。你乌鸦嘴。
你在八月的装甲车和摩托车的风暴之中反而平静得
仿佛
刚刚学会的铅块主义谣曲——
你所谓沉重之中的轻正是
孩子们追求的,而你目睹
松花江边的餐馆犹如近卫军官挺括的制服,
扯脱一粒包金纽扣,面貌自然就焕然一新,
仿佛被灰狼抓破的松树表皮偶尔听见
来自冰窟深处模糊而细碎的喘息之声——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不是离开哈尔滨而是离开我的饿螺丝,
因为谢廖沙·王正在审判多出来的犰狳。
你看见夏日正在离开榆树之巅,
正在离开欢迎的纪念碑和灰尘。
木板栅栏刷着新鲜的绿漆,而钩结的白线窗帘
即使是在微风的帮助之下仍旧不能拼写
构成恐惧一词的西里尔字母,更别提那些深奥的中文。
对标语来说你确实不怎么亲切。
算了,既然你的结局已经如此,那么不朽就不过如此。
你冲我点头,呼唤更高的鸟语。
重读《日瓦戈医生》
恐惧不是狼叫,
不是狗叫,而是来自肚皮深处
尖锐而绵长的叫声。
从更大的痛苦之中获得
对付小痛苦或者在小痛苦之中
熬下去的力气。
景色宜人或者相互驳斥,
构成复杂的只有人类才能会意的关系。
桦树冷漠地瞪着褐眼。
怀念是创造。
越来越远离人物原型而接近于
不认识的故乡。
我不是在说俄国
或者革命,而是在探讨生存的技巧,
或者如何回归单纯的雪道。
瓦雷金诺不适久居,
正如五连与兴凯,正如柳园旁边
这幢七层的灰色建筑。
阳光照着白杨树林,
呈现迷人的蜂蜜的颜色。
但风是冷的。
是被夜色嫌弃的
匆匆行驶的绿皮火车。
人和人相互提防,
相互倾诉而不信任。
墨水瓶能够储存正在等待表达的
酸楚的个人生活。
死和离婚只能
幸福一刻而不能常见常新。
集中营只是一块刻字木牌。
追求不断缩小围栏。
从一个肥硕的苹果变成一粒坚硬的而且被胃肠
视为恒敌的麦种。
但愿又能熬过
这一个无聊而又漫长的秋夜。
为了谁也不爱。
去外县
到处都是暗黄的稻田,
而小麦已经多年不见。
馒头面包的面粉来自何处?
广播的解答难以置信。
你我争夺车厢的座位,
站立的人嫉妒坐着的人。
你的奢侈是喝碗面的浓汤,
我的克制是紧咬嘴唇。
另一个车厢异常空旷,
行脚商放肆脱掉鞋袜,
舒服地躺进三人沙发。
混合臭气仿佛农贸市场。
妇人大声地交谈私情,
而脸皮微红代替或混淆
内心深处羞愧的砖红。
细节类似相声而非小说。
低头浏览手机内容,
她的朋友或者熟人构成
粘稠生活的乱哄哄。
乳沟仅仅是竖纹的暗影。
腿皮的颜色仿佛
采摘后放置多日的鸭梨,
而他膝盖的书上,
雕刻着来自南非的茶印。
火车好像刚刚启动,
转眼就停在石人城。
行人果然都像石人,
手势热情眼神冷漠。
哀 度
这把蓝色的尺子
我用来衡量
丁香的哀度
以前没有哀度
这种计量单位
这是我今年最胆大的发明
它指悲哀的刻度
如果普通雨的哀度是五
那么冷雨的哀度就是十六
哀度的热与冷
代表什么其实
只是接受美学的任务
各种想象与我无关
我只能讲述
丁香的哀度
在我身边发生
而不是十八世纪小说之中的
芙蕖或者落红
丁香花落的哀度是多少
连根拔除的哀度是多少
生死衡量肯定不同
那么一条小河呢
那么一条蜉蝣般的鱼或者
一块高美的玉呢
与哀度对应的
是暗度——
就是指黑暗的刻度
那把灰色的尺子
我还没有发明
嗯,明年初冬制作
那样一来
我的生活就会比现在
更加精确
我特别喜欢
精确的生活
一如喜欢模糊的自由
但是此刻或者上午
对哀度的测量工作
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
我的病毒性眼疾
导致无法流泪
直接妨碍哀度读数的考核
我只能用
玻璃酸纳药水
顶替眼泪
这样的弄虚作假
反而使哀度的真理边缘
变得含糊
眼泪指望不上
而心井的愁眉却因太深
而不能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