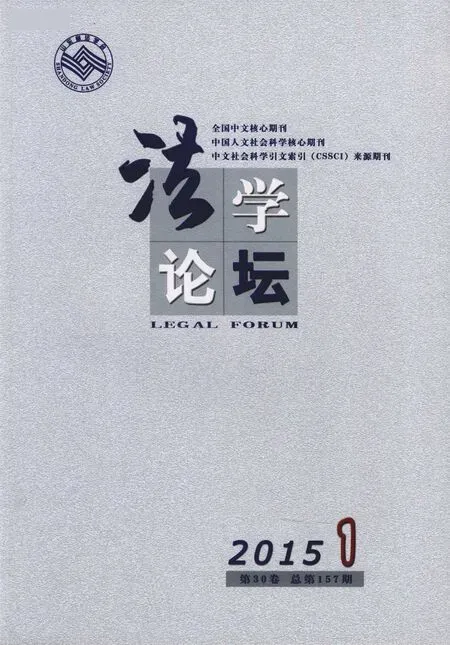“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刑法解释适用
魏 东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刑法解释适用
魏 东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在具体认定“收受干股型”受贿数额时,应将行为人因收受干股而实际分得的红利计算在受贿数额内;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应将行为人收受干股按其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其在案发时对应的公司实际资产收益价值计算在受贿数额内;已确定分红的具体标准或者具体数额而尚未实际分得的红利也应将其计算在受贿数额内,但股份未实际转让的干股不得将干股虚设价值作为受贿数额认定。同时,要依法认定“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犯罪停止形态,对于干股及其收益应依法予以特别没收。
干股;受贿罪;刑法解释
“收受干股型”受贿构成受贿罪,其刑法依据是《刑法》第385条、第388条、第163条第3款、第184条第2款的明确规定,依照《刑法》第386条、第383条的规定对其适用刑罚。由于“收受干股型”受贿罪在认定处罚上具有相当的特殊性,2007年7月8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条专门作出了以下规定:“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意见》属于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文本,其关于“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解释性规定相对于刑法典的相关规定而言更为明确具体,但是其中仍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释法不明、释法不当且引发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较多争论,因而存在“司法解释也需要解释”的必要性。*曲新久:《刑法解释的若干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但是在刑法解释论上,刑法解释的文本对象只能是刑法“立法文本”而不能是刑法“司法解释文本”。因为“司法解释文本”也是对刑法“立法文本”的解释,因而尽管“司法解释文本”自身客观上也需要解释,但其最终的、作为刑法解释对象的文本对象仍然是刑法“立法文本”。为此,本文就“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刑法解释适用略陈己见,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干股”本质特征的刑法解释
依照《意见》第2条规定,“收受干股型”受贿之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这一简要规定应当说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收受干股型”受贿之“干股”的本质特征,但是,其并不代表在刑法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就不存在争议。关于“干股”的本质特征,刑法理论上大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干股”是指不出资但可以享有完全的股权并享受红利的股份。例如,有观点将“干股”界定为“权力股”,认为其是指不投入股金,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但对股份享有所有权并享受红利的股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国有公司经理在公司职工承包的下属经营部中“搭干股并分红”的行为如何定性》,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6日第6版。或者认为其实质是未出资而占有股份,是请托人无偿提供的享有股权并享受分红的股份。*孙国祥:《新类型受贿犯罪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二是认为“干股”是指不出资而享受红利的股份(但不享有完全的股权)。例如,有观点认为,“干股”是指无须支付对价的奖励股,只享有分红的权利,对股份本身不具有所有权;*薛进展:《论商业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认定》,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或者认为,“干股”属于分红股,是基于奖励或赠与而形成的,资金来源多是由其他股东转让或公司利润转化而来,其本质属性在于它是不缴纳出资而享有的公司股份。因而,“实践中,干股持有者一般只享有依据干股份额进行红利的内部利润分配的权利,并不享有表决权、公司经营事务的参与权等股东的共益权,对股份也没有所有权”。*郭竹梅:《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但是,这两种见解似乎都过于绝对而不完全符合实务观察结论。
实务上观察可以发现,“干股”尽管在我国民商事法实践中也较多地存在,但是其在国家法律层面上尚缺乏明确规范,*某些部门规范或者地方性规范中有此规定,例如江苏省《关于推进技术股份化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干股的所有权仍归公司原有股东所有”。参见李成杰、侯铁红:《干股薪酬制探析》,载《经济论坛》2005年第8期。此外,有学者认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所规定的“股权激励”实质上也是对干股的规定。参见郭竹梅:《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266页。就普通公民和法人的民商事行为而言,其仅限于“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意义上存在,以作为对那些“未出资”的管理者、技术人员或者普通员工、亲友以及其他关系人的“奖励”或“赠与”。但就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干股”具有特殊的法律意义。“干股”是否是作为股东身份和权利的统一体,这在刑法解释上可能并不重要,其给获得干股的人员能够带来实质的经济利益可能才是刑法解释关注的核心。因为,就获得干股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言,持有干股的国家工作人员不但其所获得“股东身份”(假若其能够获得这一身份)的背后是实质的经济利益,而且其“权利”的内容也是实质的经济利益,因而“股东身份和权利”二者无论分裂还是统一,其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就是干股所实质内含的全部经济利益——“有资本依托的干股”本身所内含的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和公司利润分红上的经济利益(红利),或者“无资本依托的干股”所主要内含的公司利润分红上的经济利益(但是无法包含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关于“有资本依托的干股”与“无资本依托的干股”的划分及其含义,详见刘为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解读》,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7月17日第6版。而这正是“收受干股型”受贿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此而论,将“干股”直接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是十分精准的,其抓住了“干股”的本质特征,即未出资而获得股份并以此能够获得或者已经获得经济利益。至于“干股”是由特定公司虚设的股份(公司本身无法设立实实在在的股份),还是由特定股东单独或者共同虚设的股份(以公司名义)、单独或者共同真实设立的股份,以及“干股”持有者是否享有完全的股东权利(包括股份所有权、股东表决权、公司经营参与权等),都在所不问。
综上,笔者认为,“干股”在刑法解释论上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既可以是享有完全的股权而获得经济利益(即内含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和公司利润分红上的经济利益)的干股,也可以是只享有获得红利的分红权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即主要内含公司利润分红上的经济利益而无法包含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的干股;既可以是“有资本依托的干股”,也可以是“无资本依托的干股”。其中“有资本依托的干股”通常享有完全的股权,其在享有获得红利的分红权的前提下,还可以特别约定可获得或者不获得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关于“干股”的这一刑法解释结论,有助于司法上恰当认定“收受干股型”受贿的具体数额,后文对此问题再作具体研讨。
不过,刑法解释应当同时关注民商事法原理和刑法原理以进行体系性解释,不得作出明显背离整体法理的解释结论。我国《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而,若国家工作人员“用货币出资”或者“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依法不得解释为“干股”。
“收受干股型”受贿之干股,在实践中通常表现出各种名目,例如管理类干股、信息类干股、技术类干股、其他奖励类干股等,对此也应注意恰当运用民商事法原理和刑法原理进行精致化的法理分析,同时还应当进行刑事政策上的必要考量,而不能被一些名目(语词)表象所迷惑。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可否在有关公司兼职并作为“未出资”的管理者或者技术人员而获得作为“奖励”或“赠与”的干股?本文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否在特定公司兼职从事管理工作或者技术工作,其收受特定公司任何名目的干股在本质上都是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且这也是国家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即使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在特定公司兼职,其也不能收受特定公司任何名目的干股。此种收受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在刑事政策上必须对此予以特别考量和禁止。在刑事政策上,应当对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相对人财物的行为之定性作出理性选择,这种选择的依据应当是法益价值的权衡判断。其中就成为问题的模糊权钱交易(即有权钱交易之虞)而言,它主要涉及以下两种法益价值的判断权衡: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公民的自由接受赠予和奖励的权利(这种权利属于公民财产权利中的很小部分)。基于这两种法益价值的权衡判断和刑事政策上的价值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在规制受贿行为时应当将那些明显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具有一定“模糊性”的模糊权钱交易行为囊括在受贿罪范围内,*魏东:《受贿罪中权钱交易形态研究》,载《法制日报》2004年4月15日第10版。以有效防范腐败滋生。因此,即使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在特定公司兼职,该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任何名目形式的“干股”在本质上和刑事政策上均应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本身收受经济利益,这是刑事政策考量上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二、“收受干股型”受贿的具体样态
明确了干股的刑法解释意义之后,有必要进一步检讨“收受干股型”受贿的具体样态。依照《意见》第2条的规定和实务上观察可以发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具体情形上可以表现为纯粹的“收受干股型”受贿、变相的“收受干股型”受贿和交织的“收受干股型”受贿三种。
(一)纯粹的“收受干股型”受贿
所谓纯粹的“收受干股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收受请托人以好处费、感谢费、奖励费、慰劳费、管理股、信息股、技术股等名义而给予的干股。此类纯粹的“收受干股型”受贿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太多争议,无论其干股是由相关公司给予的,还是由相关公司的股东给予的,无论其干股是“有资本依托的干股”、还是“无资本依托的干股”,也无论其干股是享有完全的股权,还是只享有获得红利的分红权,均在所不问。因此,此类纯粹的“收受干股型”受贿,其突出特征在于行为人所收受的干股鲜明地体现了“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之干股的纯粹性、赤裸性、直截了当性,而不存在某种非纯粹性、掩饰性、间接性;否则,如果行为人所收受的干股存在某种非纯粹性、掩饰性、间接性特征时,则其已演变为后文所述的变相的“收受干股型”受贿与交织的“收受干股型”受贿。
就纯粹的“收受干股型”受贿而言,其受贿内容主要有三种类型:股权取得时的出资款或者转让价(仅限于“有资本依托的干股”)、内含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仅限于特别约定)和公司利润分红上的经济收益。其中,只有收受“有资本依托的干股”且享有完全的股权的干股,才有可能同时获得上列三项受贿内容;而收受无特别约定的干股或者“无资本依托的干股”,通常只能享有获得红利的分红权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即主要内含公司利润分红上的经济利益而无法包含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
明确和细化纯粹的“收受干股型”受贿之内容,具有重要的刑法解释论意义。在司法实践中,若认定行为人收受了“有资本依托的干股”且享有完全的股权的干股,则应根据案发前行为人实际收受的干股之股权取得时的出资款或者转让价、是否实际享有内含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是否实际分得公司利润分红上的经济收益等情况,综合评判认定行为人的受贿数额;若认定行为人收受了无特别约定的干股或者“无资本依托的干股”,则应根据案发前行为人是否实际享有内含公司资产上的经济利益、是否实际分得公司利润分红上的经济收益等情况,综合评判认定行为人的受贿数额。关于具体的数额认定问题将在后文详述。
(二)变相的“收受干股型”受贿
所谓变相的“收受干股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以借代收”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给予的干股。表面上看,此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借款出资,甚至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还向请托人出具了“借条”、“借据”等书面文件,产生一种国家工作人员有实际出资而非收受干股的误导;但是在实质上,国家工作人员把玩的游戏是“借(请托人)骨头熬油”、“借鸡生蛋”等掩人耳目的把戏,根本就没有实际出资,而是从干股分红中将部分红利“归还”干股所代表的出资款,或者直接用请托人所在公司的资金“归还”干股所代表的出资款,甚至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到案发前都不“归还”干股所代表的出资款。
应当承认,此种“以借代收”之变相的“收受干股型”受贿会在刑法解释论上面临理论诘难,为何以借代收的情形“这个可以有”?其理由还是应从刑法规范文本之中寻找。通过对《刑法》第385条、第388条、第163条第3款、第184条第2款的规范实质解释,以借代收情形之下的行为人在客观上具有收受“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此处借用司法解释文本规范语言)之行为,符合刑法规范“索取他人财物”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实质含义。不过,若行为人不是向作为相对人的相关公司及其股东“借”款,而是向其他公司或者自然人借款(并投资到作为相对人的相关公司),则依法不宜解释为“以借代收”的情形。
(三)交织的“收受干股型”受贿
所谓交织的“收受干股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为掩人耳目而采取部分出资或者低价受让股份的方式,而实际获得部分干股。例如部分出资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10万元,但是实际上获得了需出资50万元才能获得的股份,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就获得了超出其10万元出资额的部分干股(即40万元的干股,亦即50万元中扣除10万元后之余额)。再如,低价受让股份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10万元却通过“转让”获得了价值50万元的股份,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实质上也获得了价值40万元的干股(即50万元中扣除10万元后之余额)。此两种情形,均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有部分实际出资而获得股份、又有部分股份是没有实际出资而获得的干股,是部分实际出资与部分未实际出资两者交织的一种状态,从而应依法认定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因未实际出资而获得的那一部分股份为“收受干股型”受贿之干股。除此两种情形外,还可能存在交织的“收受干股型”受贿之第三种情形,即国家工作人员在部分实际出资或者低价受让股份的同时,还有部分股份是通过“以借代收”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给予的干股。对于第三种情形,应当在准确查实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额部分的基础上,将其实际出资额扣除后的股份份额折算成干股资金数额。
三、“收受干股型”受贿的数额计算
“收受干股型”受贿的数额计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前面部分论述中已涉及部分情况下的干股数额计算的问题,这里对此进行系统探讨。但需要指出,“两高”《意见》的部分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部分做法可能不完全符合刑法规定,值得检讨。
《意见》第2条规定,“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这种规定存在的问题在于:其一,自相矛盾。无论作为干股之股权是否已实际转让,按理说行为人因此而实际分得的红利均应作为受贿数额计算,为何反而在规定“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针对“股份未实际转让”而言)的同时,又规定“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针对“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而言)?在解释结论上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应当说也是明显缺乏合理性和说服力。其二,违背《刑法》的明确规定。按照《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处罚,那么,司法解释对于行为人“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针对“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而言)之规定,就明显违反了《刑法》规定。应当明确,行为人受贿后因现金或者房屋等自然生成之孳息,依法当然可以“按受贿孳息处理”;但是,“收受干股型”受贿的行为,通常行为人并非只在意干股,而是该干股之红利,“干股及其红利”依法都属于受贿数额。如果将“干股及其红利”人为地分解开来,仅将其中干股价值认定为受贿数额,不将红利认定为受贿数额,此种本末倒置之做法其实严重违背了《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明确规定。其三,实践中可能造成严重失当。设若行为人实际获得价值9万元干股并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在案发前已实际分得红利100万元,那么,按照“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之规定,就只能认定行为人受贿数额为9万元(而将另外实际分得红利100万元按受贿孳息处理),这样在行为人无任何其他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从重处罚情节时,通常可能只能处以不超过10年有期徒刑之刑罚;而设若行为人名义上获得9万元股份但未实际转让,在案发前同样已实际分得红利100万元,那么,按照“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之规定来处理,却应当认定行为受贿数额为100万元(而仅仅将未实际转让的9万元干股不计算在内),这样在行为人无任何其他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从中处罚情节时,通常就应当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之刑罚。两相比较,两种情形之下行为人的受贿罪行在实质上大致相当,但是刑罚处罚适用却差异悬殊,显失妥当。
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386条规定,“收受干股型”受贿数额的认定应当采取以下办法处理:
其一,无论作为干股之股权是否已实际转让,行为人因收受干股而实际分得的红利应作为受贿数额计算在内;
其二,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应将行为人收受干股按其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其在案发时对应的公司实际资产收益价值计算在受贿数额内;
其三,股份未实际转让,不得将其作为受贿数额计算在内;
其四,未实际分得的红利,通常不得将其作为受贿数额计算在内,但是有证据证明已确定分红的具体标准或者具体数额而尚未实际分得的红利应当作为受贿数额计算在内。
顺便指出,对于第二、第四种情形,应当在具体认定其受贿数额的同时,依法认定其犯罪停止形态属于犯罪未遂,对干股及其收益予以特别没收。
[责任编辑:谭 静]
Subject: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e of Acceptance of Bribes about “Accepting Gangu”
Author & unit:WEI Dong(Law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China)
The concrete patterns of the crime of acceptance of bribes about “accepting Gangu”embody the pure crime of acceptance of bribes about “accepting Gangu”, the changed one and the interlaced one; The amount of bribes should include the dividend which is actually given to an actor because of his accepting Gangu; When an actor finished the registration of share transfer or actually transferred his share based on some evidence, it should includes the value of the Gangu accepted by the actor in time of his transfer and the real assets interests of company in time of a criminal revelation. It also includes the dividend which is not given to an actor but has been set the concrete standard or amount, but not concludes the false value of the Gangu which is not been transferred.
Gangu;crime of acceptance of bribes;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2014-11-28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刑法解释原理与实证问题研究》(12AFX009)的阶段性成果。
魏东(1966-),男,重庆人,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刑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D924.3
A
1009-8003(2015)01-00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