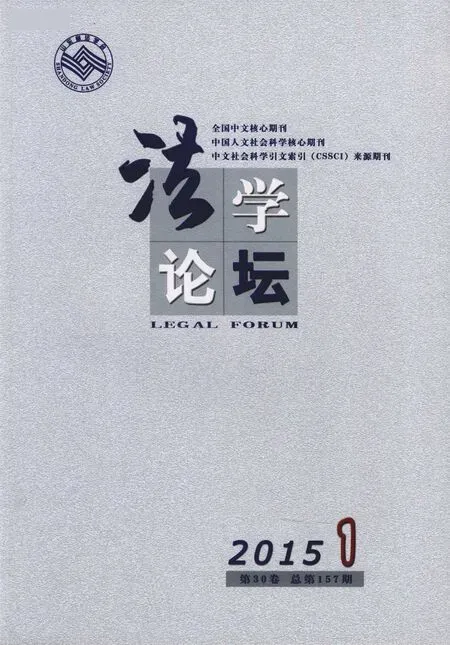《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与东海共同开发
——结合钓鱼岛与防空识别区问题的讨论
罗国强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与东海共同开发
——结合钓鱼岛与防空识别区问题的讨论
罗国强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为东海共同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本身并非正式的共同开发协议而是其准备性法律文件,在缔结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需要进一步细化。钓鱼岛问题和防空识别区问题是目前阻碍东海共同开发实现的两大桎梏。中方应当坚持以原则共识为基础展开后续谈判,致力于在后续谈判中达成涉及具体权利义务的、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平衡和保障双方利益从而令双方均具备主观执行意愿的共同开发安排;阐明中方对于钓鱼岛的主权立场,同时确认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主张在共同开发安排中忽略钓鱼岛的法律效力;坚持本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阐明防空识别区的法律性质(作为自卫权间接准备措施的必要技术信息管控),指出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防空识别区存在重叠乃是正常现象,不妨碍海上共同开发。
东海争端;共同开发;钓鱼岛;防空识别区
2014年11月7日,在双边关系因东海争端等原因而陷入较长僵持与停滞的情况下,中日双方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并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1)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即1972年《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及2008年《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3)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4)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新华网:《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http://www.js.xinhuanet.com/2014-11/07/c_1113165451.htm.以上原则共识的达成,为久已停滞的中日东海共同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为此,理论界有必要依据《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结合钓鱼岛与防空识别区等涉及东海共同开发的关键问题,进一步探讨东海共同开发的可行性并提出合理建议。
一、《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及其后续进展
2008年6月18日,中国与日本达成《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以下简称《原则共识》)。该《原则共识》以此前韩日达成的东海共同开发协议为模板,旨在让双方暂时性地共同开发相邻海域的大量资源;*See Joseph Jackson Harris, The Pacific War, Continued: De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 Dispute,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42, 2014, p.594.这对于以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重叠资源主张、缓解东海紧张局势而言,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突破。*参见 Suk Kyoon Kim, China and Japan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 Note on Recent Developments,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43, No.3, 2012, p.299.就共同开发政策的实现程度来讲,该《原则共识》已经是中国在东海南海争议海域内所达成的距离共同开发协议最近的法律文件。
《原则共识》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中日在东海的合作。《原则共识》指出,为使中日之间尚未划界的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中日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第二,中日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原则共识》指出,双方本着互惠原则,经过联合勘探,在指定区块(面积约为2700 平方公里)中选择双方一致同意的地点进行共同开发;《原则共识》同时指出,双方同意,为尽早实现在东海其它海域的共同开发继续磋商。第三,关于日本法人依照中国法律参加春晓油气田开发的谅解。《原则共识》规定,中国企业欢迎日本法人依照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有关法律,参加对春晓现有油气田的开发。
《原则共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不损害各方在东海问题上的立场与主张。《原则共识》不损害中国在东海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不损害中国在东海有关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和主张,包括中国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不承认日本的“中间线”主张,不存在以“中间线”划界问题。第二,中日在春晓油气田是合作开发,不是共同开发。日本同意依照中国法律参加春晓油气田有关合作,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承认春晓油气田的主权权利属于中国,此方式为合作开发不是共同开发。其最重要的标志为,春晓油气田的开发必须要依照中国法律进行。*参见金永明:《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内涵与发展趋势》,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2期。日方过去一直强调“春晓”油气田的“吸管效应”侵犯了日本的利益。实际上,春晓也成为东海谈判的一个“死结”,使谈判一直停滞不前。日本在谈判中曾经一再要求将中方“春晓”油气田纳入共同开发的范围。但是,从文件内容看,日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而从中方角度来看,这个方案既维护了中国对“春晓”油气田的主权权利,又解开了这个“死结”,*参见薛桂芳、迟远达:《浅议中日东海共同开发》,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从而缓解了东海争端,为进一步的谈判提供了可能性。第三,《原则共识》旨在为将来的东海共同开发铺平道路。共同开发的实现需要有关当事国缔结具体协议,《原则共识》距离具体协议尚存距离,但可以作为试探性的第一步。
在《原则共识》的缔结形式上,可能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在于,由于双方没有致力于达成一份通用的英文作准本,双方遂各自提出了一份英文本,而这两份英文本在行文表述上存在细微差别,故而可能导致法律解释上的差异。*参见 Shigeki Sakamoto, Japan-China Dispute over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From a Japanese Perspective, Japa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1, 2008, pp.116-117.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3条来解决。*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条约约文经以两种以上文字认证作准者,除依条约之规定或当事国之协议遇意义分歧时应以某种约文为根据外,每种文字之约文应同一作准;以认证作准文字以外之他种文字作成之条约译本,仅于条约有此规定或当事国有此协议时,始得视为作准约文;条约用语推定在各作准约文内意义相同。由于双方并未约定英文本为作准文本,故而各方所提出的英文本都只能作为参考,而应以中文本和日文本为作准文本,并推定两者的用语具有相同意义;如果确有歧义,则应由双方协商解决;而在此后进一步的缔约谈判中,双方可以考虑提出一份共同作准本以避免条约解释上的冲突。
在《原则共识》的具体内容上,中日双方可能存在的争议点包括:第一,《原则共识》的法律性质为何?第二,“共同开发”的准确含义为何?第三,“为尽早实现在东海其它海域的共同开发继续磋商”是否意味着达成协议之前禁止开发?第四,日本法人参与春晓油气田开发的性质为何?*参考 Suk Kyoon Kim, China and Japan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 Note on Recent Developments,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43, No.3, 2012, pp.299-301.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原则共识》当然是一份有效的国际协议和法律文件,但该文件仅仅给出了共同开发区块的初步范围(最终范围的确定有赖于双方一致同意的选择)、规定了某些粗略而模糊的“进行合作”、“尽快达成必要的双边协议”的法律义务;文件没有也不打算为双方规定明确的共同开发权利义务(这留待正式的共同开发协议来规范),而是为双方指出下一步的谈判方向并为达成正式的共同开发协议铺路,因此在性质上属于正式共同开发协议的准备性法律文件。其次,《原则共识》并没有为共同开发规定明确的含义,而现有国际法也不能对此提供现成的准确界定,*共同开发的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接受,70-80年代加速发展,并最终在90年代形成了如今关于共同开发的原则。参见 Gao Zhiguo, The Legal Concept and Aspects of Joint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Ocean Yearbook, Vol.13, 1998, p.109.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于共同开发的认知是原则性的而非具体性的。有学者指出,国际共同开发的概念并非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被认知和使用的,只不过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可以建议将这一概念限定在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上。参见 Masahiro Miyoshi, The Basic Concept of Joint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The Basic Concept of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tunrine and Coastal Law, Vol.3, 1988, p.5.也有学者阐述道,从与海洋边界相联系的角度出发,共同开发通常被理解为涵盖重叠主张区域的临时协议,其可能伴随着划界也可能不伴随着划界,通常涉及海洋边界地带的油气和渔业资源。参见 S. P. Jagota, Maritime Boundary and Joint Development Zones:Emerging Trends, Ocean Yearbook, Vol10, 1993, p.112.因此,这一概念通常是在国家缔结正式共同开发协议的时候,根据具体需要予以界定。故而这也有待于未来的正式共同开发协议来规范。再次,《原则共识》原本就只规定了某种模糊的尽快磋商并达成协议的合作义务,没有明确而具体的拘束力,更不可能禁止任何开发行为;*尽管理论上,依据《海洋法公约》第83条第3款似乎可以得出涉事各国有义务相互容让的结论,但实际上国家开发其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并不受此影响——不论该大陆架是否划界;另一方面,一方声索国并不能否决另一方的单边开发行为,除非该行为明显地侵犯了其权利。参见 David M. Ong, Joint Development of Common Offshore Oil and Gas Deposits: "Mere" State Practice o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3, 1999, pp.798-800.其他海域的共同开发问题有待在完成《原则共识》业已确定海域的共同开发安排之后,通过进一步的谈判来落实。最后,日本法人参与春晓油气田的运作,在目前看来并不属于共同开发的一种形式,但在以后的谈判中,双方可以就此协商和探讨,不排除将这种形式纳入共同开发的范围之内。总体说来,只要双方愿意继续谈判和推进共同开发事宜,上述争议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2010年,中日两国启动落实该共识的政府间换文谈判,这是落实两国政府首脑达成共识的具体措施。但有学者指出,即使两国经过谈判取得一定的成绩, 东海问题的全面解决仍很遥远。因为两国针对东海问题的立场与主张严重对立,无法消弭;同时,换文谈判的依据《原则共识》只是一个局部性和过渡性的安排,特别是其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没有界定东海问题的内涵、没有对钓鱼岛列屿问题作出交代),需要补正。*参见金永明:《论东海问题的本质与解决思路》,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甚至有学者认为,中日之间要实现共同开发所面临的挑战绝不比正式划界更加简单,因为这都需要两国决意做出让步。*参见 Gao Jianjun,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China Sea: Not an Easier Challenge than Delimit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23, 2008, p.39.而在此之后,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有关的谈判不仅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而且陷入了停滞。当然,2014年11月中日双方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有可能成为双方新的合作契机。
二、东海共同开发的法律障碍
(一)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争端的由来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目前的现状是:中国一直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认为它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并为此举出诸多历史证据;而日本则依据先占原则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长期实际控制该岛。故而从客观上讲,钓鱼岛属于主权归属存在争议的岛屿。钓鱼岛争端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岛屿的主权归属,另一个是岛屿附带海域以及海洋权益的归属。钓鱼岛争端的焦点,表面上看是岛屿主权,实际上是岛屿所附带海域及其以及海洋权益的划分。
当前的现实是:中日双方既无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意愿亦无解决有关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意愿,或者在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上均无法达成合意。如此一来,争议就只能被搁置,钓鱼岛的法律效力和东海划界均无从谈起。*参见罗国强、叶泉:《争议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法律效力》,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1期。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为了不妨碍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钓鱼岛争议就被搁置(当时还谈不上“共同开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愈发显现,尽管各方曾经一度认为具有独特优点*共同开发既可延缓双方的冲突,又可通过合作开发获得实际的资源利益;不仅有利于维护国际、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增进两国在经贸、科技、知识产权、能源和环保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参见金永明著:《东海问题解决路径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能够缓解钓鱼岛争端,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钓鱼岛争端已经成为实现东海共同开发的桎梏。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为实现钓鱼岛的“国有化”,与钓鱼岛的“拥有者”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岛屿的买卖合同,购买金额为20亿5000万日元。日方“购岛”之举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但日本声称“不接受”中方对“购买钓鱼岛”的抗议,并将如期实施“购岛”后工作。*如果仔细审视本次“购岛”事件的始末,其实不难发现,在整个过程中,日本政府其实是作为一个平等民商事主体,与“岛主”谈判并签订所有权转让合同的。然而,钓鱼岛的主权争议,本质上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公法争议,日本政府不依据有关国际法,积极地与中国政府协商,以求解决或者缓解争议,反而转向作为国内私法主体的所谓“岛主”并与之签订“购岛”合同,显然是一种刻意混淆法律概念,指望通过私权之变动来影响主权之归属的行径。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并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主权归属有争议岛屿的现实状态;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购岛”,确认或者强化对钓鱼岛的“主权”,从法律逻辑上是讲不通过的;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不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参见罗国强:《日本“购岛”之举的国际法效力解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此后中日政府各自就此问题,在包括联合国大会在内的诸多国际场合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两国国内出现了带有民族情绪的群众示威,两国之间多个层面和领域的合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客观上,此次事件打破了长期以来勉强维系着的中日博弈平衡,导致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东海共同开发再度搁浅、《原则共识》成为空谈。
不难发现,在目前的钓鱼岛争端中,双方政治沟通难有结果、经济制裁两败俱伤、军事行动虚张声势,博弈已经陷入僵局,双方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变得很小,若仍旧遵循如此进路则争端难有解决之进展。而且,在日本高调提出以国际法解决争端的背景下,中方仍旧仅仅强调在历史上拥有钓鱼岛主权并频频展示这方面的历史依据,已经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应对这一争端。对此笔者认为,诉诸国际法,乃是解决或者缓解争端最为可行的和有效的途径。
不论中方是希望共同开发、和平划界还是武力解决涉及钓鱼岛的海洋争端,都必须加强在钓鱼岛主权归属和钓鱼岛海洋划界效力等问题上的研究,拿出能够论证本国观点的有力法律根据,再辅之以其他手段的配合,才能在争端解决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如果选择在东海推进共同开发的话,那么钓鱼岛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即便在开发区块设计中可以不涉及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也至少要对钓鱼岛问题有一个(哪怕是暂时的)交代,否则双方根本没有办法坐下来谈判、两国民众也不会支持这样的共同开发进程。
(二)防空识别区问题
防空识别区(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ADIZ),是指从一个国家的陆地或水域表面向上延伸的划定空域,在该空域内,为了国家安全,要求对航空器能立即识别、定位和管制。美国和加拿大先后于1950年和1951年建立防空识别区,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延伸几百海里。凡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必须报告身份,以便地面国识别、定位和管制。*参见[加拿大]伊万.海德:《防空识别区、国际法与邻接空间》,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冷战开始后,为了及早发现前来轰炸的苏联飞机,美国率先设立了防空识别区。虽然后来由于射程远、速度快的导弹的出现,使得防空识别区的战略意义有所减弱,但这一制度对于一国航空安全仍然具有较大意义,故而得以保留下来并不断被改进。美国要求,外国航空器必须随时报告飞行状态及所处位置,并遵守美国制订的有关规则,否则美国将随时要求该航空器离去,并可派军机进行拦截驱逐。*参见赵维田著:《国际航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24 页。目前,美国关于防空识别区的规定是2003 年联邦法规中的《空中飞行和一般操作规则》,其设置的防空识别区包括:毗邻美国防空识别区、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关岛防空识别区和夏威夷防空识别区。*参见李居迁:《防空识别区:剩余权利原则对天空自由的限制》,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尽管对在美国防空识别区航行的他国航空器的主权豁免问题规定较为含糊,但在实践中,美方还是对在其专属经济区上空行使传统飞越权的外国军机的权利给予了尊重。*参见 Peter A. Dutton, Caelum Liberum: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s Outside Sovereign Airspa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3, 2009, p.700.继美国之后,至今已有2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仿效其做法,设置了防空识别区。*具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缅甸、韩国、古巴、芬兰、希腊、冰岛、意大利、日本、利比亚、阿曼、巴拿马、菲律宾、德国、泰国、土耳其、印度、越南、中国台湾等。这其中与东海相关的就包括日本、韩国*韩国防空识别区最早于1951年3月由美国太平洋空军划定,韩国于2013年12月8日对该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定,令其防空识别区得以扩大,区域范围延伸至半岛西南部的中国苏岩礁、马罗岛和红岛上空。和我国台湾地区。
关于设立防空识别区的理论基础,由于此类区域不符合行使自卫权的必要性与相称性之条件,且战时之必要不足以成为在平时维持该区域之理由,*参见 Elizabeth Cuadr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s: Creeping Jurisdiction in the Airspace,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8, No.3, 1977, pp.502-503.故而其依据不是国际法业已确立的、受到严格限定的“自卫权”(right of self-defense),而是某种更为宽泛的、尚未形成国际法规范的“自保权”(right of self-protection/self-preservation);因此若要为该区域的设立寻求切实法律基础,就只能对自卫权作出解释。*参见 Ivan L. Head, ADIZ,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ntiguous Airspace, Alberta Law Review, No.3, 1964, pp.193-196.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只能够是,国家出于“安全的必要”而设定领空附近区域为防空识别区并要求获取飞经该区域的外国航空器的某些信息;该区域设立之本质在于为自卫权的行使提供某种技术信息支持,属于自卫权的间接准备措施而非直接行使措施;国家在该区域的管控实为某种技术信息管控,只有当发现危害国家安全之信息的情况下才能转而采取预警措施,并在本国领土、领海或领空受到侵犯的情况下采取自卫措施。
目前国际社会上没有规制防空识别区的相关法律或国际公约,也没有任何禁止国家建立此种区域的国际法规则。因此, 是否建立防空识别区属于国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除了上述20多个国家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外,许多国家也正在考虑建立这类识别区。*参见张林、张瑞:《建立海上防空识别区的法理依据及其对策》,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一制度可以被称为“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参见 Elizabeth Cuadr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s: Creeping Jurisdiction in the Airspace,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8, No.3, 1977, p.485.
日本于1969年划定了防空识别区。此后日本多次扩大该区域范围,距离海岸线最远处有800千米,覆盖钓鱼岛空域,最西侧距离中国海岸线130千米,涵盖东海大部分空域。日本的防空识别圈主要包括北、中、西、西南四个区块,基本上覆盖了日本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且涵盖了钓鱼岛。北区为北海道和本州部分地区;中区为本州大部、四国部分地区和首都东京地区;西区为本州西部、四国大部分和九州全部;西南区范围较大,呈五边形,包括冲绳、日本西南岛屿、钓鱼岛、甚至我国东海地区。
日本防空识别区涵盖中日争议海域和广阔的国际空域,故而其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6月,日本防卫省宣布,扩大与那国岛上空的防空识别区,把与那国岛西侧的日本领空和其外侧22海里纳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此举导致日方与中国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与那国岛海域上空产生部分重叠。*参见王崇敏、邹立刚:《我国在专属经济区建立防空识别区的探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可见,日本所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存在一个范围过大的问题。日方在东海上空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基本上是沿着东经125 度往南,经北纬30度后,再往北纬25度、东经120 度的方向斜向西南,至东经123 度再折向正南。这一区域离中国最近处,距浙江省的海岸仅约130公里。不但包括钓鱼岛,还跨越日本自己主张的东海中间线,将中国东海油气田全部涵盖其中。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飞机即使在本国沿海和东海专属经济区上空正常飞行,也会被定义为“闯入”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日本防空识别区的西北部更是过分到距离俄罗斯海岸不足50公里。毫无疑问,日本将防空识别区划得如此宽广,甚至深入邻国的专属经济区是极不合适的,中俄等邻国也从来没有承认日本的防空识别区。但日本却利用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形成了很大范围的海空立体巡视空间,进行所谓的“实际管控”,这一过程中也造成与邻国的不少摩擦。*参见李大光:《日本非法扩大“防空识别区”》,载《北京日报》2013 年2月6日。借助防空识别区,在东海海域争端中,即使中国在所谓东海“中间线”以西毫无争议的海域开采“春晓”油气田,也会遭到日本军机的干扰,而中国军机即使在自己沿海及东海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行,也会被定义为闯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受到日本战机骚扰。*参见迟强:《坚决打破日本防空识别区》,载《世界报》2012年11月21日。
为了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土安全,中国国防部根据1997年《国防法》、1995年《民用航空法》和2001年《飞行基本规则》,于2013年11月23日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遵守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并向中方提供飞行计划识别以及无线电识别等识别方式。尽管日本提出了要求中方撤回防空识别区、本国航空公司不服从中方识别要求等无理主张,*参见 Mizuho Aoki, Airlines Urged to Defy China's ADIZ, JAPAN TIMES (Dec. 2, 2013), at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3/12/02/national/airlines-urged-to-defy-chinas-adiz/#.UtNH1vQW0vw.少数美国军方鹰派人物也乘机鼓动美国政府联合其盟友对华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参见 Raul Pedrozo, The Bull in the China Shop: Raising Tens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Vol.90,2014,p.93.然而多数国家均认可了中方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美国政府虽然并不甘愿承认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但也仍然建议本国民航服从中方的识别要求。*参见 U.S. Dep't of State Press Release No. 2013/1498, China's Declared ADIZ--Guidance for U.S. Air Carriers (Nov. 29, 2013), at http:// www.state.gov/r/pa/prs/ps/2013/11/218139.htm.
综上,当前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存在着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多方的划界冲突,而其中又以中日之间的冲突尤为剧烈,这必将直接影响中日在东海进行共同开发的前景。
三、推进东海共同开发的法律建议
当前的东海共同开发因上述法律障碍的存在而搁浅,乃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局面下,如何有效运用国际法,推进东海的共同开发,促进有关争端的缓解以及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做出尝试。
第一,坚持以《原则共识》为基础展开后续谈判,并致力于在后续谈判中达成某些涉及具体权利义务的、至少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平衡和保障双方利益、从而令双方均具备主观执行意愿的共同开发安排。
共同开发政策对南海的适用程度很低,*参见罗国强:《“共同开发”政策在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实际效果:分析与展望》,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而东海海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东海争端涉及的当事方数量较少,而且在相当大的海域内,所涉当事方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国,这就为双边“共同开发”协议的达成和履行提供了较为现实的可能性。其次,东海涉及的争议岛屿较少(主要是钓鱼岛、独岛),尽管当事各方对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颇为敏感,但毕竟只要解决或者暂时搁置这么一两个问题,就可以做出关于“共同开发”的安排;更何况,由于争议岛屿较少,有相当大的海域不会受到此种争议的影响(比如《中日东海原则共识》所列出的共同开发区块就不涉及钓鱼岛),共同开发在这部分海域率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正如有学者在分析有关问题之后所断言的,共同开发是日本可以接受的最现实可行的争端解决方案,是中日接受的解决东海油气争端的最实际可行之策。*参见余民才:《论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共同开发解决方案》,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国际法分析》,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再次,东海争端的焦点不在于那一两个弹丸小岛的归属,而在于其背后隐含着的对于相关大陆架油气资源的争夺。可见,在东海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可行性是相对较大的;如果双方能够充分抓住眼下的这个和解契机,以务实的、*有学者指出,共同开发本身具有“务实性”。参见 Gao Zhiguo, The Legal Concept and Aspects of Joint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Ocean Yearbook, Vol.13, 1998, p.119.还有学者论证说,共同开发协议本质上是由经济目的所驱动的,其具有实用的特点并以有关国家的利益和区块的特点为最根本考量。参见 Vasco Becker-Weinberg,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Deposi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Springer Press, 2014, pp.201-202.诚信的、*以诚信的态度来进行临时安排的协商,乃是一般国际法和《海洋法公约》第300条的要求,;海洋争端当事国有义务以诚信的态度来磋商有关问题以促成共同开发合作的实现——尽管这不意味着必须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参见 David M. Ong, Joint Development of Common Offshore Oil and Gas Deposits: "Mere" State Practice o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3, 1999, p.784, p.798; Masahiro Miyoshi, The Basic Concept of Joint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The Basic Concept of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tunrine and Coastal Law, Vol.3, 1988, p.13.合作的*尽管争端当事国相互合作并同意共同开发争议区域并非一项法律义务,国际习惯法上无此要求;然而从有关国际判例、国际条约与协定、协定的一般构架来看,国际社会具有一致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实践以促成上述目的的趋势。See Ana E. Bastida, Adaeze Ifesi-Okoye, Salim Mahmud, JamesRoss, and Thomas Walde, Cross-Border Unitization and Joint Development Agreements: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Hou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9, 2007, pp.375-420.态度进行磋商,是可以争取达成协议并展开切实合作的。*笔者认为,尽管在初始状态下,国家无论是在条约法还是习惯法上都没有合作实施共同开发的义务;但在中日双方业已达成作为正式共同开发协议准备法律文件的《原则共识》,且该文件规定“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双方将努力为实施上述开发履行各自的国内手续,尽快达成必要的双边协议”的前提下,这种务实、诚信、合作地谈判并力争达成协议,而不恶意地挑起海洋争端、阻碍共同开发协议达成的国际义务性是能够得到确立的。因为,上述规定虽然不甚具体,但其大致方向和思路还是清楚的,那就是双方要真诚合作、力争达成共同开发协议,至少对于那些明显恶意破坏和阻碍共同开发谈判的行为,还是可以有一个是非曲直的判断的。有学者指出未来的谈判要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是否将其他东海争议区域纳入共同开发范围、共同开发协议的具体条款(共同开发的模式、收益、税收、争端解决、安全、环保、卫生健康)以及两国国内法的衔接问题。*参见 Suk Kyoon Kim, China and Japan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 Note on Recent Developments,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43, No.3, 2012, pp.301-302.笔者认为,未来东海共同开发区的制度设计不宜再模仿广受诟病且滴油未出的日韩共同开发协定,而应借鉴南海泰国湾地区运行良好的“马来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共同开发案的制度设计,在共同开发区的管理机构与模式、合同制度、费用分摊与收益分享机制、管辖权及其冲突之解决、争端解决方式等法律制度层面*参见罗国强、郭薇:《南海共同开发案例研究》,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做好规划与谈判工作。但归根结底,不论具体的制度如何设计,最需要关注的是,双方在未来的共同开发协议中均有利可图、均具备达成协议并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行协议的主观意愿。*迄今为止各国在执行共同开发协议方面并不一致,且基本上都是出于合作的意愿而非迫于义务去执行协议。参见 Vasco Becker-Weinberg,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Deposi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Springer Press, 2014, pp.201-202.这说明,不能给予当事国足够主观动力的共同开发协议是没有执行保障的。有了这个前提,其他一切程序与实体内容都好谈。
第二,阐明中方对于钓鱼岛的主权立场,同时确认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主张钓鱼岛在海洋划界中享有零效力,争取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并在有关共同开发安排中忽略钓鱼岛的法律效力。
在2014年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中,采用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的说法,这相对于此前日方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是进了一步。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提法首次仅使用中方惯用的“钓鱼岛”而不同时使用日方惯用的“尖阁列屿”来表述,更为关键的是其点出了争端的状态——尽管用词仍是比较含糊其辞的。中方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日方明确而清楚地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存在。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确认,将直接影响到钓鱼岛在海洋划界中的法律效力——因为若在不明确主权归属的情况下对争议岛屿所涉及的海域进行划界,则岛屿只能被赋予零效力。*参见罗国强、叶泉:《争议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法律效力》,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1期。而若是钓鱼岛对于中日海洋划界没有影响的话,那么对于该岛的主权争议也势必降温;更为重要的是,日方通过钓鱼岛而将其大陆架“中间线”西移的想法就将必然落空。尽管确实有学者主张钓鱼岛应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为此将这一弹丸之地描述成“富含资源、有饮用水和永久性设施、有人口居住”,*参见 Marika Vilisaar, Sino-Japanese Maritime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cta Societatis Martensis, Vol.4, 2010, p.249.然而这种状态不过是日方强行派军驻守的非自然产物,其对《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所列岛屿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条件——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符合性存在很大疑问。就公约的本意和该区域的实际情况而言,赋予钓鱼岛零效力,不仅更符合实际而且也是诸多学者的共识。综合钓鱼列岛的法律地位、地理位置及面积,再结合国际划界实践,在中日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中赋予其零效力为宜。*参见王可菊:《钓鱼岛及其在东海划界中的地位》,载《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6年第1期。中日双方越不坚持钓鱼岛是海洋划界所必不可少的,就越有可能解决复杂的大陆架划界争端。*参见 Wei-chin Lee, Troubles under Water: Sino-Japanese Conflict of Sovereignty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in the East China Sea,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18, 1987, p.598.
第三,坚持本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同时阐明防空识别区的法律性质,指出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防空识别区存在重叠乃是正常现象,其不应妨碍海上共同开发的谈判与进行。
本质上讲,防空识别区不等于领空,国家只是为了安全与方便计,才划设这样的一片区域并进行技术上的必要识别。早在防空识别区出现伊始,就有学者指出国家只能是出于防卫目的而实施有限的管控,各国仍然应当竭尽全力维护该区域的飞越自由。*参见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s: Are They an Extension of Territorial Limits of a State? New York Law Forum, Vol.4, 1958, p.369.飞越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只是承担某种提交识别信息的任务,并不受防空识别区设定国的管辖;设定防空识别区的国家,也只是有权要求飞越的航空器提供识别信息并在信息异常情况下采取预警措施——切实的防卫措施应仅在本国领土、领海或领空内采取,而无权对整个区域实施管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防空识别区主要体现了某种技术和信息需要,而不直接体现主权或者管辖权;防空识别区不存在先占、独占或者优先权的问题,不是说某国率先设立了防空识别区该区域就不能再由其他国家设为防空识别区并正常使用。既然是技术和信息领域,那么邻近国家之间在设置运用技术、获取信息的区域方面存在重叠,应属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将其拔高到国际争端的高度、甚至影响海上共同开发的谈判与推行,有关国家完全可以在同一区域内各自运用相应的合法手段采集技术信息而互不干扰。实际上,在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以前,东海上空已经有日本和韩国划设了防空识别区,两国所划区域也存在重叠,但这并不影响两国于1974年达成在东海部分区域实施共同开发的协议。*《关于共同开发邻近两国南部大陆架的协定》明确该共同开发区域位于北纬28°36′至北纬32°57′、东经125°55′5″至东经129°9′之间,面积24092平方海里。但是该区域的划定没有顾及中国的立场,故而存在明显的法律缺陷,并且由于该区域无商业性油气流,故而协定无法实施。参见朱凤岚:《“日韩大陆架划界协定”及其对东海划界的启示》,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11期。可见从国际实践上看,防空识别区划设的重叠问题,并不必然会成为共同开发谈判的障碍。中方可以在主张本国划定防空识别区的权利、提出日方所划防空识别区范围过大的同时,表示上述问题不会妨碍关于东海共同开发问题的谈判,并就进一步的谈判做好准备。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The Sino-Japanese Principle Consensus of East China Sea and Joint Development in East China Sea——with respect to Issues of Diaoyu Islands and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uthor & unit:LUO Guoqiang(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The four principle consensu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asts new light on the joint development in East China Sea. The 2008 Sino-Japanese Principle Consensus of East China Sea does not amount to a binding agreement, and possess certain defaults in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al matters. The issues of Diaoyu Islands and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re the shackles of joint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continue negotiation based on the 2008 Consensus and make affords to achieve a binding arrangement with detailed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 confirm the sovereignty-disputed situation of Diaoyu Islands and suggest ignoring its legal effects in joint development arrangement; to clarify the legal nature of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nd point out that the overlapping of such claimants shall not hinder the joint development.
east China sea dispue; joint development; diaoyu island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2014-11-26
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重大项目《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案例与实践研究》(13JZD039)、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东海南海的岛屿主权与海洋划界争端中的国际法问题》(13JJD820008)的部分成果。
罗国强(1977-),男,四川成都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协同中心”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
D99
A
1009-8003(2015)01-00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