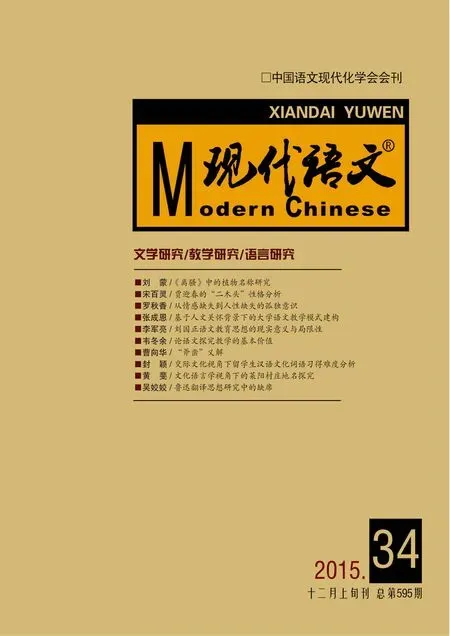《涅朵奇卡》的主题及形象分析
○魏超群
《涅朵奇卡》的主题及形象分析
○魏超群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涅朵奇卡》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这部著作不但对人类心理意识领域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是对陀氏颠倒而又对称的美学世界淋漓尽致的展示。文章将从作品的主题及人物形象入手,探索其独特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自我他者儿童成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坛璀璨群星中最明亮的之一。陀氏的艺术世界怪异又真实、陌生却熟悉、遥远但发生在人的内心。他笔下的幻想家系列不仅是对精神变态者的深入探索,更剖开看似正常人的虚伪表象,展示人类普遍存在的病态心理。
《涅朵奇卡》是陀氏的早期作品,于1849年以——“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一个女人的遭遇”为题,发表在《祖国纪事》上。全书分为三部分:“童年”“新生活”和“秘密”。作家用时两年写成前半部分,后因被捕和流放而没有完成。在1860年作家自编选集时对原稿做了大量修改,改成了现在出版的样子。
《涅朵奇卡》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陀氏研究者的评论专著或俄国文学史对其都鲜有提及。多数研究者只是在研讨陀氏笔下的儿童形象时,才对其略有涉及,或是单纯把它归于作家的幻想家形象家族里的一名普通成员,更有俄罗斯评论家只拘泥于批评作品的文字和形式。Л.В.布朗特认为小说的第一部分中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叶菲莫夫的行为毫不引人入胜,叙述单调,独白太多,烦人的说教也不少。[1]
然而,《涅朵奇卡》是陀氏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未完的长篇小说中酝酿着诸多作家的重要创作主题和思想,除儿童问题和幻想家主题外,还包括:女性生存权利的主题、艺术家形象、“双重人格”的主题、“偶合家庭”主题、“罪与罚”的主题、“根基派”思想等。小说中未尽的构思和人物形象也出现在后续的作品中,如小说第三部分里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可以说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瓦尔科夫斯基的雏形。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在《绿毛水怪》里写道:“我看了这本书,并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分。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2]
一、自我与他者
小说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的是涅朵奇卡的继父叶菲莫夫的故事。他原本是地主私人乐队的单簧管乐师,因为有着惊人的音乐天赋而自命不凡,梦想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然而,过分的自负使他疏于练习、荒废业务,过起了酗酒放纵,消磨才华和意志的浪荡生活。为了得到千把卢布的嫁妆,他娶了涅朵奇卡的母亲,并将自己的失意归咎于琐碎的家庭生活。当成为音乐家的幻梦彻底破灭时,他杀了妻子,自己死于精神错乱。
艺术家形象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主题,同时,叶菲莫夫也是陀氏早期幻想家形象的继承者。在《同貌人》(1847)中就曾出现过精神分裂的小官员戈里亚德金,他在幻觉中看到了自己的化身——小戈里亚德金。如果说在《同貌人》中,只有戈里亚德金是真实存在的,而化身小戈里亚德金只是他的幻想,那么《涅朵奇卡》中的叶菲莫夫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个荒诞的存在。
首先,叶菲莫夫在自我认知上与他者发生了倒置,但就是这样一个镜像中虚构出的他者形象让叶菲莫夫如痴如醉,正如拉康学说中阐释的那样:“人们在这种自己成为自己的最初场面中抱定了这种自相矛盾的想法,即在他者中生存,在他者中体验自我。”[3]。叶菲莫夫欣喜若狂地认同了这一给予他肯定情感的他者形象,但同时也遭到了他者形象的控制和支配。著名小提琴手无须像初学者那样做过多练习,于是,叶菲莫夫傲慢放纵,不愿参加供人娱乐的商业演出,也不甘心在乐队里当个小小的演奏者。最终在真正的小提琴家C来到当地举办音乐会的时候,伪音乐家叶菲莫夫无处遁形,其虚假身份在曝光的真相中骤然萎缩,走向消亡。
二、儿童与成人
在俄国社会发生剧变的动荡时代,当资本主义蔓延,传统的宗法制伦理道德基础受到了威胁时,社会大团体的变迁引起了作为社会小单位的家庭的变化,这也正是陀氏创作的另一重要主题——“偶合家庭”。叶菲莫夫便是存在于偶合家庭中的一个伪父亲形象。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与孩子的角色倒置,他并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鄙视商业演出和乐队的职务,整天无所事事、分文不获。实际上,他像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那样完全靠妻子养活自己。然而,他却认为正是妻子阻碍了他艺术道路的发展,正是穷苦琐屑的生活磨平了他的音乐天赋。于是,他要消除那个牵绊着他的障碍,杀了妻子便会成为像小提琴家C那样的音乐大师。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伪父亲,涅朵奇卡却爱得异常热烈,甚至胜于爱自己的母亲。“我觉得父亲总是那样可怜,那样受欺凌、遭践踏、吃苦头,以致在我看来,如果不发疯地爱他,不安慰他,不跟他亲热,千方百计为他着想,那简直是可怕的,不近人情的事情。”[1]涅朵奇卡具有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她甚至觉得母亲是阻挡她和父亲幸福的绊脚石。她幻想着母亲死后,他们就会变成富人,父亲会带着她到那栋“挂红色帷幕的豪华楼房”里去。于涅朵奇卡而言,她也没有安守自己女儿的角色,她对母亲的感情极为复杂,对她充满了嫉妒、恐惧和憎恨。为了获得父亲的爱,她就必须与母亲敌对起来,以取代其妻子的地位。
在《涅朵奇卡》中,母亲就是维系叶菲莫夫和涅朵奇卡的存在基础,她供养他们,是他们生存的根基。然而,母亲却成了所有阻碍的象征,所有人都要铲除她、毁灭她。事实上,母亲的死亡没有给叶菲莫夫他想要的自由,没有给涅朵奇卡渴望的幸福,相反,失去了母亲这一俄罗斯大地一样的根基,他们注定是要走向灭亡的。在“根基派”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根基”就是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生命价值,国家的发展方向最终要回归到“俄罗斯精神”的“根基“上来。
在《涅朵奇卡》中陀氏构建了一个颠倒的、却极具对称美的世界,其间充满着折回、重叠,却又疏离、互相厮杀。主人公们迷失在庄生晓梦的美丽世界,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梦幻,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相互消融了,叶菲莫夫和涅朵奇卡仿佛都在追求一种极致,那是一处被挂满的红色幔帐遮挡着了真相的楼宇,他们活在自己向往的那个极致里,抹去了通往它的道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原则不能让人满足,好像在玩折纸游戏一样,为了使现实和梦幻之间的距离无限缩短,他们将谱写命运的白纸对折,使两点重合起来,把三维空间变成二维。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涅朵奇卡被X公爵收留并开始新生活的故事。在陌生又新奇的环境里,涅朵奇卡结识了公爵的女儿——小郡主卡佳并陷入了对她的疯狂热恋。小说中,涅朵奇卡几次发生精神性惊厥,她不断地晕厥、苏醒,穿梭于现实和幻梦之间。在继父杀了母亲逃跑后,涅朵奇卡又一次晕倒,当她醒来后看到了X公爵。他正直善良、生活富裕而且无拘无束,满足了她对父亲的全部幻想。公爵告诉涅朵奇卡,他还有一个跟她一般大的女儿,不久就会从莫斯科回来,于是,她那遥远的、模糊的、不可言说的幻梦开始与现实发生重叠,公爵府就是那栋挂满帷幔的房子,X公爵就是父亲,他的郡主女儿就是自己。当她再一次晕倒醒来,那个早已经勾勒好的完美的自我形象就出现了,“当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一个孩子——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俯视着我,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她伸出双手”[1]。涅朵奇卡迫不及待地走向那个全新的自我,她疯狂地爱着小郡主,那个美丽、活泼、人人喜爱的形象。“我”总是想吻吻她,甚至在夜里醒来时会偷偷来到她的床边吻她的手、肩膀、头发甚至是脚。涅朵奇卡对小郡主的爱更像是一种自恋,亲吻是她与小郡主融合的标志。当两个人互相吐露心曲时“我们的嘴唇都吻肿了”“我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4]。
“人们从童年步入成年,就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蒙昧走向文明,并且形成相对稳定的思想、性格、气质。这个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吸收知识、积蓄经验、从单纯走向复杂的获取过程;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逆向过程,即抛弃、失落、退化的过程。”在陀氏的创作中,这种将成人与儿童倒置的意图是明显的,人没有按照自然成长过程去发展,相反,作家将成人和儿童放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进行对比考察,竟发现相对于成人而言,有些儿童要更加成熟,更加包容。
成人叶菲莫夫和儿童涅朵奇卡对自我的完整性的理解完全不同,叶菲莫夫的终极世界是孤立的、割断与他人的联系的、绝对自我的世界。而涅朵奇卡更多的是寻求与他人的联结和融合。前者越是追求自由孤立,对他人的依赖感反而越强烈,当他失去妻子后随即精神崩溃而亡;后者虽寻求与他者的联系,但精神主体变得更加自信和强大,敢于挺身而出保护他人。
人不只是在镜子面前认识自我,更多的是从他者中反观自我,前者在自己的狭隘世界中迷失,后者在荒芜中开辟自己独立的世界,两者虽有相同的目标,却达到相反的结果。
三、罪恶与清白
在第三部分中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涅朵奇卡的养母,也就是“秘密”的主人——亚历山大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与卡佳分别后,涅朵奇卡被卡佳的姐姐收养,她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封亚历山大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情人写给她的告别信。信中显示她曾爱上过丈夫以外的其他人,并且这件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因为有罪,她对丈夫有着近乎崇拜的爱恋,完全依附于他,屈从于他,而他则保持着自己绝对的威严和优势。在《新约·约翰福音》中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试探耶稣,抓住他的把柄,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的回答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人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5]米哈依洛芙娜犯了罪,她承受着自己良心的折磨和丈夫无言的审判,在这段似曾相识的父亲、母亲、女儿的三人结构中,涅朵奇卡不再妄想代替女主人妻子和母亲的位置,相反地,她同情这个可怜的女人,鄙视她丈夫以蹂躏她感情的方式报复她。米哈依洛芙娜有罪,但是在涅朵奇卡眼中却是纯洁无比的。戏谑的是,涅朵奇卡的清白却被米哈依洛芙娜随意揣测、践踏。她怀疑涅朵奇卡与自己的丈夫有染,怀疑敢拿清白保护自己的这个女孩儿并开始对她忽冷忽热。
涅朵奇卡的纯洁之心受到继父的无视,遭到米哈依洛芙娜的怀疑,唯有在敢于坦诚自己的自私和过错的卡佳那里得到了真诚的回报,成人习惯于用清高和无辜来掩藏内心的肮脏,正如他们的身份一样:继父、养母、养父,与儿童的真诚比起来,他们不过是虚伪的代名词。
四、结语
在研究陀氏的成果中鲜有对其美学的分析,在其看似平铺直述的叙事下隐藏的是颠乱倒错的内部关系,像是精神错乱病人的呓语,而在乱码的逻辑当中却是极具对称美的深层结构。当然,这种结构与内容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涅朵奇卡》所建构的是一幅倒置的混乱世界,仿佛有一面巨大的镜子树立在人物的面前,他们活在当下,却观察着镜中的影像,迷失在疼痛感消失的幻梦中。
注释:
[1]陈燊:《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王小波:《绿毛水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3]王小峰等译,[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4]徐葆耕:《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魏玉奇:《圣经新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魏超群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院1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