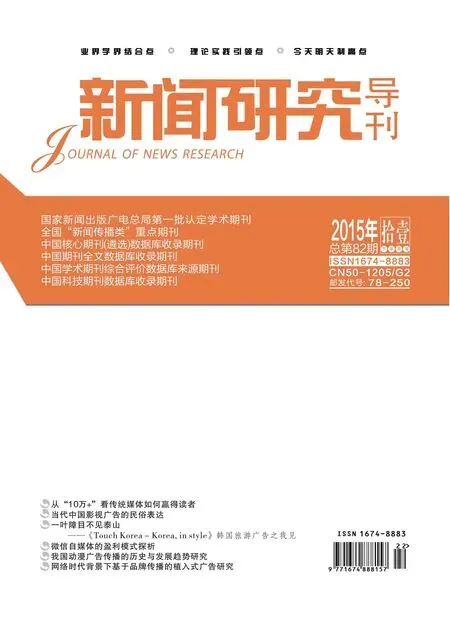浅析美国公共新闻运动中的受众观
胡晓静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浅析美国公共新闻运动中的受众观
胡晓静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公共新闻运动给美国新闻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新闻改革运动里,美国新闻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受众观:它要求受众参与到新闻活动中,并鼓励受众提出以及解决自己的问题。时至今日,这样的受众观对于当代媒体的改革创新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公共新闻运动;受众观;议程设置
“公共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场新闻改革运动。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对于“公共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讨论成为了美国新闻界一大热点话题,被著名新闻学学者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誉为是一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内部社会活动”。如今,随着新闻理念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进步,公共新闻理论曾经的地位虽不复存在,但其中关于“社会”和“公众”的革命性理念,在今天依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其中就包括了公共新闻的受众观。
一、公共新闻运动
“公共新闻”理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公共新闻学最早的基本观点被认为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中倡议,将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纳入新闻界自身的责任,也能从中看到与公共新闻学思想的相似之处。
1988年是公共新闻活动实践的重要年份。它的第一次实践由美国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纪事问讯报》(Ledger-Enquirer)发起:通过系列稿件《展望千禧年之后的哥伦布市》及随后该报主编组织的市政会议,即让市民与官员、专家一起讨论了该市现有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1]这次尝试第一次让原本仅停留在报纸上的议题跻身于公众中间。同年,在媒体关于美国大选的报道中,呈现出对于候选人个人的关注超过公众利益的倾向,这个现象吸引了之后公共新闻事业的创始人——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Wichita Eagle)主编梅里特(David Merritt)和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罗森(Jay Rosen)的关注。
罗森为公共新闻内容下了这样的定义,即,公共新闻事业有四点基本价值:第一,视人们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第二,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了解问题。第三,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第四,帮助改善公共生活。所以,除了日常报道公众所面临的问题之外,公共新闻的倡导者还呼吁新闻工作者通过组织市民会议,建立新的公共空间,在那里为普通公众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新闻工作者应该更关注市民协商的过程,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二、公共新闻中的受众
大众传播理论进步的一个表现在于受众观的改变。受众从一开始被视作被动、无条件地接受媒介的所有消息的对象,到有了自己的能力甄别、解读和选择信息;从之前单纯地被告知,到自主地发出反馈;从被当作一个同质整体的传播对象,成为了有自我特征的“个体”。在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受众的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现代的媒介也就不能再只是单纯的报道新闻,而是要更加关注受众的需求。践行公共新闻理念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所以,公共新闻学的受众观更加突显了受众的自主性。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重视公众参与讨论及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认为新闻的作用仅是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真正的决策者是公众自己。在此,公众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新闻改变了传统的议程设置方向。“议程设置功能”最早见于美国学者M.E.麦库姆斯和D.L肖1972年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2]媒介的“议程设置”是指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升某个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如果某个问题能引起大众媒介的关注,那么它在公众心中的重要性也会得到提升。传统的议程设置方向是自上而下的,一般由媒介充当报道新闻的“把关人”,给受众设置议程,告诉受众应该关注什么。而在公共新闻事业中,由谁来设置议程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以美国公共新闻的实践先驱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为例,它在报道1990年地方选举的时候,采取了特别的议程设置方式:通过民意测验(如电话调查),筛选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然后再进行深度报道,以促成公众对于特定问题进行讨论。[1]以《威奇托鹰报》为代表的践行公共新闻理念的媒体的议程设置是分为两个步骤的:首先,公众为媒体设置议程。媒体通过调查公众关心什么话题,来决定深度报道的对象。其次,媒体再通过自己的报道为公众建立议题。来让公众进一步讨论,并引导公众在讨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媒体在公众身上所实现的传播效果,通常被界定为是认知层面上的,但在图示的第二个步骤中,媒体希望能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到的是公众的态度,甚至是行动。同时,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也深受公众意见的影响。可以看到,践行公共新闻的媒体不但再现了自身议程设置的完整过程,还使公众成为了议程设置的一个主体。但在这个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无论对于谁应该成为议程设置者还是如何选择话题的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通过少数公众所反映的问题是否能代表占更大多数的公众群体?从受众角度来看,他们作为单独个体提出的问题,并不一定符合在公共新闻理念中一再被强调的“协商公众”的理念。而且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只依靠公众为媒体设置议程,他们就失去了一定的工作自主性,这就违背了工作者接受专业知识培训的初衷。
(2)公共新闻旨在培养更加主动的受众界。在公共新闻运动之前,美国新闻业经历了另外几次重要的改革。例如,以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为标志提出的“社会责任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一些新闻工作者希望通过改变报道形式来吸引读者而发起的“新新闻主义”尝试。纵观这些改革,无一例外是新闻界探索如何与受众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尝试。随着传播学理论的发展,作为媒体受众的大众,不再只是单向的信息接收者,媒体更希望看到他们对信息的反馈。通常情况下,媒体基于经济利益和媒介质量的考虑,都以输出优良产品,赢得更多受众为目标和运营方针。这一点造成了公共新闻理念提出之前的美国新闻界的困境:新闻界庸俗化、娱乐化倾向严重;新闻内容煽情化造成了民众的不满,民众对政治活动也缺少热情,而他们所关心的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媒介又报道甚少。实践公共新闻学的媒体希望通过报道让公众参与其中,来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主动性。公共新闻运动中的几次尝试,如《纪事问询报》《威奇托鹰报》以及《威斯康星州报》(Wisconsin State Journal)“我们的人民”(“We the People”)计划等,它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让民众自己提出问题,还鼓励民众自我解决问题而非依赖专家学者的建议。所以,无论这些报道在当时的反响如何,都为整个公共新闻运动和美国新闻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实践让参与公共决策的公众更加充分地利用了媒介所提供的资源和机会,来完善自身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使公众的媒介素养得到了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媒介的自我进步。在这场运动中,受众的角色从之前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转变成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者,而这正是罗森在定义公共新闻时所倡导的:视人们为公民和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
三、启示与展望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定义为“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公民可以不受干涉地自由讨论。可以看出,公共新闻实践的目标也是为公众建立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因此公共新闻的倡导者十分推崇“协商公众”的理念,要求新闻工作者听到来自公众的声音而不再仅为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服务。
可是,公众通过共同协商提出的问题,是否就能代表全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哈贝马斯定义的公众是拥有普遍利益、具有自愿性,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但“公众”不能等同于“每个人”。社会是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及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它具有多样性和高度异质性的特征。拥有“普遍利益”的公众不等于全社会,如果过度地寻求解决“普遍利益”,就极有可能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根据社会学家帕克(R.E.Park)的理论,应该将拥有“普遍利益”的公众活动空间合理地归结为“社区”而不是“社会”。帕克认为,社区的特征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当中。[3]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常常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实践活动。虽然也不乏大型媒体进行尝试,但据统计,美国75%的公共新闻运动都是由日发行量二十五万份或不足二十五万份的小型新闻媒体展开的。[4]小型的新闻媒体覆盖的受众面更小,代表的利益更多样,更容易参与新闻实践活动。
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注定了公共新闻运动无法在极大的范围内展开,公共新闻运动的影响力也在十余年之后逐渐消弱。在电子媒介的产生以及传统社区衰退的背景之下,公共新闻理论的实践注定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今的世界媒介高度发展,传媒手段更加多样化,受众也拥有更多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媒体进行反馈。这时,需要媒体引领受众对繁杂的信息进行筛选,新闻界充当“把关人”,“告知”和“教化”公众的功能变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公众更容易表达意见,甚至打破地理限制,在更大的环境中进行讨论,让公众更加积极主动地争取发言权。网络创造了新的“社区”,空间流动性更大,受众参与更加便捷,同时受众也被进一步细分成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小群体,能对所选择的公共事务投入更多的关注。网络时代为发展公共新闻学创建了更好的条件,它所拥有的特质,能够将公共新闻践行者培养参与公众、复兴公共生活的目标变为现实。因此,如今的公共新闻实践应该有如下几个变化:第一,将目标受众集中于拥有共同利益的少数群体,让公共新闻媒介成为他们发声、争取利益的渠道。第二,将公共新闻开展的场合从纸媒转向网络媒体,以及时得到反馈,并开展更广泛的讨论。第三,将重点放在培养公众的媒介素质方面,在其中充分地发挥自己议程设置方式的优势。
四、结语
社会学理论表明,社会信念和判断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它影响人们的感知和行动,促使人们通过行动改变现实。[5]所以,即使过去的数十年中,对于公共新闻实践、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建立怎样的媒介和怎样的社区始终充满争议,但无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受众本身,对于公共新闻保持着自身的信念,能帮助新闻工作者建立以受众为中心的报道观念,受众也在参与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中,解决自身的问题,得到自我的提升,这样的实践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1] 西奥多·格拉斯(美).公共新闻事业的概念[M].曹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3,17.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4.
[3]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07.
[4] L.弗里德兰,S.尼克尔斯.公共新闻运动进程探究:十年发展报告[R].华盛顿特区:皮尤公共新闻中心,2002.
[5] 戴维·迈尔斯(美).社会心理学(第8版)[M].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89.
G210
A
1674-8883(2015)22-0162-02
胡晓静,贵州大学新闻学(新闻社会学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