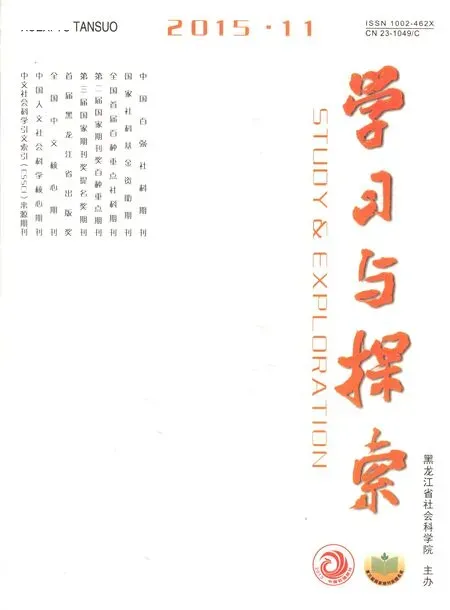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文学传统
袁 琳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2.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武汉 430070)
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文学传统
袁 琳1,2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2.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武汉 430070)
“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尽管带有强烈的政治文化特征,但其丰富复杂的存在蕴含着多重阐释的空间。这种丰富复杂的存在其实与滋养它的多种文学资源息息相关,美颂和怨刺传统为政治抒情诗创造了两种对立的抒情范式;左翼革命传统让政治抒情诗将视野投向底层民众,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体现强烈的人文关怀;自由传统为政治抒情诗注入建构诗歌精神的营养,诗人主体性意识的介入避免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
“十七年”;政治抒情诗;文学传统
政治抒情诗作为诗歌形态的一种,是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资源滋养、孕育的结果,并非“十七年”特定时期的产物。古代文学的文学传统为政治抒情诗创造了两种相对立的抒情范式——美颂和怨刺;左翼文学的革命传统为政治抒情诗确立了抒情主人公,他必须是战斗的、有阶级立场的;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为政治抒情诗注入了自由的精神,不论是诗歌形式的创造还是诗歌精神的建构,都需要诗人主体独立意识的参与。
一、古代文学的美颂和怨刺传统
所谓美颂传统就是用诗文歌功颂德的文学传统,即歌颂本民族的神灵、君主、民族英雄,以彰显其美德;用华美的语言赞扬祖国的山川河流,以展现其壮丽。而怨刺传统是指用诗文讽喻批判的文学传统,即讽喻现实政治生活,批判时政和君侯将相,抒发抑郁不平之气。中国古典文论也相应发展了“美颂说”和“怨刺说”,强调美颂之声的教化作用,而怨刺之声多用来讽谏君主,以帮助君主行仁政。怨不仅仅是指政治怨刺即“怨刺上政”,还可指向更广泛的内涵,正如黄宗羲《南雷文定》所言:“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谴责、讽喻皆是也。”[1]
《诗经》中《周颂》的产生标志着美颂文学传统的诞生。例如,《周颂·绵》是一首表现周民祖先古公亶父丰功伟绩的颂诗,全诗按照时间顺序绘制了周族的发展历史,生动呈现了古代周民的生活画面。《大雅·文王》通篇用“赋”的手法歌颂周文王受命于天建立周朝的功绩,叙述商周兴亡更替的道理,告诫后世君王要效法周文王,实施仁政。这些美颂作品不单纯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更是让后世见证祖先披荆斩棘开创基业的崇高伟大,激发子孙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需要这种美颂文学的存在,它们成为表现昂扬向上的情感基调和自信团结的民族精神之艺术载体。此后,屈原的《九歌》也延续了美颂传统,颂扬天界的神灵;西汉的大赋用铺陈夸饰的语言描绘大汉朝的辽阔无边、周武王的神威天下。当时有名的汉赋大家扬雄曾以“劝百讽一”[2]评价汉赋的功用,认为“劝”者,歌颂之谓也。汉赋的创作倾向、主流精神、表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之颂歌的写作。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子虚赋》,艺术地展现了汉朝盛世景象,塑造了一个既懂得享乐、又勤政爱民的英明君主形象。司马相如之所以铺陈渲染上林田猎的壮观,其终极目的是表达诗人止诸侯之争、扬天子之威、明“大一统”之义、存兴而戒亡的政治诉求[3]。之后东汉的班固撰写的《两都赋》等深深地烙上了政治文化的印记。而“十七年”时期的颂歌也是如此,将歌颂盛世和革命偶像作为主要的创作主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批颂歌应运而生。例如,郭沫若激动地写下《新华颂》,歌颂新政权的诞生。何其芳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回顾了犹如黑夜一般的苦难岁月,无数烈士在鲜血淋漓、布满荆棘的征途中英勇奋战,终于推翻了“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迎来了“东方巨人”的诞生。无数群众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庆祝这个最伟大的节日,他们欢呼、雀跃、歌唱,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始新的征程。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胡风的《欢乐颂》(《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等以歌颂新中国、歌颂革命领袖毛主席为主题,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政治文化气象。
“怨刺”传统即现实批判的文化精神,构成了“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另一个向度,也深深影响了“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怨刺”文学传统也起源于《诗经》,《诗经》中共有103篇怨刺诗,代表性作品有《大雅·荡》《小雅·节南山》《王风·黍离》《唐风·鸨羽》《豳风·鸱鸮》《召南·羔羊》等。这些诗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对社会生活的认知与感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政治生活的本质。如《大雅·荡》再现了周王朝民怨沸腾、国势将倾的局面,讽刺周厉王暴虐、荒淫、昏聩的行迹,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忧虑之情。全诗借古讽今,以周文王的口吻写对殷纣的慨叹,来隐喻对现实的讽喻。《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而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4]该诗则是周朝大臣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表现了主人公忧国忧民、直言敢谏的精神。
《诗经》的“怨刺诗”蕴含的“篇诫规谏”精神和讽刺批判精神[5],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的《离骚》继承其志,发愤抒情,针砭时弊,抨击佞臣祸国,劝诫国君,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建安诗人关注民生,致力于反映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抒发诗人在乱世的痛苦感受,表现出重建开明、安定、统一社会的政治理想。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等诗人的政治诗赋运用比兴手法、影射手法等,曲折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讽喻时政,这种“假托影射”的手法在李商隐的咏史诗中也运用娴熟。唐朝的杜甫和白居易等继承了“怨刺诗”干预社会政治的创作精神,揭露批判政治的腐败。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又从杜甫、白居易传到南宋爱国词人,一直到清初遗民诗人,代代相传、不绝如缕。
尽管“十七年”时期政治、思想和审美高度一体化,强调诗人们作为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必须严格按照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规范进行诗歌生产,但还是有一些诗人秉承现实批判精神,创作出具有“怨刺”意味的政治抒情诗,如沙鸥、邵燕翔、公木、王志杰、穆旦、蔡其矫等。1950年8月,沙鸥看到作家楼适夷的小孩因华北人民医院的误诊致死的报道,愤而写下童话诗《驴大夫》,该诗发表在《大众诗歌》第九期,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官僚主义作风对革命工作的危害”(沙鸥语)[6]431。这首诗发表后遭到段星灿的猛烈批评,认为沙鸥把新中国写得太黑暗和阴冷,“政策观点错乱”“立场不稳”[6]428,并且最终导致《大众诗歌》在出完十二期后被迫停刊。邵燕翔的《贾桂香》、公木的《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王志杰的《给沉浸在会议里的人们》、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等诗作不回避社会现实的阴暗面,指斥政府“文山会海”的弊端和官僚主义作风,对个体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注。1957年底,蔡其矫在考察汉江流域时,直面苦难的社会现实,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勇敢地唱出《雾中的汉水》与《川江号子》,表达对社会冷峻的思考。“文革”结束后,一些被政治放逐归来的诗人重返诗坛,如艾青、流沙河、白桦、公刘、邵燕翔等,他们通过饱经沧桑的“个人自白”,深刻反思历史,表达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守。
二、左翼文学的革命传统
中国的左翼文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浪潮的洗礼中诞生的,苏联的“拉普”、日本左倾的福本主义思想与“纳普”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翼文学倡导的“革命文学”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乃至武器,认为作家应该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去,表现民族或阶级情感。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左翼文学的先声,它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被视为“无产阶级的五四”[7]。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先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文化批判和价值重估,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文学:“文学为与有产者对立起来的革命文学”,并且革命文学“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文学形式应该是“讽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8];成仿吾则认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现阶段必须完成“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历史转变,要求知识分子“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迈步走向工农大众、表现工农大众的社会生活[9]。尽管左翼文学在批判和清算五四文学革命方面有失偏颇,但它所秉承的革命传统却值得褒奖,为当代的政治抒情诗创造了新的抒情主体——群体的“我们”,以抒发激愤、战斗的情绪为主要内容。
这种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普罗诗歌就是在这种文学潮流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红色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郭沫若、蒋光慈、殷夫等。他们自觉地为无产阶级代言,关注普通大众的不幸,鼓舞受欺压的人民起来抗争。郭沫若在《上海的清晨》[10]中描绘了一幅劳苦大众的生活图景:“赤着脚、蓬着头”的“我”徒步在马道旁的树荫下,上班的男女工人们脚步飞快,“伸手求食的乞儿们”在路旁踟蹰,我们相互紧握双手,互相激励。同时诗人无法抑制心头的愤懑,用激烈的语言声讨富人的罪恶:坐汽车的富人们在道路中间疾驰,而这条道路不知道榨取了多少劳苦人的血汗与生命。最后诗人相信穷苦人一定会喷射出反抗的火焰,反抗这罪恶的世界。蒋光慈《新梦》诗集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热烈礼赞了大时代的革命斗争。殷夫的诗歌饱含激情,《血字》[11]595-596是其政治抒情诗的佼佼者,这首诗是为纪念“五卅”惨案而作,诗人追忆了“五卅”惨案血淋淋的经过,耳边是“千万声的高呼”、双目所触及的是“斜斜地躺在南京路”上的烈士尸体,还有那“狞笑”着的“叛徒”。接着诗人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呼吁这一庄严伟大的“五卅”精神能像巨人一般地“立起来,在南京路走”!最后,诗人以坚定的语调预言,我们的革命必将胜利。整首诗洋溢着豪迈的革命激情,带有鲜明的反帝反封色彩。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强调要表达“一种群体的意识与呼声”,要表现出反映时代本质的、独特崇高的情绪[11]52。穆木天创作的《我们的诗》旗帜鲜明地道出中国诗歌会诗人们的心声,认为诗人应该抛弃“形式主义的空虚”,塑造“全民族危亡的形象”,表现“庞大的民族生活的图画”;诗歌是“自由的民族史诗”,要发出“民族的憎恨和民族的欢喜”[12]之声。他们加强了对诗歌社会性内容的关注,蔑视象征派的“形式主义”,甚至忽略了诗歌的艺术性创造。中国诗歌会代表诗人有穆木天、蒲风、任钧、王亚平、温流、杨骚、关露等,底层的工人、农民、渔夫、卖唱的姑娘、流浪儿、报童、洋车夫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不仅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悲哀,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试图融入大众的生活,表达民族独立、自由的政治诉求。任钧在《祖国,我要永远为你歌唱》中不仅呈现敌人的残暴与猖狂,还描摹汉奸的无耻和丑恶行径。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漆黑的暗夜”,但他充满信心地憧憬祖国的未来;用嘶哑的喉咙唱出“全国民众的觉醒”和“抗敌怒潮的高涨”,并深情地呼喊我要把你“从镣铐当中得到解放”!关露的《马达》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温流的《打砖歌》、《搭棚工人歌》、关露的《童工》、王亚平的《纺织室里》《两歌女》等再现了贫困民众的悲惨遭遇。蒲风的《茫茫夜》《动荡的故乡》、穆木天的《流亡者之歌》、杨骚的《乡曲》等表现了劳苦大众从麻木到觉醒的抗争过程。
在左翼诗人那里,人民是他们真诚关注的对象,就犹如臧克家所说:“我爱农民,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爱。”[13]他们诗歌中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反帝反封的革命激情激励着后来的诗人,推动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大量的歌颂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颂歌之外,还有不少诗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甘蔗林——青纱帐》等)犹如向困难进军的号角,唱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激情。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用高亢激越的语言,传达了支边青年义无反顾奔赴祖国大西北的理想主义情怀;张万舒的《黄山松》寄情于物,字里行间充溢着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豪情;张志民的长诗《擂台》“以榕树的形象承载阶级斗争的历史”[14],一个个历史画面在读者眼前呈现:陈胜吴广的大军走过,宋景诗起义大旗飘过,水浒英雄伸张正义的镜头掠过,太平天国运动由辉煌走向惨败,秋收起义的枪声打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诗人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具象符号突出了斗争的主题。还有公刘、李季军旅生活的歌唱表现了革命战士的爱国热情,他们的诗作通过展示军队典型的生活场景和意象的组合,塑造了一个个具有高度自豪感与神圣使命感的抒情主人公。不过,由于这些战歌要履行政治宣传的功能,有些诗人用一个个口号代替了形象构思,用议论代替了抒情,致使诗歌沦为政治理念的“传声筒”。
三、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传统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欧洲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是“自由精神普遍深入到情感领域的产物”[15]。不少浪漫运动的先驱都对浪漫主义的自由本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史雷格尔认为浪漫主义的诗是“无限和自由的”[16]382,海涅也说:“浪漫主义艺术表现的,或者不如说暗示的,乃是无限的事物。”[16]401无限就是自由精神深入到情感领域后才有的审美感受。雨果对浪漫主义的自由精神阐释得比较清晰,他指出浪漫主义的实质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并且宣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和社会领域里的自由,是所有一切富有理性、合乎逻辑的精神都应该亦步亦趋的双重目的,是召集着今天这一代如此坚强有力而且强自忍耐的青年人的两面旗帜”。据此,他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文学的自由主义一定和政治的自由主义能够同样地普遍伸张。”[16]134-135而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内涵的理解更为透彻,他指出:“自由是免于障碍的自由,自由是创造自由的自由,自由意味着你在充分发挥了创造力时免受任何事物的障碍。”[17]
浪漫主义对自由精神的坚守实质是浪漫主义诗人不断铲除道路“障碍”的一种生命创造状态,其以此获得“文学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这就呈现出其生命创造的两大向度,一是浪漫主义诗人在创作中不断深入心灵世界,激发强烈的生命意识、张扬自我的个性以期实现灵魂的自由;二是借助政治抒情勇敢地与束缚人性、禁锢自由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外部力量做斗争,不断推动社会朝着自由、民主、文明方向发展。所以雅克·巴尊不无深刻地总结,“浪漫主义者为之奋斗的问题比一己之私大得多。那是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美学的问题”[18]。
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精神与20世纪中国浓厚的革命浪漫气息非常契合,再加上新诗诗人又以年轻人为主体,因此浪漫主义诗歌成为对新诗产生最大影响的外国诗歌流派。鲁迅是较早介绍浪漫主义诗歌的作家,他在《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并称赞这些浪漫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悦”的个性主义和反抗精神[19]。“五四”之后中国还出现了浪漫主义诗歌介绍热潮。20年代初,开始翻译较多的是海涅的爱情诗,新月派的文人们也开始译介雪莱、拜伦、歌德等浪漫主义诗歌。20世纪20年代,革命甚至暴力革命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拜伦、歌德、雪莱、普希金等激进的浪漫主义观念及其政治抒情性作品成为主要译介对象。这些观念和译作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年轻的新诗诗人,他们开始唱出属于自己的歌。郭沫若的《女神》横空出世,其汪洋恣肆的情感、张扬的个性和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显示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情感至上、主体性意识和自由精神等质素;新月派的诗人徐志摩、林徽因用优美的语言吟唱着自由、平等和爱;湖畔诗人赞颂自然,歌咏爱情,给诗坛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红色的革命如暴风骤雨般袭来,左翼诗人们毅然抛弃了自我的抒情,开始了“大我”和集体的抒情,并将阶级意识带入诗歌的写作,他们的政治抒情诗重在表现民族独立、自由的诉求,缺点在于忽略了主体性的独特体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苏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下,40年代的“七月派”诗人艾青和穆旦等承继了欧洲浪漫主义的自由传统,在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根据主题自由选择诗歌体式,在抒发民族国家情感时强调自我表现、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反抗阶级压迫,充满了革命的斗志。“七月派”诗人遵从“主观战斗精神”进行创作,注重选择能够显示诗人主体意识的意象,表达民族或者阶级的情感。如阿垅的《纤夫》[20]用油画般有质感的语言勾勒出了纤夫的群体形象,生命的强力夹杂着嘉陵江的水气扑面而来:在北风肆虐的江面上,纤夫们伛偻着腰,“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构成倾斜的45度角,“匍匐着屁股,坚持而又强劲”地向前。他们的脚步无比的艰辛,走过了一条条路,越过了一个个村落,无论风是如何的逆向、江水是如何的汹涌,他们用“最大的力和最后的力”,用“坚凝而浑然一体的”意志力,终于让木船“行动于绿波如笑的江面了”。他们用纤绳维系成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群”,有整齐的脚步、有严肃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有沉默的脚步团结一致地行进在崎岖的道路上。“七月派”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在“十七年”时期依然留存,如绿原潜在写作的诗歌《又一名哥伦布》里面,那个作为文学对象而存在的人物(又一名哥伦布)在漫长、苦难的时间海洋上航行,执着地追寻着自己的自由和理想。所以“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21]。艾青的《太阳》和穆旦的《赞美》都诞生在黑夜笼罩、暴风雨肆虐的旧中国,两者在意象的选择和意境的营造方面凸显了各自生命的质感,充沛的个人情感与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的豪情壮志有机融合,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尽管“十七年”时期的大多数的政治抒情诗人放逐了“自我”这个抒情主体,诗作的国家话语消解了个人性的审美经验,但有一些诗人依然坚持诗歌审美价值的追寻,他们以对抗性的话语呈现身处一体化时代复杂的个人化体验与表达。芦甸的《我活得像棵树了》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寄予一棵饱经风霜的树,外来的风暴和同类的攻讦都无法让其低头,“我”默默地扎根于深深的泥土之中,“挺拔地屹立着”[22]316-317。何其芳的《回答》在政治局势严峻的时代,面对曾经的青春岁月,真诚袒露自己复杂和丰富的内心世界。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鼓励下,不少的诗人释放出了原来刻意隐藏的情感和感受力。北京大学的学生沈泽宜、张元勋高举“五四”民主自由的旗帜,呐喊出他们的声音:“是时候了/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他们要“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22]463-464,烧毁阻碍自由的一切藩篱,道尽社会生活的酸、甜、苦、辣。穆旦的《葬歌》《妖女的歌唱》等诗作真实表达了诗人内心的苦闷和矛盾,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担忧与反思。郭小川在《望星空》第一、二小节仰望灿烂的星空,感慨宇宙的浩渺与永恒,表现对人间生活的犹疑与困惑;但作为一名“战士诗人”,他又被迫放弃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独立思考,在第三、四小节转入对人间生活的讴歌,认为人间定会胜过天堂。这样文本前后两部分造就了巨大的罅隙,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这就如学者孟繁华评价的那样:“一方面他唯恐落后于时代,有辱自己的历史和时代使命,因此他必须努力在主旋律的高音区捕捉并实现自己的声音;一方面,他对‘作者的创见’又有深刻的觉醒,对现成的政治语言的翻版有特别的警觉。然而郭小川的苦闷、矛盾在他的犹疑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后来的创作虽然名重一时,但他的慎重也越发明显了。”[23]
在“十七年”时期,由于大多数政治抒情诗往往专注于政治理念的传达,忽视了诗歌的内在肌理,一些政治抒情诗读来没有任何实在的内涵,只有一些空洞的口号或乏味的政论充斥其中,并且缺乏丰富而真挚的情感。陈晓明曾经提醒,“如何超越历史的困厄,在概念化的历史与自我的真实体验之间,找到一种表意策略,是这个时期的诗人面临的难题,能穿越这一难题,则有能力在历史给定的情境中透示出个人的诗情,如果不能,则使诗的歌唱流于空洞的概念。”[24]因此,身处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代社会,诗人们应该努力汲取各种文学资源的营养,关注群体意识的诗意化处理;学习如何处理主体性抒情的诗意表达,如何通过在个体与群体的情感之间建立诗意连接,获得强大主体性和崇高性的诗意资源。
[1] 黄宗羲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25.
[2] 司马迁.文白对照全译史记:第4册[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342.
[3] 刘南平,班秀萍.司马相如考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132.
[4] 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6:272.
[5] 赵明.先秦大文学史[M].长春:吉林出版社,1993:228-233.
[6] 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7] 史铁儿.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J].文学,1932,(1).
[8]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J].文化批判,1928,(2).
[9]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创造季刊,1928,1(9).
[10] 郭沫若.上海的清晨[J].创造周刊,1923,1(2).
[11] 孙玉石.中国新诗总系:1927—1937[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2] 穆木天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24.
[13] 臧克家文集:第1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593.
[14] 吴尚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转型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01.
[15] 陈国恩.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概观(上)[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3).
[16] 朱光潜.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7] 伯林 以.浪漫主义的根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94.
[18] 巴尊 雅.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6.
[19] 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788-789.
[20] 阿垅.阿垅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2.
[21] 陈思和.春泥里的白色花[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4.
[22] 谢冕.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3] 孟繁华.“突围”欲望与重返起点——郭小川创作道路再评价[J].人文杂志,1996,(5).
[24] 陈晓明.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60年[J].文艺争鸣,2009,(7).
[责任编辑:修 磊]
2015-06-04
袁琳(1977—),女,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
:A
:1002-462X(2015)11-014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