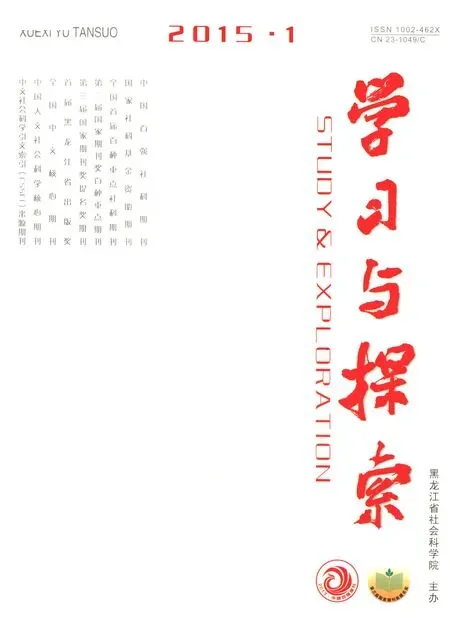叙述与修辞:电影音响与音乐辨析
何 一 杰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叙述与修辞:电影音响与音乐辨析
何 一 杰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电影声音通常分为人声、音乐与音响,其中音乐与音响时常显得难以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单独的电影音响或电影音乐研究。以广义叙述学为基础,用“是否参与事件”来划分音响和音乐,将音响和音乐纳入电影叙述——修辞的体系中,不仅讨论了音响和音乐交融的情况,还能够为厘清电影声音这个复杂的混合体提供一种思路。
电影;音响;音乐;音响音乐化;音乐音响化;叙述;修辞;符号学研究
对电影叙述中音响和音乐的讨论一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两个概念如何区分。这条 “界线”看似无关紧要,然而现代音乐已经发展到了足以令人困惑的程度,音色音乐、偶然音乐等等先锋类型混淆了常识中的音乐和音响,音乐早已不是古典时期和谐悠扬的音符了。就电影而言,电影本身独特的符号属性,使我们比较容易分辨出音响与音乐的界线。
一、电影中的声音
波德维尔将电影中的声音分为三种形式:人声话语(Speech)、音乐(Music)与噪音(Noise)或称音效(Sound effect)[1]310,这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划分。大多数情况下,声音形式的划分很明显,然而,正如波德维尔指出的那样,“有时,一种声音可能涉及多种形式……而导演正可以自由地运用这类声音的暧昧之处来进行创作”[1]310。人声话语涉及语言符号,有较多的限制条件,因而更容易辨别,相比而言音响与音乐则更为“暧昧”。贾培源先生在《电影音乐概论》中提到,“音乐与音响似乎更容易结合使用,因为从表面看不存在一定要听清楚音乐或听清楚音响的问题”[2],认为音响与音乐需要这种“暧昧”,但若以分析一部电影的声音为目的,音响与音乐还是需要明晰的。
就音响和音乐而言,声音“暧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先锋音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诸多音乐流派,如“偶然音乐”“概率音乐”“整体序列音乐”“音色音乐”等等,将杜尚以来的“融合”行为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先锋艺术家将音乐的疆域扩大到前代无法想象之处。电影配乐从这些音乐中吸收了相当多的营养,尤其是恐怖片的配乐[3],使音乐和音响变得更加难以区分。
划分的模糊还根源于划分标准的不恰当,相关讨论中,鲜有给音响、音乐下明确定义的,似乎都是在探讨一个最广阔的概念。为了更好区分音响和音乐,进而能够在讨论音响音乐化和音乐音响化的时候不至于含糊,我们需要一个彻底而明确的划分。
二、以“叙述”为标准的划分
消除电影叙述中音响与音乐“暧昧”的关键在于“叙述的加入”,即能够将音响音乐从其广义中隔离开来,赋予其电影“独特性”的东西。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述学》中对叙述作了如下的定义,即“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此文本可以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4]5。时间和意义向度似乎可以无限细分,因此一个叙述能够被切分为无数个更“小”的叙述,这种“分叙述”与原叙述虽有联系,但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叙述了。以叙述为标准划分电影中的音响和音乐,不能将叙述细化从而去推敲某一个分镜或片段中两者的属性和关系。叙述文本与其时间意义向度的联系不是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我们在分割非语言文字文本的时候常常容易将两者对应起来,使得细分成的片段无法被判断为叙述,好比将语言文字的叙述“我走出房门”生硬切分为“我”“走出”“房门”,并且逐个分析一样显得滑稽。
在以整体为框架的电影叙述中,音响和音乐可以这样区别:音响参与组成事件,音乐参与构成情节。这里首先要明确“事件”和“情节”两个概念,“情节牵涉到‘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方面:事件之选取,即说什么;事件的叙述方式,则是如何说,这两者的结合才构成‘情节’”[4]166。换言之:音响是事件中的音响,音乐是修辞;影片叙述中的一个非人声(包括歌词)的声音,如果参与事件,那么必定是音响,如果修辞,则必定是音乐。
1.音响与事件
音响不是情节事件的必需品,默片时代是最好的证明。早期理论家多对有声电影抱有偏见,所以即使爱迪生的《迪克森实验音膜》(DicksonExperimentalSoundFilm)作为现存最早的声画同步影片比卢米埃尔兄弟的“首映式”早了4个月[5],有声电影也花了30多年才开始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经验世界中,音响也不是事件的必需品。若说任何事件皆有音响,倒不如说任何事件皆有发出音响的可能。一个隐喻(“我的心飞向了远方”),也有发出音响的可能(“我的心扑腾扑腾地飞向了远方”)。然而声音的出现大大增加了电影的叙述效率,同时丰富了电影的内在运动,拓宽了其表达的可能。现在的电影中,声音、音响已经成了事件的必需品。
音响和事件的关系似乎不用再过多举例,因为几乎每一部有声电影都在解释两者的密切联系。而若是以文字描述,则无法列举“事件”,只能得到一个文字的“转述”——一个情节,其中包含了文字的修辞;不过,若是能忽略掉最后媒介化的过程,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些影片中的例子。
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话谋杀案》(Dial‘M’forMurder)中,丈夫汤尼企图谋害妻子而给她打电话,他啪啪啪地投币和拨动电话,交换机咔咔地转动,电话铃声叮叮响起,正要转身离去的列斯停下脚步……在酒吧里的声音如果说“可有可无”的话,汤尼公寓里的电话铃声则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在情节事件还是在经验世界中,它是一个完整的《电话谋杀案》此刻唯一的促成力。而在《西北偏北》(NorthbyNorthwest)那场著名的飞机戏里,罗杰在干枯玉米地里狼狈地逃窜,忽远忽近的引擎声和干枯枝叶的摩擦声成了叙述的着力点。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电影《1936年的岁月》(Daysof36)里,囚犯们在听完广场上放的音乐后用水杯敲打着铁栏,哗哗的嘈杂声持续了两分多钟,直到最后一声枪响,音响成了事件的主干。而在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舞台剧作品中,音响甚至超越了画面,独立构成一个事件。这些略显特殊的例子所展示的音响与事件的关系,实际上在每一部有声片中都存在。电影所叙述的一个事件包括了这个事件所有呈现出来的视觉以及听觉,这是文字无论如何都无法重现的。一个完整的电影叙述,如果除去了音响,就成了另一个叙述,即使这两个叙述几乎一模一样。
2.音乐与修辞
音乐可以叙述,但是笔者认为,电影之中的音乐是修辞。*这里所说的音乐不包括歌曲,准确地说是歌词叙述。一旦电影中的歌词能够被判断为叙述,电影叙述就产生了分层。除了具有叙述性歌词的歌曲之外,电影中的音乐都在协助完成着“如何述说事件”。在电影外部,音乐叙述学的研究从作者、文本、听众等不同角度入手。弗雷德·莫斯(Fred Maus)用“戏剧模式”来解释音乐叙述,“认为戏剧模式的分析主要依赖于听者的解释作用,需要听者主动通过音乐材料去发现和建构戏剧性”[6];另一位叙述学家拉比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也从听众入手,认为听者的个体因素会影响音乐的解读。而即使是塔拉斯蒂(Eero Tarasti)般精细的文本划分,音乐叙述所建构的世界和情感对电影而言也太过庞大和不可捉摸。克劳迪娅·戈尔卜曼(Claudia Gorbman)指出:“如果我们必须在两个单词以内,概括音乐与形象和音乐与叙事之间的关系,那么互相喻指(mutual implication)一语是较为准确的。”[7]她说的“应用于电影某一环节的任何一种音乐,都会有所作为,都会产生某种效果” ,这种“效果”实际上就是修辞——电影中的音乐能够帮助事件更好地成为叙述。
仍然以《电话谋杀案》为例,从列斯注意时间开始到电话铃响起,背景音乐不断地在紧张的和弦中重复着一个简短的动机,玛格被勒住后,音乐从弦乐纤细的减三和弦瞬间转入了粗暴的铜管乐之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将紧张、胆战心惊的感受更丰满地表现出来。音乐不在事件当中,《西北偏北》的悬崖上不可能有乐队,音乐也不制造新的事件,而是为说服努力。大卫·里恩(David Lean)《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ofArabia)用充满民族特色的旋律曲喻指沙漠,用民族音阶带出阿拉伯民族,再由此推及其居住的广袤的沙漠;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黄金三镖客》(TheGood,theBadandtheUgly)则用简单的电子音色和人声以及打击乐来塑造西部风情。有的音乐甚至在完成着嗅觉通感的任务,比如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的《香水》(Perfume:TheStoryofaMurderer),使得“‘跨符号系统表意’具有了摆脱语言限制的可能”[8]。
电影中使用的“非原创音乐”也大多属于反讽、隐喻等修辞。不否认很多现存的音乐作品能够叙述,但是音乐的叙述只能非常模糊地进行,更多精确的叙述依靠着伴随文本的努力,这些模糊的叙述一旦进入电影,就被电影中那种强力并且精确的叙述取代。巴赫、贝多芬、瓦格纳等等经典作曲家的作品在各种电影中反复出现,很多学者也专门针对这种引用进行了研究。“非原创音乐”拥有比原创音乐更丰富的伴随文本,这些伴随文本所发展出的一套叙述,将增强音乐在影片中的修辞能力。
三、音响与音乐的融合
音响与音乐通过这个叙述学的标准能够得到清楚的划分,但实际上的情况是,一个声音通常是两者兼有。很多文章在讨论的时候称这种现象为“音响音乐化”或者“音乐音响化”,但由于音响和音乐两种分类根源上的不清晰,致使在讨论两者交界的时候更难准确定义和区别。我们通过对声音进行“事件”或者“修辞”的判断来划分其应当属于音响还是音乐,也能够对混杂着两种类型的声音进行判断,这种判断的依据已经由上文确立:“音响音乐化”即是进入修辞的音响;“音乐音响化”即是参与事件的音乐。
1.音响音乐化
音响音乐化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声音必须作为音响参与事件;其次,作为音响的声音被用于修辞。不参与事件的声音,哪怕其在我们的经验中再接近音响的定义,也只能是音乐;“被用于修辞”,意味着这种声音除了音响的属性之外,附加了强烈的“意图”。音响仅仅具有音乐的形态是不能够算作“音乐化”的,就如同我们不会将每一辆火车那种充满节奏的“咔嚓咔嚓”声视作音乐一样——除非这个节奏进入修辞。大卫·林奇(David Lynch)《象人》(TheElephantMan)中火车站中出现的列车声反映着象人不断加快的脚步以及不断紧张的内心,一声鸣笛像是他的尖叫(隐喻),这样的音效才能算作是“音乐化”。
拉斯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intheDark)似乎是一部说明音响音乐化绝好的例子。这部被称为“良心三部曲”之一的影片按理应该遵从导演提出的道格玛95(DOGMA 95)运动的要求,不使用无声源音乐,但是影片中却出现了数场歌舞片段,由此我们得以进入女主角塞尔玛的内心世界。其中那场著名的工厂歌舞片段音响与音乐的转换被多次讨论,不过很少有人仔细追究这个转换确切的“界线”在哪里。在工厂片段里,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从第一个没有手持的镜头开始,机器的碰撞声就已经是音乐了,然而在此之前,塞尔玛和同事琳达谈话时的背景是否也算音乐?同样的疑问还有在之前出现的工厂片段,那时的机器声和歌舞片段之前的声音如出一辙,如果我们将谈话时(即仍然手持拍摄时)的背景音视作音乐化,那么之前的片段是否也算?通过对其参与事件、修辞的判断,我们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工厂的声音作为音响参与到事件之中,而它的修辞属性也不断增长,即是其音乐性不断增强。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剧情,以及演员的表演——我们得知塞尔玛对音乐的热爱,她的眼疾,以及她听到机器碰撞声时入迷的神情。一旦音乐性出现,音响也就兼具了音乐的属性。
《黑暗中的舞者》这样大量音响音乐化的例子并不常见,因为这需要剧情的支持,对人物音乐感的极端强化,《声梦奇缘》(AugustRush)可以算另一个具有这种素质的影片。科斯汀·谢里丹(Kirsten Sheridan)的这部影片同样讲述了一个对音乐特别“敏感”的小孩,一个初识五线谱就能够谱写音乐、一个能够体会自然界以及生活中的乐感的天才。当埃文第一次踏进城市的时候,地铁声、喇叭声、脚步声、挥舞旗帜声、口哨声、狗吠声等等,为从未听过这些声音的埃文上演了一出城市交响曲。后来他在教堂学会了五线谱,窗外的那些玩耍嬉戏的声音——拍球声、踢踏声、秋千晃动声等,也变成了音乐被他记录下来。
我们可以发现,音响在电影中的音乐化大多都通过赋予其节奏来完成,因而本身具有节奏属性的那些声音比如列车行驶声、脚步声、打字机声等被更多用来强调这种音乐性。大段的音响音乐都演变成了与乐器的配合,《黑暗中的舞者》与《声梦奇缘》都是如此,让·维果(Jean Vigo)的《操行零分》(Zérodeconduite)甚至让火车的音响提速来配合乐器的节奏。音响音乐化需要更多伴随文本的支持,其达成的修辞效果近似于艺术家的“出位之思”意图[9]——让观众处于一种倾向音乐的迷惑之中,而对经验产生怀疑。
2.音乐音响化
音乐音响化的条件是:作为修辞的音乐进入到电影叙述的事件之中,成了事件的音响。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较音响音乐化更多,画内音乐就是一个最普遍的例子。音乐来自于剧情中的某个声源,被人物听到,成为事件的一个音响。这个音响若是换成文字叙述可能就是“窗外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咖啡店里放着舒服的爵士乐”“嘴里哼着《佩尔金特》的调子”等等。音乐音响化,着重强调的是音乐的声音属性,以及这种属性在影片中的存在(“歌声”“音乐声”“口哨声”),与音乐的内容没有关系。画内音乐为大部分的电影使用,我们只要想想那些有关钢琴、大提琴,有关摇滚乐、舞蹈的影片,甚至回想任何一个酒吧或者咖啡店中的电影场景就能找到。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在《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Now)中将瓦格纳的音乐作为音效放在进击的直升机上,似乎想要强调音乐叙述的分量,让音乐与画面形成叙述分层,而实际上这样只是增加了画面与声音的张力。麦克特格(James McTeigue)的影片《V字仇杀队》(VforVendetta)中同样用大喇叭播放古典音乐——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音乐和画面形成隐喻。虽然两者在获得的影片内涵深度上相差甚远,但这种将音乐刻意转化为音效的手法共同的作用都在于——强化音乐的修辞。
音乐除了以真实音源的方式进入事件之外,也通过与动作一定程度上的同步来参加事件,这种同步实际上是在模拟动作,或者人物发出的声音。比如《精神病患者》中最为著名的浴室场景,“希区柯克再一次改变了音乐必须潜意识地存在于电影背景之中的传统观念:在这场谋杀场景中,音乐的侵略性如同闪亮的匕首一般令人恐惧”[10],音乐显现为事件的音效,让我们在看到匕首每一次刺下时仿佛听到了玛丽安的尖叫,甚至感到了匕首的尖锐和身体的刺痛。这种同步最极端的形式便是米老鼠步,这种源自迪士尼的命名在动画片中盛行不衰,在很多早期的喜剧片中也随处可见。《摩登时代》(ModernTimes)里面工人拧螺丝时配合的音乐,《城市之光》(CityLights)中主角遇见富翁投河时的配乐;1933年《金刚》(KingKong)里野蛮人穿着皮毛舞蹈,《蜘蛛侠》(Spider-Man)里彼得第一次爬墙,音乐都紧密地和动作结合起来;更不用说迪士尼梦工厂以及皮克斯的动画电影中的例子了。在这些情况下,音乐参与事件,成为事件的音响,理应属于音乐音响。
音响音乐化和音乐音响化,在上文给出的定义中,似乎成了相同的东西,即一个声音,既参加事件又进行修辞。这难免会使人进行另一种推断:一个既参加事件又进行修辞的声音应该怎样归类?有时候我们的确一时无法判断一个突然出现的声音的归属,但是往往剧情能够给出答案。若定在一刻分析、不涉及整个影片的全部,那么得到的便不是一个忠于文本的结果。对于声音属性的判断来自对叙述的判断,而对叙述的判断则需要整个剧情的支持。
电影相比起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虽然兴起较晚,但是其本身强大的吸引力正在吸收许多其他的艺术体裁与风格,因而越来越成为一种现代奇观。对电影的分析探讨,从来不局限在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的范畴之内,电影的魅力正在于能够经受其他领域诸多理论的再梳理,并且为这些理论提供新的视野。音响和音乐可以说是现代电影中难以缺少的两个元素,本文用叙述学的标准对两者进行划分,使得我们能够确定两者的界限,同时也描述了两者相互的转换方式。
[1] 波德维尔 大.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2] 贾培源.电影音乐概论[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14.
[3] NEIL L. Listening to Fear/Listening with Fear. Music in the Horror Film[M].London:Routledge,2010:9.
[4]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5] WIERZBICKI, EUGENE J. Film Music: a history[M].London:Taylor & Francis,2008:72.
[6] 陈德志,车文丽.音乐如何叙事——近三十年的音乐叙事模式研究[J].人民音乐,2013,(1).
[7] 戈尔卜曼 克.关于电影音乐的叙事学观点[J].当代电影,1993,(5).
[8] 何一杰.嗅觉通感的视听传达[J].符号与传媒,2013,(2).
[9]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5.
[10] JACK S. Hitchcock’s Music[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224.
[责任编辑:修 磊]
2014-1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何一杰(1988—),男,博士研究生,从事电影符号学研究。
I0
A
1002-462X(2015)01-01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