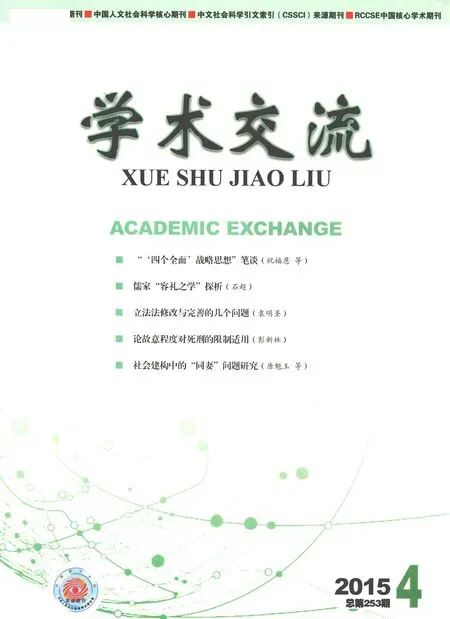论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之构建
章 程,董才生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社会学研究
论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之构建
章 程,董才生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社会关系构成了残疾人自身人际层面与组织层面的社会支持,这些支持主要来自家庭及其相关人员、社区和社会组织等。通过社会支持的结构主义、互构主义和主观评估三种研究取向,对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支持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构建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应立足于专业化的家庭危机干预、社会化的社区服务保障和规范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
残疾人;社会支持;家庭;社区;社会组织
一、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差序格局的语境下,残疾人的社会支持格局主要以家庭为核心,由社区、社会组织等为同心圆构成。因此,残疾人的社会支持结构大致可按照其社会关系(支持)顺序分为家庭成员支持、社区组织支持以及社会组织支持等方面。就残疾人人际层面的社会支持而言,主要来自家庭内外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包括家人、亲属、邻里、朋友在内的非正式支持系统;在组织层面,则主要包含了社区、社会组织等组成的正式支持网络。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家庭为残疾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情感慰藉等方面”[1]。在这里,残疾人人际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初级关系,属于家庭成员内部关系(支持);另一种则属于家庭外围的社会关系(支持),即次级关系。家庭包容其成员,并为其履行相应的义务,家庭成员则有责任扩大家庭总体的财富,并为其增加可支配的资源。可见,家庭是内部成员之间长期互惠的内生机制,但是残疾人与其家庭成员的关系又存在其特殊性,往往表现为家庭成员对残疾人的单向付出与给予,这主要是由残疾人在经济自主权和独立生活能力方面的弱势所决定的。因此,残疾人对其父母和其他亲属有着很大程度的依赖性。对残疾人来说,次级关系的人际支持不仅来自残疾人个人的社会交往,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其他家庭成员的社会网络,即由血缘家族关系之外的人组成,如一些与残疾人家庭有着密切联系的朋友、邻里、同事等。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残疾人家庭户规模开始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主要体现在由传统的家庭模式向核心家庭的转变。有关资料显示,“2011年度残疾人家庭户平均规模为3.5人,其中,残疾人家庭户规模为2人的所占比例最高,达到25.9%,3人户家庭比例为19.4%,4人户家庭比例为17.3%,5人户及以上家庭所占比例合计为27.2%,1人户残疾人家庭比例为10.3%”[2]。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残疾人家庭失去了部分来自原来传统扩展家庭的支持,导致过去以依赖血缘、婚姻为纽带的家庭保障也受到了挑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残疾人对社会支持的需求范围不断扩大,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升,逐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就对残疾人家庭产生了新的诉求。另外,在残疾人家庭外围社会关系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经常变化的环境和科层化的组织运作改变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性质特征,大都市中的人是理性和功利主义的”,从而也造就了现代日渐式微的残疾人家庭“外围”人际支持。同时农村城镇化迁徙和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口加速了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次级群体支持的弱化。总而言之,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残疾人与家庭成员、亲属、邻里、朋友等之间面对面的联结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并造成了残疾人人际关系支持的弱化,残疾人依赖的各种支持平台也逐渐解体,继而影响其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对于残疾人来说,社区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现实载体,同时也是残疾人社会支持的重要组织。在政府缺位、单位制度变迁的宏观背景下,社区居委会成为社区组织的核心。社区就其组织构建来讲,主要依托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建立社区(村)残疾人协会,即残协。“社区(村)残协要从残协委员中选聘残疾人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协助社区(村)残协主席开展工作。”[3]到2011年底,全国范围内已建社区残协就有61.1万个,达到了95.4%的建设率,同时选聘了46.2万名残疾人任专职委员。社区残疾人协会是联系残疾人与社区组织及政府的纽带和桥梁。此外,在我国社区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支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社区自行开展的互助服务。主要依靠发动社区成员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利用社区资源,满足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多层次需求,是一种自下而上形成的支持体系,属于居民自治范畴。2.社会服务机构在社区开展的相关院舍服务。经济条件发达的区域,可以依托当地公共服务设施设立残疾人之家,如温馨家园,还有残疾人康复中心、特教学校等形式的残疾人服务机构,为社区残疾人提供服务支持。3.政府委托社区有关部门具体实施的保障和配套服务措施。一般来说,是指政府和组织以强制性措施,或者以法定形式作为后盾,推进相关国家政策在社区内的实施,从而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支持体系,主要包括政府委托社区具体实施的经济救助和帮扶,以及涉及残疾人康复、就业、教育等领域的具体社会服务措施。这三类服务支持涉及的主要内容有:社区康复(残疾人康复辅导、托养、居养)、社区教育(残疾儿童特殊教育、成人教育)、就业培训(残疾人职业指导、再就业培训)、社区心理辅导、社区信息指导(求职信息)。社区支持网络为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相应的资源,并使得残疾人具有更强的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
我国社区组织的支持网络为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服务保障,然而其自身的运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从社区构建来说,一方面,其行政网络的动员模式造就了自上而下的支持体系,很容易忽视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使得社区残疾人委员及其他社区成员空有参与形式而无参与内容;另一方面,其行政主导的强制性特征也限制了社区其他团体组织的发展空间,这主要是指行政网络导致的服务供给垄断对其他服务队伍的“挤出效应”。从社区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支持来看,社区互助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和政府保障服务之间缺乏资源的有效整合,可供开展服务的资源较为分散。从横向看是同一区域内的各个社区之间无法达到各种设施、资源的共享;从纵向看是社区、街道和委员会之间缺乏梯度网络支持,使得现有服务资源得不到有效运用,甚至出现闲置浪费现象。从社区服务涉及的内容上来看,主要侧重于残疾人社区康复、残疾人职业指导、再就业培训等,致力于残疾人生理和扶贫等方面的生活保障,而甚少关注残疾人社区心理辅导、社区信息指导和社区教育等事关残疾人心理健康和发展的服务内容。
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工作思路的提议,在政策方面,我国社会组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支持。同时,十八大也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的政策要求。对残疾人个人而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服务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残疾人的康复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如对残疾儿童的早期康复干预等。另外,残疾人文化生活、精神需求等方面也开始对社会有了更高的期待,由此,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爆发式”和“高质量”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大批专业残疾人社会组织,在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残疾人社会组织主要涉及职业技能培训、智障儿童康复、智障未成年人寄宿护理、残疾人社会康复、精神病托管、精神病康复等领域。无论是在服务类型、方式,还是服务人群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业规模。在残疾人的就业指导方面,如为残疾人提供招聘信息的汇天羽信息咨询中心、自强人公益网,等等。深圳的残友集团,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残疾人集中就业社会企业,为残疾人高层次就业提供了机会和示范。在残疾儿童的康复、教育方面,如天津的“牧羊地”儿童村,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星星语”“扬爱”,青岛的“仪琳”、长春的“星光”;还有专门为服务智障儿童开设的天赋园智障艺术调理康复中心、启智特教学校以及为听力障碍儿童提供服务的沙利文康复中心等。
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属性各异。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其一,我国残疾人组织的活动需要较强地体现政府的行政目标,同时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政府又希望通过支持这些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实现残疾人社会化服务供给的最终目的。然而,大多数残疾人组织是基于政府的需求成立的,其存在的价值主要体现了领导意志而非真正服务于残疾人本身,因此缺乏明确的实践目标,也无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其二,部分残疾人社会组织主要是由助残团体发展而来,其中许多发起人要么本人是残疾人,要么是残疾人的亲属,他们因为某些共同的问题聚到了一起,慢慢形成了一个互助团体,经过发展壮大,从而成为正式的专门服务于残疾人的社会组织。但是,其中一些组织由于缺乏规范化的治理能力,加上筹资渠道受限,故而要么过多地依赖政府支持,要么倾向于营利性经营,甚至出现因竞争而互相诋毁的行为,其社会公信度也随之下降。其三,我国残疾人组织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一方面,就从业人员而言,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面临培训资源短缺,就职薪酬普遍偏低等问题;另一方面,组织本身还未形成专业化的规范管理体系,缺乏针对性的组织管理运作理念,然而随着组织的发展,机构规模与业务不断扩大,届时需要更为完善的管理体系来维持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问题产生的根源
20世纪70年代,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作为专业术语在精神病学领域被正式提出来,并随着社会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吸纳,社会支持的涵义也得到了丰富,其理论也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主义取向、社会互构取向和主观评价取向。笔者根据社会支持的三种研究取向,对当前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问题产生的根源作以下分析:
“结构主义取向的社会支持关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认为人与人之间通过一些直接和间接的纽带相联系,形成家庭、朋友、同事、邻里等关系,而这些纽带就是社会网络。……它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发挥着社会支持的功能。”[4]这一取向的社会支持重视人际层面的关系对个人的作用,主要包含了人际交往的方式、强度等,其中多数学者认为人际交往关系的强度与社会支持是高度相关的,并提出了“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假设。“强关系往往是在个人特质相似的群体内部形成的,因而个人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也往往是自己所知道的,重复率高;而弱关系往往是在不同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形成的,由于这些个人间相似程度低,难以形成共同的志趣,因而关系强度是弱的。他们掌握的信息大不相同,因而弱关系可以将信息传递给不熟悉此信息的另一群体的人,从而起到信息桥的作用。”[5]从社会支持理论来看,家庭及相关人员(邻里、同事、朋友)为残疾人提供的社会支持不可避免地具有同质性,属于强关系。但是随着家庭结构的变迁,单位制度环境的改变,这种“强关系”生存的土壤受到侵蚀,造成了残疾人人际关系的弱化或断裂,进而使得以人际间的亲缘关系和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导致残疾人个体也面临社会风险;同时,残疾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弱关系的支持,即社会支持的介体缺失,从而无法实现“弱关系”“信息桥”的功能。具体而言,就是残疾人家庭及相关人员没有得到及时的介入干预,以获得专业化的知识与信息,造成社会连接的弱化和断裂得不到加强与修复,从而加剧了家庭支持弱化的外显。
结构主义取向的社会支持涉及的“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这种社会交换思想强调的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支持不应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度一维支持,即将社会(或社会网络)作为主体,将弱势群体作为客体,从物质与心理两个角度寻求主体对客体的救济与帮助;而应该是两方面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支持者与被支持者‘互构’的过程”[6]。由此可见,残疾人社区支持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本其实就是社会互构过程的缺失,即单纯地强调社会支持施者与受者关系,从而忽略了残疾人群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社区支持构建与发展的作用。在当今社会,残疾人这一群体内部也存在多元化的特征,具有各自的特殊需求,因此,要求社会支持能够提供更具多样化的服务项目。虽然近阶段我们逐渐了解了培养社区支持形成“互构”意识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残疾人社区支持依然延续着过去的传统,对残疾人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参与态度还停留在形式支持的层面上,造成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也是目前社区服务单一、僵化的主要原因。在这种“互构”意识缺失的前提下,无论是残疾人社区组织构建、服务主体还是其服务内容往往受到特定政策的支配,无法清晰地体现残疾人社区支持的实践目的,也无法充分利用残疾人社区支持的相关资源,更别说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来满足残疾人群体逐渐多样化的生活所需。这样的残疾人社区支持会进一步促进残疾人群体的边缘化,而不是促进社区的有效整合与团结。
主观评价取向的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何种程度相信他所需要的支持、信息和反馈得到了满足,注重强调个人的主观认知,而非客观的社会行为,是一种个人对他的社会环境及其所能够给予支持的认知性评估,也是他对可以得到的支持的有效性及可靠性评估[7]。进一步了解,可以说若某种现有的社会支持不能获得其接受者的赞同,则无法构成这一群体的支持。从这一价值取向出发,可以看到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支持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对残疾人群体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方面,还要从残疾人个人的体验出发,考察社会组织支持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上述社会组织所存在的问题,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残疾人群体主观体验的忽视,从而造成了现今社会组织缺乏针对性的长效管理机制,且存在公信力下滑和专业水准普遍偏低的状况。具体而言是残疾人主观价值无法得到社会组织的采纳,并嵌入实际行动目标中;残疾人群体对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没有反馈渠道,无法及时评估组织支持的效用;残疾人对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职业资格、服务水平等缺乏授权的监督评估系统。因此,目前建设规范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对保证残疾人个人体验与评估得到社会回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构建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对策建议
社会支持与残疾人的存在相伴相生,无论是家庭、社区还是社会组织对保障残疾人来说都是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提高残疾人群体社会支持的成效已成为政府与社会的重要职责与任务。通过对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改善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条件、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应立足于专业化的家庭危机干预、社会化的社区服务保障和规范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
(一)专业化的家庭危机干预
残疾人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其人际交往除了基本的家庭关系还包括家庭外围的交往,所以其他人员(邻里、朋友)的态度对其心理状态同样重要,尤其是联系比较频繁的人。因此,对残疾人家庭及相关人员的危机干预,不仅要重视残疾人本身的变化,也要适当地介入其周围人员当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调整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且利用这种人际关系资源,为处于社会关系弱化状态下的残疾人提供各种改善状况的机会和条件,即由“信息桥”摄取新的社会资源。社会工作者作为残疾人社会支持的重要介体,与残疾人之间是一种“弱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是残疾人家庭及相关人员获得异质性信息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当残疾人自身无法妥善处理好个人的情绪问题时,容易引发家庭、婚姻以及社交矛盾,这些冲突的出现会促使残疾人人际关系的恶化、不信任程度的加深等问题的出现,从而有可能导致其家庭系统、社交系统的均衡性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来自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咨询信息或危机援助服务信息,如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以提供精神支持和抚慰。当然,也需要其提供取得现实帮助的机会,例如联络其他助残个人或团体,获得物资救助的机会等;同时,还需要减少负面影响,这主要是指在那种缺乏感情、以职业化官僚主义态度处理问题时发生的消极冲突。另一方面,家庭及其相关人员对残疾人所患残疾信息的了解有利于他们解决生活中的诸多困难。其中,家庭成员的培训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社会工作者联系专业的人员教授残疾人日常护理知识和相关的教学技巧等,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满足残疾成员的日常康复和教育需求,并在增强残疾人生活独立性的基础上,提高他们对生活的信心,进而减少他们对父母的依赖感。而对相关人员的干预,则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对他们进行的心理辅导工作,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残疾人(邻居、同事、朋友)的需求,缓解残疾人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压力,为残疾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
(二)社会化的社区服务保障
社区支持应更加注重“互构”意识的形成,从而为满足残疾人的实际需求提供社会化的服务保障。第一,社区组织应培养残疾人对自身权利与自我实现的意识,鼓励残疾人广泛地参与社区组织建设。具体而言,社区专门为残疾人设立的协会除了应吸纳残疾人参与社区管理外,还应有效地提高残疾人在社区服务事务决策中的政治权重,为政府相关政策在社区的实施提供及时的反馈信息,并为进一步的社区服务提供需求导向。残疾人社区支持应培育社区内互助团体的责任分摊意识,从而减轻社区政府组织的服务负担,并在社区组织的实际工作中鼓励并扶持社区内部服务队伍,积极引导其规划和发展方向,为残疾人营造一个服务主体社会化参与的生活环境。第二,社区组织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本社区已有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并鼓励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互动,保障部分残疾人的特殊需求能够在跨越特定社区范围的支持网络系统中得到满足。即当本社区的相关服务资源受限时,可以从彼此相邻的其他社区的服务组织中得到帮助。同时,加强纵向的社区服务组织与街道、委员会服务组织之间的联系,形成一层一层的梯度网络支持,在满足残疾人不同层次需求的同时,也能整合不同社区的支持网络,避免资源的闲置或浪费。第三,多元化服务内容的开发是残疾人社会化参与的服务保障。因此,除了要加强建设社会化的康复服务体系,还应该注重残疾人其他方面的服务内容。具体而言,残疾人社区就业指导与培训必须与社区教育相结合,在提高其文化素质的同时又能掌握相应的劳动技能,增加其就业的竞争优势。在开展心理辅导方面,应该更注重了解残疾人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培养残疾人的自主意识,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形成主动寻求与开发社会支持的能力。就社区信息服务而言,为满足残疾人动态地掌握服务信息,应建立一个固定的、被广知的社区助残服务信息平台,是保证残疾人信息“互构”的前提。
(三)规范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
为扩大残疾人个人体验对社会组织支持的影响力,应加速残疾人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体系的构建,促进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首先,有效地运作残疾人社会组织并实现组织的功能性目标,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组织规范来保证组织的稳定发展,避免组织出现“因领导而异”的局面。如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由残联组织监控社会组织,或建立残疾人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政策监督机制。在社会组织相关管理规范推进和实施过程中,保证让残疾人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建构、监督中来,使得社会组织真正实现为提供残疾人公共服务的社会目标。其次,增强残疾人社会组织的公信度,要求组织规范化运营。在组织运作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要建立以残疾人为主的评估系统,定期对残疾人社会组织的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并对科学有效的工作模式进行奖励,同时宣传其成就以增加社会组织的影响力。从残疾人社会组织自身来说,需积极争取和维持政府及残疾人群体对其合法性的认可,提高自治意识,建立起严格的自律规范,并将社会组织的相关服务信息、社会捐赠信息等进行标准化公开,进而提高残疾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最后,要提高残疾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就应该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机制的规范化。创造社会组织成员的再教育及培训机会,例如与高校或培训机构合作,并结合残疾人的服务评估体验,共同开发适合残疾人组织服务工作的教材与课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专业化的职称考核系统,使得从业人员就业更具规范化,并与其工作薪酬相挂钩。另外,残疾人社会组织人员的发展,离不开高效的管理机制,即应当开发适应残疾人群体的科学管理模式,如对组织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的分权管理,等等。
[1]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救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1,(4).
[2]2011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EB/OL].百度文库网,2013-12-20.
[3]纪刚.国务院残工委印发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意见[J].中国残疾人,2005,(11):5.
[4]李宁宁,苗国.社会支持理论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从刚性管理向柔性支持范式的转变[J].江海学刊,2011,(6):112.
[5]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1,(1).
[6]梁君林.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社会保障再认识[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43.
[7]Tracy E M.Identifying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of At-Risk Families[J].Social Work,1990,(3):35.
Building Our Social Supporting Network for the Disabled
Zhang Cheng,Dong Caisheng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ety,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Social relation forms a kind of social support for the disabled in their own interpersonal leve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and these supports mainly come from family and its members,commun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etc.The paper takes an analysis on the root of social support problems concerning family,commun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through society-supported structuralism,mutual constructivism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Our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handicapped should be built from solving family crisis by professional interference,socialized community service guarantee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disabled;social support;family;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
C91
A
1000-8284(2015)04-0160-05
〔责任编辑:常延廷 巨慧慧〕
2014-09-25
章程(1987-),女,江苏无锡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研究;董才生(1964-),男,江苏无锡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社会政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