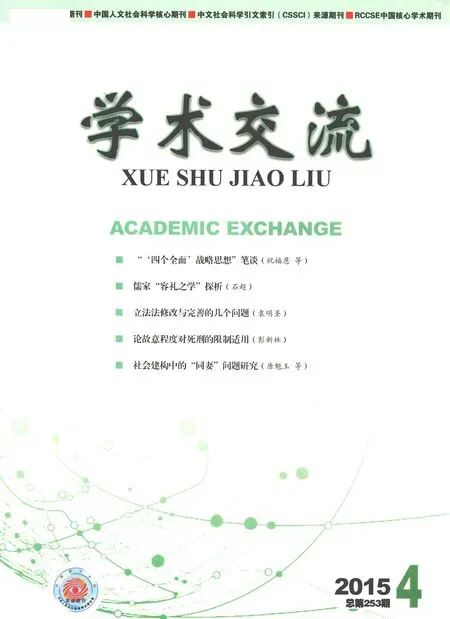论去殖民化时期黑非洲文学的发展
焦 旸
(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32)
论去殖民化时期黑非洲文学的发展
焦 旸
(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32)
去殖民化时期的黑非洲文学突破了疆域和民族的界限,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即讨伐殖民主义,建立属于非洲人的非洲。在这一时期,黑非洲法语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黑人性”理论更增强了黑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直至今天,依然是黑人文化的强大内核。英语文坛以阿契贝、索因卡为代表,以小说和戏剧等文学形式揭示非洲的深层社会问题。同时,以斯瓦希里语为代表的黑非洲本土语言文学也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的黑非洲文学,凝聚了黑非洲大陆的自尊、自醒和自豪感,成为世界人民对黑人文明的共同文化认知,并开始前瞻性的探讨独立后的非洲未来。
去殖民化时期;黑非洲法语文学;黑非洲英语文学
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将非洲横截为两部分,即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两者在语言、文化、人种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因而人们习惯于将非洲文学分为北非文学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文学。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相对于欧美文学研究,黑非洲文学在很多领域尚不为大家所熟知。20世纪60年代,黑非洲国家民族独立浪潮推动其文学走向世界。非洲大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以及在殖民时期同西方文化碰撞所形成的非欧文化结晶极大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涌现成为黑非洲文学迈向高峰的标志。本文主要研究二战后黑非洲国家逐渐走向独立时期的非洲文学,并从语言角度入手,通过介绍法语文学、英语文学和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各自的主要作家及代表作品,来解析这一时期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一、法语文学:以“黑人性”为思想内核
去殖民化(Décolisation)是殖民化的衍生词,指“人民致力于独立,停止从政治上依附此前殖民国家的过程”[1],是对黑非洲国家二战后追求独立阶段的总结,它有别于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平等为前提的民族复兴。尽管1958年戴高乐总统试图以“法语共同体”[2]的形式阻止黑非洲人民独立的脚步,但1960年近20个黑非洲国家的相继独立,宣告了其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至1970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完成了去殖民化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义为“去殖民化时期”。
此时法语文学的主基调是抨击非洲殖民统治。1947年,由塞内加尔作家阿辽纳·狄奥普倡议的学术杂志《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在巴黎问世,成为了非洲法语文学崛起的标志。这本旨在“尊重非洲传统,帮助非洲融入世界”的杂志一时间云集了如纪德、加缪、塞泽尔、桑戈尔等当时法国和非洲文坛的众多重量级人物。作为黑非洲文学的重要阵地,《非洲存在》出版了大量年轻小说家的作品:如喀麦隆作家阿莱克桑德尔·比伊迪·阿瓦拉(Alexandre Biyidi Awala)的《残忍之城(Ville Cruelle)》(1954),他的另一部作品《完成的任务(Mission terminée)》更摘得了法国文学大奖“圣勃夫奖”。1956年,阿辽纳·狄奥普在索邦大学组织了第一次黑非洲作家与艺术家论坛,是黑非洲文学获得世界认可的标志之一[3]。
在这些法语作家中,桑戈尔是最重要的一位。2006年,法国国民议会甚至为桑戈尔诞辰100周年举行活动来纪念这位非洲法语文坛巨匠。桑戈尔的第一部作品是抒发思乡之情的《阴影之歌(Chants d’ombre)》。诗集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表现了作者眷恋家乡的痛苦和无奈;第二部分表达了作者重回孩提时代的强烈愿望;第三部分是爱情篇,主要讲述不同肤色女人的爱情故事;最后一部分则是对作者政治诉求的诠释,即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作为一部黑人文学作品,作者勾勒出了美好的、充满黑人性的童年王国,这种淳朴的情怀成为了这部诗集的灵感源泉。“既然让我解释这些诗,那我坦白:所有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来自我的家乡。在这里,很多平原、森林、海边的村落都消失了。我希望让它们能够在童年王国中复活。”[4]1948年,桑戈尔用诗集《黑色的奉献(Hosties noires)》抨击第亚洛瓦军营的血腥镇压。同年,被萨特称为“黑色的俄耳甫斯”的《马达加斯加和黑人法语诗集(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de langue franξaise)》问世,它收录了包括艾美·塞泽尔、保罗·尼日尔、比拉哥·迪奥普等几乎所有名家的作品,其中桑戈尔本人的诗作占一半以上。可见年轻的桑戈尔在当时的非洲诗坛已经奠定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文学领域,桑戈尔的最大贡献是将“黑人性”(Négritude)思想融入作品中。不仅使其逐步深入人心,也为后续的黑人文学创作指引了方向,以至于萨特赞其为“这种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是破除种族不平等的唯一办法”。“黑人性”一词最早于1935年3月由塞泽尔提出。在报纸《黑人学生(L’Etudiant noir)》上,他最初提出“黑人相似性”的概念。1939年,他在诗歌《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中第一次使用了“黑人性”一词。随后“黑人性”出现在桑戈尔的诗集《阴影之歌》中,并沿用至今。桑戈尔将其定义为“黑人世界文化价值的总和”。自此,这一概念得到了大部分非洲学者的认同,成为不同形式的黑人文学作品价值共性的理论依据。我国著名学者刘鸿武认为,可以将去殖民化时期“黑人性”的提出视为一场“文化复兴运动”。“首先,这场文化复兴运动,在全非洲民众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深处唤起了自我意识……使黑人种族重新建立起了他们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联系,恢复了黑人与自己往昔伟大传统与精神故园的纽带。其次,非洲文化复兴运动对于动员起非洲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产生了直接而广泛的推动作用……第三……因而它具有超出非洲大陆本身的更加广泛的世界意义。”[5]
去殖民化时期的非洲法语文坛堪称百花齐放。保尔·罗马尼·辛班巴(Paul Lomami Tshibamba)的荒诞小说《恩甘多(Ngando)》(1949)是刚果作家第一部在欧洲公开发行的法语作品,尽管其中很多章节略显晦涩难懂,但作品中对非洲殖民统治的辛辣讽刺依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49年,卢旺达作家萨维里奥·耐吉兹吉(Saverio Naigiziki)凭借作品《卢旺达逃亡(Escapade Rwandaise)》获得了布鲁塞尔殖民区文学奖,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在统治者和基督教领袖统治下商业雇员们的生活。[3]1952年,诗人亚历克西·卡加梅(Alexis Kagame)以卢旺达口语文学格律创作了24卷法语长诗《神圣田园(La divine pastorale)》。四年之后,他的代表作《班图-卢旺达哲学(La philosophie bantu-rwandaise de l'être)》问世,作者通过对大量文学、历史和哲学资料的梳理以及对班图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分析,呼吁将传统班图哲学作为构架社会的思想基石。在这部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中,社会被划分为人类(Muntu)、非智力生物(Kintu)、时间与空间(Hantu)和行为规范(Kuntu)四部分。尽管卡加梅的大胆设想很难付诸实施,但班图哲学由此再次被点燃了生命力,成为了黑非洲人民去殖民化运动的思想阵地之一。
黑非洲文学的重大事件还包括:1953年,卡马拉·拉耶(Camara Laye)凭借《黑孩子(L’enfant noir)》摘得了Charles Veillon国际文学奖;1954年,谢客·安塔·迪奥普发表了《黑人民族与文化》,提出了“非洲中心主义”;1956年,罗曼·加里(Romain Gary)的《天根(Les Racines du ciel)》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同年,费丁南·奥约诺(Ferdinand Oyono)凭借短片小说《男孩的一生(Une vie de boy)》和《老黑人和奖牌(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一举成名,作品借主人公汤迪(Toundi)和麦卡(Meka)的生活经历,着力抨击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此类作品还包括塞姆班·乌斯曼(Sembene Ousmane)的《神的儿女(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和谢客·阿米杜·卡恩(Cheikh Hamidou Kane)的《歧义冒险(L'Aventure ambiguё)》。前者讲述了非洲铁路工人罢工的故事,以表达对法国工人和非洲工人不平等的不满。后者在1962年获得黑非洲文学奖。在小说中,作者借助主人公桑巴·迪亚洛(Samba Diallo)的经历传递“在非洲欧洲化的背景下的道德危机”[3]。
60年代后期,科特迪瓦作家库鲁马和马里作家扬博·乌奥洛冈(Yambo Ouologuem)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库鲁马的小说《独立诸阳(Les Soleils des indépendances)》获得了魁北克法语文学奖,小说围绕马林凯人最后一位王子法码展开,展示了法码传统身份与社会变革中的冲突下悲剧的一生。作者通过这部作品批评了殖民统治者和独立后的非洲政府,这也被认为是对于后殖民时代非洲体制的一种反思。乌奥洛冈的小说《暴力的责任(Le devoir de violence)》一反常规,以虚幻的非洲王国为素材,内容充斥暴力和色情,小说颇具去殖民化后期的思想,意在说明这些并非是殖民统治的产物。这部小说也获得了1968年的法国雷诺多文学大奖。
除了诗歌和小说之外,法语戏剧也得到了发展。贝宁人让·普利亚(Jean Pliya)的黑非洲文学奖获奖作品《孔多,贪婪的人(Kondo,le requin)》(1966)就是非洲早期戏剧中的经典作品。作者将原本高傲而怯懦的国王贝昂赞塑造成了反殖民统治的英雄,尽管最终贝昂赞为了避免子民的牺牲而向殖民者妥协,但依然不失为勇毅、智慧、勤政的化身。这部作品深受百姓喜爱,但由于很多地方与史实相左而饱受历史学家的非议,以致未能参加贝昂赞国王逝世百年纪念演出。另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乡间喜剧,居伊·曼加(Guy Menga)1966年创作的《孔卡·穆巴拉的锅(La marmite de Koka-mbala)》和纪尧姆·奥约诺·姆比亚(Guillaume Oyono Mbia)1964年创作的《三个求婚者,一个丈夫(Trois prétendants,un mari)》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1967年,为了鼓励戏剧的发展,非洲还设立了非洲内部戏剧奖。
二、英语文学:小说与戏剧的双星闪耀
这一时期黑非洲英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两位尼日利亚作家齐诺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和沃莱·索因卡(Oluwole Soyinka)。
较其他非洲作家而言,中国学者对阿契贝的研究较多。姚峰就阿契贝的后殖民主义思想[6]以及阿契贝的国家文学观给出明确的定义,并对参照文本《黑暗的心》和目标文本《瓦解》进行对位分析,得出非洲小民族文学是“独裁”空间下的游牧政治的结论[7]。颜治强通过研究《瓦解》《神箭》《人民公仆》等阿契贝代表作中的白人描写,认为阿契贝的作品淳朴自然反而比欧洲人的作品更加开放而不狭隘[8]。由此可见,阿契贝的作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始终流露出去殖民化的思想内涵。因此,尽管其创作时期跨越了去殖民化时期和后殖民主义时期,我们还是将其归于前者。
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阿契贝年少成名。1958年,其成名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被翻译成45种文字,销售量在400万册以上。阿契贝着力刻画了伊博部落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主人公奥贡喀沃(Okonkwo)的悲惨经历诉说作者去殖民化的思想。1960年,阿契贝发表小说《动荡》、1964年发表小说《神箭》以及1966年发表小说《人民公仆》,这三部队作品与其成名作《瓦解》合称为“尼日利亚四部曲”。除诺贝尔文学奖,阿契贝几乎获得了所有文学大奖。1960年获得尼日利亚国家文学奖,1972和1979年先后两次获得英联邦诗歌奖,并在1979年捧得了尼日利亚文学最高荣誉——尼日利亚国家优秀奖,2002年获得了德国国际书业和平奖,2007年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奖。同时阿契贝也是《泰晤士报》评出的20世纪伟大作家中唯一入选的非洲作家[3]。阿契贝通晓西方文化,又熟知伊博文明;他有民族独立意识,更关注独立后国家的命运;他原汁原味地展现伊博社会观,即使是男尊女卑的思想也不加回避,同时承担起非欧文化交融的使命,同康拉德的论战更堪称非欧文化碰撞的经典。
同阿契贝不同,索因卡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戏剧方面。他的代表作包括《狮子与宝石》(1959)、《森林之舞》(1960)、《强种》(1964)、《路》(1965)、《死亡和国王的马夫》(1975)等。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索因卡在中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宋志明认为,其作品是西方诗歌文学同非洲殖民地社会文学的结合产物,作为矛盾的载体在抗争殖民统治的同时,流露出浓重的悲观主义倾向[9]。高文惠通过对《死亡和国王的马夫》的分析,探讨索因卡定义的“第四空间”和诗歌悲剧的文化与认知内涵[10]。王燕通过对诗歌中所体现的西方现代戏剧技巧和非洲民族文化传统的分析,剖析“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有关人生的戏剧”的内涵[11]。元华、王向远主要抓住了索因卡戏剧创作的文化取向,在比较了他60年代后的戏剧创作和西方现代戏剧后,发现索因卡是一位包容而开放,既有强烈的民族气息,又站在时代前沿的戏剧作家[12]。因此,我们不难从其政治主张、创作技巧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勾勒出索因卡的戏剧创作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却鲜有作品问世。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非洲作家都像阿契贝和索因卡一样含蓄地表达自己去殖民化的思想。肯尼亚作家詹姆斯·恩古吉(James Ngugi)就是相对激进的一位,他的《大河两岸(The River Between)》(1965)讲述的是两个因信仰不同的村落在年轻领袖外亚基领导下团结起来反抗殖民统治的故事。另一部作品《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1967)围绕着两个肯尼亚青年展开,作品中的形象被分成正反两派,揭示了大部分肯尼亚人民英勇不屈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和少部分人卑躬屈膝的嘴脸。在两部作品中,恩古吉都鲜明地表达了去殖民主义的思想。在后面的创作中,他主张非洲文学创作应该摒弃英语,而采用非洲民族语言[6],为此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并宣称不再用英语写作。
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家还包括乌干达作家奥考特·庇代克(Okot p'Bitek),他的长篇叙事诗《拉威诺之歌(Song of Lawino)》讲述的是非洲黑人妇女拉威诺被丈夫遗弃后,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中赢得尊严的故事。该诗在黑非洲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如今拉威诺已经成为非洲妇女追求解放赢得尊严的代名词。南非作家彼得·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的作品《矿工(Mine Boy)》(1946)在历史上第一次向人们描述了南非黑人矿工的苦难生活,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南非种族歧视的关注。[3]
三、非洲民族文学: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崛起
英语和法语文学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黑非洲文学国际化的进程,让世界揭开了黑非洲文学长久以来神秘的面纱,但在去殖民化的大背景下,黑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主动发展要求同样强烈。作为外来的阿拉伯语同东非当地的班图语结合的产物,斯瓦希里语以更加“正统”的身份,承担着延续地域文化和思想的使命,成为众多黑非洲民族追求的“黑人性”共同价值观的语言载体,以及东非诸多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殖民主义影响的语言武器和思想纽带,其发展也因此受到了包括坦桑尼亚政府在内的很多东非国家的高度重视。早在1928年的蒙巴萨会议上,各国就对斯瓦希里语的标准化达成了一致,并以“东非地区语言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出版了《斯瓦希里语》1—4册,随后陆续推出《斯-斯词典》和《斯英-英斯词典》。这一系列保护性措施为斯瓦希里语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保障。1964年,坦桑尼亚政府正式决定将斯瓦希里语定为国语,从而确立了斯瓦希里语的正统地位。
夏巴尼·罗伯特(Shaaban Robert)是这一时期斯瓦希里语文学的代表人物。自20世纪30年代起,他开始用斯瓦希里语创作并发表诗歌,这些作品在二战中成为班图人反对纳粹德国的战歌。这些诗歌作品题材广泛,涉猎战争、家庭、部落族群、社会生活以及语言等问题。其代表诗集包括译著《鲁拜集》、描写人们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新生活的《农夫乌图波拉》和用象征手法影射殖民统治的《可信国》[13]。荷兰斯瓦希里语专家简·科纳颇尔特(Jan Knappert)曾这样评价:“毫无疑问,他是斯瓦希里语创作的杰出代表,是这门语言发展的先驱。”在夏巴尼·罗伯特的推动下,斯瓦希里语在二战后开始出现在非洲当地的报纸和音乐剧中[3]。
除夏巴尼·罗伯特,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其他斯瓦希里语作家,肯尼亚诗人阿布迪拉缇夫·阿布达拉(Abdilatif Abdalla)和坦桑尼亚作家穆哈穆德·萨义德·阿卜杜拉(Muhammed Said Abdullah)都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斯瓦希里语文学创作的代表。
段汉武将这一时期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的共同发展;现代题材和神话故事的结合;以反帝反殖民为主要思想以及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14]。这说明斯瓦希里文学已经开始走出殖民主义的阴影,从历史的角度凝练民族文化的精髓,从现实的角度关注社会面临的问题,对西方的扬弃、对传统的思考让斯瓦希里文学成为凝结东非人民的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思想内核,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就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的原因,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面对英语、法语文学发展的外在压力和去殖民主义思想逐步成熟的内在动力,作为东部黑非洲地区的主要语言,斯瓦希里语根植于当地传统文化,它的发展引起了黑非洲人民的共鸣,是一种东非乃至整个黑非洲文化荣誉感、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体现。第二,东非国家政治上纷纷独立,为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从民族语言到官方语言,从幕后走到台前,斯瓦希里语文学离不开去殖民化时期的社会背景。此后,黑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让这些国家人民谋求主人地位的意识不断增强,进而要求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也成为了斯瓦希里文学发展的客观条件。第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刺激了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发展。同历史上阿拉伯文化的涌入一样,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也促进了斯瓦希里语文学腾飞。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素材更加丰富,作品思想更加深刻,文明碰撞激发的火花点燃了文学创作的热情,进而对不同文明融合的反思使得文学走向成熟。
四、结语
综上所述,黑非洲文学在上世纪40-70年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得到巨大发展,并迅速融入世界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滚滚浪潮,因而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首先,黑非洲文学成为全体黑非洲人民共同的精神纽带。它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部落、族群和国家的壁垒,以法语和英语为主要工具,以“黑人性”为思想内核,迎来了文学创作的新高潮。遭遇了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文化侵蚀后,民族觉醒的呼声响彻非洲大陆,同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割裂,让黑非洲人民在遭受政治压迫、经济压榨的同时,沦为文化领域的流浪儿。这一时期黑非洲文学所展现的“黑人性”精神,进一步凝聚了黑非洲大陆的自尊、自醒和自豪感,成为世界人民对黑人文明的共同文化认知。
其次,黑非洲文学在这一时期已逐步走向成熟。其主要素材来源不再局限于英雄史诗、宗教传说,其形式亦逐步摆脱了口口相传的行吟文学,转而直面贫穷、战争、种族歧视等复杂而沉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或针砭时弊,或以古喻今,运用小说、诗歌等形式,向全世界诉说黑非洲社会的苦难进而揭示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去殖民化时期的黑非洲文学不仅是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思想武器,更是人们对推翻殖民统治后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寄托。在去殖民化后期,黑非洲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再次发生变化,部分作家与时俱进,开始前瞻性的探讨独立后的非洲未来。
最后,黑非洲文学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白人性”相比,“黑人性”追求平等的思想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心声,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去殖民化时期,黑非洲文学逐步摆脱了对“白人性”文学的依附,在传承古老黑非洲文明的基础上,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实现了文学跨国度的横向联合和跨历史的纵向飞跃,淳朴而厚重的黑人文明与严谨而思辨的白人文化交织融会,在世界文学百花园中绽放。自二十世纪50年代,先后有5位非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这一时期黑非洲文学的蓬勃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1]Hachette.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Z].2000:1099.
[2]曹德明.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看法国与非洲的特殊关系[J].国际观察,2010,(1):29-34.
[3]Alain Ricard.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M].Paris:Ellipses,2006.
[4]Léopold Sédar Senghor.Liberté1:Négritude et humanisme[M].Paris:Le Seuil,1964.
[5]刘鸿武.“非洲个性”或“黑人性”——20世纪非洲复兴统一的神话与现实[J].思想战线,2002,(4):88-92.
[6]姚峰.阿契贝的后殖民主义思想与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J].外国文学研究,2011,(3):118-168.
[7]姚峰.阿契贝的《瓦解》与小民族文学的游牧政治[J].当代外国文学,2013,(4):105-114.
[8]颜治强.帝国反写的典范——阿契贝笔下的白人[J].外语研究,2007,(5):83-88.
[9]宋志明.“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3,(5):113-118.
[10]高文惠.索因卡的“第四舞台”和“礼仪悲剧”——以《死亡与国王的马夫》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11,(3):127-134.
[11]王燕.整合与超越:站立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临界点上——对于索因卡戏剧创作的若干思考[J].外国文学研究,2001,(3):66-71.
[12]元华,王向远.论渥莱·索因卡创作的文化构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5):20-28.
[13]魏媛媛.本土与殖民的冲突与共生:1498—1964年斯瓦希里文化在坦桑尼亚的发展[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
[14]段汉武.现代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创作背景及其特点[J].许昌师专学报,1995,(1):68-72.
〔责任编辑:曹金钟 孙 琦〕
I106.9
A
1000-8284(2015)04-0209-05
2014-09-30
焦旸(1981-),男,吉林长春人,讲师,法国赛尔齐-蓬图瓦兹大学法语语言学博士研究生,从事法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