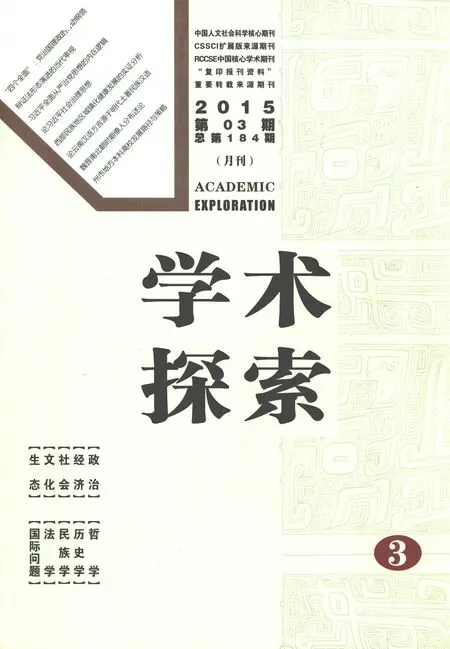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赈灾应对措施与政府角色转换研究
赖静
(成都学院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赈灾应对措施与政府角色转换研究
赖静
(成都学院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民国时期(1912~1949年)虽然只有38年,但天灾人祸频仍不断,真可谓十年九荒,其中水旱灾害影响最重。面对灾荒民国政府采取相应策略予以应对,成立了相关赈灾机构,颁布灾荒政策,采取具体赈灾措施。尽管由于战争及政策具体实施时存在一些弊病,影响赈灾效果,但是国民政府应对灾荒采取的政策措施在赈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有效彰显政府的责任意识,成功呈现其政府角色的有效转换,其中,亦反映国家认同与民族心理认同之历程。
民国时期;赈灾;国民政府
灾荒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重要方面,它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灾荒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的措施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赈灾研究成为非常重要的领域,池子华对民国灾荒史的研究从流民与移民潮的角度进行过深入研究,[1]周秋光对于慈善史研究中亦有涉及赈灾方面的研究,[2]有对于古代赈灾进行研究,[3]其中亦有不少论文对于民国时期一些区域的灾荒概况及赈灾政策进行过研究。[4]本文试图对民国时期政府赈灾措施与政府角色转换进行研究,对于今天赈灾制度与机制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民国时期灾荒的基本概况
民国时期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十年九荒”,其中水旱灾害尤其严重,仅以官方报道可见一斑。1912年湖南等六省水灾;1913年湖北等九省水灾;1914年广东等十一省水灾;1914年湖南等十二省水灾;1916年淮河、运河、长江中下游水灾;1917年河北等七省水灾;1918年湖南等九省水灾;1919年安徽等十省水灾;1921年河南等八省水灾;1922年江苏等四省水灾;1923年水灾遍及十二省;1924年广东等十二省水灾……1928年湖南等九省水灾;1929年四川等三省水灾; 1930年陕西等十一省水旱虫灾……1944年湖南等数省水灾;1945年湖北等数省水灾;1946年湖南等十九省水灾;1947年湖北等数省水灾;1948年湖南等数省水灾;1949年全国各地水灾,华东、华北五省水灾最重。[5]
其中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平原发生过的三次洪水灾害,史料记载较为详尽。第一次较大洪水灾害发生于1923年,称为“癸亥年大水”。当年7月上旬,成都北部龙门山前连旬大雨,平原大水,冲决新河,淹没良田十万余亩,淹毙千余人以上,为彭县、新都及郫县西北原崇宁县境一带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灾害。崇宁、彭县、新繁、新都、什邡一带,连日淫雨经旬,其中3日至6日连3日暴雨,使彭县湔江、土溪河、灌县蒲阳河、什邡石亭江河水暴涨,发生近百年来特大洪水。金堂地处众水尾闾,由于北河、中河、毗河三江洪水同时暴涨,使金堂县城遭受巨大浩劫。当时的报纸也描述了洪水所带来的巨大灾害,据《川报》报道称:“7月3日起,连日大雨,江水暴涨二丈余,赵家渡淹没,淮州河街亦淹大半,冲毁民房数百家,沿江多数良田变沙洲,公私财物损失无算。至县境内中、北、毗三水同时陡涨,沿岸尽成泽国,溺死约千数百人,毁民房数千家,淹没田地在百万亩以上,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奇灾。”[6]7月上旬平原淫雨,使郫县清水河泛涨,沿河多处冲决,成都市城区也遭水灾。据《四川日报》报道:“连日大水骤涨,东、北、南三门外,民房、木料冲毁甚多,南门大桥已涨上鱼嘴,鱼嘴破裂二个。”[7]可见这次洪水的破坏强度之巨。
第二次是1933年发生的由岷江叠溪地震引发的山崩堵江、积水溃决洪水大灾。当年8月25日,岷江上游叠溪地震山崩壅江成大小海子,堵水坝高各百余米。[8]同年10月9日夜,下游小海子积水满溢溃坝水发,沿江民田房舍漂没无遗,洪峰于10日晨至灌,测算洪峰流量10200立方米/秒,都江堰首全毁,仅余江中外江索桥石砌桥墩一个,余皆沙砾一片。离堆右侧人字堤冲决新河。[9]这次洪水使金马河沿河各县遭受惨重损失,其中尤以灌县为巨。[10]
第三次特大洪水发生于1947年夏秋。当时成都平原暴雨大水,灌县6月底至7月初连续暴雨,实测6月30日至7月4日、5日雨量,灌县为551.0毫米,成都为358毫米。岷江水涨,飞沙堰决,郫县一线大雨,汇入府河,7月4日望江楼水文站实测最高水位489.46米,洪峰流量1200立方米/秒。成都全城街道,几全淹没,低处流水盈尺成河,城外房屋冲塌不计其数。郫县城内水深过膝,四乡冲毁稻田8000余亩,双流冲毁稻田2万余亩,中兴场府河水位高出地面1~3米,龙泉驿柏合寺鹿溪河桥面水深2米。8月12日灌县又大暴雨,岷江大涨,8月14日都江堰首岷江洪峰流量3790立方米/秒,宝瓶口水深达19.5划。灌县城墙倒七八丈,压毁房屋5间,死10人。大邑县7月4日暴雨,全县有23个乡受灾,以安仁、龙凤、蔡镇、韩镇乡为重,安仁镇上水深0.7米,路断行人,蔡镇乡白马寺一片汪洋。崇庆7月1~5日及9月12日两次大雨,使全县江河泛涨,受灾农田达到20万亩以上,冲毁房屋1548间。[10]此次洪水是成都城区近百年来发生的最大洪水。即便是天府之国的成都其洪水灾害亦如此之重,可见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之重。
不仅是成都如此,中部地区产粮大区安徽等地亦不为轻,有史记载,1922年,“颍上七至八月间霪雨二十余日,造成涝灾,受灾面积占半。”“1931年,全省特大水灾”。“寿县阴雨连绵,月余方晴,淮淝水暴涨,低洼之地悉成泽国,在北门城墙上可伸手向河中洗衣物,田禾淹没,房屋被淹倒许多。凤阳五月下旬霪雨客水河涨,破堤烂麦,大涝灾重,损失房屋多,民有死伤,七月底退尽,比国民10年水大……颍上自入夏以来,大雨兼旬,山洪暴发,颍淮齐涨,岸溃堤决,全县尽成泽国。而沿淮之赵家集、润河集、秋稼湖、灵台湖等处,屋庐冲没不下5千余户,人畜漂亡无算,无家可归者不下2万余口。”[11]历来尚有一地洪水,一方旱之俗语,因此,民国时期,旱灾亦为非常严峻。
见成都旱灾记载,1936~1937年的“丙丁大天干”致使成都平原山丘大旱。四川于1936年丙子前一年,川中、川东、川北已有不同程度干旱,丙子年旱区扩大到川南、川西一带,全川除成都平原有都江堰水利灌溉外,普遍大旱,受灾人口占全省四分之三以上。1936年丁丑继续天干,许多地方吃水都感困难。龙泉驿东山地区春荒、夏旱、秋涝、冬干,灾害延续至次年,沿龙泉山一百余里,“泉干井涸,田土龟裂”,人称“丙子丁丑大天干”。大邑、邛崃、蒲江民堰灌区迟至农历五月半、阳历7月10日小暑前后始下种插秧。另一次较为严重的干旱发生于1942年,这年干旱使龙泉驿坝丘区连旱,稻谷收成不及七分之一,旱粮损失也在二分之一以上。邛崃西山干旱,水井河断流,秧苗枯死,收成大歉。[10]
民国期间旱灾非常普遍,其中影响较大的旱灾见官方记录的还有:1913年河南等四省旱灾; 1914年四川等三省旱灾;1915年四川省旱灾; 1916年河南等三省旱灾;1919年云南、四川旱灾;1922年湖南旱灾;1926年东北等五省旱灾; 1927年山东等五省旱灾;1931年陕西等四省旱灾……1936年青海等九省旱灾;1937年安徽等十省旱灾;1940年陕西、湖北等旱灾;1941年河南等四省旱灾;1942年四川、湖北旱灾;1945年河北等数省旱、涝灾;1947年河北等数省旱灾、虫害。[5]水旱灾害的强度非常大,破坏力极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上述典型的水旱灾害资料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水旱灾害总体上持续的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强度较大,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二、民国时期政府赈灾措施与政府角色转换
面对日益严重的水旱灾害,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主要包括灾前防御和灾后赈济两种措施。民国北京政府1913年8月颁行了《义赈奖劝章程》,此章程大力鼓励社会力量捐款赈灾,规定捐助资金数额超过一千块大银的团体或个人,皆由大总统依据《褒扬条例》进行褒扬,低于一千元者由地方官员予以奖励,此法大大激励社会力量参与赈灾活动,有助于推进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赈款给奖章程》《赈务委员会助赈奖给章程》相继出台,并具体规定由政府或赈务会对于社会力量参与赈灾的行为进行实质褒彰,如1930年颁行的《办理振务人员奖恤章程》;1931年的《办振人员惩罚条例》与《办振公务员奖励条例》;1932年的《办振团体及在事人员奖励条例》与《办振团体在事人员恤金章程》等。1934年11月,国民政府对某些特殊群体关于赈灾进行明确规定,出台了《公务员捐俸助振办法》,逐步建立了一套包括奖励、惩罚和抚恤等事项的赈灾相关政策,明确相关救灾团体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并完善相关救灾人员的奖惩制度。
1929年和1930年决定发行赈济公债一万万元,并于七月一日起,先发行三千万元,以济急需,其用途,拟暂作如下之支配:(甲)难民救护、运输、收容、给养、配置,及临时发生天灾之救济费用六百万元。(乙)办理采矿、植林、公路修筑、水修工程等,及其他预防灾荒之小规模工程,及各项小工业,小本负贩,经费共九百万元。(丙)难童教养经费三百万元。(丁)难民垦殖经费一千二百万元。[13]1931年底公布了《振务委员会收存振款暂行办法》和《振务委员会提付振款暂行办法》,对赈款的管理做出明确规定,发行赈灾公债是民国政府开辟的一条新的救灾资金筹集渠道。1938年7月1日颁布了《赈济公债条例》,第一条国民政府为赈济难民,扩充生产事业,发行公债,定名为民国二十七年赈济公债。第二条本公债总额国币一万万元,分期发行。第一期债额定为国币三千万元,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发行。其余各期及债额,由财政部于必要时定之。第三条本公债按照票面九八发行。第四条本公债年息四厘。第一期自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一日起算,每年分两次付给,即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日各付一次。第五条本公债还本期间,第一期自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一日起算,定为二十年还清,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各抽签还本一次。每次偿还数目,依次偿还数目,依还本息表之规定,至民国五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全数还清……第十条本公债用途赈济难民及扩充生产事业之详细办法,由赈济委员会商关系部会定之。第十一条本公债之募集,由财政部会同赈济委员办理。第十二条对于本公债如有伪造及毁损信用之行为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治。第十三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14]
民国时期相关赈灾法令法条的制订有利于将传统灾荒救济活动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纳入立法的范畴,使之法治化、制度化;另外通过立法建立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型灾荒救济制度,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灾荒救济活动的法治化,得以推进赈灾活动过程中国家现代化角色转换,有效呈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效果,这是民国政府积极发挥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将赈灾措施法制化正彰显政府职能、政府角色的转换。
进入民国后,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相继设立赈灾机构以保障赈灾工作顺利开展。1913年北洋政府曾在安徽设立官赈、义赈合一的赈抚局。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些全国性影响较大的赈灾机构,1928年成立了“全国赈灾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1930年易名为“赈务委员会”,1945年11月,该会撤销,其职能归并“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其他官方赈济机构有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等。抗战时期,灾荒更显严重,为此,1938年特设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分设七个救济区:以京沪沿线及苏北浙江属于第一区;皖北鲁南属于第二区;皖南及苏浙边境属于第三区;鲁西豫东冀南属于第四区;豫北晋东属于第五区;绥察晋北及陕北属于第六区,豫西陕东办理救护收容运输给养等事项。在卫生防疫方面与内政部卫生署密切联络,在宣传安抚方面,与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随时合作,俾利进行。沦陷区域,则酌托国际慈善团体,或宗教人士,缜密进行。务必于救济之中,宣示中央之德意。暗为维系,以待时机。至收复地区,如晋北、鲁东、鲁南、豫北各县,及绥远蒙旗等,虽地区辽远,交通艰阻,亦均尽量设法。分拨救济费,交由各主管区前往赶速办理赈济,借以抚辑流亡,恢复民力,安定人心,增进抗战力量。[13]也有半官方性质赈灾机构如“中国红十字总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
另外,民国时期,非官方赈济机构也很多,这些机构与团体对于灾荒赈济起了重要作用。其中1921年成立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最为有名,影响力最深,它分别在12个省份设分会,在上海、南京、安徽、江西等地设有事务所。
国民政府在受灾的省份设立农赈局,并设立农赈委员会监督协助。农赈局根据受灾各县的灾情,分出轻重灾害等级,在每个县或者是几个县设立一个农赈办事处,再设立县农村合作社,作为农赈工作的基本团体,最后由此基本团体向灾民提供小本贷款。小本贷款以受灾贫户为对象,尽先贷给其中之衰老嫠孤者。如双流县在1948年5月成立贷款委员会,商定将5000万元之下拨数额存入银行生息,每年6月和12月以所得息金发放给被灾赤贫户,以免放贷还本之累。[10]这种救济措施有利于恢复灾民信心,扶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
全国各地省份相应成立诸多自发性赈灾团体,如河北建立了华北灾振会,它制定了较为详尽的入会章程。华北基督教赈灾会成立后相继开展了一系列赈灾活动。1928年7月,华北灾振会送到捐款内开以华北各省水旱频仍,迭经战事,饥民载道呼号,会门嘱为代募捐款,以资赈济等因,查比年以来华北各省迭遭兵灾水旱等灾,哀鸿遍野,触目伤心。理宜各尽其力,以资救济。更因朱庆澜将军自己牺牲一切,专办善泽,活人无算,此次发起斯会,吾人应予赞助,以救灾荒。慨念灾情奇重,望救孔殷务请广为募集捐款,迅行送会以凭汇交,俾俟振放。[15]1930年7月,发启示函请办灾员乘轮准予减收半价:“迳去岁京直一带水灾之重,向所未有。而文安为尤甚。敝会竭力绵薄,奔走赈务半载,于兹仰赖各机关资助。凡电报,铁路皆准予免费,近以在该县除赈粮留养所等事外,更有兴办堤工,移民垦荒等策。办事人员来往频繁,拟请贵公司于敝会办灾负乘轮者准予减收半价,则灾黎受福无形不止,敝会铭感己也。”[16]
国民政府制定相关赈灾法律法规,设立相应赈济机构,为赈灾提供政治、经济保障。不管是国家的还是社会团体性质的赈灾机构都在经济领域、政治及思想领域,对建构公民社会、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增强国人国家民族意识方面起了催化作用。当然,又因为战争及政治社会环境致使赈灾效果日显式微。1931年安徽特大灾国民政府拨给安徽急赈款30万元,但直到11月还未下发,灾民嗷嗷待哺,死亡枕藉,仅皖北26县即死亡6万余人,其中空待赈济而死的占多数。何以如此?安徽查赈专员张公衡道出实情,“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先将此款归他支配,继则主张办粥厂,后来因为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督促分配此款,陈调元仍假工赈为名扣留不发,因而形成急赈缓办,以致引起公愤,不断上告、请愿”。[17]又如,1945年8月25日,成都金堂县江水泛涨数丈,次年省府拨赈款450万元,按特重灾、重灾两等合计23乡镇,以一与二之比照分配。1947年7月3日至5日大雨,双流县遭洪水。8月,华阳县即发放赈款,重灾每乡1200万元。黄龙乡按各保大小人口比率配给,计发1094万元。双流县政府也实施急赈,赈款数额按灾情轻重分发,共发放赈款555.60万元。但是,在赈银的发放过程中,克扣、挪用、贪污及其他舞弊行为时有发生。如1947年11月,郫县政府配发水灾赈济款1500万元。水灾过后,有的乡镇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县政府又一再催迄,延至1948年元旦。郫筒镇太平永定古城太和、回龙、普兴、龙溪等乡仍未将调查册具报。殊有未合,兹再展现至元月3日。更有甚者,敲诈勒索灾民,四川省有的保甲长苛勒灾民手续费,有的地方税吏乘灾民领取赈款时,跟踪追索旧欠。[18]贪污挪用赈灾款项者为之不少,“……动用积存金之事乃益多发现。1930年蒋阎战争,宋子文特派湖北省财政部特派员陈某,一次即挪用1000万余元(此额或谓为1600万元或谓1200万元,总在1000万元以上)。因之,积存金几倾数流用,此费当然作为军费……后保管委员会因欲由此以肥私囊,而有监督权之省政府亦默不一言,最为可怪。总之,近三年来上下一致地将数千万元之积存金全部挪用为军费,并饱私囊”。[19]
三、结语
灾荒一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邓拓所言“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20]据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就有1,056次旱灾和1,029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出,可见灾荒之何其严峻。[21]面对灾荒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令条文,成立了相应赈灾机构,颁布灾荒政策,采取具体赈灾措施,这些将原来的宗族内部互助、地域性组织赈济、个人捐助等传统赈灾形式有效整合,彰显赈灾过程国家力量、国家责任、政府角色。尽管由于战争及政策具体实施时存在一些弊病,影响赈灾效果,但仍然明显地体现出国民政府在建构公民社会、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增强国人国家民族意识方面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成功呈现其政府角色的有效转换,有效推进民国政府现代化进程。[22]
[1]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2]周秋光.中国慈善事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赖莉云.晚清广西的自然灾害及赈灾政策[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2);赵晓华.清末民初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08,(3);杨鹏程.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J].阴山学刊,2003,(4).
[4]王斌,曾昭伟.论抗战时期的湖南赈灾[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于文善,吴海涛.民国时期皖北的灾荒及赈灾措施[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卜风贤.民国时期农业灾情及其成因[J].古今农业,1999,(2).
[6]川报[N].1923年8月2日(2).
[7]四川日报[N].1923年7月10日(3).
[8]成都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成都市志·地震志[N].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9]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地震资料汇编[N].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10]成都水旱灾害志编写组:成都水旱灾害志[N].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11]安徽地方志办公室.安徽水灾备忘录[N].安徽:黄山书社,1991.
[12]焦润明,张春艳.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C].财政经济(八).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14]潘金生,刘宏懿,张学.中外证券法规资料汇编[N].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15]天津市档案馆档案[Z].档案号:128-3-006207-23.天津总商会.为募集华北水旱灾捐款致茶叶等商函.
[16]天津市档案馆档案[Z].档案号:J54-2-2649.华北基督教赈灾会.华北基督教赈灾会函请办灾员乘轮准予减收半价.
[17]皖灾周刊第三号[N].1931-11-21.安徽地方志办公室.安徽水灾备忘录[N].安徽:黄山书社,1991.
[18]振务月刊(四川)[N].1937-6.
[19]陶直夫.1931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N].新创造.第1卷第2期:13-14.1932年5月。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C].126-127.
[20]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1]新华社记者驯水记[N].人民日报,1974-10-16.
[22]刘达禹.优化国家控制:在秩序与活力的平衡中寻求稳定[J].东疆学刊,2013,(3).
Research of the Disaster Relief Measures and Government Role Transform 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LAI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Chengdu University,Chengdu,610106,Sichuan,China)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though lasting only thirty years,was constantly stricken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man-made calamities,the so-called“impoverished 9 years of10”,amongwhich the flood was themost serious.In the face of famine,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took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it.The relevant relief organizations were established,policies during the Disaster Time promulgated,and specific disaster reliefmeasures adopted.Despite the unsatisfactory relief effect,affected by the war and the disadvantag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the leading role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acted had beenmanifested.It presents an image of governmentwith sense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role.It also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state identity and national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disaster relief;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K05
:A
:1006-723X(2015)03-0136-05
〔责任编辑:李官〕
赖静,女,成都学院政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