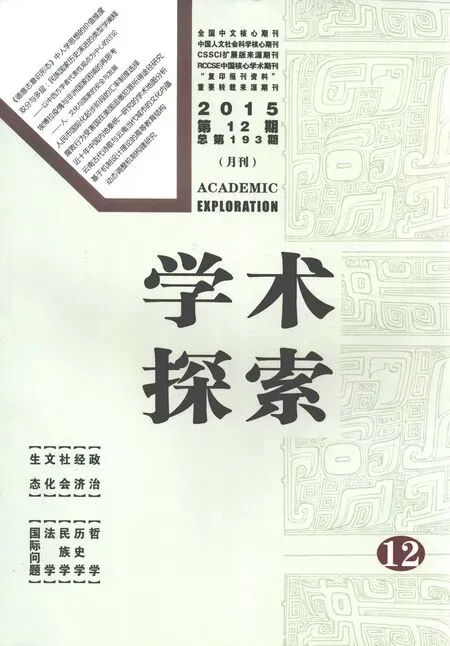新《食品安全法》的刑事责任优先
顾永景
(盐城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新《食品安全法》的刑事责任优先
顾永景
(盐城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新《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全面、严格的法律责任,更树立起刑事责任优先的法律理念。刑事责任优先是对刑法谦抑原则的相对突破。食品安全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与某些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表现一致、特征相符,导致实践中出现行刑不分、以罚代刑的责任混淆,亟须甄别两种不同责任承担方式。在此基础上,坚持刑事责任优先的法律理念,需要在理念层面上采纳“刑罚优先适用说”,在操作层面上完善行政违法行为与食品安全犯罪的执法、司法案件相互移送和结果互认,整体上实现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规制。
食品安全法;刑法;刑事责任优先;刑法谦抑性;衔接
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因其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大了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而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1]笔者认为,仅就其法律责任的规定而言,即包括有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经济法责任,详尽程度诚为同类立法所少见,而在各种法律责任的关系方面甚至体现了“刑事责任追究优先”的精神。[2]本文在厘清《食品安全法》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对刑事责任优先对刑法谦抑性的突破及相关问题予以探讨。
一、《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
相较于旧法,新《食品安全法》为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达到“重典治乱”的监管目的,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规定了最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
(一)刑事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条为附属刑法,旨在表明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触及刑事责任的前提必须首先违反《食品安全法》之规定,由于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的具体特征在《食品安全法》中已有规定,该法条便不再予以表述。同时,强调该违法行为必须构成犯罪,需要依据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款加以确定。譬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制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较为广泛,涉及食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监管等许多环节。而《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仅限于生产、销售行为,对食品流通过程中的运输、储存等行为没有详细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之下,似乎难以依据刑法分则之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站在刑法解释学的立场上,举凡涉及食品运输、储存等重大违法行为,只要符合刑法总则关于犯罪的一般规定(《刑法》第十三条等),亦可构成犯罪。首先,因为食品运输、储存等重大违法行为与生产、销售行为的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均可达成一致(下文详述),满足“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本质要求。其次,思考刑法概念,须以刑法目的为出发点,而刑法目的在于保护法益。[3](P342)对《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生产”“销售”概念的理解,完全可以基于保护法益即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通常认为,本罪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但恰如张明楷教授对毒品犯罪法益的论证,将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作为食品安全犯罪的保护法益,不能说明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范围。*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说食品安全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4](P190)[5](P372)的需要做目的解释(理由上)和扩大解释(技巧上)。前述两罪的主观方面均为故意,即排除了过失犯罪之可能。而故意运输、储存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始终伴随生产、销售而产生(获利的犯罪目的使然)。若生产者、销售者本身实施运输、储存行为,则运输、储存或为其预备行为,或为其结果行为,本身可以涵摄于生产、销售行为之中;若运输、储存行为的实行者并非生产者、销售者,且明知相关食品存在安全问题,则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十三条中使用“法律”而非“本法”一词,亦照顾了适用《食品安全法》等附属刑法规定的合法性。据此,可以认定运输、储存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等重大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构成《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此外,广义的食品安全犯罪还涉及《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一百四十九条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的法条适用原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及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第四百零八条之一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等规定。
(二)行政责任
《食品安全法》详细地规定了不同主体违反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总体上可分为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管主体的行政责任(行政处分),前者尤其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规制措施,无疑是法律规定的重要内容和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食品安全法》针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财产等。*本文将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处罚措施作为经济法责任的承担方式予以讨论。有学者提出,责令改正也属于《食品安全法》上的行政处罚,并认为其立法本意是在不影响被处罚者继续开展正常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情况下实施的,从客观上看,应该是违法事实与情节较为简单和轻微,对社会和他人没有造成太大危害,采取“责令改正”符合“过罚相当原则”。[6](P200)笔者认为,尽管《食品安全法》中共有6处使用“责令改正”表述,但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处罚。首先,《行政处罚法》并未将责令改正作为有名的行政处罚种类加以规定;*《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其次,责令改正本身不带有惩罚性,而更多具有纠正违法行为之意图;再次,责令改正往往作为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或同步要求,限期不改正的,则意味着需要承当更严厉的行政处罚后果。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因此,《食品安全法》最轻的处罚措施即为警告,通过谴责、告诫等负面评价,对违法者予以警示。次之是罚款,包括绝对数额罚款和货值倍数罚款,其适用标准一般由监管机关合理裁量。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而没收财产,则是监管机关依法将违法行为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违法生产经营工具、设备、原料等予以强制性剥夺并收归国有的处罚方式,主要针对违法行为性质较为恶劣的情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拘留”,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拘留,应当理解为《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六项中的行政拘留,是由公安机关依法对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加以短期限制的一种惩罚方法,较之前述声誉罚(警告)、财产罚(罚款、没收财产)而言,更具有严厉性。
(三)民事责任
食品安全的民事责任主要在于食品安全侵权责任。其既符合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特征即食品存在缺陷、缺陷食品造成了损害事实、缺陷食品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包括侵害主体的多元性、侵害客体的双重性、侵害后果的社会性、侵害行为的间接性。[6](P147)笔者认为,应当将实际损害赔偿作为食品安全民事责任承担的基本原则,而将惩罚性赔偿纳入食品安全经济法责任予以特别规定。事实上,《食品安全法》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分别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不同承担方式,而且,前者责任主体范围不限于食品生产经营者,还包括编造、散布虚假食品安全信息的媒体及相关责任人员(如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同时,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首次明确了提出食品安全损害赔偿的“首付责任制”,该条款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付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此外,该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对网络食品经营做出了具体规定的同时,其第二款中关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违法责任同时也体现了首付责任制。这实质上是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的具体落实,最大限度便利消费者的追偿得以实现,有效避免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责任推诿与赔偿延误。
(四)经济法责任
通常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指人们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主要包括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经济行为方面的责任、经济信誉责任、经济调节管理行为责任。[7](P69~73)经济法责任突出表现为惩罚性赔偿和业务资格限制。其中,“惩罚性赔偿是指由于被告所犯下之侵权行为蕴含有超出一般的放任、故意或欺诈等极端恶劣性质,故而法院会在给予原告补偿性赔偿之外,判处被告必须另行赔付给原告的一笔远超其实际损失的金钱赔偿,以求实现惩罚被告、震慑恶行以及抚慰原告等目的。”[8]如前所述,《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主体仅限于食品生产经营者,如其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这里的十倍价款、三倍的赔偿金及一千元中超出赔偿金额的部分,即是惩罚性赔偿。本条源自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并将十倍价款的定额赔偿改为三种赔偿方式的选择适用,有利于消费者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索赔方式,消费者即使花钱买几元钱的食品,一旦该食品被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也可获得一千元的赔偿金,显著增强了惩罚性赔偿的灵活性、威慑性。业务资格限制是指限制或者剥夺各类主体从事食品生产、经营、贮存、运输、装卸、检验、认证、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网络食品交易等活动的资格和能力,如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及五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此类经济法责任在《食品安全法》中分布广泛,值得关注的是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一年内累计三次因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外处罚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本条明确了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从承担责令改正、警告等行政责任(行政处罚)向承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经济法责任的具体条件,尽管其思想渊源或许来自刑法上的累犯理论,但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监管机构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一种妥当性进路。此外,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实质上是资格罚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由于我国《刑法》上相应的资格刑的缺失,使得该资格罚呈现出高于或严于刑罚的不正常现象。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禁止令”的规定,具有资格刑的某些特质,但由于仅适用于管制犯和缓刑犯,且只在管制执行期间和缓刑考验期间适用,急需通过进一步修改刑法以实现《刑法》与《食品安全法》在规制犯罪主体能力上的衔接。
二、刑事责任优先与刑法谦抑性的突破
刑法谦抑性(The principal of compress and modesty)本是现代刑法的应有之意,自20世纪末由日本*日本学者代表性观点,如平野龙一教授认为刑法谦抑性在于刑法的补充性、不完整性和宽容性。[9](P21~22)引入我国刑法研究领域之后,一方面,提供了对严刑峻法传统和刑事司法简单粗暴的反思性、批判性工具,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当下人权保障高涨的发展现实和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刑法谦抑性理念得到了我国刑法学界的普遍认同,将其理解为着眼于限制刑法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适用刑法的必要性,强调刑法的最后手段性。*我国学者代表性观点,如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10](P353)*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11](P289)易言之,对于任何侵犯国家、社会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鉴于其危害性有限,如果能在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部门法框架内进行规制,就不必要也不应当通过发动刑法的方式予以制裁。一些学者进而提出了“非罪化”“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主张,以规定免刑制度和免除处罚情节、运用非刑事制裁措施、实行保安处分为路径,弥补刑法功能之不足,限制刑罚之适用。[12~13]以此为指导,在我国执法、司法实践中,不乏以行政法(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及行政处罚替代刑法及刑罚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谦抑性的背景下,对刑法的克制往往被过分强调,而忽略甚至歪曲了刑法应当起到的积极作用,导致刑法虚置。
笔者认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是最广泛的,刑法的强制性是最为严厉的,将“非罪化”“非刑罚化”理解为当代刑法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不妥当的。相反,正是基于刑罚的严厉性和威慑力,其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金融秩序等重要领域的适用,日益得到各国立法的重视和支持,*日本于1970年制定了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罪处治法,全面确立了对危害环境行为的刑事制裁制度;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将违反清洁水法、资源保护和再生法等犯罪行为从轻罪纳入重罪。[14](P134~137)生态刑法、经济刑法、金融刑法等专业刑法领域也得以深入拓展,这些都表现出对上述重要法益的突出保护正在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共识。如果刑法的谦抑性是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的纠正,那么在当今风险社会之特征愈加明确的情况下,保持刑法适度的张力,进行积极和富有前瞻性的刑法调控,同样也是一种理性和务实的选择。[14](P134~137)由此,一种全新的刑法理念得以展开,即通过对现代生活的直接介入,体现刑法最高等级法益保护之价值。现代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证明,当社会发展使得国家认识到一种特定的利益对社会具有至高重要的意义时,不管这种利益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时代是如何无关紧要,例如,著作权、信用、环境、食品、药品,甚至家庭暴力,国家都有可能依据宪法使用最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加以禁止,为这些利益提供最高等级的保护。在人民民主的国家中,刑法“谦抑性”的那种自下而上乞求式地限制刑法保护的思想已经过时,而刑法“辅助性”的这种自上而下民主式地分配刑法保护的思想正在高扬。[15](P2)《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与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尚不构成犯罪的”表述以及第一百二十一条中食品安全案件移送的规定,实质上就确立了刑事责任优先的法律理念。由此,在刑事责任优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食品安全法》与《刑法》相关规定的有效对接,得以确立完善而稳妥的食品安全调控体系,达到重点法益的优先保护与刑法谦抑性品格的常态维持。
三、食品安全犯罪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比较
广义的食品安全犯罪除了《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外,还涉及第一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一百四十九条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的法条适用原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及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第四百零八条之一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等规定,本节主要以《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为例,对食品安全犯罪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予以比较分析。
(一)食品安全犯罪构成
《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直接规定集中在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本文认为,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基本相同:犯罪客体都是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个人和单位,都可构成犯罪,至于个人和单位是合法(有经营许可)的生产、销售单位还是非法(无经营许可)单位,在所不问;犯罪主观方面都只能是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两罪均不以犯罪目的为构成要件,但行为人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牟利。
而两罪的区别主要在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象范围、行为方式及既遂形态等的不同。一是对象范围不同。两罪的对象分别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和“有毒、有害的食品”,具体到《食品安全法》,都是指其第三十四条所规定*《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五)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六)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七)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八)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九)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十二)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所谓食品,概言之可食用之物。《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发布的178/2000号指令也规定,食品包括饮料、口胶糖和其他任何用来在食品生产、准备和处理中混合的物质(包括水),但不包括饲料、活动物、未收割的作物。而可食用性又突出表现为食用安全性。食品承载的价值丰富多元,包括安全、营养、感官愉悦、传统等,但无论如何安全首当其冲,特别是在风险不确定性与科学不确定性并存的当下。[16]就程度而言,“有毒、有害的食品”强调食品的“毒害性”和“非食源性”,而“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仅仅强调“不安全”,但对此又不宜绝对化。两类食品都可能存在毒害性,但前者的毒害性多来源于食品本身的被污染,后者则多来源于生产者、销售者的直接掺入,如白酒由于生产环境不合格,而造成酒水变质后继续生产就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而直接向白酒里掺入农药就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17]就法条关系而言,两罪存在竞合,当二者竞合时,以重罪处罚,通常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理。二是行为方式不同。《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除生产、销售行为以外,特别强调有在食品中人为“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第一百四十三条则只要求单纯的生产、销售行为即可。三是犯罪形态不同。第一百四十四条是抽象危险犯或行为犯,只要实施本罪的行为即构成犯罪;第一百四十三条则是具体危险犯,除实施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行为外,还要求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具体危险。
(二)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甄别
通常认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系典型的法定犯,客观上表现为违反行政、经济管理法规的犯罪行为。而《食品安全法》“法律责任”承担的前提即是“违反本法规定”。因此,某些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与食品安全犯罪在行为表现上存在一致性。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情节在行为方式上即满足《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要求;又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中“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的情节,也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特征。上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规定多有重合,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区分食品安全行为违法行为与食品安全犯罪:(1)从客观方面而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判断其罪与非罪的标准即为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品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是否“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及“后果特别严重”等。这里所说的严重程度、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后果,一方面,有赖于最高司法机关做出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参见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另一方面,也可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结合相关指导性案例,*例如,2014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四批指导性案例,选择柳立国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为办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提供业务指导。考察案情后做出“其他食源性疾病”“其他严重情节”的预判。(2)从主体而言,存在多个违法行为人时,主犯如果情节较轻,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则从犯、胁从犯可视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适用《食品安全法》处罚。(3)从主观方面而言,食品安全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而认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则无须考虑其主观过错,过失也可以构成违法。如有食品生产厂商基于增加食品营养成分的目的,在卤味食品中添加按照传统不作为食品的中药的行为,即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四、法律责任承担与衔接
(一)法理上的衔接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一旦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就会发生食品监管行政处罚与刑罚适用竞合的问题。实践中,经常出现以罚代刑,甚至有意限缩刑法实际适用的范围与场合,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关于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问题的解决,理论上大致有三种思路:(1)选择适用,即行政处罚与刑罚只能择一适用。(2)附条件并科,认为二者竞合时可以并科,但在执行任何一个后,没有必要时,可免除执行另一个。(3)合并适用,既适用刑罚,又适用行政处罚。[18](P21)其立论依据在于行为的双重性(既违反行政法又触犯刑律),必然导致结果的双重性(既有行政责任又有刑事责任),对同一行为进行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
本文认为,尽管通常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罚”多在行政法领域讨论,但广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针对同一主体的同一违法(犯罪)行为,只能作出一种法律性质的处罚措施”。理由如下:(1)处罚行为的公权性。无论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还是审判机关做出的刑罚,都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具有法定性、权威性和强制力。(2)处罚措施的替代性。两类处罚措施多有共通、功能相似:刑罚上的罚金与行政处罚上的罚款都属于财产罚,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与拘留都属于自由罚,而且前者对后者多具有替代性,做出罚金,即无须另行罚款,因为罚没款项都归属国库;做出有期徒刑等,即无须另行拘留,因为犯罪行为人的自由已被束缚;而死刑对于自然人而言更具有终极性,一旦执行,即无法另行发生任何其他处罚;即使如资格罚、声誉罚等经济法责任,一旦刑法上对同一主体予以评价,其消极影响自然及于经济法责任领域,如对食品生产者处有期徒刑、拘役,即天然具有警示效果,无须再做警告之处罚。(3)处罚目的的一致性。与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权益和实现救济不同,责任承担上多具有补偿性;刑罚与行政处罚二者目的都是代表公权力对不法行为予以制裁,责任承担上多具有惩罚性。综上,笔者提出“刑罚优先适用说”,即在符合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刑罚较之行政处罚应优先适用。
(二)操作上的衔接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均将“尚不构成犯罪”作为行政处罚的前提,易言之,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首先要监管部门进行责任判断,如果涉嫌犯罪的,就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如果尚未构成犯罪,就由监管部门按照《食品安全法》处理。为了实现操作上的衔接,《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发现涉嫌食品安全犯罪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在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和监察机关,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公安机关商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环境保护等部门提供检验结论、认定意见以及对涉案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等协助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提供,予以协助。”当然,实践中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监管部门适用行政处罚后才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此时,监管部门应立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之前做出的行政处罚并非当然无效,而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由审判机关在宣告刑罚时,将行政罚款折抵罚金刑,将行政拘留折抵相应的刑期。笔者认为,贯彻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后一种情况只能作为食品安全执法、司法活动中纠偏之举,常态、规范的法律适用仍应在准确把握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做出,由此整体上实现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规制。
[1]央视新闻.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通过[EB/OL].[2015-08-22]http://m.news.cntv.cn/2015/04/24/ARTI1429859409507491.shtml.
[2]许成磊.新《食品安全法》体现“刑事责任追究优先”[EB/OL].(2015-04-24)[2015-06-15].http://www.ce.cn/cysc/sp/info/201506/15/t20150615_5646446.shtml
[3]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马克昌.百罪通论(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廖斌,张亚军.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7]漆多俊.经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8]李响.食品安全诉讼当中的惩罚性赔偿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3,(4).
[9]平野龙一.现代法II——现代法与刑罚[M].东京:岩波书店,1965.
[10]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2]梁根林.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J].现代法学,2000,(6).
[13]刘明祥.非刑罚化——我国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J].法学,1993,(6).
[14]刘媛媛.刑法谦抑性及其边界[J].理论探索,2011,(5).
[15]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M].王世洲,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6]孙娟娟.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再认识[J].财经法学,2015,(3).
[17]赵秉志.刑法分则要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18]汪水清.行政处罚运作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黎 玫〕
On Criminal Liability Priority inTheNewFoodSafetyLaw
GU Yong-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Yancheng Normal University,Yancheng,224051, Jiangsu, China)
TheNewFoodSafetyLaw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strict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establish the legal principle of criminal liability priority. This is a relative breakthrough on the principle of modesty in criminal law. Food safety crime is a typical legal crime, whose features are in line with some food safety illegal activities, thus leading to confusion of civil liability and criminal liability in practice. Therefore we need to identify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To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criminal liability priority, we should adopt the theory of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penalty; and in practice we should improve the process of the convergenc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cases.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illegal food safety activities and crimes be achieved on the whole.
TheFoodSafetyLaw;criminal law; criminal liability priority; the modesty of criminal law; cohesion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项目资助(2015YYHZ018)
顾永景,男,盐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刑事、法律实务研究。
DF613
A
1006-723X(2015)12-00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