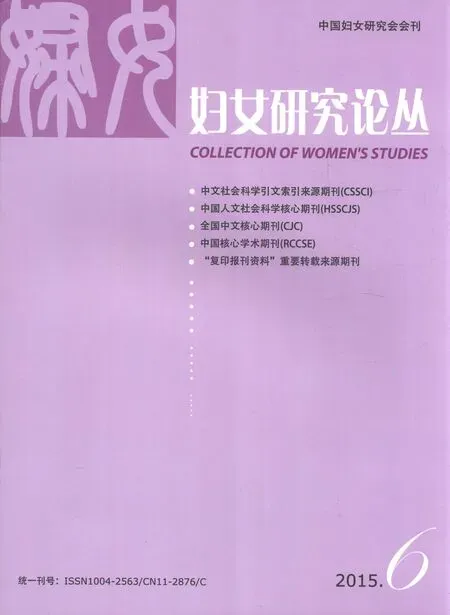女性存在的改写
——论左拉笔下的百货商场对女性社会身份的再造
杜莉莉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女性存在的改写
——论左拉笔下的百货商场对女性社会身份的再造
杜莉莉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左拉;巴黎;百货商场;消费;女性社会身份;妇女乐园
左拉的《妇女乐园》借助清贫的外省女孩黛妮丝在巴黎百货商场工作的经历,书写了一曲步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赞歌。新时代的轰鸣召唤着女性的参与和回归。文章选取小说中的女性作为整体研究对象,探讨了19世纪巴黎百货商场引领的商业变革如何在消费狂欢的表征下对女性群体进行集体洗礼和社会身份的再造。
Abatracts:The Ladies'Paradiseby Zola is a poem of modern life by depicting what a poor provincial girl named Denise experienced in a Paris department store.The new era calls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action.This paper studies how commercialization led by department stor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oke the boundaries of the tradition and re-forged the identity of the female group by the appearance of consumerism.
左拉的《妇女乐园》问世于1883年。小说的展开紧密围绕着女主人公黛妮丝这个清贫的外省女孩与巴黎最奢华的百货商场妇女乐园的命运纠葛。在历经了各种不堪的劳苦与委屈后,黛妮丝最终以高雅的人格和卓越的见识在妇女乐园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了老板慕雷的爱慕,实现了事业和爱情上的双丰收。情节跌宕而结局圆满的爱情故事自然为小说的可读性增色不少,但却远非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法国,为巴黎百货商场的诞生及其日后的巨大成功提供了硬件保障。与此同时,传统店铺在现代零售模式的冲击下全面崩盘。时刻对社会保持深刻体察的左拉,敏锐地捕捉到商业革新对传统世界的震撼,并决定以此为题创作一部小说。为了更加真实还原社会现实,左拉采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事先多次走访了世界第一家百货商场——波马舍(Le Bon Marché,创建于1852年)以及与之齐名的卢浮百货(Les Grands Magasins du Louvre,创建于1855年),总共留下了长达71页的手稿。1882年,在小说创作结束前夕,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提道:“《妇女乐园》讲述了一个像波马舍或卢
浮百货这类大型百货商场的诞生是如何震动、变革法国商业的故事。我把百货商场与小型商业的对决以及后者被逐步吞噬的过程展现出来。”[1](P329)由此可见,《妇女乐园》是一个社会进程的宏大叙事、一种时代精神的文本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百货商场的现实意义不单单停留在商业革新这个经济层面。借助奥斯曼公爵改造巴黎市貌的东风,它的出现打碎了城市原有的空间格局,重塑了市民的生活版图,使巴黎在城市功能、建筑风格、文化艺术、休闲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副超前之态。除此之外,百货商场之所以成为法国现代社会的先锋之一,还与女性群体密不可分。是它率先发现并挖掘了一直默默耕耘于家庭生活的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是它开创性地揣摩、分析了女性消费的“阴性特质”①根据小说对女性消费者的塑造,这里的阴性特质主要指在消费层面上,女性的消费倾向较男性而言,更容易直接受到感官体验(如视觉、触觉、嗅觉、情感等)的左右。例如妇女乐园实行的各种促销手段,美轮美奂的商品展示并允许顾客近距离观赏、触摸、试用商品,奢华梦幻的商场装修,周到殷勤的销售服务,等等,都深深吸引了女性顾客;这里的女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感性消费。、心理驱动以及行为范式,成功将女性打造为一支现代经济生活的消费大军。此外,作为城市新生的公共空间,百货商场还为19世纪女性参与公众生活、改变自身命运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百货商场不仅是女性消费的乐土,还是女性自我实现的乐土。左拉将小说取名为“妇女乐园”,与百货商场这一明一暗两个现实寓意完全暗合。然而,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女性为何会成为百货商场力争的销售对象?她们在这个空间里消费的诉求从何而来?百货商场如何改变了她们的消费行为和社会生活?女性消费的行为模式传达了何种信息?百货商场启用大量的女性职工对当时的社会有何现实意义?所有这些问题都引领我们选取左拉小说《妇女乐园》中的女性人物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以便考察19世纪的百货商场是如何对女性这一群体进行集体洗礼和社会身份的再造。
一、欲望的制造与现代女性消费群体的出现
小说《妇女乐园》为世人揭开了百货商场大获成功的秘诀,即运作模式上的突破。工业革命确保了产品的大批量生产,百货商场在明码标价下实行薄利多销的原则,通过加速物流提高资金的回流,从而以基数大、速度快的方式实现利润的激增。但是,对于能够将大量不同行业的商品汇集一堂、既能保证供货量又不断推陈出新的百货商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找到一批为数众多、具备消费潜力而又热衷时尚的消费者进入商品流通环节,快速消化应季产品。波马舍的创办者阿里斯蒂德·布西科(Aristide Boucicaut,1810-1877)凭借之前打工时多年积累的销售经验,颇具前瞻性地把目光转向了女性。从此,女性在时代的召唤下踏入了崭新的社会疆域,而这其中的缘由与当时女性在公共话语中的形象不无关系。
19世纪的法国社会,虽然经过大革命的震撼,在立法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有关男女不平等的思想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这一时期,法国在科学、医学以及人类学领域的探索研究与法兰西帝国在海外的殖民遥相呼应,在将种族歧视和偏见植入公众舆论的同时,继续强化了女人劣于男人的错误认识。“在天主教和医生的声援下,政府首脑和法学家们视女人不同于男人,认为她们缺乏男人身上所具备的某些能力,特别是思考能力。”[2](P20)更有甚者,如法国医生、解剖学家兼人类学家保尔·布罗卡(Paul Broca,1824-1880),就声称女性自身在身体和智力上的劣势导致了她们的大脑要小于男性的大脑[3](PP155-241)。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依附于科学研究的鼓吹,在当时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偏见,女人被贴上了感性、冲动、盲目、脆弱、易受操控、意志力薄弱的标签。1847年,曾有一位法国企业家如是说:“女人没有敏锐的头脑”“她们天真地相信自己读到的东西”“当她们逛薇薇安大街的商店或在商业拱廊的玻璃橱窗前流连时,总是通过想象或眼睛占有所有陈列出来的漂亮东西……”[4](P41)左拉就在小说中安排了多处女性疯狂抢购的场景,与当时公共话语对女性形象的意识操控相契合。左拉的妻子亚历山德琳(Alexandrine)本人也是百货商场的忠实消费
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为左拉的创作提供了女人的独特视角和切身感受。因此,左拉塑造的女性顾客可信度很高,她们绝不会毫无顾忌地立刻释放自己的消费热情,而是会在一番纠结、挣扎中寻找各种理由试图打消内心不断膨胀的欲望,如价格偏高啦,材质不够结实啦,大小款式不太合适啦,预算有限啦,等等。只可惜,纵然心中也“暗怀戒惧,怕被如此奢华的洪水捉了进去,而又有不可抗拒的欲念要投身下去把自己毁灭掉”[5](P89)。想尽办法激起女人的欲望就是百货商场的高明之处。小说男主人公慕雷,在不断大胆扩张业务之际,果断坚持用小惠乃至不惜亏本出售某种商品的手段作为诱饵,因为他深信女人的欲念一旦被激发便会失去理智、无所顾忌地掏空自己的钱包。正如他在试图说服合伙人亏本销售一种名叫巴黎幸福的布料时所分析的那样:
“在这样东西上我们损失几生丁,我是十分愿意的。以后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女人都吸引过来,如果我们用小惠掌握住她们,让她们站在我们大堆的商品面前,受着诱惑,疯狂的购买,毫无计算地倒空了她们的钱包,这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最要紧的,我的朋友,是要燃起她们的热火,这样就必须用一种商品骗住她们,轰动一个时期。以后,你可以卖别的货物像任何人家一样的贵,而她们仍然相信你家的东西卖得便宜。”[5](P33)
如果把当时女性在某些方面逊于男性或无法胜任社会工作归咎于阴性特质的主观臆断或偏见的话,那么在消费层面上,这些阴性特质恰恰为现代商业征服女性消费群体提供了一定的依据。19世纪的百货商场利用了当时社会对性别所进行的意识操控,开创性地揣摩、研究了女性消费的心理驱动和行为模式,带来了一场“量身定做”、全新刺激的购物体验乃至身体经验。通过制造欲望,百货商场也制造了一个崭新的、顺应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需求的消费群体。因为女性最终会说服自己跟随心愿,一买为快。欲望的决堤冲破了理性的枷锁,给予了女性在身心上的双重震撼。左拉在文本里频繁使用类似“狂热兴奋”“面红耳赤”“血肉颤抖”这些近乎情欲的词汇,描写女性顾客面对商品诱惑时的不能自持。此外,对于少数女性顾客来说,情绪上的欲罢不能甚至还极端异化为偷盗癖。“虽然她满口袋装着钱,可是她还是要偷,为偷而偷”[5](P367),因为重点不再是占有,而是占有的方式是反常理的违禁手段,它触发了一种堪比乃至超越肉欲的快感与刺激,成为一部分女性追逐存在感与满足感的病态希冀。
二、意义多重的女性消费诉求
单凭欲望不足以支撑一个消费群体的形成,消费实力以及消费诉求必不可少。19世纪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要数新兴资产阶级家庭的主妇们,事实上她们也是百货商场最主要的支持者。由于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无法像传统贵族阶层享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急需找到一种可以帮助其确立阶级身份、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巴黎最初几个百货商场的创建者,如波马舍的布西科、卢浮百货的肖夏尔(Alfred Chauchard,1821-1909),尽管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劳动阶层的出身使他们在有生之年没能得到符合世俗规范的礼遇和认同:“没有一个人是巴黎工商会或巴黎商业法庭的成员。”[6](PP53-70)可见,新兴阶层社会身份的确立和被接受绝非易事。然而,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消费社会的前奏,“消费社会改变了以往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之间相对固定的关系,消除了生活方式选择与社会地位选择之间的区别”[7](P104)。消费便成为一个阶层自我彰显、自我认同并与其他社会阶层靠近或疏离的渠道,它暗示了一种社会结构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把社会中的人进行分类,商品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传递了人们相互的关系”[7](P29)。而根据托斯丹·邦德·凡勃仑(Thorstein B. Veblen)的“有闲阶级”理论,如果想赢得社会的尊重,仅拥有财富或权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出相应的证据[8](P36)。于是,被他称为“炫耀式消费”的实践,便成为有闲阶层的标志之一。对于新兴资产阶级来说,经济上的优势取代了政治上的短板以及无法改变的社会出身,通过向公众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主动选择靠近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来增强身份认同并提高社会声誉。由于男主人们终日忙于事业,“炫耀式挥霍”的任务就自然而然由他们的妻子承担:物质生活的富足以及社会生活的赋闲,使得主妇们有合理的借口、一定的资金以及充沛的时间精力徜徉在百货商场这个专门为女性发明的世界里,以便为她们各
自的家庭树立一个优越阶层的社会形象。就这样,“消费本身也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替代”[9](P185)。
尽管凡勃仑关于有闲阶层的女性消费主要是为了丈夫、为了家族荣誉而进行“炫耀式挥霍”这个理论有一定的道理和现实依据,但是他忽略了女性在这个看似为家庭义务的“挥霍”中扮演主动角色和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可能性。百货商场彻底革新了传统的女性消费,使之不再是一件必办的家务事、一个繁复冗长的体力活,而成为一种紧扣时代脉搏、充满新鲜刺激的乐趣。女性挣脱男性、家庭的传统情境,自行斟酌买还是不买,为谁买或者买什么、买多少、何时买。这些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却为女性的个体独立和社会身份的再造提供了一个突破口。曾有心理学家表示,“Shopping是人类了解周遭世界并发展自我人格的最初几种方式之一”[10](P22)。《妇女乐园》里出现的重复性消费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女性服饰用品上:装饰花边儿、手帕、领带、纽带、面纱、布料、手套、帽子、内衣、成衣,等等。这说明:一方面,主妇们期望逐渐向社会潮流引导的理想化女性形象靠近;另一方面,女性也开始重视自身的精神需求,凸显个人的风格与品位。同时,女性在百货商场获得的畅快淋漓之感还使得消费对象从之前的生活必需品逐渐转化成满足欲望的时尚品和奢侈品。物品的使用价值转移到具有符号功能的交换价值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时尚产业也随之诞生了。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在对时尚心理所做的社会学研究时分析指出:“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11](PP94-102)。小说中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见什么买什么的玛尔蒂夫人,最后把当中学教员的丈夫都拖垮了,这显然不是为维护家庭的社会声誉而进行炫耀式挥霍。尽管玛尔蒂夫人无休止的消费对于她的家庭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她本人而言却是一种自我实现、个体建设的途径。
然而,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消费,百货商场成功吸引女性走出家门这件事本身,就是意义深远的社会改良。由于当时的公众偏见认为女人的脆弱决定了她们的附庸地位,女性只有在男人的指引和保护下才能立足,“就好像她们的身体需要紧身胸衣的支撑一样,她们的精神同样需要被看管、被指引以避免胡思乱想和无所顾忌……”[2](P20)。女性的活动范围和生存意义仅局限在或作为妻子或作为母亲的个体家庭单位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法国中上层家庭的女性基本上与世隔绝,与社会生活的交集非常小。偶尔出门还须有男性家庭成员的陪伴才算是符合身份的得体做法,而且所去的地方常常限于像教堂、朋友家之类的狭小范围。衣食无忧的安逸和足不出户的封闭,无形中瓦解了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属性与独立。随着19世纪巴黎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百货商场,像世界博览会、画廊、图书馆等文化休闲场所一样,也逐渐成为被世俗道德伦理所认可的、女人可以单独出入的公共场所[12](PP56-91)。就这样,女性慢慢从家庭束缚中脱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而百货商场正好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一举多得的日常机会实践这迟来的社会归属:在满足家庭或个人消费需求的同时,还能体验城市公共空间、参与社会生活、亲历现代进程,顺便还可以打消丈夫们对为妻者离家的忧虑(原来她们是去买东西而不是红杏出墙!)。至此,女性的消费诉求也逐渐从一个必办的家务事,质变成转变自我的实践和休闲体验;女性也自然加入了城市“漫步者”(flâneur)的队伍,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践行者,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公众审视的对象。
三、女性消费体现的社会分层
不管是出于“炫耀式挥霍”的义务还是纯粹为了满足一己之欲,走出家庭的女性所购买的商品,都建构了一个有关她的现实,体现了她对社会、对自我的认知。“奢侈品的大众化”(la démocratisation du luxe)在给予女性选择权和决定权的同时,无形中还向社会透露了她的出身教养以及审美情趣。比如,小说男主人公慕雷的情人——优雅的戴佛日夫人,出身上流社会家庭,花钱不眨眼,虽然同样热衷在妇女乐园制造的梦幻仙境里徜徉,但她“仅仅买某些物品,如手套、帽袜、各种粗内衣等等”[5](P67)的小物件和类似象牙制品的奢侈品。因为在当时的上流社会,还残存着过去贵族量体裁衣的传统做法;而材料昂贵的奢侈品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阶级品位的标志,其
符号价值则大大超越了本身的实物价值。因此,女性的消费行为最终反作用于女性自身,同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一起成为社会快速判断一位女性出身门第和社会地位的依据。正如妇女乐园的售货员,都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丝绸部的雨丹,扫一眼客人的着装、样貌就能推断出她的购买力从而锁定自己的服务对象:比如“这位太太满脸雀斑,头戴一顶黄帽子,身穿一件红衣服,雨丹立刻就看出来这个女人不会买什么东西。他急忙缩下身子躲在柜台后面,假装系鞋带”[5](P82)。店里最受欢迎的顾客之一是一个被销售人员集体称为“漂亮太太”的金发美女,因为“她总是买很多,叫人把东西放到她的马车上,然后就走。她身材高大,态度风雅,打扮得非常漂亮,像是很有钱,而且是属于最上等社会的”[5](P83)。
可是,不同于上流社会中那些家道尚未没落、依旧养尊处优的贵妇们,依靠丈夫辛勤劳作的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往往会具备一种精打细算的务实品质,她们更容易受到减价商品的蛊惑或者想尽办法寻找实惠。她们不会像戴佛日夫人那样,任性地为一个25法郎的扇面去装配一个200法郎的刻花象牙扇子骨。因为同样的成品也就卖到120法郎,在百货商场更是不会超过90法郎。经常与戴佛日夫人一起喝下午茶或在妇女乐园购物的夫人们,都有着中小资产阶级主妇的消费风格。布尔雷德夫人,尽管丈夫身居财政部次长的位置,她本人也出身旧式的资产阶级家庭,却“具有既聪明又实际的小市民的眼力,一直走向便宜货的地方去……给自己节省下大笔开销”[5](P67);为了补偿在妇女乐园的消费,还会带着三个孩子重返商场的饮食间大享免费饮食。而与律师丈夫分居的居巴尔夫人为了实惠,在妇女乐园允许无条件退换商品后,只要看到喜欢的衣服就先买回家,照着样子剪下后再退回去。就连美丽的德·勃夫伯爵夫人,由于丈夫把当养马场总监每年9000法郎的收入都挥霍在风流韵事上,她和女儿在其体面家庭的光鲜外表下却苦于手头的拮据,常常“怀着怨恨观望着那些她不能拿走的货物”[5](P67),即便什么东西都没买,她也会设法不空手离开,比如索取个商场分发的红气球。总之,百货商场成全了主妇们的精打细算,既允许她们通过找实惠获得心灵上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又让她们在现实世界里维护了家庭和个人的阶级体面。
尽管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是百货商场消费群体的中流砥柱,但是百货商场还明智地兼顾到了劳动阶层的女性这个劣势群体,这也是它社会成就的意义大于经济成就的地方之一。左拉每次描写妇女乐园的消费狂热时,都不忘提及“穿着素净的抹布衣服的小市民妇女”与“浑身罩着花边的富豪的贵妇人”混合在一处。妇女乐园新店开张的当日下午,就有近十万的客流量,从这个数字上不难推断出下层女性顾客存在的事实。左拉在小说创作前的实地考察期间,就观察到出现在百货商场的公众是鱼龙混杂的:除了贵妇人、中小资产阶级主妇,还有带着婴儿的保姆、女仆和带着竹篮的乡下妇女们,等等[13](P185)。劳动阶层的女性消费者由于受到百货商场现金支付要求的限制,再加上自身购买力的薄弱,她们的消费对象基本上是价格低廉的打折品。妇女乐园正门前的花车里永远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廉价商品;小说开篇,连一件多余换洗衣服都没有的黛妮丝一走出巴黎火车站就在此“出神地站住了”[5](P2)。夏季大倾销时,“一大群小市民妇女和女佣”会前来染指廉价物品和零头货;门口花车里的“剔除货”很快就“搜光了那些穷人的腰包”[5](P209)。正因为百货商场推广了自由进出、可看不买的开放性经营原则,这些终日疲于生计的女性才可以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中上层女性热衷的社会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进去享一享眼福”[5](P73)。即使按照西美尔的理论,时尚也属于阶级划分的产物,但在百货商场里,劳动阶层的女性在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享受着和中上层女性一样追逐时尚、见证时尚的平等权利和休闲乐趣,进而在心理上弥补了女性群体中不同阶层间社会现状的落差;而这种落差还可以通过劳动减小乃至消除。
四、成为现代生活消费者与缔造者的新职业女性
百货商场不仅成功拉拢了各阶层的女性顾客、激发了她们的消费热情,还亲手为这个消费群体注入了新鲜血液——女职员。根据左拉的田野调查记录,1882年,卢浮百货共有雇员2404人,其中女性350人[13](P179)。同年,波马舍的雇员总数为3236人,其
中152名女性,主要分布在内衣、成衣、童装、鞋靴、嫁妆、婴儿用品、衬裙柜台[13](P157)。女性雇员的大量启用,对于巴黎的城市文明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距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的19世纪,除了给富人家庭做佣人外,卖淫仍是出身贫寒的年轻女孩们养活自己的一种无奈之举。百货商场的工作固然辛劳,但毕竟是一份体面的正经职业。《波马舍企业条例和员工待遇》②参见Le Bon Marché企业内部管理条例。Résumé du règlement général:Institutions philanthropiques en faveur du personnel [M].Paris:Maison Aristide Boucicaut,1894。这一企业内部文件显示,波马舍为这些来自外省的穷苦孩子们提供了稳定的住处(商场的顶层是单身员工宿舍)以及免费的食堂(左拉的小说中,妇女乐园的职工每人每日要付给厨师1法郎50生丁),还有一名长期驻店的医生专门负责员工的健康状况。波马舍从1872年开始为男、女职工提供免费课程,包括英文、声乐、乐器、剑术,帮助员工丰富业余生活,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最重要的是,百货商场还启用了现代的管理制度和内部竞争机制。销售人员每推销出一件商品就可以得到一定百分比的佣金。尽管工作繁重冗长,压力极大,一天往往要不停地站立走动10多个小时,但是佣金制度使勤劳肯干的基层雇员能够有机会摆脱贫穷。“在这些巨大的销售工厂里,一无所有的伙计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臂,从劳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而自己的积蓄一分钱也花不着,不仅生活舒适还能致富。”[14](P80)这些率先富起来的售货员,自然包括女性雇员,进而也潜移默化地壮大了女性消费大军。黛妮丝在妇女乐园的挚友——内衣部的保丽诺,一个在磨坊里出生的外省女孩,来到巴黎谋生时兜里仅有20法郎,在妇女乐园工作稳定后,每月可以赚到200法郎;时装部的玛格丽特则挣到了4500法郎的年收入。现实中,波马舍的销售人员,算上佣金每年都能够挣到大约3600法郎[13](P156)。要知道,19世纪的法国,3500至4000法郎的年收入足以过上小资产阶级的生活[9](P91)。即使像小说里保丽诺那样的未婚女孩,一年未挣到这个数字,由于吃住都在百货商场,节约了巴黎生活最主要的两项支出费用,也能在工作之余尽情地寻欢作乐。这些女孩们有了经济实力后很快就装扮自己,模仿讲究的中上层女性,佩戴着各种饰物,“胸针、表链和灰色长羽毛的丝绒无边帽”[5](P110)。就连只为供养两个弟弟生存和劳作的黛妮丝,在手头宽裕后也给自己置办了一些奢侈品:一床罩着镂空花边的红色鸭绒被,衣橱前的一方小地毯,化妆台上的两个蓝色玻璃花瓶[5](P235)。
如果左拉把女售货员视为一个“身份不明的阶级,浮在职工和资产阶级之间”[5](P134),是因为她们从终日打交道的有钱人那里模仿来的优雅做派与从小报、戏文习得的虚假教养是如此的格格不入,那么这种犀利的批评也实在苛刻。深入骨髓的礼仪和教养,需要长时间乃至几代的濡染与打磨,就算是资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在妇女乐园大倾销时也会仪态尽失。因此,不妨将女职工拙劣的模仿解读为她们试图提升自身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肯定与尊重的良好意愿。更何况百货商场的的确确给予了女性通过诚实劳动实现人生价值、改写自身命运的机会:除了金钱、待遇上的回报与鼓励,商场任人唯贤,不管阶级出身、性别年龄、社会关系,只要勤奋努力,都有机会得到提拔。黛妮丝就是凭借善良谦逊、吃苦耐劳的品质从最初只靠佣金和奖金勉强度日、人见人欺的见习生升到了时装部副主任的位置,年薪也随之飙升至7000法郎,最后被提拔为儿童部主任。黛妮丝在个人境遇扭转乾坤后,还积极向慕雷谏言,匡正了企业运作不合理之处,改善了职工的工作条件,终于赢得了同事们由衷的敬重和服从。一个战战兢兢的贫穷女孩就此成功完成了向城市资产阶级的转化。小说里类似的例子还有奥莱丽太太,一个阿尔萨斯小裁缝的女儿,在妇女乐园做到时装部主任的位置,年收入超过一万二千法郎,是家里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她用自己积攒下来的第一个十万法郎置办了一份产业,成为真正的有产者。玛格丽特在黛妮丝成为儿童部主任后也被提升为时装部副主任。百货商场培养的女性雇员,离开巴黎回到家乡后,往往能够凭借自身积累的经济财富和工作经验,一显身手,自主创业。小说里的玛格丽特最后就回家接管格勒诺布的小店去了。
而在19世纪的法国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位玛格
丽特(1816-1887),即波马舍创办者布西科的夫人。她本人就是当时法国女性自强自立的典范。出身贫寒的她从一个乡下养鹅姑娘到波马舍的老板娘,在丈夫和唯一的爱子相继去世后,以同样出色的工作能力续写了波马舍的神话。玛格丽特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胜任社会工作,同时还来自她慷慨博大的仁爱之心。她和丈夫一起,除了为员工提供上述各种已颇具现代意味的福利待遇外,还制定了带薪假期乃至退休制度。这些卓越的作为,左拉在小说里将其转嫁到了黛妮丝身上,她向慕雷的谏言催生了20世纪工会的胚胎。左拉作为敏感的社会观察家,在小说中还借慕雷之口,赞扬了“劳动的贵族”这一新的劳动女性成分:家道衰败的女侯爵,来到百货商场通过诚实劳动,自食其力,捍卫了个人的尊严。由此可见,在新一轮的社会资源重组中,阶级地位无论是攀升还是跌落,女性都以一个共同体的群体面貌和社会力量昭然于世。
五、结语
19世纪下半叶,巴黎百货商场掀起的远非一场简单的商业变革。作为与传统的决裂和抗衡,它是对19世纪法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应答,更是一针强力的催化剂。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一场完全依托于女性的消费狂欢。物欲横流的集体无意识下,涌动着一股女性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暗流。传统的女性世界被彻底颠覆了。随着女性消费的嬗变,女性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社会偏见中的弱者、家庭义务下的贤妻良母;她们转而紧跟时代脉搏勇于实现自我,以一个自主消费者、社会劳动者、命运主宰者的姿态,集体改写了女性的论述架构。左拉的《妇女乐园》完美地预示了对于日后的社会建构与公众生活,女性的缺席已不再可能。
[1]Zola,Emile.Correspondance[M].B.H.Bakker(ed.).10 Vols.Montréal and Paris: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and Éditions du CNRS,1978原1995.
[2]Harran,Nathalie.La Femme sous le Second Empire[M].Paris:Éditions Errance,2010.
[3]Broca,Paul.Sur Le volume et la forme du cerveau suivant les individus et suivant les races[A].In Paul Broca.Mémoires d’Anthro原pologie[C].C.Reinwald,1871.
[4]Hahn,H.Hazel.Scenes of Parisian Modernity:Cultur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New York:Plagrave Macmillan,2009.
[5][法]左拉著,侍桁译.妇女乐园[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Bourienne,Véronique.Boucicaut,Chauchard et les autres[A].InLa Révolution Commerciale en France:Du Bon Marché à l’hyper原marché[C].Jacques Marseille(dir.).Paris:Le Monde原Éditions,1997.
[7]王敏.文化视阈中的消费经济史.迈克·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消费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美]凡勃仑著,李华夏译.有闲阶级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9]Miller,Michael Barry.The Bon Marché: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1869原1920[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美]托马斯·韩恩著,夏嘉玲、陈光达译.Shopping演化史[M].台北:雅言文化,2003.
[11][德]西美尔著,顾仁明译.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A].刘小枫主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Modernity's Disavowal,Women,the City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A].InThe Shopping Experience[C].Pasi Falk/Colin Campell(ed.). London and California:Thousand Oaks and Sage Publications,1997.
[13]Zola,Emile.Carnets d’enquêtes:Une ethnographie inédite de la France[M].Paris:Plon.1986.
[14]D’Avenel,Georges.Le Mécanisme de la vie moderne[M].Armand Colin&Cie,1896.
责任编辑:含章
DU Li-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Zola;Paris;department store;consumption;women's identity;the ladies'paradise
I109.9
:A
:1004-2563(2015)06-0083-07

杜莉莉(1980-),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城市文化、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