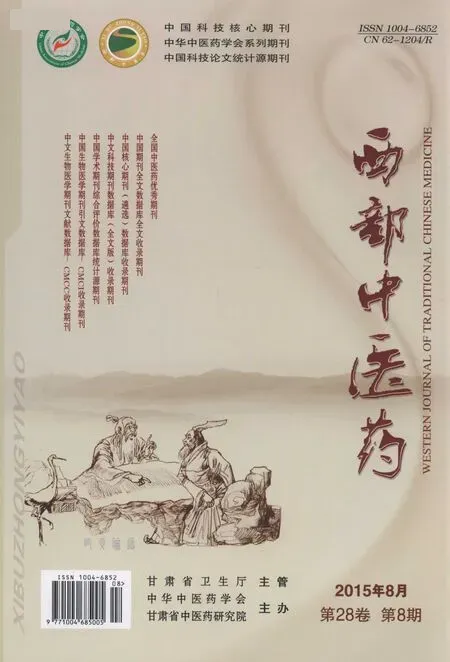从古典中医源流探究“得气”的发展*
屈红艳,王瑞辉,殷克敬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从古典中医源流探究“得气”的发展*
屈红艳,王瑞辉,殷克敬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从古典文献入手,引用《内经》及其他经典著作关于得气的注释、论述,并结合针灸学现代研究对得气的相关研究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得气与疗效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得气的因素。
得气;针刺;《内经》
“得气”一词,最早记载于《灵枢·九针十二原》:“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是指毫针刺入腧穴一定深度后,施以一定的手法,使针刺部位获得一定的经气感应,包括患者对针刺的感觉与反应和医者的手下感[1]。得气与疗效的关系一直是针灸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关于针刺过程中气的反应,最早记载于《黄帝内经》,曰:“见(现)其乌乌,见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这种非常玄妙却又难以具体感知的感觉要求医者细心体会揣摩方可体察,如《灵枢·小针解》曰:“空中之机,清静以微”。《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云:“中气穴,则针游于巷。”就是说,刺中穴位,针下之气好像在巷道上来回串行。一般情况下,如果患者平时机体功能较好,腧穴部位在针刺后就容易产生各种程度不同的的特殊感觉,如胀、麻、酸、重、热、凉、水波样,或气泡串动样、电击样等,甚至会出现经气的游走扩散传导,局部或全身出现凉爽轻快或温煦舒畅,或莫可名状的欣快感。
1 古典文献中关于“得气”的记载
对于“得气”的描述,古代医籍中有以下几种记载:《灵枢·终始》曰:“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灵枢·小针解》云:“空中之机清净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灵枢·热病》说:“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腧及下诸指间,索气于胃络,得气也。”《素问·离合真邪论》说:“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泻”。《标幽赋》中提到:“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以至。”“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浮沉,气未至也,如处幽堂之深邃。”得气时医者手下有重、紧、涩的感觉,患者能在穴位处感觉到酸麻胀重感,有时还可出现不同程度的传导现象。
2 得气与疗效之间的关系
“得气”可明显地提高针灸临床效果,已为古今医家所认同。得气与否与针刺疗效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病证、不同的针刺部位、不同的针刺方法、不同的体质等对取得针刺疗效时的得气要求不同。《灵枢·九针十二原》说:“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金针梅花诗钞》中提到:“夫气者,乃十二经之根本,生命之源泉。进针之后必须细察针下是否已经得气。下针得气,方能行补泻,除疾病。”[2]。以上论述,均认为针刺得气与临床疗效关系密切。当腧穴受到针刺刺激时,经气被激发并产生调和阴阳、补虚泻实,最终治愈疾病的效用。毫针治疗主要是为了调整经气,不得气就不利于治疗,不得气就无效。气至,说明经通气畅,气调血和,元神发挥其主宰功能,使得相应的脏腑组织、四肢百骸等功能协调平衡,疾病消除[3]。得气与否对疗效有直接影响,也是产生治疗作用的重要标志;如小儿麻痹后遗症和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偏瘫、肢体麻木及运动障碍等,接受针刺治疗的初期,通常针感很弱或无针感,但随着疗效的增加,才渐渐出现针感或传导,同时也改善或恢复了患者的感觉及运动功能[4]。正如明代张景岳《类经》中言:“用针之道,以气为主。”《针灸大成》中亦记载:“用针之法,候气为先……以得气为度。”
3 影响针刺得气的因素
3.1 针刺穴位与得气 穴位的特异性对得气的影响在《内经》中早有记载。《灵枢·胀论》云:“不中气穴,则气内团;针不陷育,则气不行;上越中肉,则卫气相乱,阴阳相运”。《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染于巷,中肉节则皮肤痛。”针灸临床腧穴的选择对于针刺能否“得气”有重要的影响。针灸穴位一般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其作用明显而且较持久,而非穴位进行针刺则不明显或很小。如有学者[5]在针刺“大椎”穴对慢性应激大鼠行为学影响的穴位特异性中发现,慢性应激大鼠体重增加和蔗糖偏嗜度、旷场实验中活动次数较正常组显著减少。针刺“大椎”后对以上指标有明显改善作用。而针刺尾部下1/3处(即非穴位)组仅对部分指标有一定的影响,说明针刺“大椎”穴与尾部下1/3处均对其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针刺“大椎”穴的改善作用明显优于针刺尾部下1/3处。
此外不同经脉上的穴位甚至同一经脉上的不同穴位作用也有不同的效应,如针刺“内关”可使心肌电活动加强,针刺“神门”穴则可见心肌电活动减弱。肺经穴位少商可开窍泻热、鱼际行气泻热,太渊培补肺气而列缺可宣通肺气,这些穴位之间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针刺穴位必须准确,选穴皆中肯。因为腧穴的所处位置极其作用的特异性亦是影响针刺得气的主要因素。对于穴位之间的配伍及其协同效应,古人早有认识,并系统提出了可以提高针刺疗效配穴方法,如左右配穴、前后配穴、上下配穴、表里经配穴等。
3.2 针刺方法及刺激参数与得气 《内经》云:“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说明施灸针具不同,效应也会有所不同。当今社会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许多针灸的操作技法随之产生。各种不同的刺激方法和刺激参数对针灸“得气”影响较大且呈现作用环节的差别。不仅不同的刺激方法产生的效应不同,同一种刺激方法设置的参数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得气”效应。如慢性病患者或健康人的合谷、内关施行烧山火手法时,大多数受针者在穴位局部会出现皮肤温度升高,而透天凉针法则可使皮肤温度下降。烧山火、透天凉针法对体温的影响不仅有局部变化,而且有全身反应。探索不同针具治疗同种疾病的疗效差异及其规律,对进一步提高针灸的临床疗效,减少临床刺激方法选择中的盲目性,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3 针刺时间与得气 《内经》系统论述了外界环境中各种周期性变化的因素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影响,《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内经》中比比皆是。生命活动应随宇宙变化、日月运行、四时八气更替等抑扬起落、彼弛此张而呈现节律性变化。这种“天人相应”的基本思想也是现代时间生物学对人体节律产生根本原因的早期论述。古典择时针灸方法对“得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纳甲法、纳子法、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熊克仁等[6]研究不同时辰效应差异的分子生物学机制表明:11时给予2H z电针一侧“环跳”穴对大鼠脊髓和脊神经节内S O M m R N A阳性神经元的表达有上调作用,5时电针S O M m R N A阳性神经元表达最弱。
3.4 针刺深度与得气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标幽赋》据此发挥为:“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7]。
由此,人们在进行针刺治疗时,将“得气”作为治疗的有效标志。但实际上,“得气”仅仅是针刺过程中最基本的要素。而在许多情况下,虽未得气(或称之为“隐性得气”),或采用无需得气的针法(如腕踝针、皮内针等),同样可获效。反之,如取穴不准、施术不当,虽得气强烈,也只能无助其功。较之“得气”更为重要的是在穴位的什么层面上得气,以及得气强弱程度。针在穴位上得气与非穴位上得气的差别,早有定论。但针刺在穴位的有效层面上与非有效层面上对针刺疗效的不同,却鲜有人探讨。实践证明,在有效穴位的有效层面上得气时,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疗效。如取足三里治疗胃痛,在刺入一定的深度得气后,胃痛即可缓解;这时,如将针刺得更深,则虽得气强烈,止痛效果却反而下降。足阳明胃经位于小腿的前侧,而刺得过深,则针尖离开了足阳明经,失去了治疗效果,在经络实质未明之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3.5 精神因素与得气 《灵枢·邪客》云:“心者……精神之所舍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辛夷》中说:“脑为元神之府”。说明中医谓之“神”涵盖了认得精神意识活动。针刺得气须先治“神”。治神又称守神,是指医者在针刺操作过程中,要精神集中,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地体会针下的感觉,细心观察患者的精神状态和机体变化,使其精神会聚,心情舒畅,在患者心理状态较佳的情况下接受针刺。《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内经》将“治神”列在首位,表明“治神”对提高针灸疗效有积极重要的意义[8]。《素问·离合真邪论篇》曰:“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已至,适而自护”。治神,是通过医生的神志专一和患者的精神调摄,使经气畅达,促使得气而气至病所,从而提高临床疗效。其对于针刺操作手法是否成功,针下能否很快得气,都有重要意义。《灵枢·官能》篇曰:“用针之要,勿忘其神”“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懈,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灵枢·本神篇》说:“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是故用针者,察视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素问·针解篇》中说:“必正其神,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这充分说明在针刺操作过程中,医生掌握病情后,选穴操作中,既要神志专一,又要观察患者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绪,做到“必一其神,令志在针”“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宝命全形论篇》运用与之相适应的针刺手法,全神贯注,精力集中,细心观察患者的神气,体会针下的感应,随时调整针刺的深浅与行针快慢等,才能使针下得气,获得预期的治疗效果。《标幽赋》中也提出针刺要注意施术者及患者双方的“神”(精神状态),“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即刺也,使本神定而气随。”要得气行气,就要在医患双方“神朝”“神定”(精神安静集中)的前提下进行,才能产生明显的得气效果。
此外,个体因素也会影响针刺得气。这一观点早有记载,《灵枢·行针》篇曰:“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或数刺乃知”大量的针灸临床和现代动物实验研究证明,即使患者或动物的年龄、性别和生活条件完全相同,对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刺激也可能有不同反应。这与个人体质、机能状态和心理因素都有一定关系。如在对15例双侧青光眼患者的先后两次虹膜嵌入巩膜术中,将影响针麻效果的各种因素做了同体对照观察,发现个体差异对针麻效果影响大于穴位和刺激方法的作用。
从古典医籍和现代研究各方面表明,“得气”是客观存在的,其含义不等同于“气至”,而是包含“气至”和针感在内的动态过程[9]。该过程应该包括四方面:一是激发脏腑经络之气,获得经气感应,即获得针感;二是探明经气的邪正虚实;三是调节邪正双方力量,或祛其邪,或安其正,或补其虚,扶助体内的正气,驱除外来的邪气,使气至针下或气至病所;四是守气,即在针刺得气后,患者都要谨守禁忌“慎守勿失”,也就是说要遵守不同的疾病在治疗阶段的不同禁忌,以更好地顾护正气,使疾病向痊愈的方向转化。“气至”亦是在得气的基础上完成。针灸治疗得气与否,得气迟速及其强弱,不同类型的得气感以及循经感传都对临床疗效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对其机制研究得还不够深入系统,“得气”这个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概念越来越值得我们去探索。在临床方面,通过各种有效病证的针灸治疗进一步系统化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使“得气”的内涵和机理得到阐明。
[1] 梁繁荣.针灸学[M].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55.
[2] 周楣声.金针梅花诗钞[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106.
[3] 王富春.针法医鉴[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96.
[4] 王德深.针灸学基础知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20.
[5] 李晓泓,韩毳,张露芬,等.大椎穴对慢性应激大鼠行为学影响的穴位特异性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3,21(9):142.
[6] 熊克仁,赵健,李怀斌,等.不同时辰电针对大鼠脊神经节及脊髓内生长抑素mRNA阳性神经元表达的影响[J].针刺研究,2005,30(1):31-34.
[7] 高武.针灸聚英[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1:231.
[8] 邹勇.重视针灸“治神”提高针灸疗效[J].光明中医,2007,22(10):36-38.
[9] 张芳,王鸿度.浅谈针感、气至与得气[J].中国针灸,2012,32(12):1132-1134.
Exp loration of"Obtaining Qi"Based on theO rigin ofClassical TCM
QU Hongyan,WANGRuihui,YIN Kejing
Shaanxi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Xianyang 712046,China
The relation between obtaining Qi and clinical effects aswell a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obtaining Qi were furtherexplored by startingw ith classical literature,citing the explanation and the statementof obtaining Qi in NeiJing and other classicalworkscombinedw ithmodern studiesofacupunctureon obtaining Qi.
obtaining Qi;needling;NeiJing
R229
A
1004-6852(2015)08-0054-03
2014-10-25
2011年陕西省中医管理局课题(编号 lc05)。
屈红艳(1980—),女,硕士学位,讲师。研究方向: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