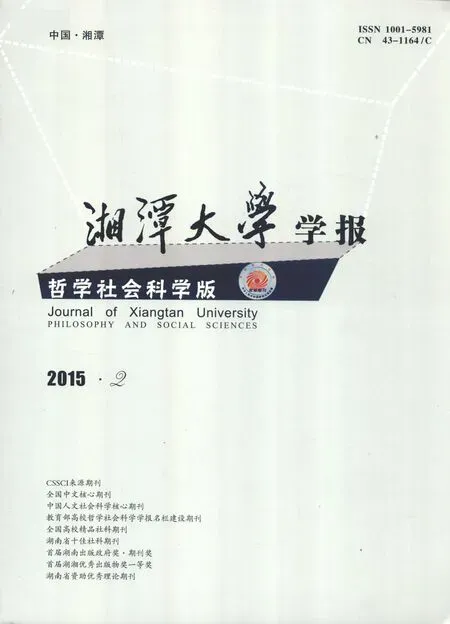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喜剧小品语言策略的嬗变*
曾 炜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喜剧小品是集“演”和“说”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大众喜闻乐见甚至有些经典耳熟能详,颇受学界关注。文学、艺术界主要侧重探讨喜剧小品的“不谐调模式”[1]60与相应的表现形式。诙谐可笑的语言是小品喜剧性最重要的载体,小品自然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如谢旭慧(2009)《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从修辞方面全面探讨小品幽默的构成机理和语言运作规律;张玉梅(2010)《当代喜剧小品语言负偏离现象研究》、曾炜(2011)《喜剧小品的语言“得体性”偏离现象研究》、宗世海(2013)《致成汉语幽默效果的特异指称策略——以相声、小品为例》等则是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如关联、合作、礼貌、预设、得体等对小品喜剧性语言的生成原理进行描写和解释,其关注的视角总体上是语言内部的、共时的。
“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2]94当代中国喜剧小品反映社会百态、揭露时弊,记录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与观念更替。同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孕育特定的小品语言策略,制约着小品的语言观、构成材料与材料组合方式。追踪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轨迹,可以全面深入地解读小品语言策略的嬗变。
一、喜剧小品登场与小品语言的“缺位”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尚处于娱乐稀缺的时代,“一个苦难的民族需要笑声”。1983年央视春晚首次把艺术学校表演考试的“小品”搬上了舞台。此时的小品在题材选择上并未与当下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如《阿Q的独白》、《逛厂甸》是文学经典的演绎或延伸,《吃鸡》、《弹钢琴》则是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以哑剧形式表现日常生活内容。小品演员一个夸张的动作与眼神,就足以笑翻全场,作为新的舞台样式,小品在功能定位与形式依托上仍处于酝酿的态势,小品的喜剧性并未与语言发生必然联系,表演者的肢体语言在小品喜剧性的构建策略中的作用远胜于有声语言,这一时期可视为小品的语言“缺位”期。
二、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小品传统修辞的继承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经济逐步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随之而来的也有思想的困惑与行为的偏离。小品作为一种舞台艺术不仅限于娱乐功能,而且及时记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赋予小品针砭时弊的讽刺教育功能。如《相亲》、《羊肉串》、《送礼》、《产房门前》等反映了诸如小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唯利是图、行贿受贿的不正之风,以及新时代陈旧观念的遗留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化复苏与反思的时代。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电视虽已走进千家万户,但尚未普及进入寻常百姓之家,仍是与报纸相提并论的知识分子媒体。电视内容的生产相应地也带有一定的居高临下的色彩,电视文化整体上是精英主义的,而以电视作为媒介传播的小品也不可避免地浸染文化的“精英性”,在小品语言上的表现便是语码选择的规范性、同质性与传统修辞的继承,其中尤以谐音修辞手段居多,用以造成歧义、产生误会,制造喜剧效果。如《吃面条》、《拍电影》、《羊肉串》、《英雄母亲的一天》等便是大量利用谐音式误会的作品。
这一时期男性“弱势语体”这种非常规语体开始出现,如《接妻》、《打麻将》夫妻对话中的非等同语体映照新兴夫妻关系中女性家庭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成为此后小品夫妻对话中的常用策略。同时,恰在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之时,小品开始引入地域方言或带有地域风格的普通话形式,如《接妻》(1988)中的四川话、《急诊》(1988)中的港台腔,还有《送礼》(1986)中的各地方言汇集等。这两种基于传统语言策略的创新,在以后的小品中得到了沿用与发展。
三、社会流动的加剧与语码的混杂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人们经济、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流动加剧,新旧观念、区域文化之间的碰撞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新问题。如《打扑克》、《如此包装》、《打工奇遇》等就揭示了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欺诈、社会不良人际关系等。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剧使得语言不仅是承载主题的工具,其本身也成了“问题”,如《乡音》、《黄土坡》等小品中就集中体现普通话与方言、与外语之间的冲突。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电视的逐步普及,传媒开始迎合大众的消费趣味,传统的话语方式发生了转变,时尚与通俗成为小品语言新的审美追求。小品《擦皮鞋》、《乡音》中大量的新词新语反映富裕起来的老百姓对新事物的接纳;《妈妈的今天》、《密码》、《鞋钉》、《黄土坡》、《老将出马》等小品中港台腔、英文、南方方言与普通话混杂,记载了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中以普通话为载体的主流地域文化在与港台文化、西方文化、南方强势地域文化等潮流文化碰撞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大量富有地域特色的俚语、双关语、歇后语引入小品,俏皮、活泼又充满生活智慧;《过河》、《红高粱模特队》、《如此包装》、《打工奇遇》、《吃饺子》等小品大胆借用地方戏曲、流行歌舞甚至rap等其他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实现语言跨语域的时尚与通俗的结合。
一个全新的新旧语码并存、跨地域跨领域语码混杂的语汇系统代替了传统的规范的同质的语汇系统,虽有学者在《语文建设》与《咬文嚼字》等刊物上发文质疑与批评方言小品[3]6,但因方言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与情感认同功能,而使方言语码的运用成为小品常用的语言策略沿用至今。
四、社会的转型与语言的“颠覆”
20世纪末21世纪初,社会生活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接触中的语言冲突在改革开放与社会流动的推进中习以为常,小品在题材上转向社会生活的深厚与宏阔,既注重揭示普通人的心理特点与人性的弱点,也加大了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在娱乐功能的基础上增强了针砭时弊、启发思考的社会功能。悄然兴起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使传统的精英文化受到挑战,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使得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主导着后现代社会的文化世界。在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小品语言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语言材料组合的混杂特征更明显。如《拜年》中权势语体与等同语体的混杂,反映市场经济之下人心的虚伪与势利;《爱父如爱子》、《我和爸爸换角色》、《祝寿》、《浪漫的事》中人物语言与身份、关系的不和谐,映照社会经济生活改变之后家庭人际关系的新矛盾;《昨天今天明天》中书面语体与口语语体的混杂,揭示人物实际身份与心理认同之间的错位与差距;《策划》通过不同语域语言材料的混杂揭示大众传媒时代语言的模式化与类型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语言材料的混杂是形式“新”与“旧”的混杂,用以标记区域性的社会流动,那么21世纪初小品语言材料的混杂则是全面而深层的,将语体混杂、语域混杂发挥到了极致。
其次是语言的娱乐功能进一步强化。为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与快餐文化对小品“包袱”高密度高响度的评价标准,小品在注重情节可笑、肢体语言滑稽的基础上,越来越倚重嵌入幽默甚至搞笑的语言。引入大段的开场说口,嵌入与剧情无关的纯语言游戏,大量运用戏仿,甚至恶搞经典,调侃名人等成为惯用策略,如《钟点工》、《卖车》、《功夫》中的脑筋急转弯,《让一让生活更美好》中的戏谑——“没您长得好看,怎么看怎么像马桶”等。这些“包袱”让观众在颠覆权威与经典中获得满足与轻松感,产生喜剧效果。
最后是“春晚小品语言”品牌意识也愈加强化。小品在春晚舞台上的空前盛况,给小品创作者、小品平台带来巨大的商机。为积极打造“春晚小品语言”这一品牌,小品创作者不再消极等待观众的筛选,而是积极地创造、引导和预测春晚小品流行语。春晚小品成为每年流行语的重要发源地,如“女人,对自己下手就是要狠一点”,“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等。再如“小样儿”、“拔凉拔凉的”、“忽悠”、“相当”等词也因小品的播出而流行,甚至影响到了《现代汉语词典》对某些词语的收录与解释。小品在这一时期已达到巅峰状态,为追求“笑”果,冲破规范的束缚,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表现手法,小品因此变得只见语言不见艺术,日趋俗化。
五、社会生活的“娱乐化”与小品语言的“狂欢”
网络媒体的普及,使大众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有了最大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小品在题材上与当下社会热点事件紧密互动,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从北京奥运到热播影视再到网络流行语都在小品中留下了痕迹,如《家有毕业生》、《同桌的你》、《火炬手》、《黄豆黄》、《北京欢迎你》、《不差钱》、《想唱就唱》等。小品与当下文化互动大多借用“戏仿”手段,以达到集滑稽与讽刺于一体的喜剧效果,实现娱乐的再娱乐。大众文化在繁荣的经济中借助传媒舞台演化为娱乐文化,“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4]98。娱乐演化成“狂欢”成为文化的潮流与存在的方式甚至生活的主题,语言狂欢则成为最日常最经济的娱乐形式,语言应用观前所未有的开放,小品的话语系统也因此彻底改变。
首先是语汇系统的趋同。继第一个以网络生活为题材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2007)出现之后,网络不仅是小品台词中的关键词,也是小品创作素材的来源,小品语言“包袱”的原创者从传统文化精英转向了网民甚至草根。如“给力、雷人、打酱油”,“唱的不是歌,是寂寞”,“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等大量的年度流行语出现在小品台词中,造成形式的雷同。流行语汇的引入,能引发受众共同的文化联想,让观众在当下生活的被观照中宣泄生活压力,但过度引入却让春晚小品几乎成为年度流行语的盘点,呈现语言的媚俗与原创危机。其次是语言结构规则突破意义与功能的制约。语言片段的组合是“语义先决性、句法强制性和语用选择性”的结果[5]1。而狂欢时代的语言则成为无意义的符号串,词语组合规律无极限地突破。如“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这些组合通过对规范与严肃的消解,形成形式与意义的荒诞关联,制造喜剧效果;但同时也让形式的输出凌驾于意义的传递之上,将语言沦为能指符号的游戏,其实质却是思想的空洞。最后是“娱乐”成为最主要的言语交际目的。说话成了娱乐式的自我或群体展演,人物的语言引人发笑便是合理的,不再受身份、关系、目的、场合的约束,也不受“合作”、“礼貌”、“得体”等原则的制约。“毒舌”风格大行其道,类似“长得跟闹着玩儿似的”、“多么漫长的脸啊,悲剧啊”之类取笑人智力上的缺陷、社会中的弱势尤其是形象上的缺憾成为最简单常用的手段,以此激发听众的优越感,产生喜剧效果;“伪娘”风格登上大雅之堂,从《不差钱》到《大城小事》、《你摊上事儿了》都沿用此策略,小品也因此饱受“庸俗”与“低俗”的非议。
综观30余年的喜剧小品,其“包袱”制造策略整体上经历了从行为举止可笑转向情节可笑,再到语言可笑的历程。小品“语言包袱”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主流中夹杂着非主流形式,继承与创新同在。近年来,“人物语言弱智化”、语言“庸俗、低俗、媚俗”、“过分套用网络语言,缺乏原创性”是小品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三:语言观的偏离使得小品与笑话、语言游戏之间的界限模糊;语言审美观的偏离使庸俗粗鄙化的语言俨然“引领”着当今语言的潮流[6]134,雷同的、暴力的、“毒舌”式的、“伪娘”式的语言代替语言智慧与语言幽默成为观众捧腹的诱因;娱乐文化背景下人们感觉的钝化和观众与日俱增的娱乐胃口对小品的创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下喜剧小品转变语言策略,走出语言困境,与当下语言生活健康的引导和语言生态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小品30年语言策略的变化,映照的是社会生活的变迁,脱离当下小品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来看待或批评小品语言,都将是主观而强求的。但小品作为语言艺术,娱乐应有节有度,至少是“戏”而不“谑”,“欢”而不“狂”的。
[1]邹贤尧.喜剧小品:不谐调模式[J].戏剧文学,2007(9).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
[3]符达维.方言小品几时休[J].咬文嚼字,1996(12).
[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鲁川.先决性·句法的强制性·语用的选定性——基于三个平面理论的汉语信息语法的构思[J].汉语学习,2000(3).
[6]胡青青.网络语言的伦理思考[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