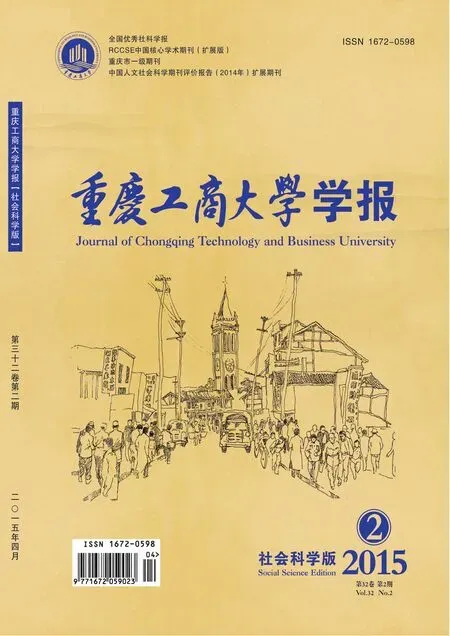评学术界对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的研究*
周德海
(合肥市行政学院科研处,安徽 巢湖 238000)
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甚至在此前的计划经济年代,资本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就客观存在着,只是由于某些非学术的原因,学术界不愿或者不敢承认。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陆续有学者对资本问题进行研究,但这种零星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1]直到1993年11月,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第一次使用资本概念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概念才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掀起了关于资本问题的研究热潮。其中,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的研究,把曾经被马克思严厉批判过的资本概念,合乎逻辑地移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为党和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学术界对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的研究概况
为了使我们关于马克思资本二重性思想的讨论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或前提,笔者认为,应当首先对“二重性”和“资本二重性”本身进行规范,然后才能对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所谓“二重性”,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属性。即一种事物同时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性质。”[2]如果人们对“二重性”的这种规定没有异议,那么“资本二重性”则应当是指资本本身所固有的互相矛盾或互相对立的两种属性或性质。而且,这两种互相矛盾或互相对立的属性或性质,应当是根本性的。
如果我们以此衡量学术界关于资本二重性的研究,就会发现有些学者所说的资本“二重性”或“双重属性”,明显不符合我们对资本二重性的规范。例如,在《论资本的二重性》一文中,庄江山把“文明的作用”和“消极的作用”,看成是资本的二重性,显然偏离了主题。[3]因为资本的作用并非资本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乾润梅和刘建伟在“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双重属性划分及其现代意义”的标题下,把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双重属性划分为“作为一般属性的资本”和“作为特殊属性的资本”。“作为一般属性的资本”,“具有增殖性、流动性、竞争性和扩张性等特征,参与生产过程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特殊属性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具有阶级性和过渡性特征,最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4]这种对于资本双重属性的划分,显然带有很大的人为的随意性。很明显,“作为特殊属性的资本”,似乎不具有“作为一般属性的资本”所具有的增殖性、流动性、竞争性和扩张性等特征,也不参与生产过程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作为一般属性的资本”,也没有它自身的“特殊属性”。尽管作者的目的是要论证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资本的合理性,但是,这种通过割裂资本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的做法,很难合理地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资本现象,但是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却不相同”[4]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按照这种对资本的双重属性的划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同时具有“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两种属性,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却只能具有“一般属性”这样一种属性,这在逻辑上似乎说不通。
何玉长和袁乐轶在《资本二重属性论》一文中指出,在西方经济学中,资本一般作为生产的技术要素来使用,体现的是生产力属性,或自然属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则将资本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5]也许是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或启示,更多的学者在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或者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作为资本二重性的具体内容。聂亚珍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6]王天祥则在马克思的“任何资本从本质上说,都要实现价值的增值”这一“资本的共性”的基础上,认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资本具有的二重属性。“资本的自然属性……属于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构成部分”,这种属性“在不同经济制度的社会中,……都是一样的”。而“资本的社会属性,是指资本归谁所有的问题”,“反映着社会生产关系发展需要的性质”,因而“就是资本的个性”。[7]
尽管周扬明在《论资本的两面性》一文中,使用的是资本的“两面性”,但其具体内容,与王天祥文中所说的资本“二重性”,颇有相似之处。周扬明认为,“资本是一种自行增值的价值,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与生俱来就具有两面性”:一是“具有生产力的属性”;二是“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这种生产力的属性和生产关系的属性,“运用辩证思维来判断资本范畴既是一般范畴,又是特殊范畴,它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或生产力性质与生产关系性质这一两面性的对立统一”。资本的生产力属性或一般性、共性,体现在资本不受社会制度的限制,而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而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或特殊性、个性,则是指“资本的占有、生产和分配关系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周扬明举例说:“例如,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具有残酷的剥削性、不平等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资本就不具有这种剥削性,而是具有很强的公有性、公平性。”[8]遗憾的是,周扬明对资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不具有剥削性和具有很强的公平性,没有进行论证。有学者认为,这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资本,“就赋予了资本新的‘特有的社会性质’”[9]。于是,有学者把这种赋予了新的“特有的社会性质”的资本,直接称为“社会主义的资本”或“新资本”,以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资本”或“旧资本”。[10]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即使是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私人资本,由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部关系上,它要受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管理和强大的公有制经济的制约;在内部关系中,私营企业的劳动者受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对雇主的经营活动有监督的权利,因而也就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人资本有了质的区别。[11]这样的说法具有典型的冷战思维的特征。在这些学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万恶的资本,只要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相结合,或者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约,立即变成了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东西。①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另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抵御一切腐朽和丑恶东西的功能。比如,所有人都知道,剥削是腐朽的和丑恶的东西。在关于剥削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告诉我们:“剥削……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产生剥削的经济基础消失了,剥削就不可能存在了。”(辛程:《不要把“剥削”概念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第19-21页)再如,所有人都知道,腐败也是腐朽的和丑恶的东西。在关于腐败问题的研究中,又有学者告诉我们:“腐败现象来源于私有制”,“从根本上来说,腐败现象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肖炳兰:《研究腐败问题的三个理论框架及其适用性》,《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第41-46页)“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与腐败政治是毫不相干的。”(李凌云:《论腐败政治的一般本质》,《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96-100页)“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本质特征是廉洁政治,是同任何腐败政治和腐败行为根本不相容的。”(白建孝:《论腐败的概念界定》,《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46-47页)其实,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人类社会中最早的剥削和腐败,恰恰是原始公有制的产物,也是导致原始公有制解体的根本原因。(周德海:《剥削理论研究中的几个误区》,《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第88-91页;周德海:《腐败理论研究中的几个误区》,《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第50-54页)对于这种认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抵御一切腐朽和丑恶东西的功能,以及认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观点,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神话”或“社会主义公有制神话”。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但是在笔者看来,以上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和资本二重性的研究,存在着缺陷。
二、资本的本质是商品,在商品中包含着学术界所说的资本二重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由货币转化而成的。在马克思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命题中,[12]171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其本身也是一种商品。无论作为货币的商品如何特殊,它与其他任何一个商品一样,都具有商品的自身规定性。况且,任何一种具体的商品,与其他种类的商品相比,都有其特殊之处。因此,在马克思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命题中,内在地包含着“一切商品都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内容。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13]345既然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那么,一切商品也应当可以成为资本。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只要有市场需求,它们的所有者都可以将其商品化为资本进行投资。甚至一些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资源,如体魄、美貌、情感,知识、技能、才干,甚至某些个人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只要有市场需求,它们的所有者或掌管者也可以将其商品化为资本进行投资。例如,人们常说的“感情投资”,就是指一些人把他们所具有的感情商品化为资本进行投资;中央纪委研究室在文章中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做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14]这就意味着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确实有一些党员、干部把成绩和贡献商品化为资本进行投资。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只要在有商品交换或利益交换的地方,人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商品化为资本进行投资。因此,只要搞清楚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本质是商品的问题,学术界的那些试图通过所谓的资本二重性的研究,把资本移植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的做法,实在是有些多此一举。因为道理很简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要搞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有资本。
既然资本的本质是商品,那么,商品的有用性和可交换性也就自然地成为学者们所说的那种资本二重性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2]47“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2]47简单地说,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商品包含的三层意思:一是商品是社会财富;二是商品是客观存在的物;三是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商品的这第二层意思相当于学者们所说的那种资本的“自然属性”,只不过还不存在学者们所说的那种资本的“增殖性”;商品的这第三层意思相当于学者们所说的那种资本的“社会属性”,因为在商品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类似于学者们所说的那种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关系”。
在作为外在物的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自身属性中,马克思首先指出的是商品的“有用性”。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的有用性时说:“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12]48这种有用性存在于商品体之中,商品的有用性使商品体成为使用价值。其中,用于社会生产消费的商品的有用性,类似于学者们所说的那种资本的“生产力属性”。因为作为生产的各种要素和作为生产力表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本身就是商品,这些商品的有用性在于它们是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是生产力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说的“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12]210那么,生产资料也应当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测量器。
商品的另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它的可交换性。因为商品本来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则不成其为商品。这与马克思所说的“纺纱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13]344“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5]922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此,在商品的可交换性中所包含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就是学术界中的一些学者所说的那种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或“社会关系属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笔者看来,商品的有用性实际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商品的生产者来说的有用性,就是商品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为的是满足他自己追求个人利益的需要;二是这种商品能够满足他人的某种消费需要。正是商品的生产者和商品所有者,在通过商品满足他人消费需要的过程中,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马克思说,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16]。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的哪一个人,不想获取尽量多的东西?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追逐金钱利益……这种物欲只会存在于人类自身,侍从、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赌徒、乞丐……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所有成员,无论有无实现这种欲望的可能性,这种欲望都存在。”[17]可以说,每一个商品生产者或商品所有者,都是经济学中所说的“经济人”,都在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18]虽然各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但不外乎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种类型。①作为公平的分配,应当把精神利益纳入到个人收入分配体系之中。由此,笔者提出“坚持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并重原则”的个人收入分配方案。(周德海:《对公平分配概念的哲学思考》,《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第33-39页)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所有者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商品作为资本本质的根据所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都能如愿以偿。
所不同的是,由于“货币或商品,……在可能性上是资本”,[15]398因而商品是用来交换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而资本则是希望获得赢利而用来经营的商品。
三、学术界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误解以及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局限性
(一)学术界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误解
在《资本论》中,由“G—W—G”公式表征的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般形式;由“G—W—G'”公式表征的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殊形式。学术界把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定义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或“能够增殖的价值”,是把马克思的特殊形式的资本普遍化和唯一化了。
尽管马克思认为,在G—W—G这个流通中,“先用100镑交换成棉花,然后又用这些棉花交换成100镑,就是说,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12]175但是,这个公式所表征的是“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12]172。通过这一运动过程,“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12]172。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由“G—W—G”公式所表征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虽然“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但这个公式中的第一个G已经成为资本。由此,我们可以把由“G—W—G”公式所表征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中的资本,看成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般形式。
由于“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每一个新资本”[12]171—172,在本质上是“自相排斥”[19]、相互竞争的个别的资本,因而在同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资本。其中,每一个资本都存在着“用100镑买来的棉花卖110镑,还是100镑,甚至只是 50镑”这样三种可能性。[12]173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至少表现为这样三种基本类型:一是“100镑—棉花—110镑”;二是“100镑—棉花—100镑”;三是“100镑—棉花—50镑”。据此,马克思把由“G—W—G”公式所表现出来的三种资本类型中的第一种,即“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 +10镑,即 110 镑”,用公式“G—W—G'”表示。[12]176他特别强调:“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12]176他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12]176,并且指出:“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12]176于是,马克思由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般形式“G—W—G”,过渡到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殊形式“G—W—G'”。这种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只是马克思资本概念中的一种形式。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主要是以“增殖”资本,即“G—W—G'”为基础和逻辑前提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排除其他两种类型的资本的存在。因此,作为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研究者,没有理由把由“100镑—棉花—100镑”和“100镑—棉花—50镑”表征的“保本”资本和“亏损”资本,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中排除出去,进而把马克思的“增殖”资本普遍化为资本的唯一形式。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障碍,而且也不符合现实中资本活动的实际情况,因而严重地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
(二)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局限性
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的奴隶制残余,当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普遍现象;二是出于对资本和资本家强烈的憎恶感情,妨碍了他对资本认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马克思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货币是如何转化为资本的,他用举例的方式所说的商人用100镑买来棉花卖110镑,以及卖100镑,乃至卖50镑,即赢利、保本和亏损三种基本情况,由于这个例子来源于人们对资本的感觉经验,因而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在现实的商品经济活动中,每一个投资者所得到的结果,无非是这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接下来,马克思把这个例子中的那种资本赢利的情况单独抽出来,并把那个赢利资本所获得的“一个增殖额”称为“剩余价值”,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剩余价值”概念,只是通过举例的方式提出的一个经验事实,它虽然符合人们对资本的感觉经验,但对于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马克思强调,对资本如何产生“剩余价值”的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论证,不能违背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因而必须以商品等价交换为起点。他说:“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12]193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造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所有商品都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其所有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即通过讨价还价所达成的交易结果,不仅实现了不同商品间的等价交换,而且对于买卖双方来说,由于谁也没有占到对方的便宜,因而实现了商品经济的公平和正义。[20]于是,当马克思在他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来论证他的这个资本所获得的那个剩余价值时,则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即根据马克思构造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构成资本的商品在以资本执行职能时,无论是在流通过程,还是在生产过程结束时,都不可能产生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论证那个赢利的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不得不把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也包括他自己过去一直使用的“劳动商品”概念,例如,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这部著名的作品中所使用的“劳动商品”概念,在《资本论》中更改为“劳动力商品”概念。
为了使“劳动力商品”符合作为全部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的等价交换原则,马克思首先是对“劳动力”概念进行定义,特别强调劳动力存在于活的人体之中,以区别“劳动”可以从人体中分离出来。①尽管劳动是人的劳动力的支出或使用,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商品”概念的含义,是劳动商品的买卖双方,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以后,以订立契约的方式,一方按照契约的要求支付劳动商品,另一方则按照契约的要求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这是一个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等价交换的活动和过程。在这里,“劳动”是由劳动者从他的自身分离出去的一种商品,劳动者到工厂里——无论是到资本家的工厂里,还是到所谓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里——做工,只是按照在合同中规定的劳动岗位,付出一定时间的劳动,得到一定数额的工资。只要双方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以后签订的劳动合同,并且严格履行合同中的各项条款,所得到的结果自然是符合公平和正义原则的等价交换。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2]195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为后来把劳动力连同活着的人一起买卖,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其次,为了不违背商品等价交换原则,马克思说明,“劳动力商品”也像其他商品一样,是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和前提的。他说:“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12]195但是,这种商品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和平等,很快就在马克思的“劳动力的买和卖”中打了折扣,而且是很大的折扣。马克思说:“这种关系(指‘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引者注)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商品。”[12]195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制中的奴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工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自由工人……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 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13]336-337据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由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区别于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制的“局部奴隶制”。也就是说,在完全奴隶制下,奴隶是一辈子当奴隶;在资本主义的“局部奴隶制”下,自由工人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当奴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家对工人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奴役关系”;[13]5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工人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13]279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则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说成是“奴隶制度”[21]。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由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局部奴隶制”为基础上的。在这里,马克思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奴隶制残余,当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普遍现象,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尽管马克思一再强调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但是,马克思似乎忽略了,再特殊的商品,都不能违背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商品。况且,任何一种商品,都有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马克思这些努力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局部奴隶制下的“劳动力商品”,纳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之中。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制造逻辑上的混乱以外,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的。关于这方面的系统论述,拟另作专题研究,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如果考虑到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被媒体称为“黑作坊”“黑砖窑”,以及某些“血汗工厂”的奴隶制残余或局部奴隶制,不时地沉渣泛起,那么,在马克思时代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制残余或局部奴隶制,也就是可以让人们理解的了。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与那种奴隶制残余或局部奴隶制所具有的本质区别。我们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引用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资料,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商品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和平等正在逐步发展,这种发展具体地表现为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工作日不断趋向合理,工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也在不断地扩大和落实。
只是由于马克思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和罪恶为己任,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活动,从而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和罪恶看得多一些,以至于说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871这样极端情绪化的言论,甚至用辱骂性的语言把英国的工厂主称为“英国狗厂主”[22]。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家的这种强烈的感情因素,恰恰犯了理论研究的一个大忌。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提出“为学”,即“治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理论研究活动开始以前,清除掉内心的一切杂念,达到“致虚极,守静笃”[23]的精神状态,以保证理论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而爱因斯坦则明确要求:“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不能任性或感情用事。”[24]因为任何带有成见或带有感情色彩的理论研究,都会在研究资料或素材的选择上有所偏好,由此所得到的结论自然有失客观、公正。这就像如果有人以当今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罪恶为依据,就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有失客观和公正一样。
也许马克思后来也意识到他的资本概念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杨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一文中说,“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马克思认识到,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也就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决定停止出版《资本论》第2卷,而且一直到10年后逝世,马克思都没有再提《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25]这至少可以说明,建立在《资本论》第1卷基础上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手稿,令晚年的马克思非常不满意。
[1]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7-6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35.
[3]庄江山.论资本的二重性[J].兰州学刊,2006(4):19-21.
[4]乾润梅,刘建伟.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双重属性划分及其现代意义[J].生产力研究,2009(24):13-14,17.
[5]何玉长,袁乐轶.资本二重属性论[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8-12.
[6]聂亚珍.马克思资本观的再认识[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00-102.
[7]王天祥.论资本的性质[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9(6):69-70.
[8]周扬明.论资本的两面性[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70-76.
[9]孟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属性的再认识[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52-54.
[10]杨圣明.论资本的二重性问题[J].学术探索,2005(4):19-26.
[11]王桂英.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范畴的思考[J].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26-28.
[12]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5.
[14]中央纪委研究室.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EB/OL].2014-01-23,10:38,http://www.zzdjw.com/n/2014/0123/c178388-24206017-4.html.2014-9-13.
[15]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
[1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7.
[18]周德海.论“经济人”的道德——兼评目前学术界对“经济人”的研究[J].管理学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会会刊),2013(2):12-16.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7):22-26.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8.
[20]周德海.论马克思商品等价交换理论中的道德和伦理——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为参照系[J].管理学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会会刊),2013(5):12-16.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1.
[23]周德海.《道德经》认识论思想新探[J].巢湖学院学报,2009(1):1-11.
[24]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0.
[25]杨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