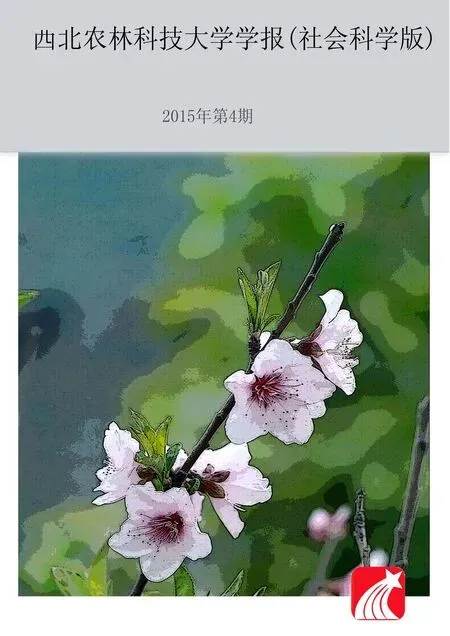阻断司法救济的村民自治
——以村委会选举权为视角
蒋 成 旭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杭州 310008)
阻断司法救济的村民自治
——以村委会选举权为视角
蒋 成 旭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杭州 310008)
不同的法院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名单纠纷案件存在受理与不予受理两种做法,但根据我国现行的制定法,法院不存在受理此类案件的依据。村民自治阻断司法救济有其历史原因和意义。立法机关未将村民委员会选举权纳入司法救济可能出于保护村民自治权的考虑,但村民自治权是法律赋予的,有其自治边界。由于当前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革,加上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村委会的角色功能发生错位。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司法介入村民自治并不会侵蚀村民的自治权。通过对政治权利内涵的拓展和村民自治边界的明晰化,司法介入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
司法救济;村民委员会;选民资格;自治;选举权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87年制定以来,已经历经1998年和2010年的两次修订。两次修改对于诸如村委会成员的任免、村民委员会选举资格异议、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等问题均没有明确指出司法救济的途径。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农村的自治问题开始日益复杂。尤其是村民选举资格问题,由于牵涉到土地权利,对村民资格选举登记名单的争议往往上升为村民资格的确认问题。选民资格如何认定,直接关系到村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当前村委会选举中村民反映最强烈、矛盾较为集中的问题,也是困扰基层组织者指导村委会选举实践的难题之一[1]。
然而实践中对于村委会选举资格的纠纷可诉与否,法院的处理方法存在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6期刊登了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吴少晖不服“选民资格处理决定”案,该案起诉人吴少晖对所在村村民选举委员会不予登记其选民资格处理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受理并判决,撤销该村民选举委员会的处理决定。而2011年发生在河南的卢菊红等不服“选民资格处理决定”案,法院却做出了驳回起诉的裁定。2012年8月在福建发生的一起同样性质的李家春案件,连城县法院却又受理并做出了判决。
对照三份判决书,在判决依据当中,2003年的吴少晖案和2012年的李家春案的判决书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言下之意便是承认了《民事诉讼法》关于选民资格案件的特别程序适用于村民委员会选举选民资格案件。而2011年的卢菊红案的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所规定的内容对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第二十八条,指涉公民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中的选举资格纠纷。而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组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选民对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可于期限内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在选举日前依法作出处理,但条款中未明确规定村民对村民委员会公布的选举村民委员会“选民”名单持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故该类案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选民资格案件。
从以上分析中至少可以归纳出这样三个问题:首先,《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选举权”是否包含村民委员会选举权[2],亦即村民委员会选举权是否是宪法层面上的基本政治权利?其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选民资格案件是否包含村民委员会选举选民资格案件,亦即村民委员会选举选民资格案件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再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条没有明确规定村民对村民委员会公布的选举村民委员会选民名单持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对于这样的案件,当事人是否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来看,似乎对于此类案件法院是可以受理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用的“公民”的提法,体系上看似乎是专为《选举法》而存在的;况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条关于村民委员会选民登记异议的规定历经两次修订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诉诸法院。早在1998年第一次修订后2010年第二次修订前,就已经有很多声音建议将司法途径纳入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当中,但2010年修订时并没有这么做。如果说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是代表了最高院的态度,那么为何在2010年修订之后仍然没有将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司法救济途径呢?纵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只是对村民委员会选民登记异议没有规定司法救济的途径,还包括第十六条对罢免村委会成员、第十七条对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规定,也没有规定其可诉性。唯一能够诉诸法院的,是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面对现实中对村民选举资格实实在在的诉讼需求,历经两次修订,立法机关为何不将司法救济纳入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 这究竟是法律上存在漏洞,还是立法者有意排除对村民自治的司法干预?对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从法解释的角度探寻规范的原意。
二、阻断司法救济的规范分析
(一)宪法与村委会组织法
学理上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指的是人们参加国家权力机关或者代表机关的创设或组织所必需的那种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广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则指的是人们为实现任何国家机关、公共团体乃至私人组织的创设或组织所必需的各种选举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3]。《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这一条是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规定之一。按照凯尔森的定义,政治权利是:“公民具有参与政府、国家‘意志’之形成的可能性。确切地说,即意味着公民可以参与法秩序的创造”[4]。林来梵教授认为应当将政治权利宽泛地界定为“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一切政治性权利的总称”[3]。联系《选举法》对人民代表选举资格的规定,《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含义应当是狭义的。而村委会选举权则显然不属于狭义上的选举权,因为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代表机关。实际上,作为一种特定范围主体才享有的选举权,村委会选举权并不排斥狭义上的选举权,两者互不包容。在选举村委会的同时,村民仍可以行使《宪法》所规定的选举国家机关、代表机关的狭义选举权。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中的村委会选举制度已实际构成我国选举制度之一种,村民选举村委会时所实际享有并已广泛行使的选举权业已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基本权利之一,亦应属于宪法学研究中的‘选举权’”[5]。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将问题复杂化了。村民委员会作为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村民的选举权与狭义上的选举权是没有关联的。也有学者认为,村组法的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直接来源于《宪法》三十四条[6]。实际上,村组法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其宪法来源应当是《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原因就在于,村委会首先是一个自治组织,其次才有村委会选举权;主体首先必须是村民,然后才有村委会选举权。所谓的“选举权”是建立在“自治”的环境之下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村委会选举权相当于是一种广义选举权中,选举组成公共团体所必需的选举权。然而这种选举权又不同于一般公共团体和私人组织的选举权,因为相比一般的公共团体和私人组织,村民的身份并不是基于村民自由选择的意志。公共团体或私人组织的身份是参与者自由选择加入后产生的。一旦参与者认为自己的选举权受侵害,他大可以用脚投票,一走了之,依据组织章程取回自己那部分财产,换个组织再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然而村民对村委会的选举权倘若被侵害,村民总不能一走了之,取回自己那部分集体土地使用权,换个村庄再当村民。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村委会选举权带有一种政治强制色彩,其核心在于村民身份或者称村民资格的确认,村民身份或村民资格的变动有政策和法律的约束。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以后在十三条第一款后面新增了一句“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样的规定和宪法三十四条几乎一模一样。立法者似乎也倾向认为是政治权利。虽然不能当然推论出村委会选举权属于政治权利,因为1989年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有同样的一条规定。但如果要将村委会选举权纳入到政治权利中去,那么就必须修正当前的广义狭义二分法的理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受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授权所作出对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的规定。然而虽然做了这样的规定,但是有两点不足,导致了当前村委会选举权纠纷越来越普遍而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其一,村组法没有明确规定“本村村民”的定义。村委会选举权纠纷背后的原因,核心的问题是农村人口与土地及其他相关集体财产利益紧密相连的。村民的经济利益与村集体息息相关,一旦具有了本村的村民资格,就拥有了占有土地的处置权和其他的经济利益。而客观上又不存在一个确认形式来确认某一个人是否属于本村村民。于是村委会选举名单登记就成了代替这样一种确认机制的方式。其二,村组法第十四条只规定了可以向村民选举委员会申诉,没有为村委会选举权预留一条司法救济的途径。这样的规定几乎没有解释的余地可以将这种纠纷纳入到司法救济。当前一些地区的村组法实施办法中还对这类纠纷规定了司法救济的途径,联系《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这样的规定是有违反上位法的嫌疑的。
(二)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这一条规定在第十五章特别程序当中。《选举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五日内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明确了对选民名单申诉的处理决定不服的是可以提起诉讼的。可以明显看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是对应于《选举法》第二十八条而设置的。何况《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是向“选区”所在地基层法院起诉。“选区”是《选举法》上的概念,而村民委员会选举根本就不存在“选区”的概念。另外,“选民”的概念也从未出现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当中[7],无论如何也没法解释出法院以民事诉讼程序(至少是特别程序)来受理村民委员会选举纠纷的法律依据。地方的村组法实施办法对于此类纠纷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规定无异于拓宽了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具有现实意义,但仍然是缺乏合法性。最高院公报2003年公布的吴少晖案,以及2012年的李家春案,法院以民事诉讼程序受理这两个案件同样是缺乏法律依据的。相比之下,撇开价值层面的问题,河南的卢菊红案,法院以该类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选民资格案件范围为由驳回起诉的做法应当是正确且合法的。
有学者提出应当将村委会视为被授权的行政机关或者“准行政机关”,其所承担的应是一种“公共职能”,可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如果村民选举委员会可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法院就可以深入考量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民资格认定行为及其他主持村委会选举工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有助于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康发展”[8]。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是根本误读了《村委会组织法》的条文。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在一定情况下也确实可以成为被授权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成为行政行为主体,然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是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的,理论上跟村委会没有直接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唯一直接涉及到司法救济的是第三十六条:“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然而这里也是村委会或村委会成员的决定才能诉诸法院。退一步讲,哪怕我们认为村民选举委员会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行使“公共职能”的组织,但村委会的选举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利”,按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政治权利”不属于“人身权”也不属于“财产权”,法院仍然可以不属于受案范围的理由驳回。当然,按照上文对宪法上选举权的分析来看,村委会选举权是一种带有政治强制色彩的广义选举权,虽然《村委会组织法》倾向于将其作为政治权利来规定,但其并非宪法上的政治权利。但尽管如此,这种选举权也很难说是一种人身权或财产权。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后该条内容移至第十二条),一则不属于第一款所列八种情形,二则特别法即《村委会组织法》也没有对此类案件规定可以提起诉讼,也不适用第二款,依然很难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综上,按照当前的理论体系,村委会选举权不是宪法上的基本政治权利,此类案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的受案范围。按照当前的规范体系,法院对这类案件不具备受理的法律依据。
三、村民自治与司法的介入
(一)村民自治及其边界
《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定义,“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此来看村民自治的概念,首先它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法律制度,是国家实现统治和治理的一种方式。在单一制的体制之下,宪法规定了政府的触角止于乡镇一级,而授予村一级以自治的权利。在这个自治制度中,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的执行机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二,村民自治的概念也指一种自治活动,它包括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自治的方式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方式,村民自治是历史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
我国村民自治的理念其实由来已久。我国古代传统的国家行政机构一般不进入乡村,亦即所谓“王权止于县政”。一方面这是一种集权需要对行政资源的妥协。因为对于古代社会来说,集权是一种根本原则,朝代更迭却又周而复始地围绕着集权而构建官僚行政制度。然而国家的行政资源有限,而农村散布全国各地,村落规模不大但数量庞大,倘若全面进入农村治理会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村落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家族的聚居地。村民的事务往往是家族内部的事务,政府干预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很难起到调解纷争的作用。反而是“乡绅”“绅士”这样长老式的人物能够较好地调解村民纠纷。基于此,国家往往将村级的治理交给村民自治。而我们现在的村民自治,实际上是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9]。
建国初期,我国的村级基层组织是作为国家政权机关而存在的,1950年政务院发布《乡(行政村)人们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们政府组织通则》,规定行政村是人们政权的基层组织,村人民政府是村人民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又是政务院统一领导的地方基层行政机关。村政府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治安保卫委员会,调解委员会调解了大量的农村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但到了1958年进入人民公社时期以后,取消了乡镇政府体制,实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村一级组织改为生产大队或耕作区,生产大队既是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时期,国家权力空前深入农村,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形成了农村公共资源由下向上集中,由行政权向党组织集中,执政者的领导权一直延伸到了农村的最基层人民公社,对农民的生产劳动、政治活动、家庭生活等均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阻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1979年至1983年,全国农村逐渐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家庭经营,对人民公社体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当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不再去直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活动以后,这种组织形式就需要改变[9]。而“村民委员会”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如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基层农民自发的创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宜山、罗城等县有些农村,农民曾经自发地建立起了村民委员会,那时,许多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瘫痪,村里好多事情没有人管,一些村的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选出村民委员会,为全村人办事[10]。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敏锐地抓住广西罗山、宜山等地农民创造的“村管会”一类经验,在他的主持下把村民委员会写进了“82宪法”。1987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时,彭真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没有什么民主传统。我国民主生活的习惯是不够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抓两头:上面,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强社会主义法制;下面基层实行直接民主,凡是关系群众利益的事,由群众自己当家,自己做主,自己决定。上下结合,就会加快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经过十年的试行,中途也遇到八九事件的波折,但到了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就基本确立了村民自治这样一种基层民主制度。
良好的村治必须建立在村务管理者和村民之间的充分合作之上,通过合作和协商的手段解决各种分歧和矛盾[11]。自治是法治下的自治,村民自治并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村民的自治权是宪法赋予的,并非源于如一般私人组织自治基于意思表示而达成的契约。在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下,村民自治的边界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有些类似。正如行政裁量是建立在依法行政基础上的裁量,并不是所有事务都可以自治,自治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自治。法律没有留下裁量余地的规定,不存在裁量的空间。同理,法律直接予以规定的,便是自治的边界。在村民选举问题上,自治的边界体现在村民选举委员会对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的登记。2010年《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以后,将原来的第十三条扩充了许多内容。其中在第二款新增应当进行登记列入参加选举村民名单的三种情况,第三项规定:“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可见对于户籍不在本村的村民,要参加村委会选举,不仅要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还需要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才行。这里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就是自治边界的体现。这意味着,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都不能代替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支持或反对某村民参加村委会选举。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不同意某村民参加选举,也不受司法的审查。这项事务是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另外,除了第十三条规定的三类情况之外的村民,则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决定是否列入选举名单。这也在村民自治的范围内。而对于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二项的情况,法律直接规定“应当”列入选举名单,村民选举委员会就不能以村民自治的名义排除。
(二)司法介入的必要性:村委会的角色功能错位
对于村民自治这个制度,立法者的本意实际上是企图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体系,通过乡镇一级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以及党组织的领导来维系农村自治和基层政府。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基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国家力求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以期生产力的提高。尽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但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且仍然立命与土地之上,农村文化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仍旧是封闭的熟人社会,社会秩序依靠老人的权威和传统[12]。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立法者不能指望在一朝一夕破除当时仍然守旧的农村文化,况且各地百废待兴,没有余力将政府的触角延伸到村级治理。在当时的情况下,立法者期待通过将治理的权力交予农民自己,以传统的人情文化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达到纠纷自我化解的目的。在20世纪80年代着手进行“乡政村治”制度安排时,由于政府过去主要管理的经济事务大多转交给农民,政府要求村干部代为办理的行政事务并不多,村组织的自主性定位较明确。彭真在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就强调:“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基层政权的‘腿’”并警告要防止“给村民委员会头上压的任务太多,‘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这样就会把它压垮”[13]。然而立法者并未预见市场经济的深入开展会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使得农村的秩序和文化逐渐瓦解,再也没有办法达到纠纷自我化解的目的。
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的深入,农村原先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大量的劳动力脱离了土地的束缚,流向城镇。在中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又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他们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城市打工,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里租房。原有的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被打破,农村不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加上得益于科技的传媒业的迅速发展,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达达改变了农村人民的观念。其结果导致村民生活的伦理色彩越来越淡化,村庄的交往规则最终摆脱“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走向以利益算计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村庄规则体系的理性化、利益化意味着村庄共同体性质的变化[12]。村民纠纷不再是单纯的村民纠纷,而是加入了租房、借贷、劳动合同等等原本不曾出现的纠纷;而原来可以由村民权威解决的纠纷,诸如村民资格问题、集体土地分配问题,也产生了外化效应。本文所引的吴少晖案,实际上就是表现为村委会选举名单异议的村民资格确认纠纷。村民成分复杂化,带来了纠纷的复杂化。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一些农村基层地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控,特别是政府对农村管理的事务迅速增多,政府要求村干部完成的任务大大加重[14]。《村委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一条规定为基层人们政府控制村民委员会留了一条路。虽然规定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委会也只是“协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基层政府普遍干预村民自治事项,加上党组织的作用下,村委会事实上成为了基层政府的“打工者”。乡镇政府常常以国家的名义在以维护公共利益目标的情况下广泛地运用基层公共行政权力来实现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中村级民主管理事务的领导[15]。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各地出台相应的实施办法甚至包括一些部门规章中,大量地规定了村委会诸如计划生育、义务教育、服兵役和税务等行政性的任务。例如,《统计法》要求村委会“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到了该法《实施细则》,变成由村民委员会指定专人负责行政村的统计工作,后者“在统计业务上受乡、镇统计员领导”[16]。这些作为规章的细则和规定从根本上就扭曲了村委会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从而使原本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会越来越脱离其最初的制度设立目的。对于国家而言,这种变化在乡村治理方面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大了农民对地方政府的期待与现实状态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所导致的不信任客观上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能力与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使村民在不知不觉之中被现代国家进一步规训,国家观念和法律意识得到了塑造和强化,地方性共同体中的“乡民”正在逐步嬗变成现代国家中的“公民”。于是,村民们一方面对抽象的国家,对遥远的中央政府保持着高度的认同;同时另一方面又对身边的具体又可及的基层政府组织严重的不满、不信任[12]。一来导致村委会的权威性质被大大地削弱,纠纷自我化解的功能退化;二来使本属自治范围内的纠纷外化,村民意识到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实质干预,找村委会来解决问题已经没有效果,不得不寻求外部的中立裁判。在传统官僚观念的作用下,无止尽地上访也就应运而生。
然而失去了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和传统的人情文化并不意味着村民自治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集体经济需要有基层自治组织的支撑。恢复和维护自治组织的活力,需要具备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还需要政府淡出村级治理,停止对村民自治的不当干预。但是寄希望于政府主动淡出是不切实际的,何况农村环境已经发生重大的变革,纠纷的自我化解已不能实现。司法介入村民自治,其意义就在于提供一个中立的裁决来化解自治的纠纷,而非干预自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倘若阻断司法的介入,那么虽然《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应当列入村民选举名单的三种情形来保护村民的选举权,但由于没有诉讼的可能,这样的规定便毫无意义。退一步讲,用不用司法救济这条途径是村民自己的选择,但给予这样一个途径则是国家的义务。国家不应当代替村民来做出选择。
(三)司法介入的可能性
有学者提出,可以在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之外设立“村民自治监督委员会”,有权对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行使自治权的行为进行日常监督[8]。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村民“自治”定位上的做法。即,肯定村民委员会自治的地位,按照理想的状态相对独立地进行村民自治活动,排除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在这样的状态下,设立一种内生的监督机构,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建构选民资格纠纷解决机制来达到纠纷化解的目的,是可行的且符合“自治”定位的。但客观上,实现自治的农村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人口流动频繁、纠纷外化严重的现状之下,要建立内生的监督机构所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没有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联想到当前这个制度存在的一个不合理之处——正如焦洪昌教授所言,对选举名单不服的是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而村民选举委员会本身是制作名单的主体,这样做出的终局决定是有违“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的自然公正原则的[7]。这就需要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纠纷解决途径。而这样的途径,基于以上分析,必须设立在村民自治范围之外。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七条,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由乡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但是基于上文的分析,导致村民委员会角色定位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的不当干预,很多情况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行政目的,培养村级“代理人”,村委会的选举候选人是在基层政府的指使下安排的[16]。显然由政府来对选举纠纷做出处理代替司法救济是不太能够达到理想效果的。
那么司法是否有介入的可能性?首先,从上文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权的分析来看,村民委员会选举权的性质和定位仍然不甚清晰——虽不属于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但显然区别于一般广义上的选举权,带有政治强制的色彩。传统的广义狭义二分法似乎不足以准确描述出村民委员会选举权的外貌,需要对其修正或补充,使村民委员会选举权的定位能够得到明确。当前的规范体系下,即使将村民委员会选举权解释为一种政治权利,它仍然因民事诉讼法上的障碍(“选民”和“选区”的概念阻止了村民选举权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的障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得不到任何司法的救济。从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后的条文来看,新增了“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使村委会选举权在理论上摆脱尴尬的境地存在可能性,在制定法上已经留出了解释的余地。如果要将村委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纳入“政治权利”范畴,就只需在学理上对“政治权利”重新进行定义,拓展其内涵。
第二,如何保证司法的介入不侵蚀村民自治?纵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历程,立法者未规定司法救济,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司法的介入会侵蚀自治,或者说,自治事务范围内应当排除司法救济。实际上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2010年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这里的“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明显地表现出立法者对村民自治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登记村民选举名单的机构是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的村民选举委员会,并非是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本身。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户籍不在本村的村民,在本村居住了一年以上,本人也申请参加选举,也经过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同意,但村民选举委员会未将他列入选举名单。相应的,户籍在本村,本人也表示要参加选举,但村民选举委员会也可能未将他列入选举名单。在满足年满十八周岁的条件下,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这样的村民是“应当”被列入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的。如果选举委员会没有这么做,那么就有违法之嫌。这就为司法的介入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司法虽然不能审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内容,代替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做出一个支持或反对某个村民参加选举的决定,但是对于这样的情况,法院可以审查未被列入选举名单的村民是否满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内容并非村民自治范围之内。村民自治在法条上的体现,一是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对于户籍不在本村的村民能否参加选举的一个决定权;二是对于十三条所列三种情况以外的其他村民能否参加选举的决定权。倘若有村民以村民选举委员会为被告提起村民选举名单登记纠纷的诉讼,法院只审查原告是否满足第十三条规定的三种情况,并不审查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这样的审查显然不会侵蚀村民的自治权。第一,对于本村村民,即满足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和第二项的村民,理所应当将他们列入选举名单,因为这是作为村民成员所应具备的基本权利,村民选举委员会对此没有类似于“行政裁量”的自治余地,不具备剥夺他们村民身份的权力,是法律规定,并非自治内容;第二,对于外村村民,即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的情况,村民的自治范围限于同意或者不同意他参加选举,这是法律规定的自治内容,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不受司法的审查;第三,对于除这三种情形以外的其他村民,村民选举委员会有权决定是否列入选举名单,也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之内。
四、结 语
村民自治阻断司法救济有其历史原因和历史意义,但在当前的法治理念和法律体系下,这样的制度安排已经显得不切实际。当前司法实务中产生的诸多龃龉,实际上是解决现实纠纷的需求与制度缺陷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在制定法上,无论是《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找不到法院受理村民选举资格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历经两次修订仍没有将司法救济纳入到村民选举纠纷中,可能是出于对村民自治的保护。但通过对村民自治这一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到,司法的介入并不会侵蚀村民自治权。村民自治是法治下的自治,法律赋予的自治权有其边界。使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而通过对村民自治边界的明晰化,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的介入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所以,对现行制定法进行修改或司法解释,使村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得到司法上的救济,是十分必要也是切实可行的。例如可以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中增加不服村民选举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的,可以向村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在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中增加一款或一条村民选举资格纠纷的规定,或者由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规定村民选举资格纠纷案件参照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审理。但具体应当如何做出规定或解释,甚至应当以民事诉讼途径还是以行政诉讼途径来救济,则还需另作讨论。另外,实践中存在村民选举委员会以村规民约为依据将某些村民排除在选举名单之外的情况,涉及法院如何审查村规民约的问题,也需要另作讨论。但归根到底,村民自治并不是,也不应当是坚不可破的牢笼。有权利即有救济,是解决村民委员会选举权问题的基本原则。
[1] 陈晓莉.农村基层换届选举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以西安市为个案[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3):139-144.
[2] 彭澎,孙昌军.村民选举权之检视:宪法价值与宪政精神[J].南京社会科学,2009(7):106-112.
[3]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20-125.
[4]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8.
[5] 刘志鹏.论村委会选举中的村民选举权[J].中国农村观察,2002(3):61-67.
[6] 马俊军.村民委员会候选人资格问题的法律探讨[J].法律科学,2002(2):22-30.
[7] 焦洪昌.选举权的法律保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9-210.
[8] 石佑启,张显伟.村民自治:制度困境与路径选择[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0(5):140-145.
[9] 高杰.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的背景、现状和政策导向[J].法学研究,1994(2):11-15.
[10] 穆生秦.村民实行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好形式[J].中国法学,1988(2):41-45.
[11] 包先康,朱士群.村民自治视野下村民代表的权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3):139-144.
[12] 董磊明.宋村的调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96-162.
[13] 彭真.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09-611.
[14] 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BE/OL].[2002-10-31].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9704023g.htm.
[15] 胡建华.宪政视野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运行的反思[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2):74-79.
[16] 何海波.通过村民自治的国家治理[M]//沈岿.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个案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36-162.
Blocking Judicial Relief Within Rural Villagers’ Autonomy in China:——From Perspective of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
JIANG Cheng-xu
(GuanghuaLawSchool,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08,China)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practices of courts on cases verifying the qualifications for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s: accepting the suits or rejecting the complaints.However,the fact is that acceptance for this kind of cases has no legal basis.The judicial review is restricted within Rural Villagers’ Autonomy of China for a long history and with legislative purposes.While the right to vote for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s is not available for judicial review,which is to protect the villagers’ autonomy system,it’s still within the boundary of rule of law.As the rural society in China has transferred in every aspect,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 improper intervention,the villagers committees’ role and function have been dislocated.Releasing the judicial review within Rural Villagers’ Autonomy,especially within the cases verifying the qualifications for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s,is one possible and important solution,which will not erode the villagers’ autonomy as long as operating within the boundary of rule of law.
judicial review; villagers’ autonomy; electional qualification;right to vote for villagers’;committee elections
2014-1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20)
蒋成旭(1990—),男,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F325.1;DF22
A
1009-9107(2015)04-01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