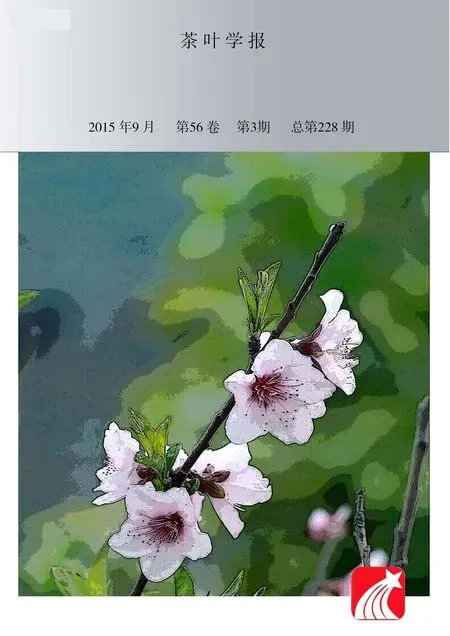山地生态茶园复合栽培技术的研究与展望
翁伯琦,王义祥,钟珍梅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态研究所/福建红壤山地农业生态过程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003)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截至2014年,我国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分别为274.19万hm2、215.84万t,依次占全球茶园总面积和茶叶总产量的59%和45%左右,均居世界第一;全国茶叶总产值已经达到 1349亿元[1-2]。就茶叶生产分布格局而言,中国茶叶生产主要集中在山区农村,尽管十几年来茶叶开发面积有所增加,但数量、质量、效益仍然无法实现同步增长,主要原因依然是大部分山地茶园建设仍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其突出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要强化水土流失防控、提升茶园土壤肥力、控制多发病虫危害、提高产量及其品质、有效减少农残含量等方面[2]。以福建省为例,全省茶园面积 23.67万 hm2,占全国茶园总面积的8.6%,居全国第五位;茶叶总产量已超过35万t,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6%,居全国第一位[1];茶叶单产达到1500 kg·hm-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现居全国第一位[3]。近年的统计资料表明,福建省山地茶园中度以上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6.3万hm2,大约占全省山地开发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3%,占全省茶园总面积的比率达33.42%,如果加上轻度的水土流失面积,即有近一半的茶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有的山地茶园的水土流失则十分严重,危及生产与区域生态安全[4]。如何寻求既保障生产又保护生态的山地茶业开发之路,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实践证明,发展生态茶园复合栽培及生产模式是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双赢的有效举措。实施山地生态茶园建设与复合栽培技术,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构建复合栽培模式,丰富茶园生物多样性,改善与优化生态环境,提高茶叶产量与品质,以求持续满足消费者对安全且富有营养的茶叶以及相关食品和饮料的多样性需求。不言而喻,搞好山地生态茶园建设与实施复合栽培技术,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求,而且也是我国茶叶转变生产方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观要求。
1 生态茶园的提出与主要内涵
自古就有茶园复合栽培的实例,刘禹锡(公元805年)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提到了竹间种茶的方法,阐述了竹下可使茶树有适宜的庇荫环境,而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5]。早在宋朝,民间则有“植木以资茶之荫”的茶园生产实践[6],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据文献报道[7],30年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根据当地农业发展和茶叶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创立了胶茶人工群落与生产体系,并在《生态学学习笔记》一文中系统总结了多年的生产实践经验,同时提出了生态茶园的概念并阐述了山地生态茶园5个方面的内在要求。即生态茶园就是按生态学原理和生态规律建立起来的生产体系,其应当具有栽培多层次、物种多成份、环节多功能,结构稳定性、系统平衡性等5个鲜明特点,有利于整个生产体系实现稳定持久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并实现开发与保护统筹协调的茶园[8]。
作者以为,山地生态茶园是随着中国现代生态农业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属于生态农业建设的内容之一。伴随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历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学者或专家对生态茶园也提出了不同的定义。
就理论意义认识,业界对生态茶园(Ecology Tea Plantation)比较认可的定义表述为:以茶树为主要栽培物种,以生态学(Ecology)和经济学(Economic)的主要原理为建设规划指导,围绕山地绿色茶业生产而构建的资源循环利用且可获取高优效益的人工复合栽培的茶园生产—生态系统[9-10]。实施生态茶园建设,可以充分发挥生产经营者对茶园生产—生态系统的光、温、热、水、肥的优化调控作用,结合实际并优化创立多种方式与多样功能相融合的人工复合栽培生产与生态系统,充分利用各种生态环境资源,力求减少山地水土流失,增加土壤水分涵养,发挥生物多样功能,从而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就实践意义认识,生态茶园一般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系统的整体性。山地生态茶园的系统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各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内各成分之间有效链接及其内在联系,这种因子之间的优势有效互补与便捷有序联系有利于茶园生态经济系统形成一个有机运转的整体。二是生物的多样性。山地生态茶园建设是充分吸收我国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要素,因势利导构建以多种优势生物因子与多种生态农业模式集成的生产体系,这种新的生产—生态系统是由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组装配套而构建起来的多功能复合性生产体系,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特点,有利于促进山地茶业转型升级,融合社会发展需要与当地生产实际,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三是生产的高效性。作者认为,实施山地生态茶园建设与复合栽培技术,其重要的环节就是要把握高效性:即通过物质循环与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要强化废弃物资源化应用,减少化肥等外源性投入,利用有机肥保育土壤生态,同时提高生态茶园的综合效益。四是产业的持续性。建设山地生态茶园与实施复合栽培技术,就是通过综合配套的技术措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合理循环利用废弃物,通过土地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同时要注重保护和改善生态条件,防控水土流失,治理面源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茶叶及其附加生产的农产品安全性。
就其主要内涵而言,山地生态茶园包括6个方面重要环节:一是注重茶园布局。山地茶园开发一般要遵循“头戴帽,腰绕带,脚穿靴”布局原则,注重水分涵养,优化茶叶栽培,配套工程设施。二是注重茶园改造。禁止毁林种茶,超坡度的开垦,分批改造茶园,合理套种牧草。三是注重水土保持。实施覆盖种植,推广沟埂配套,防控水土流失,发展生草绿肥,培育山地肥力。四是注重生态栽培。优化茶林套种,茶草合理间作,搭配茶果比例,营造良好环境。五是注重生物防治。应用生物农药,防控病虫发生;合理套种牧草,就地生产绿肥;有机无机肥料配施,物理化学方法配合;既减少污染,又能有效防控茶园病虫害。六是注重循环利用。成功的经验表明,创立山地生态茶园经营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有条件的山地茶园已经开始逐步实施山—林—路—茶—果—牧—草—沼—肥—地力等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环环相联,逐步递进,循环再生,合理利用,使种茶与养地以及开发与保护在种养结合过程中得以统一[11]。通过山地综合开发与循环利用治理,力求提高山地茶园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与污染防控率。
2 山地生态茶园模式及其研究
实际上,人们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茶园的生态栽培。早在唐朝、宋朝就有茶—林套种的成功实践[5-6]。而在明朝罗廪所著的《茶解》中也明确指出:“茶园……惟桂、梅、辛夷、玉兰、苍松、翠竹之类,与之间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12]。我国是茶叶生产大国,在丘陵山区,茶叶生产是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人们越来越重视绿色茶产业的发展,目前茶园种植面积将近4000多万亩。但茶叶栽培不同于平原作物,其所涵盖地区的地形地貌复杂。根据地形地貌,茶园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茶园是在坡度大于30°的山上,面积占60%以上;一类茶园位于坡度15°以下的相对平缓的山地上,其面积大约占20%左右;第三类的茶园的坡度在15°~30°度之间,估计面积也在20%左右[13]。山地茶园生产如何发挥优势,怎样扬长避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在长期的山地茶业生产实践中,广大茶业经营者已深入探索并成功创立了形式多样且可供借鉴的山地生态茶园高效栽培与复合生产模式,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有专家认为,中国生态茶园的建设方式大致可以分为3类[14]:一是复合生态型。以上列举的茶园生态栽培模式也多数属于该种类型,其应用在我国也最为广泛。二是循环利用型。此种建设类型讲求生产环节合理链接,实现有序递进,力求环环相扣,并注重合理利用山地茶园系统内所产生的废弃物质,以达到减量投入,降低成本,防控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目的。循环利用包括山地茶园生态系统内部能量流动和物质有序循环,力求每个参与循环的生产因子都能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的浙江、广东、广西、湖北等省的茶区大多采用这种建设类型。三是多元混合型。这种建设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有机结合,注重发挥复合生态型和循环利用型有机结合的互补优势。是一种产量高、污染少、效益高的生产方式,在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茶区都集中推广这种山地生态茶园的建设类型。
笔者下乡调研了解,山地生态茶园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各地也涌现了许多成功的经营经验与有效的生产模式。就其模式而言,主要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一是茶—林结合型模式。该模式以高山区域居多,一般在茶园四周均有森林环绕,同时配套山边沟种植方式,顺坡开垦栽培,按照一定距离布局机耕道,同时在边坡(或者边沟)与梯壁上播种多品种组合的牧草,防控水土流失。二是茶—果间作型模式。该模式以丘陵坡地居多,一般按照梯台优化开垦,拉后沟补前埂,起垄加高,种草固土,拦截水流,涵养水分,防控流失,保护茶园生态环境。同时在茶园内按照一定比例(15%~20%)套种果树,尤其以套种落叶果树为主,夏可遮阴,冬可透光。有的果园布局比较优雅,左看一条条,右看一排排,井然有序,美观简洁,其往往与休闲观光茶园融合建设,一举多得。三是茶—草结合型模式。该模式适宜性比较广,高山茶园,坡地茶园,梯台茶园皆可。其主要在茶园中按照适当比例套种牧草(多以豆科牧草为主),目的在于有效防控水土流失,同时收获生草就地翻压作绿肥,增加土壤有机质,调节土壤酸度,培肥茶园地力。四是茶—菌结合型模式。该模式通常是在茶—草模式基础上,收获牧草之后,就地在茶树之下接种栽培大球盖菇或者竹荪等食用菌品种,收取菇体之后,将食用菌的废弃物(或者下脚料)翻压作有机肥,其培肥效果则优于生草直接作绿肥的处理。五是茶—药间作型模式。其是指在茶园中套种中草药,尤其是耐阴性的中草药品种,其增收效果也是十分可观的。六是茶—牧结合型模式。在山地茶园,尤其是在边远的山地茶园,经营者往往在套种豆科牧草的茶园中适度放养鸡或者鹅等,外加一些人工饲料,形成以草养禽,禽粪肥园,循环利用模式,在生产茶叶的同时收获野外饲养的家禽等产品,起到一场多用的功效。就整体模式与技术认识,笔者将山地生态茶园模式归纳为茶—X复合型,即在完善山地茶园工程措施基础上,优化配置相关生物措施或者环节X,其中X可以为单因素,也可以多因素。经营者可以因地制宜的结合各自经营的山地茶园实际,优化选择并合理配置X因素,可以是2个因子的组合,也可以是7个因子组合。例如林-茶-果-草-菌-禽-肥有序循环利用的技术组合,或者优化选择其中2~7个不等因子构建成短链条、中链或者长链的递进模式,但要如何选择因子组合链接而成,则必须实际经营的价值,决不可盲目扩大或者无效延伸,要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讲求规模效应与生态法则,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力求实现高效经营与农民增收的目的。
3 生态茶园复合栽培技术研究
3.1 综合生产力
作物生产潜力的发挥,决定其光能利用效率的高低。实际上,太阳辐射状况是植物生长的重要决定因子之一。生态茶园的太阳辐射状况与光能利用效率必然对茶叶的光合作用和茶树的生长有着重要影响。宋清海等[15]研究报道,山地生态茶园采取不同套种模式,茶叶光合有效辐射特征明显不同。即生态茶园不同套种模式的光合有效辐射与传统茶园的比值具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在干热季节樟树—茶树复合栽培模式的光合有效辐射仅为传统茶园的65.9%,在雨季则为76.0%,而在雾凉季节则上升为87.2%。而在千斤拔—茶树套种栽培生态茶园模式中,茶叶生产过程的光合有效辐射在干热季、雨季和雾凉季则分别为传统茶园的 90.2%、91.2%和99.9%。在山地生态茶园的各类套种模式中,茶叶的光合有效辐射的比值变化规律是干热季<雨季<雾凉季。相关试验结果表明,在山地生态茶园中合理间种遮荫树可有效地截留部分太阳辐射,从而可相对提高散射辐射的比例。段建真等[16]研究报道,通过遮阴树的拦截,到达茶树冠层的散射和反射辐射量所占的比例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其中散射辐射量比传统茶园会增加6%~15%,从而有利于茶叶品质的改善。还有研究表明,通过山地生态茶园建设与复合栽培技术的实施,不仅可显著提高茶叶生物能产出密度,提高山地生态茶园产量,而且实施山地生态茶园的配套技术之后,茶叶生物能产出密度是传统茶园的215.5%[17-18]。
3.2 土壤的保育
国内外不少专家与学者广泛开展了间作茶园生态效应及其生产效益评价研究,在山地生态茶园中合理间作不同作物有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有利于改善土壤物理状况,提高土壤养分含量,尤其是生草覆盖种植,有利于有效防控山地茶园的水土流失[19]。阮红倩[20]等对重庆市有代表性生态茶园与普通茶园土壤进行调查评价,其试验结果显示,实施山地生草覆盖技术的生态茶园土壤总体肥力优于传统茶园土壤,在生态茶园中实施生草覆盖并作有机肥施用,不仅能改善茶园土壤物理性状,提高土壤肥力水平,而且可以加快茶园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同时生态茶园土壤养分呈现富集增加的趋势。林修焰[21]对间作白三叶草的茶园土壤 3 年连续观测发现,实施生草覆盖种植的茶园,其土壤养分随时间变化增幅明显,土壤流失量呈逐年降低趋势。土壤微生物和酶是评价土壤生物活性的重要指标。杨清平等研究表明[22],实施林下种茶与茶园养鸡的人工生态茶园模式,不但明显提高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微生物活性及土壤脲酶的活性,而且可有效促进土壤中的营养循环和养分代谢,提升土壤肥力水平,优化改善土壤结构。
3.3 生物多样性
在生态茶园的复合系统中,实施复合栽培技术的茶园生态系统比传统茶园具有更高的生物多样性,而且体系内的昆虫群落结构更加稳定。与传统茶园相比,山地生态茶园具有生产多层次与物种多物种的特征,不仅仅增加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同时也有效扩充了立体生态位,为系统内有益生物的保护和繁衍提供了适宜的生态条件,使山地茶园具有比较高的昆虫群落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对天敌群落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以利于提高生产—生态系统内部的天敌自然控制力度,有效的抑制茶树病虫发生,降低茶园用药水平,以减少过度用药对茶园环境和茶叶产品的污染[23]。韩宝瑜等在皖南麻姑山区对25年历史的有机茶园、无公害茶园和传统茶园的昆虫和螨类的调查结果发现,有机茶园有12727个体,分属于102种57科;无公害茶园有35117个体,分属于81种41科;而传统茶园29018个体,分属于79种4l科[24]。陈亦根等对茶园节肢动物群落的调查也表明复合茶园节肢动物群落比单一茶园节肢动物群落稳定[25]。
3.4 增加固碳量
山地生态茶园生产系统的碳循环与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规律基本相似,茶树生长过程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的CO2并有效合成有机物质,成为大气CO2的库。Hadfield等人研究结果表明,茶园年光合产量为37 t·hm-2,但其全年生长过程的呼吸消耗的干物质达到 22.4 t·hm-2,两者之间的相差量 14.6 t·hm-2就是实际生物产量。Burgess和 Carr等人研究结果则表明,2年生山地茶园年生产量9.43~12.17 t·hm-2,年净固定碳约 4.0~8.9 t·hm-2,相当于净吸收固定CO2的量则为14.8~33.0 t·hm-2。阮建云的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绍兴的山地茶园地上部的年生物产量约为 10.0 t·hm-2,如果按照茶树的根冠比为1:2.5的比例来估算,其每公顷茶园的年生物产量约为 14.0 t,进而年净固定碳则约为 7.0 t·hm-2,相当于每公顷茶树净吸收固定 CO2的量为26.0 t·year-1[26]。尽管目前国内外还缺乏生态茶园固碳能力的直接数据,但据杨如兴等的估算,如果在福建20多万hm2茶园的80%传统茶园中建立山地人工立体复合栽培的生态茶园,那么每年仅福建省山地茶园就可增加生物固碳量3.88×105t以上,同时增加山地茶园土壤有机碳储量超过7.30×105t;通过优化施肥与合理栽培,山地生态茶园有机碳储量将提高 4.70×105t。通过合理构建山地生态茶园技术体系,就可相当于固定CO2数量达5.82×106t以上,有效增强了山地生态茶园的碳汇功能[27]。
4 生态茶园建设成效及其展望
很显然,建设山地生态茶园的主要目的有3个方面:一要改善茶园的规范建设与生产条件;二要着力防控茶园水土流失,有效保护山地生态环境;三要提高茶叶产量与保障茶叶品质,满足城乡居民对风味多样,营养丰富、安全卫生的饮品的消费需求。目前北美、欧洲等国际市场有机食品的消费量每年正以 15%~20%的速度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尽管现阶段市场有机茶叶的销售量并不太高,其消费数量还达不到茶叶总销量的1%。但有人预测,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健康消费意识的增强,国内外消费者更加注重倾向于选择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也包括绿色茶叶产品),就此,中国的茶叶生产亟待需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升级。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消费者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茶叶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必须考虑并着力将生态茶园建设作为中国茶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大研发与推广的力度,其深入的实施与有序的建设,对引领山地茶产业健康发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福建省作为我国的重要茶叶产区之一,山地生态茶园建设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根据全省10个茶产业体系综合试验站的统计资料表明,近5年来共建设高效生态茶园38.9万亩,辐射带动全省80万亩[28]。但目前我国生态茶产业发展规模还较小、科学技术含量不高、生态产品的生产环境恶化呈现加重的趋势、生态茶产品优质优价制度和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些不利因素都是新时期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大力推进生态茶产业化发展,必须把茶叶的生产、加工、物流、销售、品牌等环节联结起来;必须把分散经营的农户联合起来;必须建立完善生态茶产品的质量标准,并引入到产业链的全过程中。此外,生态茶园建设也是解决茶产业环境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实现茶产业低碳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据相关资料报道,每年1万公顷面积茶园所释放出的氧化亚氮数量相当于100 万公顷旱地种植其他作物所释放的氧化亚氮数量。很显然,同样种植旱地作物,每公顷山地茶园所释放的氧化亚氮数量则相当于其他农田作物的100倍[29]。成功的实践表明,有效治理茶产业环境安全问题的关键是减少化肥施用量,推行有机茶叶生产,实现茶产业的低碳化发展。通过实施以茶树种植为主体,通过“树林—茶树—牧草(绿肥)—畜(禽)—沼气”等因子有机链接的循环利用的山地生态茶园生产体系建设,人为地创造多物种并存的良好生态环境,以充分利用光照、土壤、养分、水分、能量等自然资源,同时优化发挥不同类群生物之间和谐相处与互补的优势,促进山地生态茶园内部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使绿色茶树生长与茶园环境改善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实现有机统一。近年来福建省各地发展的“猪—沼—茶”、“茶—鸡—沼—茶”、“茶—草—畜—沼—茶”等模式,既有效解决了动物粪便直接污染环境的难题,又开辟了变废弃物为优质肥料的增效途径,其有助于改善提高山地茶园土壤肥力并增加土壤有机碳库。这种促进种植业和养殖业联动发展的山地生态茶园模式,不仅具有较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而且有助于创立一种有效的低碳茶产业的生产方式。但就茶业低碳生产的实际而言,如何因地制宜地选择技术模式以提高茶园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尚有许多技术瓶颈亟待解决。例如要加强不同景观水平的能流与物流合理配备的技术研究,其将对揭示循环利用过程生物间相互关系,优化建立合理生物群体结构,有效减少化学用品使用量,旱地土壤固碳增汇规律都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山地生态茶园建设与复合栽培技术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也亟待进一步加强,通过研究建立相配套的标准体系,满足生态茶产品产前、产中、产后认证与评价等多方面的绿色环保要求,促进茶叶产品国际贸易,显著提升我国生态茶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1] 封槐松.2014 年全国茶叶生产各项指标超历史[J].茶世界,2015,(6):17-23.
[2] 朱永兴.最近 5年世界各主要产茶国茶园面积和茶叶年产量[J].茶叶科学,2015,35(1):362.
[3] 杨如兴,吴志丹,张磊,等.福建人工复合生态茶园的构建技术与模式[J].茶叶科学技术,2010,(1):21-24.
[4] 陈文祥,游文芝,陈明华,等.福建省茶园水土流失现状及防治对策[J].亚热带水土保持,2006,18(4):22-25.
[5] 朱海燕,刘德华,刘仲华.中国古典茶诗的特点及其开发利用价值[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4):87-90.
[6]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农业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126-127.
[7] 陈红伟,汪云刚.云南省生态茶园建设现状及发展方向[J].湖南农业科学,2014,(12):62-65.
[8] 潘伟彬.生态茶园复合栽培的农学与生态学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09.21(2):65-67.
[9] 车生泉.持续农业的生态学理论体系[J].生态经济,1998,75(2):34-35.
[10] 吴秉礼,李福林.对生态林业的初步探讨[J].林业科学,1993,29(2):152-156.
[11] 田永辉,梁永发,王国华,等.人工生态茶园生态效应研究[J].茶叶科学,2001,21(2):170-174.
[12] 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中国古代茶叶全书[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276.
[13] 王方.茶园管理也要机械化[N].中国科学报,2015-8-12(6).
[14] 朱晓雯.我国生态茶园的建设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25(5):56-58.
[15] 宋清海,毛加,赵俊福,等.生态茶园不同套种模式光合有效辐射特征[J].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6(1):144-148.
[16] 段建真,郭素英.遮荫与覆盖对茶园生态环境的影响[J].安徽农学院学报,1992,19(3):189-195.
[17] 田永辉,梁远发,王国华,等.人工生态茶园生态效应研究[J].茶叶科学,2001,21(2):170-174.
[18] 田永辉,粱远发,王国华,等.人工生态茶园光效能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1,17(4):25-27.
[19] 张文瑞.豆科牧草圆叶决明在闽江下游两岸红壤山地橄榄园的应用初探[J].亚热带水土保持,2007,19(3):11-13.
[20] 阮红倩,庞晓莉,龙宝玲,等.重庆市生态茶园土壤养分调查与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1,(l3):266-268.
[21] 林修焰.亚热带红壤山地茶园间作白三叶草的水土保持效应[J].亚热带水土保持,2014,26(1):5-8.
[22] 杨清平,毛清黎,杨新河.不同生态茶园土壤微生物及脲酶活性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6(4):300-306.
[23] 彭萍,蒋光藻,侯渝嘉,等.不同类型生态茶园昆虫群落多样性[J].西南农业学报,2004,17(2):197-199.
[24] 韩宝瑜.皖南低产茶园节肢动物和虫生真菌群落结构及动态[J].贵州茶叶,1996,(3):20-23.
[25] 陈亦根,熊锦君,黄明度,等.茶园节肢动物类群多样性和稳定性研究[J].应用生态学报,2004,15(5):875-878.
[26] 阮建云.茶园生态系统固碳潜力及低碳茶叶生产技术[J].中国茶叶,2010,(7):6-9.
[27] 杨如兴,江福英,吴志丹,等.提高福建茶园生态系统固碳潜力的技术构建模式[J].福建农业学报,2012,27(6):630-634.
[28] 高峰,苏峰,刘琳燕.福建省现代茶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践与思考[J].中国茶叶,2014,(3):8-11.
[29] 陈宗懋,孙晓玲,金珊.茶叶科技创新与茶产业可持续发展[J].茶叶科学,2011,31(5):463-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