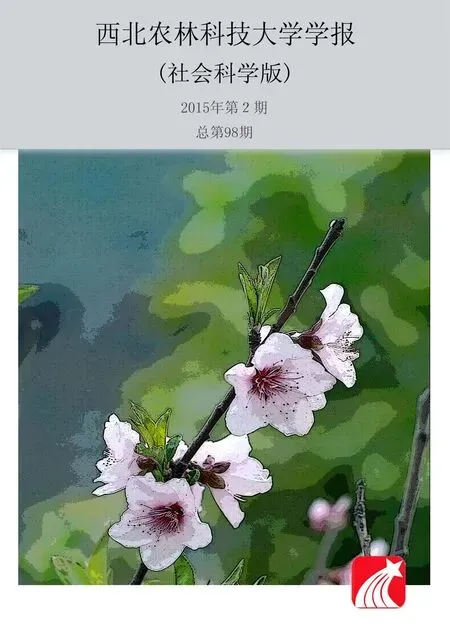现代家庭农场的准确认识、实施困境及对策
施国庆,伊庆山
(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南京 210098)
现代家庭农场的准确认识、实施困境及对策
施国庆,伊庆山
(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南京 210098)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土地家庭经营方式与商品化生产的有机结合。适度规模性土地、农场经营者、市场参与能力是家庭农场的基本构成要件。然而,实践中土地流转意愿偏低且稳定性差、经营者资本积累水平低、市场参与能力弱等却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开展能力建设、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创建良性土地产权制度环境度才能更好的推动家庭农场平稳化运行。
家庭农场;小农经济;土地流转;农村中产阶层;市场参与
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中,我国个体小农经营细碎化土地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生产资料无止境的分散,生产者无止境的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1]。通过农地使用权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大农业之路,可以有效解决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政府将家庭农场写入国家促农发展的最高文件,表明了它已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生命力,然而在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环境中能否生存下去并取得预期的发展效果,将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一、对家庭农场概念的准确认识
按照农业部给出的家庭农场定义,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把资金、劳动力和先进技术等合理地组合在单个家庭内,并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商品化生产。“家庭农场”“农场主”“职业农民”等热门词语见诸于报纸、网络,使人不由得想起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提出的“农民的终结”命题。他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农民作为一个传统的阶级早已终结了,农民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将最终蜕变为“农业生产者”(agricultural worker)或“农场主”(farmer)。孟德拉斯认为,在那些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农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分为三部分:一是占有生产资料、只负责经营的农场主;二是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大部分劳作的自我雇佣的农业生产者;三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被雇佣的农业机械的操作者,他们实际上已成为产业工人[2]。因此,我国家庭农场应该属于孟德拉斯所界定的自我雇佣的农业生产者,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雇工大农场主。
对农业部给出的家庭农场定义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解释和阐述。从制度设计目的来讲,相比个体小农经营方式和农业公司经营方式,家庭农场实现了农地效率的显著提升;从土地制度来讲,它在承认并保留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流转以地租的形式实现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化;从农场规模上来讲,以平均每个农场两个家庭劳动力,几台中、小型机器的耕作能力为宜,国际最低标准2公顷(30亩),规模太小,家庭收入难以保证,反之规模太大,劳动力、机械和资金等要素投入就会不足,单单雇工成本就可能抵消收益,适宜规模还要综合考虑种植制度、经营者能力等因素;从经营主体上来讲,农户是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拥有生产经营的决策权和收入再分配的决定权;从经营方式上来讲,家庭农场是适合农业精耕细作特性的家庭经营组织形式,保证了农业经营主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通过家庭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实现了规模经营与精细化管理的有机结合;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它是具有独立核算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适度规模性、机械化、商品化生产是其收益的必要条件;从收益分配上来讲,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资本投入带来增值收益归家庭农场所有,必然会形成其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虽然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某种程度上都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但就目前阶段来说,它们更多的是作为小农生产方式的重要补充。事实上,土地经营并没有确切的最优规模界限和最优生产模式,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行为当事人会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组织形式[3]。
二、家庭农场运行的基本构成要件及存在问题
(一)土地流转是家庭农场的基础条件
1.农村非农就业者应成为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主要流出方。家庭农场是以适度规模土地为载体,这意味着一部分农户要适度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另一部分农户要自愿流转出土地。随着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增强,农民成为一个趋于分化的群体,可以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8个阶层[4]。从理论上讲,除农业劳动者、雇工外,其他几个农民阶层都应成为土地流转的潜在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不仅群体数量大而且长期生活在城市。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1.3%,在13.45亿总人口中,约6.9亿人是城镇常住人口,其中持城镇户籍的城镇人口只有4.1亿人,约有2.8亿人城镇人口是持农业户籍的,这部分人绝大多数是长期在城镇居住的农民工及其部分家属[5]。随着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将不断增多,他们在农村拥有承包地,但却无法亲自耕种。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则由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渐减弱。
2.土地流转困境制约家庭农场的规模。由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农民对待土地的态度不同,农民在土地经营上更多地选择兼业方式,家庭成员全部脱离农业生产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是理性的,他们在做出决策时会考虑土地流转是否实现了收益最大化,这种收益包括经济性的,也包括非经济性的。具体表现在:(1)拥有“恋土情结”的农民对待土地的态度向来非常谨慎,他们明白,当退出城市就业领域时,土地就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另外,城市非农就业不稳定性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加深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即使土地流转,也多通过口头契约形式短期转包、租赁土地,以方便他们需要时易于收回土地。(2)“农业+非农互补性收入组合”保障了家庭经济的稳定性,单纯依靠农业收入不足以应付家庭支出,脱离农业收入又会极大增加家庭生活成本。如果老人或妇女从事农业,农业收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和日常支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务工收入成为家庭新增净收入,这个收入可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也可以作为积蓄存下来以应对人生风险和人生大事[6],这样农民才有可能获得一份体面的生活。另外,土地也为农民构建了一种“伸缩自如”的安全机制,当非农就业机会不足时,他们会把劳动力转移到土地上;当非农就业机会充裕时,他们及时做出调整,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以获得更高的非农收益。(3)土地流转缺少中介组织,农民忌惮于巨大的交易成本和摩擦费用而任其撂荒,即使流转也多发生在“强关系”网络中,“强关系”包括本家、亲戚、朋友和比较熟悉的人,不仅流转的双方彼此具有互信的基础,也有利于互惠型人际关系网络的维护。对农民来说,不管是选择留守村里还是外出务工,亲戚、邻里等构成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如果土地流转问题不能解决,即使家庭农场能够流转到适度规模的土地,也会因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导致稳定性差,农场主对土地经营无法做出长远规划,就会制约家庭农场的正常发展。
(二)农村中产阶层是家庭农场的最适经营主体
1.家庭农场的经营主体应当是农民。如果单纯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角度来讲,城市人一般比农村人拥有更多的资本、先进生产技术和把握市场能力,但这是否决定了城市人就是家庭农场的最适经营者,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源于制度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溢出效应”,家庭农场不仅要从土地上获取更多的产出,还要发挥其社会效益,希望藉此改善农村经济条件,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从而缓解或治愈“乡村病”,如农村产业、青壮年劳动力、住房等流失和空心化以及衍生出来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另一方面,按照资本的逐利性质,缺少了行政限制的家庭农场最终会向雄厚资本并能够支付较高租金的城市人手中集中。然而,城市人可能不会真正地经营土地,而是再将土地分租给农民赚取差价,这不仅增加了农场经营者的生产成本,也形成了农民在土地经营机会上的不平等。
2.中产阶层成为家庭农场的中坚力量。前面已提到,农业劳动力呈现出女性化和老龄化趋向,经济利益驱动下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城市生活经历让他们开阔眼界、增加市场敏感性、结交异质性社会关系,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比农村其他群体更加丰厚,理应成为家庭农场的适宜人选。结果恰好相反,城市生活经历正在加速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农村。他们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和土地情结,部分人从大中城市转向小城市定居,接替原来居住在小城市居民向上流动后留下的空间位置,完成“回流式”市民化过程[7]。家庭农场经营者还要从现有农村群体中寻找,事实上农村中已经存在着一个农业中产阶层,他们耕种外出打工邻居转入的土地,加上自己的土地,经营适度规模土地维持一个相当体面的生活[8],他们是建设农村经济和实现村庄共同体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
3.资本缺乏成为中产阶层经营家庭农场的制约因素。中农阶层以自耕形式经营适度规模土地正是家庭农场的雏形,当其走向正规化时却面临着资本存量的“短板”。首先,土地租金、土地整理、机械购置、品种改良、农田基础设施等都需要大量的现金投入,农户原本物质资本积累有限,又因农业投资周期较长、资金周转较慢、风险性高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造成家庭农场的融资难;其次,高效农业成为家庭农场的首选,由低值农产品转向更多高值农产品面临农产品结构转型风险;第三,种植品种效益越高,市场风险越大,农户社会资本水平低使得家庭农场在同行业利润分配、市场风险承担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从而直接影响其经济效益[9]。
(三)市场竞争能力是家庭农场存续的关键
1.市场竞争能力决定了家庭农场的生命力。家庭农场商品化生产模式表明它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庭消费单位,而是一个为市场需求而生产的单位,并将被纳入更大的甚至宏观的农产品贸易体系。因此,家庭农场不仅要参与到市场中来,还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利润,求得生存。市场竞争是一种综合能力,涉及市场需求的把握、市场波动的预判、市场风险的应对等,家庭农场需要具备信息采集能力、市场决策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博弈市场的能力和盈利能力。农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家庭农场与市场之间也就具有了必然的联系。
2.家庭农场面临个体农户和农业公司的双重竞争压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因空间地域性产生的差别逐渐减弱,开始形成完全竞争型农产品市场结构,市场中个体农户、家庭农场和农业公司等成为平等的农产品供应者,具备各自的竞争优势。个体小农除满足自身及家庭人口的消费外,其他农产品剩余进入到依靠产地、销地批发市场衔接形成的传统产供销体系。小农生产的低效性已被诸多诘难,然而土地精耕细作中对自身劳动力成本的忽略却成为其市场竞争的最大优势,换句话说,大部分的个体小农并不是为市场而生产,只是在满足生活需要外出售消费剩余。现代农业公司不仅具备雄厚的资本支持、先进的生产技术、高效的管理经验,还具备对生产领域、加工领域、流通领域和销售领域的整合能力,通过建立具有组织合作与流通增值特征的现代供应链,参与到农业生产或深加工之后的所有环节,赚取流通环节、销售环节的巨大利润。因此,无论进入哪一级的农产品市场,家庭农场都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3.家庭农场原子化状态削弱了农产品市场议价能力。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或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这使得单个家庭处于原子化状态,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只要“小生产、大市场”的农业市场结构尚未发生改变,家庭农场在生产决策时不仅无法正确把握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还可能因农场之间农产品的重复性生产形成过度竞争或恶性竞争。结果,个体化的家庭农场成为农产品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它们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的波动,做出迟滞性的反应。在农民致富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上,孙立平认为市场机制的缺失让农民富不起来,具体来说,就是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上没有议价能力[10]。笔者认为,缺乏议价能力问题表征的背后实际上是个体农户或家庭农场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市场是不同利益主体利用自身力量和优势相互博弈的场域,力量的强弱决定了市场的话语权,很显然,如果家庭农场处于分散的状态,在与其他农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中就会显得无能为力。
三、提升家庭农场运行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一)创新政府引导与农户自主协商相结合的土地流转机制
土地流转应坚持更多地让利于民,使得农户和农场经营者有机会享受土地经营带来的增值收益,为此,作为土地管理者的政府应从政府主导的“强干预”向政府引导的“弱干预”转变。强干预下的政府容易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威和垄断资源侵害农民利益,违背了土地流转“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基本原则。政府引导与农户自主协商相结合的土地流转机制以尊重土地流转双方的主体平等为前提,搭建了透明化的土地交易平台。
具体来讲,政府引导是指由政府收集、登记土地流转意愿和信息制定土地流转指导价格,培育土地流转供求市场,在个体农户与家庭农场之间架起一座供需桥梁,便于家庭农场获得连片土地。当流转双方达成意向时,政府规范交易双方的土地流转,并对流转后土地保护进行法律监督。农户自主协商则是指农户对是否流转土地、流转形式、流转期限、流转数量、流转价格享有充分自主权,整个流转过程交易双方以平等协商的形式完成,政府不进行直接干涉。通过这种流转机制,政府引导可以有效地减少土地交易双方的信息搜寻费用、谈判决策费用、契约履行监督费用,而自主协商又可以将土地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增值收益真正留给农民。
政府引导与农户自主协商相结合土地流转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是提升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这就需要政府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并提高非农就业稳定性,同时要解决他们转出土地后的生计保障问题,完善农村生活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11],改变“农地养老”的农村社会保障现状。
(二)加强职业农民能力建设,提升农场组织化水平
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需要引入新农业要素[12],包括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机械更新、管理经验及其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这些新要素往往是传统农民所难以驾驭的。为此,改造传统农业的首要任务是改造传统农民,通过能力建设提升农民的“资本”增量,为家庭农场培养新型职业化农民。
针对家庭农场的特点,农场经营者的能力建设具有多种途径:(1)采取积极措施有计划地进行专题培训,帮助其正确认识家庭农场的基本内涵,提高农场经营者的专业素质和科技水平;(2)通过政府牵线搭桥,帮助农场经营者寻找外来智力支持,与从事农业研发的科研院所合作,就土壤测量与配方肥、新品种选择、病虫害防治、种养结合搭配等方面提供技术力量;(3)以区域为单位,提高家庭农场的组织化水平,通过鼓励和引导家庭农场之间的合作,成立家庭农场协会,运用组织的力量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发生。能力建设的内容应当具有全面性,既要有农场经营者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又要加强农场经营者与外界资源的交流互动;既要增强农业高新科技运用这样的“硬实力”,又要增强组织化力量这样的“软实力”。这样才能实现成本降低、品质提升、农业安全和增强信心的综合效益。
(三)完善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对农业信息、融资、市场信息及风险对应等方面存在着巨大需求,除依靠农场经营者自身努力外,还需要政府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来弥补家庭农场个体化带来的不足。
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1)政府应建立农业综合信息服务网络平台,使得农场经营者能够方便快捷地查询、了解农产品生产信息、市场行情、价格预期、科技推广等信息,便于经营者及时调整家庭农场的资源配置方向、规模;(2)政府应建立多样化的支农惠农融资渠道,落实土地开发整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壤改良等长期性投资的专项财政支持,进一步加大农产品价格补贴、良种补贴、农业机械补贴等实施力度,增强政府在农业金融上的信贷支持,落实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农户贷款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3)政府应加大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投入与完善市场管理体制,培育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市场,加强市场调控力度,保障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稳定,避免出现“谷贱伤农”“菜贱伤农”的现象;(4)政府要鼓励和引导家庭农场办理农业保险,增强抵御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四)创建稳定、有序、明晰的土地产权制度环境,保障家庭农场的平稳化运行
由于我国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政策,政府相对于农民拥有更大的土地处置权,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农户与农场经营者间土地流转的可能。因此,需要创建稳定、有序、明晰的土地产权制度环境,保障农户和农场经营者应当享有的土地权利。
土地产权制度建设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应该加快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明确土地使用权的隶属关系。土地确权不仅是农户与农场经营者间土地流转的基础,也是农户实现个人财产权利的重要依据。其次是保障农户的土地流转权,政府应认可土地流转权的物权性质,有责任保护农户享有的土地物权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和侵害。第三是保障农户的市场定价权,如果缺乏了土地流转的市场定价权,那么土地流转权就是一种“虚置”状态,政府可以采用土地收益还原法和市场比较评价法,制定土地流转指导价,作为农户与农场经营者协商谈判时的参考,避免出现严重脱离市场价值规律的不平等交易行为。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09-910.
[2]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
[3] 刘凤芹.中国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研究——小块农地经营的案例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3(10):60-65.
[4] 许恒周.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偏好[J].中州学刊,2011(4):75-78.
[5] 李培林.城市化与我国新成长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2(5):38-46.
[6] 贺雪峰,董磊明.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J].中国农村观察,2009(2):12-18.
[7] 潘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路径探究[J].人民论坛,2012(32):136-137.
[8] 陈柏峰.土地资本化的陷阱——枣庄试验批判[J].经略,2011(10):55-64.
[9] 郭云涛.家庭农场的资本、市场与经济效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56-61.
[10] 孙立平.市场机制的缺失让农民富不起来[J].文史博览,2012(6):1.
[11] 黄利霞.论人口老龄化视域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J].求索,2013(12):254-256.
[12]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5.
Modern Family Farm:Accurate Understanding,Implementing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SHI Guo-qing,YI Qing-shan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ettlement,Hohai University,Nanjing210098,China)
Family farm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micro management in China,which integrates land management by family and commercialized production.Moderate scale of land,farm manager and market participation ability are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a family farm.However,in practice there are cert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such as low willingness and stability of land circulation,low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farm managers,poor ability of market participation,etc.Only through innovating land circulation mechanism,enhancing managers'ability,perfecting social servic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posi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can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family farms be better promoted.
family farm;smallholder economy;land circulation;market participation
F302.2
A
1009-9107(2015)02-0135-05
2013-04-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7ASH010)
施国庆(1959-),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管理学与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