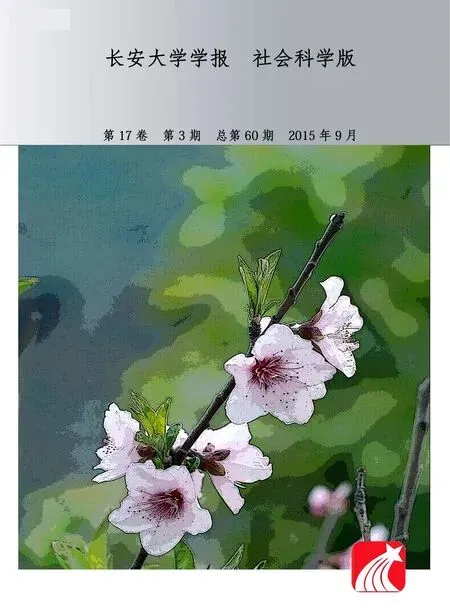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概述
喻忠杰
(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九江 730020)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概述
喻忠杰
(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九江 730020)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丝绸之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进一步廓清丝绸之路文学的发端、演进和成熟的全过程,拟从文献学、比较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经过对先秦至明清时期沿丝绸之路一带的中外各国及地区内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和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古代丝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依据它的这种特殊性,大致可将其分为散文、诗赋、说唱、戏剧、小说、神话传说及其他共七类。古代丝路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文学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丝绸之路;丝路文学;中原文学;民族文学;域外文学
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巴龙·费迪南·冯·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中把“自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的西域道路”称为die Seidenstrasse,英译名为the Silk Road,即“丝绸之路”。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mann)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绸之路》一书出版,该书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并将丝绸之路的区域概念进一步扩展至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丝路)研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涉及的范围已经拓展至自东亚经中亚及西亚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东西交通区域之间。事实上,丝绸之路自先秦时期起就在沟通中西交流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经输入印度,公元3世纪时,已经输入西方。在西汉张骞(前195~前114年)出使西域之前,中原地区就与中亚、西亚一带有过交往的痕迹[1]。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概念化与实体化相结合的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才正式开通。自此以后,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便从汉代古都长安出发,呈扇形状朝着四周毗邻国家方向不断延伸,形成覆盖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文学、艺术等的巨大文化学术体系[2],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与辐射,这一体系中还牵涉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问题。但长期以来,由于所属学科的发展、所处地域的差异和个人旨趣的偏好,在丝绸之路研究中,虽然出现了一批与文学作品相关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但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形成系统的(丝路文学)研究体系。而文学领域恰恰是构成丝绸之路学(丝路学)的重要部分,是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21世纪初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加之众多新学科的兴起和新方法的引入,丝绸之路研究的视野和规模被进一步扩大,于是在东西方世界形成了对丝绸之路的一种国际性关注,在这种强劲学术潮流的裹挟下,展开对丝绸之路文学的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无疑会提升丝路学整体研究的文化内涵和区域影响。
一、概念界定
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构成都应该有其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丝路学是一门集诸多学科为一体的研究丝绸之路的综合性学科。在这门综合性学科中,由于各自所研究的具体对象有所不同,于是便由这些研究对象牵引并生发出丝路学研究的不同分支学科。通过对这些研究对象的分析,如果能够从中抽象并归纳出一些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规律,并可将这些具有区别效果的本质规律作为该学科自身的特征时,这就意味着该学科的构成基础已经初步形成。审视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我们从中即可抽绎出它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本质特征。
首先,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主要涉及的是能够真实反映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外丝绸之路沿线社会风貌、历史文化、人物事件等诸多方面的文学性资料。它同敦煌学、西夏学一样,属于以地名学的典型代表,只不过它所涵括的区域更加广阔和复杂。从本质上讲,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贸易通道,按照其最本原的意义,它是指以中国的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中亚(西域)到南亚、西亚、欧洲、北非的陆路贸易通道。但是,近些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更为广义的丝绸之路,即凡经过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包括海上、陆路均一概称丝绸之路。现今流行的说法是:原来所说的经中亚陆路的丝绸之路称之为“绿洲路”或“沙漠路”;另有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族聚居地至中亚的“草原路”;经海上西行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云南入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等。在这些名称各异的丝路之中,仅有“沙漠路”和“草原路”可以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本文所讨论的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主要涉及的区域就是原本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即狭义的丝绸之路。但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在它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其本质既属于时间的,又是属于空间的,这就使得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会是平面化的、单向度的。
其次,丝绸之路又是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在这一文化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无不受到丝路沿线诸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体来说,古代丝绸之路文学因为特殊的地域位置而具备了异于其他文学品类的特征。从丝路走向来看,“沙漠丝路”一般可分为三段,即起自长安止于玉门关的东段,以新疆地区为主的中段和新疆以西的中亚至印度或欧洲的西段,与之相对应,这三段的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也显出各自的地域特征,东段的主体为中原文学,中段为民族文学,西段则为域外文学。这3个区段的文学形态共同构建了一个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体,少数民族文学和域外文学为侧翼的丝绸之路文学母体,它们共同孕育、催生并哺养了古代丝绸之路文学;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多内涵的“混血儿”,同时也是一种在交叉、互融基础上形成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学现象,它既有中原文学的典雅方正,又有民族文学的张扬瑰丽,还兼具域外文学的异国情调。当然,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它们三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相互的渗透与融合。与“沙漠丝路”相仿,“草原丝路”也表现出这样的地域特征,该条线路从中国内地长安或洛阳出发,经华北由戈壁沙漠、蒙古高原向西经西伯利亚森林、南俄草原到咸海、里海沿岸[3],最终至欧洲和北非地区。同样,可以按照三分法将其文学划分为中原文学、民族文学和域外文学。只是“草原丝路”的形成要早于“沙漠丝路”,据考古资料显示,在今俄罗斯阿尔泰州乌拉干区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有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内地的丝织品和绣有凤凰图案的茧绸[4],证明这里的游牧民族塞种人通过草原与中国内地即有丝绸的贸易关系。依据这种早期丝绸之路的贸易关系,结合出土文献,或许可以从外围推断丝绸之路文学起源与发生的大致情形。
最后,由于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所涉区域范围的特殊性,在这里曾经汇聚了为数众多的不同民族,为多元、丰富和复杂的丝绸之路文学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丝绸之路上除汉族之外,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戎、狄、羌、林胡、楼烦、匈奴、月氏、乌桓、鲜卑、高车、乞活、柔然、突厥、回鹘、党项、女真、鞑靼等。从先秦时期开始,他们渐次现身于丝绸之路,并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中的部分在时局的变幻、部族的迁徙或战争的硝烟中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还有部分在经历时代风雨的持续冲刷后逐渐裂变、演化或融合为新的民族,最终成为至今依然活跃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成员,如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满族等。这些少数民族以其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方式给自己的民族文学赋予了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在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中,富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习俗风情是展示其民族性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道德观念、节庆仪式等殊风异俗,是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大多在其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同时,由于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丝绸之路上不同的民族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来表现本民族的历史生活、刻画民族性格、塑造审美形象,因此丝绸之路文学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自然就体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学的多样性、变异性和复杂性[5]。
总之,所谓“古代丝绸之路文学”就是指从先秦到明清时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域所发生、形成、发展、成熟的,反映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宗教以及世俗民风等诸多方面的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以不同的体裁和形式雅俗并存,有的源自于上层社会,有的出自普通百姓;有的由汉族作者著写,有的由少数民族或域外作者创作;有的出于世俗民间,有的来自庙堂官府。其中既有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又有原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有特殊的说唱民歌、英雄史诗。对丝绸之路文学的概念进行这样大致的界定,并不是在任意扩大丝绸之路文学的内容与范围,更不是在有意消解丝绸之路文学与其他文学之间的差异,而是为了在认识丝绸之路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时,既不失之于偏狭,又不偏向于宽泛。
二、历史背景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出现都必然会有其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丝绸之路文学自然概莫能外。中国丝绸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前后就已输向亚洲其他国家并远达欧洲,这说明至迟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就已存在,但因为缺乏翔实的文献记载,我们对于这一时段丝绸之路文学的了解并不太多。尽管学术界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始于西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但文学的发生与起源并不会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理交通路线的肇始而开端。因此,对于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溯源至少应该从公元前五六世纪开始。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对中亚东部地区的地理和部落状况的记述,如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山海经》、《逸周书》、《国语》、《尚书》、《吕氏春秋》等著作。其中在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穆天子传》一书中载述了公元前10世纪时周穆王的一次西域之旅,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尚待考证,然而书中所出现的地理记载却与中亚地区相关,并与实际的地理状况基本相符。中国内地的丝织品正是从公元前6世纪左右开始沿着《穆天子传》所描述的道路运往中亚地区的,首先是到达阿尔泰山地区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之后由此向西继续传播,通过斯基泰商人运往欧洲[6]。自此以后,一条由中国内地出发,经由漠北蒙古向西经中亚草原至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的中西交流重要通道——草原丝路便逐步形成了。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蒙古高原到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的重要生活区域,在这里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长期彼此交往、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共同生活,匈奴、乌孙、月氏、鲜卑、柔然等民族均充当了草原丝路的中介者,公元前三四世纪远销印度、希腊、罗马和埃及的中国丝绸就是经由这些草原丝路上的民族中转后才输送到那些地区的。到公元一二世纪,随着丝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加之张骞凿空西域,沙漠丝路正式开通,汉朝和西域诸国的使者、商人在沙漠丝路上往来不绝,中国内地与中亚、南亚、欧洲的商贸得以迅速发展。这种商业交流,既顺应当时各国经济的发展需求,也符合汉朝统治者与西方世界加强联系的愿望,所以交流双方一方面对这种商业交往进行鼓励与支持,另一方面则着力经营西域地区,拓展和维护这条贯通东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7],于是沙漠丝路开始进入兴盛时期。与此同时,草原丝路并未因西域商路的畅通而消歇,在汉朝设立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之后,汉王朝还是输给匈奴大量的丝绢,通过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丝绸贸易依然以其固有的渠道沟通着东西方世界。
东汉灭亡之后,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其间经历了西晋数十年短暂的统一,虽然丝绸之路因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而不时受到影响,但从总体来看,由于自两汉以来东西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仍处于稳定和兴盛的阶段。内地割据政权为了扩大丝路贸易,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商旅往返更加活跃,商业活动愈显频繁;内地的养蚕、织丝等技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域;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西域的文化、艺术和宗教等进一步向内地传播。而北方草原在这一时期是由鲜卑、柔然和高车等民族所统有,战乱频发,商贸交通难于畅行,并存有极大风险。随着隋唐的统一,以及唐代丝绸业的新发展,沙漠丝路和草原丝路较前期而言有了更大的发展,输向西方的丝绸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前代。唐代国力强盛,政治安定,经由两条丝路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丝路涵括的内容更加丰富,丝绸之路到达全盛时期。唐朝统治者向西开拓,相继清除了西域道路上的通行障碍,大兴屯田、设置驿站、派军戍边,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行政管理,这一系列措施极大提升了沙漠丝路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功能。在唐代的蒙古高原和西域草原上活动的民族主要是突厥和回纥,自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前后二百年来,突厥活动在漠北和中亚草原地带,控制着中世纪东西交通的孔道。其一开始就把丝绸贸易作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并最终促成了一条盛极一时的草原丝路。继之而起的回纥则利用政治上与唐朝的特殊关系,获得了大量的丝绢,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操纵着草原丝路丝绸贸易达百年之久,同样开辟了草原丝路的一个黄金时代[8]。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再次进入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五代十国半个世纪的割据战争,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中西交通长期被阻。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以后,虽然统一了中原地区,但丝绸之路被分割于政治上互相对立的几个政权管辖境内。在这段时期内,丝绸之路尽管还未断绝,也依然存在着、发展着,但与昔日的繁荣已经无可比拟。与此同时,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中西海上交通得以迅速发展,原来陆上丝路的功能慢慢降低,加之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丝绸之路开始走向衰落[9]。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3世纪蒙古兴起之后,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东西交通再度畅通,沙漠丝路出现短期复兴。明代之后,沙漠丝路虽然并未中断,但作为中西交通的丝路已经远不如海路重要,这种衰落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与此相反,草原丝路则在10世纪以后的辽、金、元、明、清各代仍然畅通,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为中介主体继续着从中国内地到西方世界的商业往来,而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技也相继传入中国内地。
三、总体分类
任何事物的分类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丝路文学的分类亦然。丝路文学与敦煌文学一样属于典型的以地名学,因为在地域上存在部分重合关系,所以二者有着较为相似的历史地理背景。由于敦煌文学在近百年的研究过程中,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不断探索,已经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分类方法,因此这种成熟的地域性文学分类方法就为古代丝绸之路文学如何具体分类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原则和思路。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分类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全面观照,各段兼顾。丝路文学起于公元前五六世纪,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时间跨度极大。只有将其置于全景式的历史背景之中全面梳理,并对不同时段的丝路文学进行综合考虑,才可能在搜集与整理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作品时尽量避免有所遗漏,避免把本应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弃置于对象之外。第二,界定明确,层次清楚。丝绸之路地跨亚欧,所经区域错综复杂,不同路段既有融合又有区别,这种地理区域上的交叉跨越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和外在形式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在界定丝路文学作品的具体分类时,使之在类别上各有专属就显得尤为重要:每立一类,都要明确该类的基本特点,以凸显出异于他类的本质特征;同时要明确类与目的差异,丝路文学可以分为若干类,每一类又可以分为若干目,类与目之间层次要清晰,归属要恰当。第三,统一标准,形成系统。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一个庞杂的复合体,对其分类只能沿用一个标准,这是保证分类严密、科学的必备条件。通常情况下,文学作品分类所选取的标准一般是以作品的形式特点为依据,基本形式特点相同的即归为一类。常见的文学作品分类主要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4大类。敦煌文学作品的分类就是以此为主要标准,并结合敦煌文学作品的自身特点而最终形成的。以形式特点为主要标准,同样可以对丝路文学作品进行分类,当作品有了大的归属范畴之后,一个清晰、完整的类别系统就会在细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在这个综合系统中,既要有合理的纲目结构,又要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力求做到有类有目、层次分明、归属清晰、结构合理、统摄全局、系统严密[10]。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作品即可以此为依据进行分类。
在明确了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分类原则之后,便可参照以往已经成熟的文学作品分类方法对丝路文学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具体来说,丝路文学可以被分为7大类:文类、诗赋类、说唱类、戏剧类、小说类、神话传说类和其他。
(一)文类
文类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散文类作品,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学化色彩,在形式特点上显得较为灵活,主要以散文体、韵文体或是韵散相间的体式进行叙事、说理、表情、达意。这一类作品不仅包括用各种文体撰写的单篇文章,而且包括用同一种风格创作的整部文献,如在先秦时期的文类作品中就有不少关于中亚地名的记载。在《穆天子传》、《禹贡》、《山海经》、《逸周书》与《吕氏春秋》等分别提到了赤乌、曹奴、昆仑、渠搜、西戎、大夏、竖沙、月氏、莎车、氐羌等西域国名,从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中亚、西亚地区的地理、历史的认知情形;《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述了许多西域小国,这些载述丝路沿线地区的早期文献因此成为丝绸之路文学作品的先声。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1 000多个卷号的唐、五代、宋初的文学作品则成为丝绸之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类作品仅文体就有:论、录、奏议、状牒、书启、碑铭、诔祭、箴、传记、游记以及功德记等十多种。
(二)诗赋类
诗赋类包括了诗歌和辞赋两个类别,二者产生的时间都比较早,前者讲求节奏韵律,后者则介于诗、文之间,因为诗赋二者的亲缘性,在此故将其合二为一,此类作品在古代丝路文学中所占比例较大。在汉代的乐府和辞赋中均有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描述和反映,乐府诗歌《悲愤诗》,是东汉蔡琰在汉末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是汉地被掠人民的血泪写照和苦难实录;而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张衡的《两京赋》、班固的《两都赋》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由丝路传入中原地区的物品,这些原始记录都是古代丝路研究的重要资料。有唐一代,中国诗歌发展到高度成熟,这一时期边塞诗派的出现成为丝路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诗对边塞风貌、民族风俗及文化交流的描写,在对丝路进行研究时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敦煌所见王梵志白话诗则为唐诗作了重要补充。敦煌俗赋的问世则让后世目睹了与文人辞赋形制、内容迥异的民间辞赋。
另外,北朝时期的民歌也是一种类似于汉乐府的诗歌形式,只是由于其受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较深,因此与中原地区的诗歌有些区别,其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性强,多可配乐歌唱。敦煌所见唐、五代时期歌辞类作品,尽管与诗赋类中的诗歌有一定的区别,但从根本上讲它还是属于配乐歌唱的诗歌,这类作品亦可被归入诗赋类范畴之中。这类作品无论是其作者还是题材,主要来源均在民间,尽管也有文人的拟作,但毕竟只是少数,且内容与形式都完全是民间化的风格,其特点是托于曲调,倚声定辞,具备体段、平仄和音韵,能被之管弦,放声而唱[11]。敦煌文学中,此类作品数量很大,有1 300多首,在丝路文学中这类作品显然是不能缺席的,它们的存在不仅厘清了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来龙去脉,而且折射出丝路文学在中外交流过程中的部分细节。
(三)说唱类
说唱伎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瞽瞍乐师的赋诵表演,而说唱类作品大都是在中国传统的讲故事、唱歌谣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它最早是民间艺人通过通俗的语言、变化的声腔,在集市庙会等场合进行表演时所使用的底本,其形式特点是语言通俗,适于说唱。应当归入此类丝路文学的文体有变文、因缘、话本、词文和部分俗赋、民歌等。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中说唱类作品最典型的有两种,一是敦煌所见说唱文学,其在敦煌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具有很高的价值,二是丝路少数民族的部分民间叙事长诗和民歌,它们在结构上同样具有相对固定的程式化套语,二者共同体现出明显的说唱文学特色。具体来说,前者又分3种情况:一是重在讲说的作品,纯用散文或以散文为主而又间或插入少量的诗或偈语,如《庐山远公话》;二是重在吟唱的作品,纯用韵文或以韵文为主而又间或插入散文,如《季布骂阵词文》;三是讲唱结合,相互交替的作品,这种作品既讲又唱,韵散相间,《维摩诘讲经文》、《张议潮变文》即是[10]。后者中的叙事长诗依照主题思想亦可分为3类:历史英雄类,如记叙哈萨克著名英雄阿布责汗的叙事长诗《萨巴拉克》;爱情婚姻类,如极富传奇色彩的维吾尔族民间叙事诗《艾里甫与赛乃姆》;宗教传奇类,如流传于哈萨克与维吾尔民间的宗教叙事诗《萨勒—萨勒》,反映锡伯族先人创业的传奇叙事诗《亚奇纳》等。这些民间叙事长诗是少数民族在以往简短的韵文体制(如民歌)基础上逐渐加工、创作后,所形成的大容量、长篇幅的口头韵文[5]。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这类长诗主要以口传心授为特点,依靠民间说唱艺人的口头传播得以保存。随着社会的变革,手抄本文字形式的传播方式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传承路径,另一方面则直接导致了以阅读抄本来代替说唱的接受形式,从而使以口头形式创作演出的民间叙事诗的传统受到较大的冲击。
(四)戏剧类
丝路文学中的戏剧类作品包括了尚处于发生期的准戏剧和形成期的早期戏剧以及成熟期的戏剧,其中对于在丝绸之路上出现的具有演出底本的、与戏剧相关的演艺形式,也应该被纳入古代丝路戏剧文学的研究范围。
戏剧类文学作品主要来自于埃及、巴比伦、希伯来、中亚、西亚、东南亚诸国,以及西域戏剧所构成的丝路戏剧文化体系。在这一宏大的戏剧体系中,既有埃及法老剧、犹太仪式剧,又有希伯来戏剧、古巴比伦剧;既有印度梵剧、佛教戏剧,又有西域百戏、傀儡戏,以及特殊的敦煌戏剧和各地方戏曲。例如,在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中就已记载了大量原始的乐舞和戏剧形式。在南亚地区贵霜王朝统治时期(45~225),迦腻色伽王曾邀请印度佛学大师马鸣创作了梵剧《舍利弗传》。唐代戏剧《西凉伎》、《苏莫遮》、《凤归云》等剧目都是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戏剧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从敦煌所见《茶酒论》、《下女夫词》和《释迦因缘剧本》等几个戏剧写本来看,唐代戏剧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与自身相匹配的早期戏剧文学。20世纪初,在新疆地区发掘到的吐火罗文与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是公元八九世纪的一部长达27幕的原始剧本。大约与此同时,由俄国探险队在河西走廊黑水城盗掘出源于宋元南戏“荆、刘、拜、杀”之一的《刘知远诸宫调》。公元10世纪,波斯文豪菲尔多西(940~1020)创作出以古代波斯历代王朝兴衰为背景的英雄史诗《王书》,在此书基础上所产生的《霍斯罗与西琳》与《帕尔哈特与西琳》等剧在中国与亚洲诸国穆斯林地区成为长演不衰的剧目[12]。这些蕴含于丝路文化中的戏剧文学,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丝路沿线各民族多彩的社会生活、丰富的情感经历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成为丝路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小说类
小说类具体指的是见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志人、志怪、传奇、话本等小说。其形式特点是以散文为主,用通俗的语言叙述杂事、记录轶闻、掇辑琐语。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中小说类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博物志》、《拾遗记》记载了大量涉及与古代丝路有关的山川地理、交通物产、民族文化、风土人情等内容,《搜神记》、《异苑》、《幽明录》等小说集记录了一些关于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和事;唐代志怪小说集《酉阳杂俎》则有不少关于丝绸之路中西交流的内容。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唐代传奇,同样记述了部分涉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人和事,如沈亚之(781~832)《秦梦记》对秦国地理、文化的描写,白行简(约776~826)《三梦记》对唐代曲江、慈恩寺、华岳祠的载述。在敦煌文学中,从体制和内容来看,小说类作品有佛教感应记,如《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非感应故事小说,如《唐太宗入冥记》;笑话,如《启颜录》;志怪小说,如《搜神记》等。另外,丝路少数民族地区作家创作的大量小说作品也是这一品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维吾尔族著名突厥语小说作家拉勃胡兹的《先知传》、阿合买提·鄂加木·尼牙孜·鄂里创作的《集翠园》等都当属此列。
(六)神话传说类
神话传说类是指包括丝绸之路各民族的神话、民间传说以及英雄史诗在内的各类文学作品。其中丝路神话是丝绸之路各民族的先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等原始理解的最早记录。民间传说最早的产生,大都源自神话,甚至有的直接是从神话分离而来,但神话是一种借助想象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方式,其特征是以神祇为中心的原始性,而传说所叙述的内容与叙述者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不再是神话般超现实的事物,其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依附于现实中某个具体人物或事件,综合夸张、渲染、虚构等多种艺术手法,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属性。
神话与传说都是体现丝路文学奇幻浪漫特征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中神话类如哈萨克族创世神话《迦萨甘创世》、塔吉克族神话典籍《阿维斯陀》、古代维吾尔族宗教神话集《拉布胡兹故事集》、达斡尔族的自然神话《嘎西讷洞神话》等。传说类如塔吉克族民间传说《慕士塔格的传说》、维吾尔族人物传说《季帕尔汗》、锡伯族历史传说《开凿察布查尔大渠的传说》等。值得注意的是,丝路民族的英雄史诗中有部分内容同时也是构成其民族神话的核心主体,这种情况在丝绸之路少数民族史诗中较为常见,如哈萨克族神话中有不少神祇出自史诗《英雄阔布兰德》、《英雄阿尔帕米斯》、《英雄别根拜》以及叙事长诗《贾尼别克》中;在柯尔克孜族神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英雄史诗《玛纳斯》的影响;乌孜别克族的神话主要夹杂在英雄史诗《妥玛丽丝》、《希拉克》和《阿依苏鲁》之中[5]。从这一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民族的英雄史诗,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哈萨克族的《阿勒帕梅斯》、蒙古卫拉特部的《江格尔》等作品,亦可被归入神话传说这一类。民族神话与传说是早期人类留存下来的关于远古的记忆,它是各个民族情感的载体。这一类文学作品基本保持了丝路各民族原始时期的思维与文化样式,是后世追溯和研究人类早期的历史渊源、宗教习俗、艺术审美、心理情趣等轨迹的必要材料。通过神话与传说,我们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民族和人类的历史[13]。
(七)其他类
其他类的设定实际是对丝路文学中一些无法界定其性质和归属的作品所做出的一种开放性选择。大多数事物的构成通常都不是单一的,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文学作品更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构成。采取一种统一的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总体分类,并不意味着所有作品的类别归属会就此厘定。事实上,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依然会有部分作品具有多样而复杂的属性,对于它们的性质归属难以用既定的统一标准来加以衡量和审定,因此出于全面、客观的考虑,有必要将一些作品归入其他一类。
当然,对于文学作品的分类不可能只简单地透过一种视角、依凭一种方法就将其绝对地定格为一种模式,特别是对于诸如丝绸之路文学这种极具包容性和复杂性的文学类型,唯有采取审慎的态度、综合的视角,才能全面、系统、科学地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比如从地理区域角度亦可将“沙漠丝绸之路”文学分为长安文学、陇右文学、河西文学和西域文学等,这种分类同样可以用于广义的丝绸之路文学的划分和依据之一。
四、研究意义
肇始于公元前五六世纪,历经汉、唐、延及元、明,直至清代的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一种极具地域性和文化性的文学现象,是自先秦至晚清不同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上生发和形成的各类精神文化的物化形态。这一具有独特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的文学现象,既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世界文学一个核心的构成要件。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文学,并对其进行理性与科学地甄别、认定、研究、借鉴,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继承世界优秀文化遗产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从文献学角度对古代丝绸之路文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可以丰富和细化丝路文化和文学艺术研究的具体内容。古代丝路文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和地理因素给不同时期的丝路文学赋予了不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总体来看,丝路文学的具体内容既有对乡土的讴歌,又有对先祖的怀念;既有对世俗民间的描绘,又有对寺观朝堂的反映;既有对外族入侵反抗的实录,又有对民族友好相处的记述;既有对宗教思想的宣扬,又有对部族英雄的歌唱;既有对现实的关切,又有对未来的向往。这些丰富的文学内容分别以诗、文、赋、词、曲、话本、小说、民歌、变文、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等作为其表现形式,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丝路文学复合体。丝路文学这种庞杂的总体构成,导致其自身显现出较为复杂的艺术特征,从而使得在系统化整理和研究这一复合体时,就需要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较强的针对性。
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以其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后世清晰地勾勒出一段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人类精神脉搏跃动的图谱。在这里生发的边疆文学、宗教文学与民族文学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原文学、官府文学、传统文学保持着长期的沟通和联系。由于丝路沿线地区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其文学思想和内容因此而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同;同样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其文学作品中也会有具体变化的反映,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文体就会大量涌现,这些新变化无疑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起到诸多扩充作用。
第二,从比较学视角对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众多品类的相互交流进行双向观照,可以为跨地域文学互动研究提供一种形象化范例和可行性方略。由于自身特殊的地域性和延展性,丝绸之路为丰富多样的不同文化提供了能够共同繁盛的适宜土壤,滋生出敦煌文化、吐鲁番文化、龟兹文化、楼兰文化、和田文化、粟特文化、犍陀罗艺术文化、安息文化以及大夏文化等,这些既具独特性,又有互通性的文化形式在丝路沿线的不同地域孕育、生长、成熟,并不断衍生出众多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校式和内容繁杂的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持久而深远,所涉范围亦十分广阔,作品题材、表达方式、表现手法、文学形象、修辞用语等各个方面多有包括。
不同品类的相互交流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在丝路区域范围内,中原地区、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异域文学在它们彼此所能接触到的距离内进行交流、发生共融,以各自的优势促成文学的新变,开创出新的文学潮流:一方面,在两个相近或相邻地区之间,可能因为文化的相似、环境的相类,易于形成情感的共鸣和思想的共识,进而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形成地缘性文学群,最终推动该文学品类的快速发展和高度繁荣;另一方面不同地域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文学品类在交叉与融通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排异性碰撞和冲突,于是文学品类在思想和形态的生成上各辟蹊径,最终催生了地域文学的多样化。这种正向的推动和反向的阻挡所产生的合力,使得古代丝路文学在相互交流中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优。也正是古代丝路文学中不同地域文学品类之间的双向互动,使我们从丝路文学这一精神生产活动中探寻出在丝路沿线曾经存在的人类文化的历史轨迹,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区的跨区域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较强示范性和操作性的方法。
第三,从传播学层面对古代丝绸之路文学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动态研究,可以呈现古代丝路文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发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古代丝路文学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观念化存在,它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最终实现,同样需要经过创作—传播—接受这一系列过程的促动。传播环节在文学作品的正式生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作品没有传播环节,就意味着失去接受群体,最初的文学创作就谈不上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实现。
在古代丝路文学历时研究过程中,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某种文学类型的溯源以及对其历时性变化的追述,一方面可以客观呈现该类型的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具体方式的应用、接受群体的形成、后期模式的选定及接受效果的反应,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其呈现的这些传播状况大致描绘出该类型的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具体的生成、发展、繁荣与衰亡的自然状态,进而在时间坐标上找到对应的节点。而在共时研究过程中,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丝路文学进行横向的跨文化综合比较研究,则可以清晰显现出丝路文学中的众多品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同整个丝绸之路及其相关区域的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多丝路文学品类在流变过程中都表现出与自己相邻或相关区域文学品类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相同或相似性。从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和流传线索中,我们可以获悉在丝绸之路沿线生活的不同民族在历史文化、社会民俗、宗教艺术方面的诸多信息。
第四,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沟通东西方经济贸易的关键渠道,而且是一个传播中外文学艺术等文化成果的重要区域。正是丝绸之路在自然地理方面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才造就其自身在文化地理上广泛、高效的传播力,也造就了中外文化在这里反复碰撞、交融后持续繁荣的局面。
五、结语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所涵括内容的繁多、涉及题材的广阔及开拓意境的深刻,使得中国文学的内涵更加丰富深沉,使得世界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使得丝绸之路学的维度愈发逼真。丝绸之路文学是从丝绸之路学中抽绎出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古代丝路文学文献足以构成一个具有特定范围和具体内涵的研究领域。只有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学研究的相关实践和成熟理论对这一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并探寻出它的形式结构和内容层次,才能逐渐形成一个科学、完整、严密的丝绸之路文学系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更高层面上全面、准确地把握丝绸之路文学的性质、结构和功能。
[1] 卢苇.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J].史学月刊,1981(4):70-76.
[2] 黎羌.丝绸之路研究中“文学艺术”不该缺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6-14(A04).
[3] 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4] 鲁金科,潘孟陶.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J].考古学报,1957(2):37-48.
[5] 雷茂奎,李竟成.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6] 马雍,王炳华.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C]//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1-8.
[7] 齐涛.丝绸之路探源[M].济南:齐鲁书社,1992.
[8] 苏北海.汉、唐时期我国北方的草原丝路[C]//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22-33.
[9] 沈济时,丝绸之路[M].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 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11] 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12] 李强.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13] 王钟陵.神话思维的历史上限、坐标及走向[J].中国社会科学,1991(1):195-211.
Summary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literature
YU Zhong-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mication,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730020, Jiangxi, China)
The ancient Silk Road literature is a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sci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process of the Silk Road literature clear, from its origin, evolution to its mature, the research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it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philology, comparative theory and propagation science. After investing the literature works and phenomena originated in the countries and areas around the belt of the Silk Road from the Pre-Qin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present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literature has its own special historic and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and in terms of its particularity, it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prose, poetry, rap, drama, novel, myth and legend, and others. The sorting and study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literature ar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e world.
Silk Road; Silk Road literature;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ethnic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2014-08-1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70007)
喻忠杰(1979-),男,甘肃金昌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I206.2
A
1671-6248(2015)03-013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