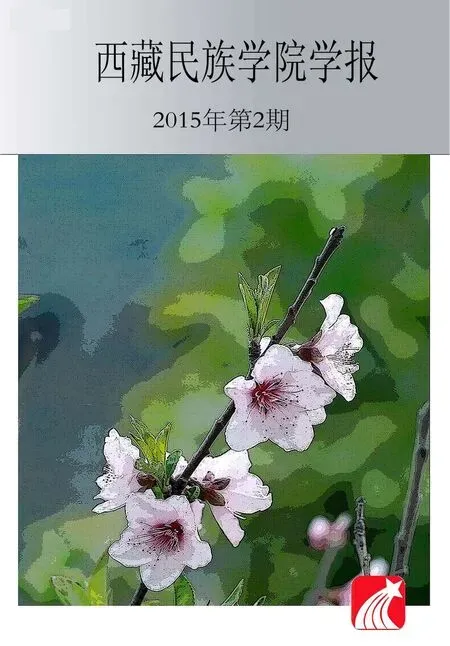《麦克马洪线》摘译(一)
梁俊艳 译,张 云 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麦克马洪线》摘译(一)
梁俊艳 译,张 云 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本文通过大量英文原始档案资料,揭示了英国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的经过,无论是会议地点、中方代表的选定,还是西藏代表是否有权参加会议,都由英国单方决定,凸显了英帝国主义的强权主义和霸权政治;另一方面也显露出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孱弱无力。文中所述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并不代表译者及本刊的观点。
中国;西姆拉;会议
二十二、中国同意参加在西姆拉举行的会议[1]
不出意料,中国政府主动地、毫不掩饰地回复了朱尔典[2]在1912年8月17日提交的备忘录。在伦敦英国本土政府(the Home Government)有足够的时间回味萨佐诺夫(Sazonov,俄国外交大臣——译者注)的言论,并针对英国对藏政策如何能够与俄国在蒙古和新疆政策相互关联而冥思苦想之前,朱尔典奉命不得就此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无论如何,袁世凯政府显然不可能不做任何带有威胁性的反驳和争辩,就轻易发表一个可以接受的关于西藏的声明。袁世凯的一些同僚,中国青年党成员、中国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博士(Dr.Yen)[3],言辞激烈地反对中国放弃清朝于1910年在西藏所获地位的一切行为。他们把西藏视作一个可以输送内地过剩人口的地方;他们在日记中怀着对西藏充满同情的语气,宣称如果英国干涉中国“在他们自己的边疆领地的殖民计划,他们[中国人]可能被迫把注意力转向澳大利亚,将其变成一个输出成百万过剩中国人的目的地。”[4]
12月3日,印度事务部(the IndiaOffice)最终决定,是时候让中国人回应英国备忘录了。[5]等待俄国人的合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此外,中国人则在整个夏末和秋季活跃于东部西藏,继续执行其在西康建省的计划;他们还再次建议将察隅纳入中国的直接管辖范围,现在,冬天的降临阻止了这一切。1913年春,在采取任何新的行动之前,应当让中国人同意在其领土边界地区划定清晰的界线,这样,中国军队和官员就再也不会直接抵达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英国边界了。[6]克鲁勋爵(Lord Crewe,1911年5月25日至1915年5月25日担任印度事务大臣——译者注)认为,现在应当迫使中国人接受沿萨
尔翁江—伊洛瓦底江(Salween-Irrawaddy)分水岭划定中缅边界(Sino-Burmese border)的界线,让他们放弃在片马(Pienma)和康提垄(Hkamtilong)的所有主权。如果英国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一事实对中国人仍无法构成足够大的威胁,那么
朱尔典爵士应当奉命通知他们,如果他们还不打算根据上述方针参与谈判,并在三个月内完成整个谈判,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视1906年中英协定不再有效,并自由地与西藏直接进行谈判。此外,如果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英国打算向西藏人提供积极的援助,以抵抗中国人的推进,他们还会帮助西藏人获得并维持独立。
当然,最后一句话的重点是强调必须划定边界。但如果中国人希望避免英国军事援助达赖喇嘛,他们究竟应当在何时停止?印度事务部最后宣称,中国人应当在收到提醒日期后的14天内回应朱尔典,实际上,这是针对8·17备忘录给中国人下达的最后通牒。
格雷(Grey,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认为印度事务部的建议颇有价值,他将该意见转交给朱尔典[7]。当然,英国外交部(the Foreign Office)意识到英藏直接对话和英国对达赖喇嘛提供军事援助会对1907年英俄协定造成威胁;显然,如果俄国在阿富汗得不到自己所希望的补偿,在当前情况下,他们不会对西藏问题作出任何让步;但尼科尔森(Sir Arthur Nicolson,英国驻俄国大使,参与1907年英俄协定谈判的英方代表——译者注)认为,在面临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俄国人或许会理智一些。无论如何,正如印度事务部指出的,不能忽略中国人将英国直接和达赖喇嘛打交道一事与最近的俄蒙关系进行类比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做,可能势必导致国际社会承认西藏独立,而这正是中国政策长期以来所反对的目标,无论是在满清王朝还是在中华民国都是如此。然而,除非能从北京公使馆等到中方回馈的观点,且除非英国内阁已经讨论过整个西藏问题,否则,格雷并不打算批准此类的最后通牒。
朱尔典赞同是时候给中国外交部施加更大压力了[8];但他并不赞同印度事务部的所有观点。第一,他认为在现阶段,将中缅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捆绑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完全赞同威胁中国的做法。中华民国若受到一定程度的胁迫或许会安然无恙,但过多的压力只会激发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满情绪。正如朱尔典所指出的,英国人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经受不起再冒这类风险,就像处理英俄关系那样。他打算做的,就是先暂缓执行伦敦的指令,向中国外交部指出,在英国人改变主意、提出更不利于中华民国的条件之前,中方应根据8月17日英国备忘录的精神,明智地与英方达成协议。
12月14日,很可能是由于受到英国公使馆的某种刺激,中国外交部提出与朱尔典面谈,讨论8· 17备忘录。被朱尔典认为“故意刁难”的中国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博士,指出8·17备忘录非常站不住脚。中国人有权控制整个西藏,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历史上,英国人承认中国的这种权利。他们怎么能为现在的立场辩护呢?朱尔典根据一些观察报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针对自1888年以来中国在拉萨权力的真实本质指出,只有当中国人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影响自己臣民之后,达夫林勋爵才将西藏人从锡金赶出去;颜惠庆博士“似乎相当厌恶”此番言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虽然双方意愿良好,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朱尔典在总结这次会面的时候提出:
根据备忘录[8月17日]的条款起草的时间,当时中国政府在西藏仍有一些权威,远比现在中国人所预期的条件有利得多。我强烈建议他们在英国人还愿意的时候接受备忘录。[9]
12月23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回复了朱尔典的8月17日备忘录,并总结了12月14日的会谈。[10]正如1906年中英协定条款规定的那样,中国在西藏拥有完整的权力。中国政府不打算把西藏变成中国的一个或多个省份,中国人提出的“国家团结,实现五族共和”与最终将西藏变成一个行省相去甚远。中国人希望根据条约权利治理西藏,“从来没有打算在西藏无限制驻军”。中国外交部认为没有必要重新订立一个关于西藏的条约:1906年和1908年的中英协定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足以满足英国人的所有合法利益,主要在喜马拉雅北部的商贸利益。随后,中国人抗议英国对他们关闭印藏边界的行为,宣称:
根据国际惯例,除非出现战争状态,否则不应借助关闭交通渠道这样的手段。中国和大不列颠历来都是友邦,当前这种举动令中国政府极其不满,中国政府殷切地希望早日恢复正常状态。
最后,中国外交部评价了中英两国的商贸关系传统——很可能是暗中威胁中国打算限制英国在华贸易——并宣称,英国承认中华民国不仅是双方友谊的象征,而且还会带来双方的共同繁荣。若公正无私地看待,所有这些说法都合情合理,朱尔典较客观地研究了这些观点。然而,这些观点无论如何没有提供解决西藏问题的简易之道。
1913年1月30日,无疑受到蒙古发生事件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总长陆徵祥(Lu Cheng-hsiang)要求朱尔典进一步与他讨论8·17备忘录。[11]现在,他打算认真考虑备忘录了,但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使用宗主权(suzerainty)这个概念来形容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在以前的条约中,宗主权一词从未被使用过。朱尔典拒绝对此问题作出评论,但认为如果不试图划定西藏的边界线,无论怎样谈论西藏,都是毫无意义的。陆徵祥回答道,边界问题极端复杂,现在考虑边界问题只会导致拖延。陆徵祥的观点似乎是,同意将中国在中部西藏的权力限定在一位驻藏大臣及其护卫队,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不能限定中国对边界地区的政策及在西康建省等事项。然而,不划定边界线,就无法分辨中国人所理解的中部西藏(Central Tibet)究竟是什么范围。朱尔典怀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他是对的,中国人理解的中部西藏,距离拉萨以东并没有多远,必然将波密和察隅等与印度政府利益攸关的地方排除在外。可以说,中国人对于驻藏大臣及其卫队的立场,与英国人对此的观点相差并不是很远。我们也已看到,当中国军队残余势力撤离西藏之后,钟颖和陆兴祺是怎样努力地劝说西藏人像1910年之前一样保留这个职位。然而,中国将他们的驻藏大臣视作他们将来能够返回拉萨的基石,印度政府却认为驻藏大臣不过是个历史古董,提醒人们中国人曾短暂地统治过西藏,但历史永远不会再现。象征着两种不同态度之间分歧的问题,正是拉萨和中国控制领土之间的边界。显然,中国边界越往东部推进,中国人重返拉萨时就越困难。
在1913年的前几个月,始终关注蒙古局势的英国人打算继续修订他们的西藏政策。现在存在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凡驻藏大臣返回拉萨,都应带一支不超过300人的卫队,印度政府估计,这个数字是在荣赫鹏使团出发前夕的1904年确定的。中国人在西藏仅剩下这种象征性的影响力。英属印度政府划定的西藏范围,不仅包括拉萨及其西部,而且包括察隅、马尔康(Markham,又作玛尔康,今西藏芒康一带—译者注)、察雅、昌都、嘉德(Gyade,部族合称,指三十九族和达木蒙古八旗—译者注)和那曲卡。这意味着中国边界就位于巴塘以西,印度政府认为这是18世纪初确立的。然而,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要接受这样一个边界,他们就必须放弃像昌都这样的地方,而当时中国仍然掌控着昌都。最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截至1913年2月,英国人已经得出结论,无论英国与中国之间针对8·17备忘录举行多么严肃的谈判,西藏人都应当出席。
西藏人直接参与此类谈判的想法在当时不是什么创新。这是至少自1886年危机以来,英国对藏政策的一个目标;该想法导致了1904年拉萨条约的签订,同时也令西藏代表出席了1907-1908年间的中英贸易协定谈判。[12]自蒙藏协定签订以来,西藏代表的出席变成最重要的问题。蒙藏协定为俄国影响拉萨提供了一张入场券;而西藏代表出席中英谈判则可以被理解为:达赖喇嘛现在已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国家首领,不打算看到本国事务由他国越过自己来决定。例如,如果没有一则明明白白的西藏协定,谁能保证驻藏大臣及卫队究竟以何种方式返回拉萨呢?西藏人参与中英谈判角逐场的机会如此近在咫尺,唾手可得。与此同时,正当英国人努力争取与中方讨论8·17备忘录时,中国人也在竭尽全力试图绕开英国,直接与西藏谈判。当然,他们坚称此类谈判的地点要么在拉萨,要么在东部西藏;在此基础上,达赖喇嘛政府拒绝参加谈判。然而,1913年初,或许担心英属印度政府会忽略自己,直接与北京达成谈判,达赖喇嘛同意和中国人举行公开谈判,条件是中方停止在东部西藏施加压力,接受英国领土大吉岭作为谈判地点。[13]达赖喇嘛的建议为把两个单独的双边谈判,即中藏谈
判和中英谈判,合并为一个三方会谈提供了机会。
截至1913年2月,在英属印度政府领土上,要么大吉岭,要么西姆拉,举行一次三方会谈,以此解决西藏问题的概念,最终被印度政府视作一项政策。回想起1905年在加尔各答谈判的命运,以及认为印度利益在1906年初的北京谈判中被牺牲而引发的诸多不满,上述政策表明印度政府非常不愿意看到涉及诸如西藏的边疆安全这样重大的问题,交给伦敦或北京的英国外交家来任意处置。该政策还指出极有影响力的一个先例:擦绒协巴作为西藏代表参与了1908年在印度举行的中英贸易协定谈判。截至3月底,伦敦的英国本土政府仍在担心,比起在北京举行的中英谈判,此类三方会谈会轻易招致俄国人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引发抗议,但他们还是同意了印度政府的观点。4月5日,朱尔典接到此通知。[14]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蒙古局势对英国对藏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例证,印度事务部或多或少下定决心:这次三方会谈应努力争取英国在拉萨设立长期代表的权利。克鲁勋爵认为,英国现在行使该权利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正如当时英国中亚政策的诸多问题那样,这取决于对1907年英俄协定的修改——但令各方在原则上接受英国人的这种权利,绝对值得尝试。克鲁勋爵长期工作在印度事务部的一些同僚则持更强硬的立场。例如,莱昂纳尔·亚伯拉罕(Lionel Abrahams)宣称:
或许可以说,我们在过去10年得出的全部教训,就是西藏没有能力独自存在;西藏必须隶属于某种影响之下;我们决不允许英国之外的势力对西藏产生影响;英国人的影响力只能通过以某种方式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得以维系。[15]
荣赫鹏(Younghusband,1903-1904年间第二次入侵西藏的英军政治首领——译者注)看到这段话一定非常高兴。
看出英国政策演变方向的中国人匆忙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他们认为,西藏人参与三方会谈,势必损害他们的威望,必然会为英藏直接谈判制造一些机会,即便这类英藏谈判是秘密进行的。3月27日,中国外交部通知朱尔典,现在中国正式提出在8·17备忘录基础上全面讨论西藏问题,并打算为此目的向伦敦派出一名全权大使。[16]似乎温宗尧将会是恰当的人选。读者或许还记得,在钟颖率领赵尔丰部下的先遣队来到拉萨之际,温宗尧曾担任过联豫在拉萨的助手[17]。由于感到中国人背离了向西藏人的许诺,温宗尧辞去职务。英国政府认为温宗尧十分同情西藏人民。中国政府任命温宗尧的目的是在鱼钩上安装诱饵。实际上,尽管可能比联豫人道一些,但温宗尧很可能和其他所有中国官员一样,迫切地希望中国能够控制西藏。他显然是五族共和政策的支持者。英国人如果期望他能作出任何戏剧性的让步,那就太愚蠢了。最后,英国人没有接受诱惑。格雷命朱尔典通知中国外交部,西藏代表和英国代表将会在大吉岭欢迎温宗尧的到来;但不会在伦敦举行任何会谈。[18]
当伦敦的英国本土政府首次讨论西藏人参与中英谈判的观点时,英国外交部的格雷认为,谈判结果不会是三方协议。谈判应当在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进行,但依然会遵循8·17备忘录的基本原则,英国人的角色应当仅限于提供“善意的援助”。[19]格雷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俄国人就会指责英国人破坏1907年英俄协定,因为该协定规定英藏之间不得违背1890年、1904年和1906年协定的规定直接进行政治谈判。然而,朱尔典现在可以极有说服力地反驳这一观点了。他说,出于现实的原因,英国参与三方会谈的讨论以及最后达成的协议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没有英国的参与,谈判必然会被无限期延长,毕竟,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外交拖延的人。第二,如果英国人不在此次会谈可能签订的任何协定上签字,在中国人看来将会是英国示弱的表现。如果英国人不参加谈判,他们如何才能作出保证呢?第三,现存的英国与西藏或涉藏条约关系中的诸多方面,例如,1908年贸易协定等,都需要修订;此外,印度政府也需要和西藏签署协定。朱尔典还辩解说,1908年贸易协定已经确立了此类三方会谈的先例,当时并没有激起俄国人的抗议;因此,俄国人现在也不会抗议三方会谈或此类协议。格雷对朱尔典的此番言论印象十分深刻。正如他所言[20]:
公正地说,我们有权成为与中国和西藏进行谈判的三方会谈中的一方,这完全没有破坏1907年
英俄协定。根据该协定,我们有权与中国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我们有权履行我们在1907年之前与西藏签订的协议。因此,我们拥有正式参加与中国和西藏举行的谈判的权利。
然而,他又补充:
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在此三方协议之下,我们不应当拥有破坏英俄协定的权利,也不应当承担违背英俄协定的责任。如此,我们就能向俄国人解释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打算停留在何种范围内。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通知俄国人发生了什么,因为这只涉及英中涉藏关系,但我们必须要让俄国了解我们的行动范围。
由此可知,举行充分的三方会谈之决定并非授予英国无限制的活动自由。正如莫利勋爵(Lord Morley,1905年12月10日至1910年11月3日期间担任印度事务大臣——译者注)在1913年7月28日对众议院解释的那样,这种局面,或者至少我们所假设的这种局面,必须维持下去:
我们暂且将中国的西藏称之为主导者。除非出现了其他情况,否则我们将会是诚实的中间人,但作为一名诚实的中间人,也要对我曾向诸位描述的诸多利益[例如,拉萨条约,等等]保持时刻警惕的状态。[21]
截止1913年4月底,在伦敦本土政府对于西藏谈判的三方会谈本质达成全面一致意见之前,1912年8月17日出台的英国备忘录原则已经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起初,英国人希望迫使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地位,以及中国在西藏的权利和利益之本质等问题给出确切的定义。现在,从表面上看英国人则充当了中藏谈判的中间人角色。这种变化有其弊端。若想要此次三方会谈顺利产生一则条约或其他任何协定,现在必须要征求西藏和中国的同意。然而,这种变化也有绝对的好处。现在,西藏方面和中国方面同时在场,各方就能对英国与西藏的关系、英国对西藏的影响之本质作出巨大的修改,这正是荣赫鹏没能争取到的。但此处又出现了1907年英俄协定带来的问题。这些修改需要俄国的同意。然而,一旦这种修改的可能性获得许可,便立刻与俄国谈判现在可能已经在西藏获得的此类特权,会不会不明智呢?正如印度事务部当时发现的(1913年4月30日),英国或许可以通过接下来的谈判获得如下特权:在拉萨设立唯一的英国代表,重新占领春丕谷的权利,直接与西藏政府各个阶层联系的自由,从尼泊尔人那里获得一些好处,诸如纠正尼藏边界,补偿尼泊尔商人在1912年拉萨动乱中遭受的损失等。[22]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上文已提到,英国外交大臣)承认此类事件需要俄国人的同意,但他认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在圣彼得堡提出这些问题显得轻率鲁莽。当前需要做的,就是告知俄国政府,三方会谈即将召开。进一步的英俄谈判很可能需要延期,直到三方会谈产生某些成果。[23]
1913年5月26日,朱尔典通知中国外交部,英国政府现已接受中方所请,在1月30日讨论1912年8月17日英国备忘录一事。[24]此次会谈在印度,或者大吉岭;西藏代表也需要参加。中国政府很不乐意。此外,就在此时,中方在边界地区再一次发动进攻,希望在没有英国人帮助的情况下,改善他们在西藏的地位。袁世凯总统对朱尔典所提建议的唯一明确回答便是:四川和西藏的边界线不应超过江达以西,距离拉萨不到100英里。[25]朱尔典认为,这是中国对沿着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西藏大片土地,包括察隅和波密等地,宣称拥有主权的一种间接迂回的表达方式,而印度政府却认为这些地方都应当摆脱中国的影响。中国军队在边疆地区的捷报显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精神,包括收复长期麻烦不断的乡城。[26]6月5日,朱尔典拜访了袁世凯,用极其强烈的语气抗议袁世凯颁布的总统令所暗含的意义,袁世凯很快表示否认,现在看起来此举不过是“挽回颜面”的一种姿态。[27]在朱尔典的压力下,袁世凯似乎放弃了在印度召开三方会谈的打算。然而,袁世凯解释道,温宗尧不能再担任中国政府代表了,因为温宗尧认为,若在伦敦谈判,中国人会受到更好的待遇,因而他拒绝前往印度。袁世凯提议张荫棠取而代之,或许是最后一次作出抵抗的姿态。朱尔典拒绝接受张荫棠参加谈判,因为此人曾在1906-1908年间给印度政府制造了很多麻烦。随后,袁世凯又建议陈贻范[28]参加会谈。此人最近担任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参赞;要不是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他可能会前往云南—缅甸边界参
加中英谈判了。朱尔典立刻宣布,印度非常欢迎陈贻范,伦敦的英国外交部也持同样的观点。正如沃特尔·兰利爵士(SirWalter Langley)所评价的:
陈贻范九年来都是中国公使馆的二号人物,我们都很熟悉他。他被任命参加谈判是最理想的,因为他对我们都很友好,英语非常流利,人又极其聪明。[29]
第二天,袁世凯总统就正式宣布,陈贻范将会参加印度举行的三方会谈。[30]
朱尔典刚刚获悉陈贻范被任命的消息,印度政府就立刻开始着手安排会议的相关事宜。6月5日,哈定(Lord Hardinge,1910年11月23日至1916年4月4日担任印度总督——译者注)致函达赖喇嘛,请他派一名代表赴印度参加会谈[31]。这显然是一封“政治”信函,被1907年英俄协定明确禁止。几天后,总督任命印度外交大臣(the Indian Foreign Secretary)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作为英国代表参加三方会谈,并由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以及中国领事机构的一名成员协助。[32]哈定还建议,会议场所应当从大吉岭转移到西姆拉,在那里,“我们能对会议实施更多有效的控制,而西藏代表也不会过分暴露在大吉岭的中国人阴谋中”,这显然表明,印度政府打算操纵西姆拉会议。[33]6月17日,哈定获悉,达赖喇嘛已经选派伦钦夏扎作为西藏政府代表参加现在为我们所知的西姆拉会议。
当然,如果英国人以为,一旦袁世凯任命了一位代表参会,他就会停止所有将此次会议变成有利于中国的企图,那么英国人就过于天真了。例如,在陈贻范被任命的几天后,袁世凯就宣布,还将有一名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地位也与陈贻范相同。[34]此人就是胡汉民[35],前任广州都督,最近因为五国贷款(Five Power Loan)一事和中央政府发生争执,如果他能离开中国一段时间,袁世凯正求之不得。胡汉民是众所周知的反英派,毫无疑问,他出现在西姆拉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陈贻范的魅力和亲和力。朱尔典休假离京期间的代办艾斯顿(Alston)立刻抗议袁世凯任命胡汉民,随后袁便取消了这一任命。袁世凯称,胡汉民本人很有可能拒绝出任该职务。[36]
关于陈贻范的头衔问题,中英双方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争议。根据总统令,袁世凯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Commissioner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ibet),代表的含义是:陈贻范将会在前往西藏首府履职途中,顺便在西姆拉停留。[37]当然,这样的解释是存在先例的,1905年唐绍仪前往加尔各答谈判期间也被任命为这一职务。[38]唐绍仪也是前往西藏的路途中顺道访问印度。英国人认为,应当反对陈贻范的这一职衔,理由有二:第一,西姆拉会议实际上需要决定中国能否在中部西藏派遣官员,袁世凯此举被英国认为是通过一种间接方式预测西姆拉会议的决定。[39]第二,“宣抚使”这一术语有着特定含义,表明中国人希望通过武力征服西藏。艾斯顿及时提出了抗议。中国外交部回复道,他们使用“宣抚使”仅仅是为了表明他们的和平意愿(后来应英国要求“宣抚使”被改为“西藏议约全权专员”——译者注)。英国政府对此回复并不满意。
围绕西藏代表参加会谈的地位问题,中英双方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在1907-1908年举行的中英贸易谈判过程中,中方竭力否定西藏代表具有和中方代表平等的地位。[40]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在辩论中占上风。现在,他们宣布伦钦夏扎应和当年擦绒协摆的地位相同,这表明其中存在的一些定式,例如,作为西藏代表,签订会议中的任何协定都需“秉承中国代表训示,随同商议”,艾斯顿表示反对。[41]随后,中国外交部又提出另一个计划。为什么不进行两套特点鲜明的谈判呢?陈贻范可以先与西藏代表谈判,随后再与英国代表谈判。1907-1908年间,中方就曾提出过这种建议。艾斯顿回答:会议必须是真正的三方会谈,要么就取消会谈。[42]最后,中国外交部又提出一个建议,他们将宣布:
现在,中国政府的责任是:命令全权代表启程赴印度,与英国全权代表和西藏全权代表一起商谈一则临时协定,签署各方可能达成一致的条款,如此,所有过去存在的困难都将得到解决。[43]
艾斯顿认为,这是他所期望的最好结果。至少中国政府在原则上同意此次会谈为三方会谈,并承认存在一位西藏全权代表(a Tibetan plenipotentia⁃ry)。中方提到的“一则临时协定”(a provisional
treaty)无疑是个略微不祥的征兆;但或许仅仅意味着一则需要批准的条约,而西姆拉会议无论将产生什么协议,都必然需要获得批准。
从此刻起,中国政府不再提出一些重大问题,但到了10月,西姆拉会议即将开始之际,他们又继续开始耽搁延迟、支吾其词,不断提出一些小问题。陈贻范似乎非常不愿离开中国。他提出将西姆拉会议延迟几周,以便他在上海量身定做一套新衣服。[44]8月25日,艾斯顿告诉袁世凯,原本计划在7月1日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将会在10月6日准时召开,无论陈贻范是否抵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才奉命出发。[45]在被任命为印度政府顾问参加西姆拉会议的领事官员阿奇伯德·罗斯(Archibald Rose。)的陪同下,陈贻范9月3日从上海启程。10月5日,陈贻范抵达西姆拉,这时距离艾斯顿的最后期限只剩一天[46],伦钦夏扎此时已经抵达西姆拉11天了。[47]此外,陈贻范此行还有一位陪同,即在中国海关供职的布鲁斯(B.D.Bruce);布鲁斯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Aglen)[48]所派,以期在西姆拉会议上协助中国代表。[49]这种在最后一刻增强中国实力的行为遭到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对,他们对于在早期西藏问题中,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欧洲员工所扮演的角色有着非常不愉快的记忆。此举立刻令麦克马洪更加坚信,中国人绝不会希望达成真正的协议。
一旦袁世凯总统接受三方会谈的决定,印度政府便希望中国停止在边界的一切军事行动,至少在西姆拉谈判期间暂时停止。然而,实际上,四川政府似乎不打算继续推迟再次征服西藏的计划了。艾斯顿奉命警告袁世凯,这种举动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他指出,中国军队在边界地区的重大推进,可能会导致中英谈判崩溃。但是,格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威胁中方即使没有中国人参与,英藏也将进行直接谈判,或者英国人将会积极支持西藏人(因为英王陛下政府会得到建议,除非已准备在发生危急情况下继续支持西藏人,否则不要轻易承诺。而英国本土政府是不会这么做的)[48]都是不明智的。因此,艾斯顿的警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无论如何,正如英国外交部的看法,袁世凯总统实际上不可能拥有挫败四川省政府野心的权威。贯穿整个西姆拉会议,边界局势始终剑拔弩张。英国人所能做的就是在打箭炉设置一位领事官员路易斯·金(Louis King),在会议进展之际监督、报告边情。[49]
在会议最终做好准备之前,西藏人也显得问题不断。7月27日,他们给哈定勋爵寄去他们准备接受的条件。[50]西藏应当完全掌控自己的内政。在外交关系方面,可允许英国人在重要事件方面具有一定发言权,其余事件则由西藏人自主决定。不允许中国官员和士兵返回西藏,即便是驻藏大臣和他的几百人卫队也不允许。唯一能留在西藏的中国人只能是诚心诚意的商人。达赖喇嘛认为,西藏的领土一直向东延伸到打箭炉。当然,根据拉萨政府的说法,以上所有这些都是西藏人民自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以来就享有的权利。这种说法蕴含着真正彻底的西藏独立,并宣称对中国统治了100多年的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拥有主权,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如果西藏人坚持这些条件,西姆拉会议必然不会产生任何有用的条约。此外,有证据表明,达赖喇嘛对于参加会议明智与否仍有疑虑,有时候他甚至认为,他还不如在没有英国人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和中国政府交涉。昌都的中国司令通过噶伦喇嘛主动向他提出的建议,令他颇为动摇。例如,8月10日,伦钦夏扎告诉贝尔,如果最近中国政府代表没有抵达印度,西藏政府将在东部西藏开启谈判。[51]最后,又出现了班禅喇嘛的问题。班禅喇嘛显然非常急于参加西姆拉会议,如果无法参加,他自己将会和中国人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印度政府认为忽略班禅喇嘛不会带来什么危险。[52]然而,麦克马洪本应毫不怀疑印度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上的目标,即:让复杂的中藏平衡关系达成妥协,原本不会如此轻易实现。
当西姆拉会议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时,英国外交部小心翼翼地确保俄国人随时了解会议进展,但只是大体上的情况。萨佐诺夫并没有试图以技术或远非技术手段利用英国可能对1907年英俄协定造成的破坏做文章——这让英国人颇受鼓舞——但他的确打算安排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出席西姆拉会议,哈定勋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俄方的计划。[53]然而,到了西姆拉会议召开前夕,西姆拉已经汇集了各个国家的间谍,包括俄国和日本间谍[54]。印度政
府意识到,相比1905年的加尔各答谈判或1907-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的谈判,如今的西姆拉会议已经被呈现在一个更为公开的舞台上。1913年10月的西姆拉会议,自然无法再像1904年9月荣赫鹏在拉萨举行的会议那般为所欲为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参见《麦克马洪线》原书(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1914,by Alastair Lamb,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6)第459-476页。
[2]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英国外交家,生于爱尔兰,就读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学院,拥有文学硕士学位。清光绪二年(1876)来华,先在北京领事馆任见习翻译员,曾于各口岸学习领事业务,谙熟中国官场。1888年升为北京公使馆馆员,1891年成为中文书记长。1896年出任汉城总领事,1898年升为驻华代理公使,1901年成为办理公使,1906年成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1920年退休之后,曾出席华盛顿会议。1925年去世。——译者注
[3]颜惠庆(Yen Hui-ching或W.W.Yen,1877年4月2日-1950年5月24日),字骏人,中国政治家、外交家、作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1909年任外交部股长。1910年兼清华大学总办。1912年4月被黎元洪委任为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13年1月出任驻德国公使,后调任丹麦、瑞典等国公使。1919年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1920年8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2年辞去外交总长职务,改任内务总长等职。1926年春,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1927年移居天津,任天津大陆银行董事长、自来水公司董事长等职。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大使、驻苏大使,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1949年2月,为反对蒋介石继续内战,和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等以私人身份到北平、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同时,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译者注。
[4]FO 535∕15,第235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9月12日。
[5]FO 535∕15,第296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2年12月3日。
[6]关于这一点,克鲁和印度事务部都倾向于给中国人留下比印度政府建议的更多领土。克鲁认为,察隅应当归达赖喇嘛管辖,但德格和昌都,“这两处被征服的地区,能有效地维持其现状”,应当继续归中国人管理。遗憾的是,印度事务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是麦克马洪坚持认为中国人应当放弃昌都,而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中国人拒绝在西姆拉协议上签字。参见PEF 1912∕29,第657∕13,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2年12月3日。
[7]FO 535∕15,第303号文件,格雷致函朱尔典,1912年12月12日。
[8]FO 535∕15,第304a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2月13日。
[9]FO 371∕1329,第55588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2月16日。
[10]FO 535∕15,第314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2月26日。
[11]FO 371∕1609,第4823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1月31日。
[12]参见BCCA以及本书第三章。
[13]FO 371∕1609,第6124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2月4日。
[14]FO 535∕16,第180号文件,格雷致函朱尔典,1913年4月5日。
[15]FO 371∕1610,第13816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3月25日。
[16]FO 371∕1610,第14001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3月27日。
[17]参见第16章。
[18]FO 535∕16,第180号文件,格雷致函朱尔典,1913年4月5日。
[19]FO 535∕16,第155号文件,印度事务大臣致函总督,1913年3月19日。
[20]FO 371∕1610,第1653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4月10日,附格雷之备忘录。
[21]《议会辩论》(Parliamentary Debates),第五系列,第14卷,上议院,1913年,第1436页。西姆拉会议本质的概念体现在委员会任命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为英国全权代表之时。参见下文。
[22]FO 371∕1610,第20005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4月30日。
[23]PEF 1913∕16,第1933∕13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3年5月15日。
[24]FO 371∕1611,第2410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5月26日。
[25]FO 371∕1611,第24103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
年5月26日。
[26]FO 371∕1611,第2545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6月4日。
[27]FO 371∕1611,第25790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6月5日。
[28]陈贻范,上海方言学堂北京同文馆学生,英国留学生,驻英公使馆通译参赞官,代理公使,云南腾越海关道驻沪通商交涉使总统顾问,参见敷文社编:《最近官绅履历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资料丛刊正编》第45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46页。陈在英国任领事时,办事随和,深得英人喜欢,因此朱尔典认为陈贻范能够很好地和英人合作,听任他们的摆布。在这种情况下,陈贻范于1913年4月15日被任命为“西藏宣抚使”。参见:何洁:《试论西姆拉会议中的陈贻范》(《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
[29]同上,兰利备忘录。
[30]FO 371∕1611,第25809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6月5日。
[31]FO 535∕16,第294号文件,哈定致函达赖喇嘛,1913年6月5日。
[32]FO 371∕1611,第27640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6月16日。
一度在云南腾越担任英国领事的阿奇伯德·罗斯(Ar⁃chibald Rose),是被印度政府选中的领事官员,为英国代表就中国事务出谋划策。在他处理有争议的云南-缅甸边界过程中,罗斯获得了很多了解中国官员如何看待边界问题的经验。1911年,他沿着中国边界进行了一次探险活动,包括访问喀什噶里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解决缅甸-中国争议边界的方案,即劝说中国放弃对片马的主权,以此换回罕萨米尔(the Mir ofHunza)放弃自己在新疆萨雷廓勒地区(塔克顿巴什帕米尔)的权利。印度政府宣称他们倾向于这个计划,该计划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换回他们实际并不拥有的东西,罕萨米尔在萨雷廓勒的地位十分脆弱,但朱尔典指出,中国人永远不会同意这样一个计划,因而这个想法就被遗忘了。罗斯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与印度政府非常契合;他与麦克马洪和贝尔的关系都非常好。
参见FO 371∕1335,第7971号文件,《中印边界报告》(Report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 of India),罗斯(A.Rose),加尔各答,1911年;罗斯(A.Rose),“中印边界”(the Chinese Frontiers of India),《地理期刊》(Geographical Journal),XXXIX,1912年,第83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5月14日。
[33]PEF 1913∕17,第2376∕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6月15日。
西藏人有些不情愿地接受了将谈判地点从大吉岭换到西姆拉的决定。他们指出,他们没有自己的密码,因此,他们和拉萨之间的联络只能通过信使。从大吉岭发出一封信抵达拉萨的时间大约是7天,从西姆拉发信到拉萨大约是11天;因此,将会议场地从大吉岭变更到西姆拉,极大地增加了西藏代表和西藏政府保持联络的困难。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印度政府很可能认为这样会让伦钦夏扎更容易被自己控制。
[34]《英国晨报》(Morning Post),1913年6月18日;FO 371∕1611,第27967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6月18日。
[35]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鸿,字展堂,号不匮室主,汉族广府民系,广东番禺人。祖籍江西吉安,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中举人,1902年、1904年两度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稍后又由孙中山指定任本部秘书,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和胡汉民在政治上再度合作。1936年5月9日突发脑出血,5月12日病逝。——译者注。
[36]FO 535∕16,第298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6月23日。
[37]FO 371∕1611,第27650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6月15日。
[38]参见本书第三章。
[39]大约就在此时,陆兴祺也正在试图进入西藏,通知达赖喇嘛他已经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取代钟颖,而钟颖则在前一段时间接替了联豫。因此可见,中国人实际上似乎试图在中部西藏设立至少两个职位,一个是驻藏大臣,一个是宣抚使。印度政府完全无视陆兴祺的要求,傲慢地拒绝了他从英国领土越过西藏边界的请求。例如,参见FO 371∕1611,第31755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7月10日。
[40]参见本书第十章。
[41]FO 371∕1611,第32442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7月14日。
[42]FO 371∕1612,第36258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8月6日。
[43]FO 371∕1612,第36932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8月10日。
[44]PEF 1913∕18,第3601∕13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8月30日。
[45]FO 6371∕1612,第39306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8月25日。
[46]FO 371∕1612,第45698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10月7日。
[47]FO 535∕16,第371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9月24日。
[48]安格联(F.A.Aglen 1869~1932),英国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进入中国海关,历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总税务司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光绪二十三年,曾以代理税务司职务,负责天津海关工作。清光绪二十五年~翌年任南京海关税务司,清光绪二十六年~翌年任江海关税务司,清光绪二十七~光绪二十九年再任南京海关税务司。——译者注。
[49]例如,FO 371∕1613,第48622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10月26日。
[50]PEF 1913∕17,第2296∕13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3年6月9日。
[51]FO 535∕16,艾斯顿致函金,1913年9月4日。
[52]FO 371∕1612,第34848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7月28日。
[53]FO 371∕1612,第37622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8月14日。
[54]FO 371∕1612,第37245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8月11日。
[55]FO 371∕1612,第38578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3年8月22日。
[56]FO 371∕1612,第39760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8月27日。
[责任编辑 陈立明]
[校 对 赵海静]
D823
A
1003-8388(2015)02-0015-10
2015-02-04
梁俊艳(1978-),女,新疆阜康人,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西藏历史,西藏近现代史,西藏与英国关系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麦克马洪线》的翻译”(项目号:XZ12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