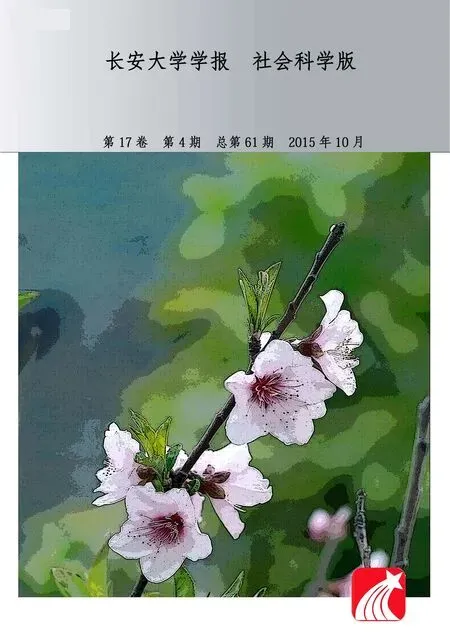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汉代社会对河东地区中条山一带的铜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在此基础上,河东的铜器铸造业兴盛,产品既供应本地,也销往关中以及河北地区,为官府及贵族所青睐。在汉代的铜产业链条中,河东本地侧重于铸造生活类铜器,并且担负着开采、冶炼的重任,为河内、河南的铜兵器生产提供原料。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得益于先秦时期河东铜矿长久的开采历史,其次得益于东周时期铜矿石冶炼新技术的引入。
关键词:青铜文化;汉代;河东地区;铜矿开采;铜器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它的下界是很明了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1]秦汉铁器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完全遮蔽青铜文化的余晖。“虽然汉代铜器已经失去了类似三代时期所拥有的辉煌地位,但它仍然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2],需要予以重视①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汉代青铜器便得到博雅人士的关注。科学的考古学引入中国后,汉代墓葬发掘中也往往有青铜器出土。因此,对金石学、考古学所得资料的整理汇编便成为汉代青铜文化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容庚《秦汉金文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研究性成果主要有陈直《关于两汉的手工业·铜器业》、《盐铁及其他采矿·铜矿》,收入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华书局,200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10章第2节《秦汉铜器与铜器制造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版;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研究表明,汉代可采铜矿分布于多个地区②比如常见的“汉有善铜出丹阳”铭文,以及朱提铜洗,表明汉代东南、西南地区皆有铜矿资源可资利用。,其中一处位于河东郡,也就是今山西省西南部的中条山一带。资源优势为河东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那么,在产业链条中,河东地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表现?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汉代河东铜矿开采的历史记录
在反映汉代历史的传世文献中,河东铜矿开采的正面记载极为罕见。不过,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以曲折隐晦的方式道出了开采的盛况。
汉武帝时,齐地方士公孙卿假托齐人申公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这个说法令汉武帝备感神往,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3]此升仙传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黄帝铸鼎所用铜料来自首山。《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反县条:“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4]可见,所谓首山实属中条山脉的组成部分,黄帝采首山铜,即是从中条山取得铜矿石。
尽管黄帝升仙的传说贴着上古历史的标签,但这个故事形成的真实年代是需要细究的。黄帝得入仙境的手段是采铜铸鼎,而战国秦汉之际的神仙方术之说,多主张通过入海寻觅三神山的手段求入不死之境,从现有资料来看,并没有铸鼎致仙的提法。而大鼎在秦汉之际似乎也没有多少升仙的功用,据说周朝灭亡时九鼎之一沦落于泗水,秦始皇兼并四海之后,曾派人打捞,此举“在意的就是它象征的权力”[5]。因此,黄帝铸鼎成仙的传说很可能是汉代前期成形的。然而,就故事的生成机制而言,有一个问题颇令人费解:西汉时代,全国范围内的铜矿产地并非仅有河东郡中条山一处,为何齐地方士偏偏将采铜地点定在中条山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上古圣王尧、舜、禹等据说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定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是极为常见的说法。当黄帝这个传说人物被塑造出来时,受惯性思维的影响,人们便将晋西南也视作他的根据地,他在本地采铜,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徐旭生针对尧、舜、禹在晋西南建都的说法,指出:“西汉人尚无此说”,“大约最先是皇甫谧这样说”[6]。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尧、舜,还是鲧、禹,他们的居住范围都在河、济地区”,也就是先秦地理书所说的兖州之地[7]。那么,同样作为层累造成的传说人物,黄帝似乎也不应当被独自安置在晋西南,他在中条山采铜的传说之所以出现,不大可能是因为汉人头脑中存在着黄帝活动于晋西南的观念,其中应当另有缘由。
实际上,在理解黄帝“采首山铜”之说的形成过程时,需要对当时重构国家祭祀体系的特殊历史背景投以更多的关注。就在公孙卿述说黄帝升仙故事的数月之前,在国家祭祀场所,河东汾阴后土祠的旁边,有巫者“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3]。而在公孙卿的黄帝成仙故事中,宝鼎恰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史记·封禅书》记载: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
很显然,正是汾阴起获宝鼎一事,使公孙卿大受启发,他由此找到了以黄帝升仙故事干谒君王的切入点,因为他那个版本的黄帝故事与汾阴得鼎一事具有很强的类比性:一是时间节点对应,即所谓“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意味着汉武帝站在了又一轮历史循环的起点;二是地点密迩,宝鼎发现于河东汾阴,黄帝铸鼎的原料采自河东地区的中条山,处于一郡之中,距离甚近。
从上述分析来看,黄帝采首山铜的说法很可能是受汾阴得鼎这一“盛世”盛事的刺激而出炉。然而,方士编造这个说法,总是要力图使人相信的,否则又如何能够成功地干谒君王,从而邀获功名?一般来说,一个新奇的说法若想得到他人的认可,大致有两种办法:一是故弄玄虚,令听者难以验证,如海中仙山之类;二是循着听者所具备的常识以立说。很多神话传说往往兼采两途,虚实杂错。即以黄帝升仙传说而言,所谓黄帝、仙境当然是无人见过、无人到过的,但其神异不经,正是征服不少听众的妙招。另一方面,所谓采首山铜的说法,是极易验证的,汉代关中贵族所用铜器产自河东的不在少数(见下文),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说的可能性会大为增加。反之,如果河东地区没有铜矿的分布,或者河东铜矿的开采利用是零星分散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有限,那么,公孙卿声称黄帝在首山采铜,便成了信口开河,恐怕会使得其说对汉武帝的诱惑力大打折扣。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孙卿造作“黄帝采首山铜”以铸升仙神鼎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西汉前期中条山铜矿大规模开采利用的实际历史背景。
东汉时期,河东铜矿的开采继续进行。《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6著录有河东铜官弩机,其铭文曰:“永元八年(96)河东铜官所造四石石鐖。”虽然这件文物是制成品,但以常理来说,在河东当地有铜矿的条件下,生产原料似不必从远处输送。陈直依据铭文推断东汉“河东有铜官,河东必然产铜无疑”[8],其说可从。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在中条山区的洞沟曾发现过古代矿洞,矿洞附近的崖壁上有东汉时期的石刻,其中一行有“光和二年河内”字样[9],“光和”为汉灵帝时期的年号,崖壁石刻说明,直到东汉晚期,中条山一带仍在从事铜矿开采。
二、汉代河东铜器的行销
两汉时期中条山铜矿的开采,从源头上保障了河东地区铜器铸造业的兴盛。河东所铸铜器的行销,即是其产业兴盛的显著表现。
一件被著录者称为“安邑鼎”的铜器有铭文曰:“安邑共厨宫铜鼎,容一斗重八斤十两,第十二。”[10]安邑是河东郡治,此鼎当为安邑县饮食供应机构所用。另有一件被命名为“杨鼎”的铜器,铭文为:“杨厨铜一斗鼎重十一斤二两地节三年十月造”[10]。所为“杨厨”,与“安邑共厨”相比,少一“共”字。但汉代铜鼎中有一件刻写着“卢氏厨”字样[10],卢氏属弘农辖县,标识该县的饮食供应机构,亦未着“共”字,因此,“杨厨”应当是指杨县的饮食供应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下辖杨县,则杨鼎使用地亦在河东。考虑到河东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安邑鼎、杨鼎所反映的极有可能是本地铸造而为本地所用的情形。
考古发掘中还曾发现过另一件安邑宫铜鼎,铭文曰:“安邑宫铜鼎一,容三斗,重十七斤八两。四年三月甲子,铜官守丞调、令史德、佐奉常、工乐造。第卅一。”[11]观其铭文格式,当属西汉时器。有学者认为该器物“制作方为中央铜官”[2],但西汉中央政府水衡都尉下有“辩铜”官号[4],并无“铜官”一职。倒是丹阳郡内设有“铜官”[4]。由此看来,铭文中的“铜官”也很有可能是某郡所设机构。众所周知,“汉有善铜出丹阳”,于是丹阳乃有铜官。中条山有铜矿,西汉政府在河东设铜官,并不奇怪*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汉“产铜之地甚多,但汉朝政府设置的铜官只有丹阳一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673页)如果笔者的推论可从,则西汉河东亦当有铜官。。安邑鼎既在河东使用,其由河东铜官铸造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山西闻喜县西官庄汉墓出土有“铜制的生产工具如斧、铲、口锄等”,“是专为随葬的明器”[12]。而在其他地区,铜质的明器性质的生产工具很少发现。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由河东地区得天独厚的铜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如果此推想属实,则西官庄汉墓的发现就是河东铜器自产自用的又一实证。
除了自用,河东出产的铜器也会受到其他地区的青睐。金石学家著录有“馆陶釜”,铭文作:“河东所造,三斗铜鏖釜,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二。”黄展岳判定此釜为“窦太后赐其爱女馆陶公主”的器物*见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铭文中的“鏖”字,原释作“庆”,黄先生认为有误,当以“鏖”为是,鏖乃“温器,引申为以温器煮烂”。笔者以为此说可从。。窦太后是汉景帝之母,因此,馆陶釜应为西汉前期由河东生产的铜器。西汉后期,赫然标明产自河东的铜器更是屡见不鲜。“河东鼎”铭曰“汤官元康元年河东所造铜三斗鼎重廿六斤六两第廿五”[10],元康是汉宣帝时期的年号。“敬武主家铫”铭曰:“敬武主家铜铫五升二斤九两初元五年五月河东造第四富平家。”[10]。“博邑家鼎”铭曰:“博邑家铜鼎容一斗重十一斤永光五年二月河东平阳造。”[10]初元、永光均为汉元帝时期的年号。所谓“河东所造”、“河东造”、“河东平阳造”,都是西汉河东地区铸造铜器的实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3件铜器的使用地均已超过河东区域。河东鼎属汤官所有,而汤官为少府属官[4],在京师。馆陶釜所有者为汉文帝之女馆陶公主,敬武主家铫的所有者为汉宣帝之女敬武长公主,而博邑家鼎的所有者应当是食封博邑的贵族。《汉书·地理志》无称“博邑”者,可能与此地存在对应关系的有九江的博乡侯国与泰山的博县。尽管汉代的县级政区中确有称乡称邑者,前者如山阳郡内作为县级侯国的中乡、栗乡、曲乡,后者如常山郡石邑、河东郡左邑,但在记事的时候,作为县级政区的某乡,其地名中所缀的“乡”字,是不能随意略去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地名混淆。因此,所谓“博邑”,应当是指泰山郡的博县。汉制规定:“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4],所谓“博邑”,即是博县被朝廷封给某位公主之后的称谓。支持这一推论的另一旁证是汉代所封公主的汤沐邑多有在齐鲁之地者,如阳石公主封在东莱郡,诸邑公主封在琅邪郡,二郡与泰山郡毗邻。可以说,汉王朝存在着让公主食封齐鲁之地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博邑”视为泰山郡博县封给汉家公主之后的称谓,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此一来,博邑家鼎与馆陶釜、敬武主家铫的性质便是一致的,均属汉家公主使用的器物。而汉代公主食封的县邑在当时叫做“汤沐邑”,有学者指出,汉代“皇室女性大多呆在京城之内”,“不到自己的封邑去”[13],他们只是坐食汤沐邑所贡献的租税而已。由此推断,上述3件公主家器物的使用地与汤官所属的河东鼎一样,亦在京师长安。
在京师贵戚之家以外,远离京城的诸侯王府内也会使用来自河东的铜器。满城二号墓编号2:4106的铜器铭文曰:“中山内府,铜鋗一,容三斗,重七斤五两,第卌五,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贾八百卌。”编号2:4034者铭文曰:“中山内府,铜鋗一,容三斗,重七斤十三两,第五十九,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14]另外,1965年河北行唐县曾发现铜鋗一件,铭文:“中山内府铜鋗一,容二斗,重六斤七两,第八十三,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15]根据铭文记载,这3件铜器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购自河东,说明河东铜器贸易比较活跃。不过,对于山东诸侯来说,河东地区并非他们满足自身铜器需求的首选市场。比较而言,洛阳的铜器市场受到诸侯的关注度似乎要高一些。
满城一号墓编号为1:4326号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14]1:4327号铭文:“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十两,第十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14]1:4328号:“中山内府铜盆,容二斗,重六斤六两,第六,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14]1:4098号:“中山内府铜盆,容三斗,重七斤四两,第二,卅四年,中郎柳买雒阳。”[14]与二号墓发现的3件铜器相比,这4件铜器购买的年份与二号墓相同,但经办人不同,一为郎中定,一为中郎柳;购买地点也不同,一为河东,一为雒阳。
在汉人心目中,“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商业氛围极其浓厚。在利益的驱使下,有的洛阳商人甚至可以“贾郡国,无所不至”[3],他们的行商范围没有局限。而这个状况实际上也意味着,全国各地的人到位于天下之中的洛阳来满足贸易需求,也是十分便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再考虑到黄河以南的洛阳周边区域并不是铜矿资源的富集区,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洛阳的铜器贸易大体存在两种可能的形式,或为纯粹的中转贸易,或为来料加工,然后予以出售。以常理而论,作为贸易集散地的洛阳,其铜器种类应当是十分丰富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山王府仍然派人到河东去采购,这反映什么问题呢?
笔者颇疑,中山王府前往河东采购很可能属于特例,是在洛阳铜器市场不能满足需求之时才予以执行的备选采购方案。理由在于,汉代的河东地区虽然可以“西贾秦、翟,北贾种、代”[3],确实具备从事商业活动的一定优势。但受地理条件的制约,该地区的商贸范围及于所谓秦、翟、种、代,很明显,大体上局限于太行山以西。而京师贵戚较多使用河东出产的铜器,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商贸格局。反观中山国,由于处在太行山以东区域,该地区并不是河东铜器直接输出的传统市场,王府派人南下采购,首选目的地自当在洛阳。
三、河东地区在汉代铜器生产中的分工
如果对进入消费环节的河东铜器种类稍加留意的话,有一个特点是不难发现的,那就是河东铜器绝大多数属于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鼎、铫、釜、鋗莫不如此,即便是明器性质的斧、铲、锄,亦取象于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工具。那么,汉代河东地区的铜器生产是否如文物资料所展示的那样,存在着器物种类方面的分工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考察视野仅仅局限于河东是无法作出合理判断的,我们还需要关注同属汉代“三河”区域的河南、河内两郡的铜器生产与使用情况。
在河南地区,除了上文已展示的洛阳铜器贸易的兴盛,洛阳当地也确实进行着铜器的铸造。著录者称之为“阳泉熏炉”的铜器铭文曰:“阳泉使者舍熏炉一,有般及盖,并重四斤一□,□□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内史属贤造,雒阳付守长则、丞善、掾胜、传舍啬夫兑。”*铭文拓本参见容庚编著《秦汉金文录》,第420页,同书第476页有释文。不过,本文所引释文及标点据徐正考《“阳泉熏炉”泐字考》(《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徐文对缺字处的标识及所缺字数与容著稍有不同。有学者认为“五年”前所缺二字为“元康”[16],元康为汉宣帝年号,则此器物为西汉宣帝时铸成。关于铭文中的“内史”一职,由于当时中央政府的内史早已分置为京兆尹、左冯翊,因此,只能是六安王国所属的内史*《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而诸侯王自汉初便设内史“治国民”,至汉成帝时始“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而铭文中所见“阳泉”,乃是西汉六安国下辖的五县之一[4]。综合这些信息,铭文大体是说熏炉的使用权属于六安国阳泉县传舍,但它并不是六安国的自产器物,而是由王国内史派属吏到洛阳去督造的。器物铸造完毕,由内史属吏带回国内,交付阳泉县。然后由阳泉县大吏逐级签收,最终送达阳泉传舍。由此可见,铭文中的“雒阳”,当指熏炉的铸造地*如果雒阳为铜器铸造地的推论有理,则本文所引熏炉铭文中的“雒阳”二字,在句读时应上属,断作“内史属贤造雒阳,付守长则……”。。
另一件被称之为“成山宫渠斗”的器物,其铭文曰:“扶成山宫铜渠斗重二斤神爵四年卒史任欣杜阳右尉司马赏斄少内佐王宫等造河南。”[10]“神爵”亦属汉宣帝年号,不过,比阳泉熏炉的元康年号稍晚。铭文中的“成山宫”,据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掘,今陕西宝鸡“眉县第五村秦汉遗址就是汉代的成山宫”[17],在汉代属右扶风辖区。而渠斗购置者的籍贯“杜阳”、“斄”亦皆为关中右扶风属县。很显然,铭文的意思是说成山宫渠斗是由宫殿所在的右扶风地区派员到外地购置的,而铭文最后的“河南”二字,标示的即为该器物的铸造地。
河内地区也有铸造日常生活类铜器的实证。如被著录者称作“步高宫高镫”的铜器,段玉裁认为:“镫,豆下跗也”,而“豆之遗制为今俗用灯盏”[18]。陈直说:“镫的名称因形式而变,有手柄的曰行镫,高足的曰高镫,有足的曰锭,专燃烛的高者曰烛豆,低者曰烛盘,燃油燃烛两用的曰鹿卢镫。”[8]可见,铜镫为照明用器件,属日常生活所用。其铭文曰:“步高宫工官造温。”[10]温县在汉代河内郡,根据阳泉熏炉、成山宫渠斗的文例,“造”字之后的地名乃是器物生产地,则这件铜镫是在河内温县铸造的。
不过,如同上述器物那样能够确证由河南、河内当地铸造的生产、生活用铜器十分稀见。就目前资料来看,两地的铜器生产似乎以兵器为大宗。
洛阳曾发现两件西汉铜弩机,其铭文中有“河内”字样,分别是“河内工官旉,三千九百廿三号”、“河内工官旉,四千一百八十四号”,两件弩机的郭身上各有铭文“三十八”。研究人员解释说“旉”为工官内“管理官员的名字”,“三千九百廿三号”和“四千一百八十四号”是“弩机的编号”,郭身所刻之“三十八”“应为生产弩机的作坊编号”。由此得出这样的认识:“这两件弩机同由河内工官旉监造,在第三十八号作坊内生产,且其编号已至数千,反映了当时弩机生产的管理之严、规模之大。”[19]汉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发现的一件弩机牙,铭文曰“河内□□二万二”,出土的Ⅰ型弩机栓塞共12件,其中9件有铭文。而在这9件中,除了1件的铭文显示为南阳工官所生产外,其余8件所刻文字分别是“河内工官二万一千”、“河内工官第百十六”、“河□工官第二千二百五十一”、“河内工官第八百廿八丁”、“河内工官第五十九”、“河内工官第七十九丁”、“河内工官第三百卅八”、“河内工官第三百八十二丙”。Ⅱ型弩机栓塞共3件,其中两件有铭文,分别是“河内工官第八百七十四”、“河内工官第七百六十七丙”[20]。河内工官所造弩机的大量发现,以及铭文所示可多达2万余的生产序列号,经由这些线索,我们可以约略窥知河内铜器生产的侧重点在于兵器。
河南工官的生产着力点与河内一样,都以兵器为主。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建筑遗址出土刻字骨签57 000多片,其中有一类被称为“‘河南工官’类骨签”,发掘报告仅给出了92例,其格式多为“纪年+‘河南工官’+职务(令、丞、护工卒史、作府啬夫、工等)+人名+造”,如“元年河南工官令谢丞种定作府啬夫辅始工始昌造”之类[20]。汉长安城武库遗址亦出土骨签,其中有的刻着“三年河南工官令”、“五年河南工官长令丞”字样*编号分别为4:T4③:6B和4:T4③:10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有学者在对骨签刻文进行研究之后认为,河南工官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生产兵器”[21]。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骨签所对应的河南工官兵器,并不一定都是铜器。但骨签多达5万多件,其中必有一部分是铜质兵器。
在感知河南、河内铜器生产侧重于兵器的基础上,回头来看河东铸造的日常生活类铜器在本地以及贵族阶层中的广泛使用,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河东地区的铜器生产侧重于日常生活类铜器。当然,这并非彻底否定河东的兵器生产。见于著录的铜器有冯久鐖、李游鐖,其铭文分别是 “河东冯久”、“河东李游”[10],陈直说:“弩机属于地方性的,有由河东造的,则有河东李从、河东冯久弩机。”*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62页。所谓“李从”,是陈直先生对“李游”二字的释文,未知孰是。揣摩陈先生之意,似认为两弩机乃河东所造。不过,这未必就是确论,因为目前并不能排除铭文表示器物所有人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的情形下,“河东”指的是冯久、李游的籍贯,并非兵器的产地。退一步说,即便两件弩机确为河东所产,与已发现的河南、河内兵器的数量相比,那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除了铜器生产种类方面的分工,在铜产业发展的不同环节,应当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工。河东地区蕴藏着丰富铜矿,河南、河内无此天然优势,这决定了在铜器冶铸的产业链中,河东必然要扮演原料产地的角色。河南、河内工官从事大规模的兵器生产,需要大量铜料,但因本地无法满足,必须由其他地区提供。考虑运输成本的问题,距离河南、河内最近的河东地区应当是供给的主力。至于供给的具体方式,河东地区直接将铜矿石运送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河北承德西汉铜矿遗址的调查表明,该遗址包括汉代矿井、选矿场、冶炼场。“虽然看起来很分散”,但距离都不远,“是一个整体,是从开采到冶炼的一连串生产过程”。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数块铜饼,“直径约33厘米,体重约为10~30多斤”[22]。有学者据此推断,“汉代铜的冶炼一般是在铜采矿场附近进行的,而有的炼铜工场还兼及铜制品的铸造”[23]。河东中条山一带是矿料来源地,这一基本地质特点决定其生产形态与承德铜矿遗址不会有太大差异,其选矿、冶炼很可能也是在矿区附近进行,然后将提取出的铜锭之类便于运输的精铜输往河南、河内,用以生产兵器。
四、汉代河东青铜文化兴盛的历史动因
汉代河东铜产业兴盛的局面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仅就矿藏开采的历史来讲,如果没有汉代之前长时期的采矿实践,也就不会有汉代的大规模开采。
中条山一带拥有铜矿资源,这一资源在先秦时代即已为时人所注意到。《山海经·北山经》曰:“《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自此东北行470里,有咸山,“其下多铜”。又东北行200里,继而东行300里,有阳山,“其下多金、铜”。由此东行350里,“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根据以上描述,从归山至王屋山,一路需循着东北方向或东向而行,而王屋山在今晋、豫两省交界处,因此,《山海经》描述的归山至王屋山区域,对应的实际就是山西西南部,而位于归山与王屋山之间的所谓咸山、阳山,应即中条山脉的组成部分*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02、105、106页。《山海经》一书在古代目录学中曾被列为地理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认为该书所叙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出于这样的考虑,《提要》将其列入小说家类。就本文所引归山至王屋山这一区域来看,东西绵延1 300多里,以战国尺度折合,约当现今的近450公里。但今山西运城市辖区县的东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因此《提要》认为《山海经》所述道里“率难考据”,还是比较中肯的。但并不能由此完全否定《山海经》的地理书性质,毕竟,通过其中的某些比较显著的地理坐标,判断《山海经》所述山川的大体位置,还是有可行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先秦传说认为咸山、阳山有铜,这并非无稽之谈,其历史背景很可能是先秦社会对中条山铜矿资源的地理认知与切实利用。
近年来,有团队组织了对中条山铜矿的考古调查,在其中一处遗址“采集到大量早商或与东下冯类型近似的陶片及亚腰石锤、石钎等采矿工具。种种迹象表明,中条山地区的铜矿开采可能在商代即已开始”[24]。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对垣曲县胡家峪铜矿店头矿区的店头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在遗址的古矿洞中,调查人员从门字型木支护上取得两块样品。碳14测年结果为距今2 315±75年(前365±75),树轮校正年代为2 325±55年(前375±85),从而以现代科技手段确切证明中条山铜矿至战国中期仍在开采[25]。
中条山一带持续千年以上的铜矿开采,至少为汉代的开采活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惯性,使得汉代社会得以循着先民的足迹,继续从事相同的事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先秦阶段,河东虽说天然地拥有丰富的铜矿,人们也在陆续进行开采,但此地的铜矿对商周青铜文化的辉煌成就似乎并没有十分突出的贡献,在铜器铸造过程中,河东铜矿所受到的关注度也不高。
20世纪80年代,金正耀采用铅同位素示踪的手段,判定殷墟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原料产地在距离殷都甚远的滇东北[26]。后来李晓岑沿用这一方法将研究时段延伸至周代,认为“不仅商代,而且西周、东周中原地区部分青铜器的矿质也来自云南”[27]。对商周铜料来自云南的论断,有一些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选取16件样本,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样本的铅同位素在高、中、低比值区皆有分布。结合现代勘明的不同铅比值矿藏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他们的最终看法是:高比值铅的青铜器来自于“商王朝统辖的北方”;处于中比值区的样本,“取自湖北或江西是有可能的”;低比值青铜器的铜料“有可能来自江西、湖南等地区的浅成多金属铀矿床”[28]。山西绛县曾发现一批西周铜器,检测表明,这批铜器的微量元素模式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大井矿冶遗址铜矿石“非常吻合”,研究人员由此推定其铜矿原料“很可能来源于辽西地区铜矿带”[24]。
虽然上述有关商周时代青铜器原料来源的结论不尽相同,但种种说法都将目光盯在了远离器物使用地以外的区域,甚至河东本地出土的铜器亦不能例外。这也就意味着,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表明,河东铜矿对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很有限。
不过,仍然有学者在解释商周青铜文化时注意到了河东铜矿。李延祥指出,考古发掘已在晋南的中条山地区及其附近发现了不少与早期炼铜技术有关的遗存,如洛阳北郊的西周铸铜遗址、出土大批西周铜器的三门峡虢国墓地、侯马地区的东周铸铜遗址等,这些考古发现“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条山地区铜矿的开发,绝非仅仅始于战国晚期。从地质资源上看,中条山地区也是夏商时期中原最近的铜矿产地”[25]。很明显,论者认为中条山铜矿也参与了商周青铜文化的发展,只是参与的程度并不明晰。比较而言,有学者认为中条山铜矿“是先秦时期中原青铜器的另一主要矿源”[29],似乎说得更为明确,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注意到中条山铜矿在先秦青铜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存在阶段性差异。
实际上,在商周时代河东铜矿的重要性经历了漫长的逐步提升的过程。李晓岑曾注意到,“东周以后,中原及附近地区确实已不见有云南矿质特征的青铜器了”,原因在于“商周以后靠近中原一带的矿产已被开发”[27],此说很有启发性。“中条山地区铜矿以贫矿为主,单个矿体一般规模不大”[30],在开采冶炼的过程中,投入较大,显然无法适应商代青铜文化的发展规模,因此必须向中原以外的地区获得铜料。但是,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河东铜矿的地位势必得到提升。
先秦时期炼铜已使用3种技术:一是“氧化矿—铜”工艺,二是“硫化矿—铜”工艺,三是“硫化矿—冰铜—铜”工艺。3种工艺中,前两种技术“简单、流程短、数日可完成,但矿石资源有限”,第三种“技术复杂、流程长、冶炼时间可达数十日,但矿石资源量大,是炼铜技术的重大进步”[31]。历史早期如河南安阳殷墟的炼铜遗物使用的是“氧化矿石直接还原冶炼成铜的技术,可简称为‘氧化矿—铜’技术”。但在中条山矿区,“铜矿氧化带一般不甚发育,氧化矿多呈薄膜状,无次生富集带”[32]。早期的氧化矿成铜技术显然不能在这一地质条件下大显身手,因此,河东地区也就只能在商代青铜文化的辉煌期寂寂无闻。
到西周时期,内蒙古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已能够开采品位较高的硫化矿石,经死焙烧脱硫后再还原冶炼成铜”,使用的是“硫化矿—铜”技术”。而据学者研究,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铜器的生产原料即来自大井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在两地铜产业如此密切关联的情形下,河东地区引入大井遗址采用的并且更适合河东铜矿地质条件的“硫化矿—铜”技术,并非令人感到意外之事。横水墓地的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初年,即便考虑技术交流的滞后性,我们推测东周时期中条山铜矿已采用“硫化矿—铜”新冶炼技术,应当不至于出现太大偏差。引入了新技术,中条山铜矿的开采利用便可以克服“贫矿为主”、氧化带“不甚发育”等地质条件的限制,从而大幅度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笔者认为,正是在先秦漫长时期内冶炼技术进步对铜矿利用效率的提升,才使河东地区在铜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河东产业地位逐步提升的过程正值青铜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青铜器正经历着一个“由礼乐器向日常生活实用器迅速转化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652页。原文将这一过程的发生限定在秦汉时代,实际上,这一进程自先秦礼崩乐坏之时即已开始。。这也就意味着,在河东承接生产青铜礼器的重要任务之时,已经先期埋下了铸造日常生活类铜器的基因。比如同样是生产铜鼎,战国时代或许还是礼文重器,进入秦汉时代,铸造的器物种类还延续着历史习惯,但铜鼎本身的性质却变为生活用器。从这个角度来说,汉代河东地区所承担的以日常生活类铜器为主的铜产业分工,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蕴含其中。
五、结语
河东地区特殊的资源优势,在先秦时期即已得到长期利用。但由于该地铜矿的地质特性对矿石冶炼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以致于先秦时期河东在青铜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并不突出。随着冶炼技术的改进,到了汉代,河东铜资源的利用率大幅提升。大量考古材料还表明,河东地区不仅以其资源优势为汉代铜器生产提供原料,在铸造的器物种类上也有分工。与河东毗邻的河南、河内多生产铜兵器,官办的色彩更浓厚一些,河东本地铸造的铜器多为日常生活所用,大量供给京师及河北地区,备受贵族阶层欢迎,体现出较强的民用色彩。由此可见,在产业链内开采、冶炼、铸造的纵向分工中,河东均有深度参与;而在兵器、日常用器等器物种类的横向分工中,河东亦占据半壁河山。两种分工中的角色,便是对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历史表现的重要诠释。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5.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沈长云.上古史探研[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8.
[9]安志敏,陈存洗.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J].考古,1962(10):519-522.
[10]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上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11]朱华.西汉安邑宫铜鼎[J].文物,1982(9):21-23.
[12]王寄生.闻喜西官庄汉代空心砖墓清理简报[J].考古通讯,1955(4):46-48.
[13]薛瑞泽.汉代汤沐邑研究[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99-105.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5]郑绍宗.河北行唐发现的两件汉代容器[J].文物,1976(12):89.
[16]徐正考.“阳泉熏炉”泐字考[J].考古与文物,2000(1):71.
[17]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眉县文化馆.陕西眉县成山宫遗址试掘简报[J].文博,2001(6):3-17.
[1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9]赵晓军,姜涛,周明霞.洛阳发现两件西汉有铭铜弩机及其相关问题[J].华夏考古,2010(1):115-120.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21]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22]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J].考古通讯,1957(1):22-27.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4]宋建忠,南普恒.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青铜器科技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5]李延祥.中条山古铜矿冶遗址初步考察研究[J].文物季刊,1993(2):64-67,78.
[26]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D].北京:中国科技大学,1984.
[27]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再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3):264-267.
[28]彭子成,刘永刚,刘侍中,等.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3):241-249.
[29]魏国锋,秦颖,王昌燧,等.若干地区出土部分商周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研究[J].地质学报,2011(3):446-458.
[30]罗武干,秦颖,王昌燧,等.中条山与皖南地区古铜矿冶炼产物的比较分析[J].岩矿测试,2007(3):209-212.
[31]李延祥,洪彦若.炉渣分析揭示古代炼铜技术[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5(1):28-34.
[32]魏国锋,秦颖,杨立新,等.若干古铜矿及其冶炼产物输出方向判别标志的初步研究[J].考古,2009(1):85-95.
PerformanceofHedonginbronzecultureofHandynasty
CUIJian-hua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Shaanxi,China)
Abstract:The copper mine in Zhongtiao mountain of Hedong was largely mined in Han dynasty,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Hedong’s bronze casting flourished. The products of bronze were provided for not only locality but also Guanzhong and Hebei, which were favored by official departments and nobility. In the copper industrial chain of Han dynasty, Hedong mainly casted bronzes for daily life, and undertook responsibility of mining and smelting, providing the raw material to the production of cooper weapon in Henei and Henan. The phenomenon that Hedong took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bronze culture of Han dynasty is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Firstly, it benefited from long-term mining in Pre-Qin period. Secondly, it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new technology of smelting copper mine in Eastern Zhou period.
Key words:bronze culture; Han dynasty; Hedong; cooper mining; bronze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33-07
作者简介:崔建华(1981-),男,河南渑池人,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