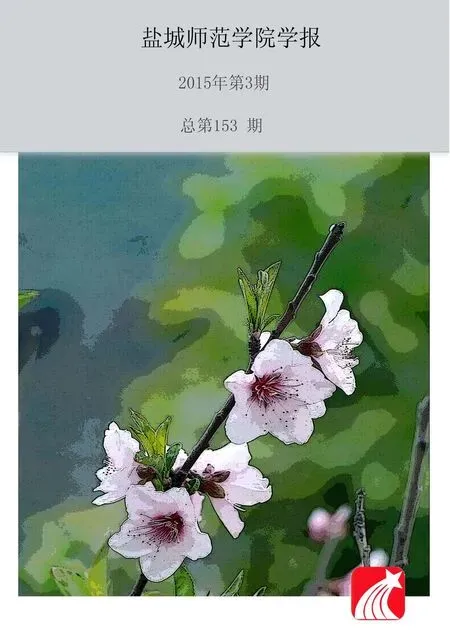我国文艺批评标准的前世今生
陈 辽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我国文艺批评标准的前世今生
陈 辽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我国的文艺批评标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诸子提出的批评标准比较雅驯;陈子昂痛陈南北朝文学的绮丽、浮靡,提出“兴寄”“风骨”的批评标准;其后韩愈、严羽、李贽、王士祯、王国维相继提出代表各自时代的批评标准;毛泽东首创“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评标准。我国的批评标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文艺批评;批评标准;延安文艺座谈会
“批评标准”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大创造。在他之前,两三千年的中国文艺批评史,谁也没有说过这么一个词语。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的文艺批评就没有批评标准。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中国古代至近代以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的批评标准。我国的批评标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总结,这才有利于今后文艺批评的健康开展,有益于今后我国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一、批评标准的历史发展
先秦时期的文艺创作,主要是诗歌。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作品呢?孔子率先作了回答,“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阳货》)他认为,那些发抒真实感情(“兴”)、有助人们认识生活(“观”)、团结民众(“群”)、批判现实或历史(“怨”)、能够对父、君很好服务(“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给听众、读者以有益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应该说,孔子树立的这一批评标准是很高的。自孔子以后,我国的作家、诗人、批评家,绝大多数把“兴、观、群、怒……”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作为自己创作的目的。也因此,我国的诗歌创作长盛不衰。孟子和庄子则对散文提出了批评标准。孟子说,“充实之为美。”(《尽心下》)在他眼里,艺术内容充实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庄子宣扬,那些“得心应手”、“得意忘言”(《庄子》)的作品是好作品。荀子则在《乐论》中对诗乐提出了他的批评标准,“乐中平”、“乐之中和也”、“乐言事其和也”、“中声之所止也”。他把是否“中和”作为诗乐好作品的标准。这些意见,也都有一定道理,对散文创作和诗乐创作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如果说,先秦时期诸子提出的批评标准,比较雅驯,不易掌握,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批评标准就比较具体了。他明白地提出了六项标准,即“六观”。“一观位体”,看作品不同体裁的艺术内容是否恰当、精深。“二观置辞”,看作品的语言运用是否合适,是否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三观通变”,看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是否吸取了前人之长而又有所创新和革新。“四观奇正”,看酌奇而不失其真,执正驭奇,讲究真实性。“五观事义”,事类者,“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文学作品用典是必要的,但不能“引事怪谬”或“实谬”,看作品在引经据典方面是否恰切得当。“六观宫商”,看作者在声律方面的修养如何,处理是否完美。把这“六观”完整地整合起来看,刘勰的“六观”批评标准,既涉及作品的真实性、艺术内容又涉及作品的艺术形式;既关乎作品的思想性,又关乎作品的真实性、艺术性。所以,这一“六观”批评标准提出后,南北朝以降,也为多数作家批评家所遵循。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相统一,这便是刘勰对文学作品的高要求、严标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径行直遂的,批评标准的发展也如此。南朝文学一度向“绮丽”、“浮靡”发展,朝形式主义倾斜;即使到了初唐,“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卷二○一)这时,陈子昂拍案而起,他把有无“兴寄”、“风骨”作为作品好差的标准。他在《陈伯玉集》卷一《修竹篇序》中指出,“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他称赞东方虬的诗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兴寄”,指的是诗歌的比兴寄托;“风骨”,指的是作品从内容到艺术表现,都是刚健清新,“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陈子昂这一批评标准提出后,扭转了南朝文学以来的“绮丽”、“浮靡”的局面,的确是“卓立千古,横制頺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其后出现的盛唐文学,流传千古,和陈子昂新的批评标准的提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唐以后,“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批评标准。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昌黎集》)他认为,载道之文(作品)才是好作品,否则,便不是好作品。这一批评标准,有其积极面,也有其消极面。积极面是弘扬了所谓由周公、孔子、孟子以来的“道统”,对培养、发展中国人的爱国思想、集体观念、国大于家等理念,是有好处的。但他只讲“文以载道”而忽视了文学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个性和艺术性,是这一批评标准的缺失,对我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韩愈以后,真正提出批评标准的,是严羽(生卒年不详),南宋人。他在《沧浪诗话》中提出,有无“妙悟”、“气象”、“兴趣”、“本色”、“传神”,乃是区分作品好差的标准。“妙悟”,在严羽那里,是从前人书本上悟,从自己的主观上悟。“气象”,指诗的风度,“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诗评》)。“兴趣”,反对以理为诗。“盛唐诗人惟在兴趣”(《诗辨》)。“本色”,指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迹。“须是本色,须是当行”(《诗法》)。严羽的最高要求是“传神”:“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诗辨》)在严羽看来,好诗、优秀诗的妙处,全在于有“妙悟”,有“气象”,有“兴趣”,“有本色”,能“传神”。虽然这只是严羽对好诗歌提出的要求,但后来的“性灵”说、“神韵”说,无不受到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批评标准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一些知识分子倾向个性解放。批评标准也有一些新提法。李贽提倡“童心”:“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焚书》)他以为,有了“童心”,就能写出没有束缚的“天下之至文来”。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则宣扬“性灵”。举凡“任性而发”、“率性而行”的“真人”的文学作品,就都是好作品(《叙小修诗》)。尽管以有无“童心”、“性灵”作为是否好作品的标准有片面性,但他们敢于揭橥新的批评标准,有助于促进新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及至清代,王士祯倡导“神韵”,“……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指出。”(《池北偶谈》,《带经堂诗话》卷三)何谓“神韵”?“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带经堂诗话》,《香祖笔记》)“隽永超诣”(《带经堂诗话》,《渔洋文》)。“自然入妙”(《池北偶谈》)。“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昼溪西堂诗序》,《蚕尾续文》二,《带经堂诗话》卷三)。总之,“神韵”是可以意会而不能具体言传的、好得不得了的东西,作品中有“神韵”才是好作品。王士祯的“神韵”批评标准,在清代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到了晚清和民国初年,王国维标榜“词以境界为最上”的批评标准。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卷上)“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人间词话》卷下)“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卷上)强调一个“真”字。王国维的“境界”批评标准,在诗词研究者中间,几乎无不奉为鹄的。
开宗明义提出“批评标准”,并把批评标准规定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是毛泽东。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十分清楚,“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又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毛泽东在批评标准问题上发表的上述意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那时,文艺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政治,从属于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并为抗日战争的政治服务。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的文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做了,确实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对抗日战争尽了应尽职责。而且,第一个正式提出“批评标准”的是毛泽东。可以说,他所提出的批评标准,是中国历代批评标准的总结和集大成,在文艺批评史上具有开创性,它的意义和价值必须充分肯定。
二、批评标准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训
即使从孔子提出“兴、观、群、怒……”的批评标准算起,我国的批评标准史也有两千几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有深刻教训。
经验之一,我国自古至今的批评标准,都是以创作实践为基础,为了进一步发展创作而提出的。孔子在收集、编辑、修订《诗经》的过程中,阅读了商、周时期数以千计的诗歌,研究了诗歌作者的创作实践,这才认为,那些“兴、观、群、怨……”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孟子、庄子、荀子之所以能够提出“充实之为美”(孟子)、“得心应手”“得意忘言”(庄子)、“中和”(荀子)的批评标准,也是这样。刘勰提出“六观”的批评标准,更和刘勰了解、熟悉和研究自古至南朝的文学创作实践分不开。陈子昂把有无“兴寄”、“风骨”作为好作品的标准,是因为当时文坛出现了“绮丽”、“浮靡”的片面性很大的创作倾向,他把“兴寄”、“风骨”视为纠正这一倾向的救治法门。韩愈把“文以载道”作为好作品的标准,以之与陈子昂相呼应。严羽的“妙悟”、“气象”、“兴趣”、“本色”、“传神”等标准,并非空想得来,仍然是来自创作实践。“童心”、“性灵”、“神韵”、“境界”诸说,虽然标新立异,但都以创作实践为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政治路线,也是从抗战文学的实践中提出的。由于我国历代提出的批评标准,都来自创作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创作,因此,其积极面、正能量是主要的。
经验之二,我国的批评标准,都是由个人提出的,绝大多数不代表官方,不带有强迫推行的性质。孔子在鲁国执过政,但时间不长就下台。他下台后,办私学,编《诗经》、《春秋》,他从民间文人的角度提出了“兴、观、群、怨……”的批评标准。孟子、庄子、荀子、严羽、王国维等都不是当权派。刘勰、陈子昂,当的也只是小官。他们都是以理服人,并不以权势压人,人们接受他们提出的批评标准,是因为他们掌握的是文艺批评的真理。韩愈是个副部级干部(当过侍郎),王士祯是部级干部(当过刑部尚书),但他们对文艺并无生杀予夺之权。即使是毛泽东,身为共产党中央主席,但那时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只是在野党。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个人名义提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评标准,也只是建议性的,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文艺界都得这么办。总之,迄新中国成立时为止,两千几百年间,我国的批评标准,都是由个人提出的,不带有强迫、命令的性质。人们之所以乐意采用这些批评标准,是因为它们有道理,能够说服人。
经验之三,批评标准提出后,总有一些人持有不同意见,于是发生了争论,发生了笔战,发生了相互批判。但是,从未因争论、笔战、批判而搞政治迫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庄子并不宗奉这一批评标准,而是提出了他自己的“得心应手”、“得意忘言”的批评标准。至于“童心”、“性灵”、“神韵”、“境界”诸说提出后,持有不同意见的更多,彼此辨驳,相互质疑,都没有产生过不良后果。也就是说,在批评标准问题上,两千几百年来,我国的文艺界都是持“宽松、宽容、宽厚”态度的。
正因为在批评标准问题上有此三条宝贵经验,因此,我国的文艺批评,自古以来都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出现过大问题。
当然,在批评标准问题上我国也有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主要出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出在对批评标准的官方强制和片面理解和执行上。
先说封建社会里在批评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教训。自周、秦至明代,除了“五胡乱华”到北朝和元代以外,都是汉人在中国执政。北朝和元代的执政者基本上不管文艺,对批评标准问题也采取不干预态度。但是,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都制造过不少文字狱。他们制造文字狱,只有一个批评标准,即对清王朝是否不敬,对清王朝的统治是否有干碍,是否在文字里隐含反清意图。“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仅仅这一句诗,即被清王朝高层统治者视为反清、叛逆,诗作者被严处。乾隆皇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对从全国收集来的诗、文、书、集,都过细审查,凡有蔑视清王朝的疑似字样者,都严加处理。如果他们认为,书中文字对清王朝不利,轻则革职、查办,重则处死,甚至祸及三代、亲朋。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这一批评标准而被陷入文字狱受到株连的人数以万计。它不限于诗、文,还涉及历史、法律等领域。可见批评标准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一代知识分子及其亲属的命运。
再说新中国成立后因官方强制及片面理解和执行“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政治路线的批评标准而造成的历史教训。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长期封建社会的中国,本有个人迷信的土壤和条件,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就一时(抗日战争时期)一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做好文艺工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被奉为文艺圣经,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实,正如胡乔木同志于1981年8月8日在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矛盾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第324-325页。胡乔木同志对《讲话》中存在问题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譬如说,毛泽东在批评标准问题上,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政治路线,这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党的政治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没有回答,一旦党的政治和政治路线不正确,譬如说,在“大跃进”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难道文艺仍然要从属于这样的政治和政治路线吗?再如,文艺的内容不能等同于政治,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一些风景诗,咏物诗,爱情诗,知识小品,科学文艺……,它们的艺术内容都不能等同于政治,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性。再加上一些对《讲话》中有关批评标准的片面理解和执行,任意开展文艺思想斗争,于是从新中国成立起,在文艺领域内出现了一系列的冤错假案。“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从上可见,在批评标准问题上,我们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我国进入新时期后,在批评标准问题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近,上海《文学报》总编辑陈歆耕,在2014年6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批评也是明亮的阳光》中告诉大家,该报《新批评》专刊在批评标准问题上“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概括为‘真诚、善意、锐利’。”它们可以说是“新批评”专刊提倡的批评标准。这一批评标准能否为大多数作家、批评家所践行,还有待今后创作和批评实践的检验。但至少它在批评标准问题上是新的一家之言。
〔后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阅并采用了亡友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二版)中的若干资讯,特此说明,并以此文表示我对敏泽兄的怀念。
〔责任编辑:陈济平〕
I022
A
1003-6873(2015)03-0038-04
2015-04-08
陈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3.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