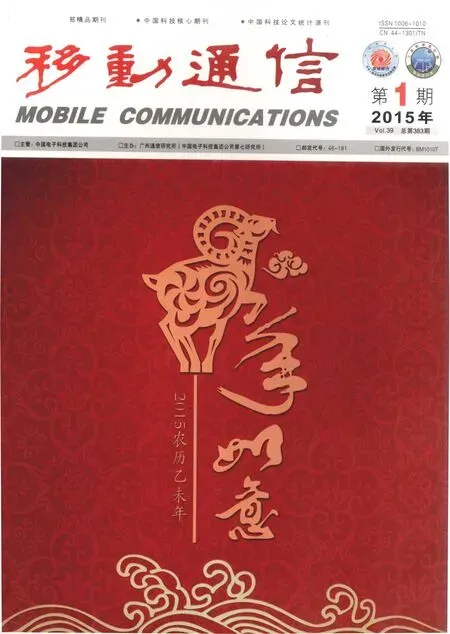TD-SCDMA发展、移动网演进及技术的国际化探讨
1 引言
我国TD-LTE牌照发放已逾一年,中国移动已建成70万TD-LTE基站、发展LTE用户5 000万;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先后在56个城市开启TD-LTE/LTE FDD混合试验网建设及试验网放号。特别地,近期关于我国TD-SCDMA网络的未来和成败讨论一时热烈,引发笔者思考,在此与同行探讨相关的网络演进问题。
2 TD-SCDMA等3G系统退出及网络演 进分析
我国3G和LTE网络建设均滞后于通信发达国家,这与我国通信业及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有关。欧美、日本、韩国的一些主流运营商在其3G网络运营阶段停止建设2G网络,乃至停止接纳2G用户,甚至最终关闭2G网络,改以新建的3G及LTE网络承接服务。从而也衍生出将2G的GSM/CDMA频段重耕(Refarming)用作3G(UMTS)和LTE技术的情况。2014年中也有报道显示中国移动将“停止投资2G业务”,类似地,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对其GSM和CDMA网络也均以优化为主,不再是建设和发展的重心。我国早已在移动用户规模上跃居世界移动通信第一大国。而“大”之外,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靠采购、应用国外设备商的产品和技术服务来运营和发展,不仅缺乏国际技术领域的话语权,而且因在系统采购的技术和商务谈判中更多的是在不同设备商中做比选,技术壁垒之外同时承载的是发达国家水准的研发制造成本。拥有近二十年运营经验和庞大的用户规模之时,提出新的标准制式、创建新制式网络是自然之事,相反,安于只利用引进技术获利倒是中国通信人应该惭愧的。创新的思想不应被压制,有实现能力的创新更应该被鼓励和扶持。
新一代网络具备更高的频谱效率、更好的性价比,旧一代的退出就是必然的趋势。而GSM/CDMA系统原先占用的较低频段的频谱资源还可以被重用,这点对缓解频谱资源紧张以及增强系统覆盖性能都有帮助。
同理,TD-SCDMA以及CDMA2000、WCDMA系统也终究有停建、退网的一天,不在LTE阶段就在5G或以后。
然而,从停建到最终退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可能将经历漫长的周期。
首先,网络停止建设只是表示现阶段规模和品质可以满足用户市场需求,并不意味着弃用。运营商在不同的阶段出于对现网利用率和发展策略的考虑,建设工程量消长是很正常的,甚至停止建设也不等于不发展用户。2014年7月底,中国移动的3G用户累计达到2.41亿;TD-SCDMA网络还将需要承载现有和未来新增的3G用户以及4G用户通过互操作回落到3G网络时的业务接续,同时还将长期维护和优化;在LTE网络建设过程中,与TD-SCDMA、GSM和Wi-Fi网络的共享共建、协同覆盖、干扰协调、互操作优化、业务负荷分担等也将是持续的多系统配合建设运营工作。
对于3G用户统计口径的歧义,现实用户的使用行为多样,目前终端成熟度的影响已很有限,更多取决于资费和用户习惯;主观不使用3G网络的用户往往也不使用2G数据业务。这点与是何种网络制式并无必然关系。
其次,网络演进更迭的策略因境而异。VoLTE进入大规模商用还有待时日,在此之前仍需要通过2G或3G网络承载移动网的话音业务;此外,前代的网络在长期经营中通常覆盖更完善,用户在LTE覆盖不良及无覆盖区域也转由2G/3G网络接续数据业务,并且运营商可以设置接入优先级和负荷分担策略以充分、合理地使用各系统资源;而用户手机卡和终端全部更换为支持LTE的状态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此前网络需保证大量2G/3G用户的业务使用。更早部署LTE网络的海外运营商在Refarming利旧原有网络频谱资源时,多有采用GL(GSM/LTE)做重耕的,也有保留GSM承载老用户业务、做UL(UMTS/LTE)重耕的。对于中国移动,以2014年7月底的数据,总用户7.94亿中3G/4G总数为2.61亿户,2G用户占近七成;而GSM制式全球普遍通用,对国际漫入漫出行为支持度好;TD-SCDMA基站更容易改造升级为TD-LTE基站。因而如果选择GSM作为LTE的首选辅助承载也很自然。但如果要TD-SCDMA系统完全卸载,需要TDLTE网络建设足够完善,这里的“足够完善”包括覆盖能力与TD-SCDMA相当,并且在容量性能上能足以分流TDS系统承载的数据量。在此之前,还应充分利用已建TDS的网络能力,保障好非LTE的3G用户数据业务并合理调度分流TDL负荷,提高多网整体利用率。
技术的生存和退出更多与产业环境相关。CDMA/CDMA2000技术在全球的应用相比GSM和WCDMA规模小、生命周期也短很多,但不能简单否认其技术先进性的一面。中国电信的CDMA2000-LTE共存演进中的难题也是源于CDMA产业阵营的大背景影响。此外,3种同代的3G技术制式本身各有特点,而现实网络中的使用感受(QoE)还跟网络配置、部署、优化甚至配套等环节紧密相关,诸如站点规划合理性、天馈等器件品质、设计施工水平、有线承载网能力等均会影响网络品质。除技术体制本身、建设运营能力差异之外,影响最大的还是产业链成熟度,而“成熟”与“创新”本就是一对矛盾。
最后,一个系统的下线最终还要取决于终端用户。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普遍服务的运营商,要顾及各地域、各阶层的用户,引导用户购买支持3G/LTE等新制式的终端、更换手机卡,将业务迁移至下一代网络。这又必然与用户的消费能力、使用习惯有关。如我国小灵通业务,工信部早在2009年初就通知要求2011年底前完成清频退网,实则至今仍未彻底关闭;国际先进运营商AT&T两年前公布计划于2017年前关闭其GSM网并“促使”用户升级手机,澳大利亚电信也计划在2016年底关闭GSM。面对中国移动庞大的2G用户群,这一迁移过程预计将很漫长。但目前升级终端的用户会同时具备3G和LTE功能,于是TDSCDMA系统的可替代性显得更强,其话音和数据业务可分别由GSM和TDL承载。
对2 G/3 G 用户的迁移,富通信或融合通信(RCS)将发挥推动作用,使不习惯使用数据智能业务的用户将其话音、消息类通信无痕地转移到RCS的数据通信中,并降低用户的通信消费。而GSM/TDSCDMA电路域业务的最终退出还有赖VoLTE的成熟。
3 TD式创新的意义和展望
我国早已在移动用户规模上跃居世界移动通信第一大国。而“大”之外,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靠采购、应用国外设备商的产品和技术服务来运营和发展,不仅缺乏国际技术领域的话语权,而且因在系统采购的技术和商务谈判中更多的是在不同设备商中做比选,技术壁垒之外同时承载的是发达国家水准的研发制造成本。拥有近二十年运营经验和庞大的用户规模之时,提出新的标准制式、创建新制式网络是自然之事,相反,安于只利用引进技术获利倒是中国通信人应该惭愧的。创新的思想不应被压制,有实现能力的创新更应该被鼓励和扶持。
所以,现在所谈的“技术中立”不是纯粹技术理论的优劣,而应该是产业的成熟度或者是直接获利能力的难易。而这个“利益”的评判不应只是某个企业某几年的经营指标,而应该立足于国家乃至全球格局的产业发展,各尽其力、各得其所。所谓“公平”,不应把中国永远定位在低技术、劳力密集和资源输出状态。在TD-SCDMA的研制和网络建设中,研究机构、运营商和设备商密切合作、共同推进系统上线和优化,各方在标准参与、研制工艺和运营技术等方面都有显著提升,主设备、芯片、终端等一批国有厂家受到带动,研究机构为后续LTE、LTE-A和5G的国际标准制定参与积累了经验;中国移动深度参与了产业成熟的过程,近乎定制化地推进产品实现,提高了在移动通信领域技术引领和在设备市场的驾驭能力,拉近了与Vodafone、DoCoMo、AT&T等一流运营商的差距。如小区合并、多小区联合检测优化技术等TDS领域的创新技术值得肯定,并且有些技术也为同时代其他制式所借鉴应用。
回看TDS的发展历程,应该抱以更大的胸怀和自信。中国拥有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市场本身就是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技术能在中国市场中成功运用对国际市场会有重大影响,不必苛求在国外推广了多少这样的国际效应,不应把中国排除在全球之外。同样在标准制定环节,为了纳入3GPP标准,TDS和TDL都做了让步改写、牺牲技术性能的准备,标准国际化的道路颇显艰辛。除了“国际化”的身份,应该更多是出于争取和共享产业界先进设备商、芯片商等的研究和开发能力;而不可回避的,产业成长在我国与政府决策和管理机制息息相关,决策的犹疑、拖延增大了产业链各环节投入的风险,对央企运营商的经营考核以及全制式的牌照发放又造成紧张的竞争环境,如此会降低自主研发的动力,增加了难度,使将更多依赖于寻求底层技术的国际支持。中国也可以有基于自主的国际化的标准组织,开放欢迎全球同行加盟,但不必苛求其他某个标准组织的接纳,尤其是受地域和阵营影响更多的组织。ITU本身也接受以国家政府名义提出的技术方案,而且根本上是否被ITU采纳也不绝对影响某项技术在国内的执行;如果在国内运行成功、有优势,也自然会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来效仿、采用,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
最后,中国从3G时代开始,在LTE、LTE-A、5G研发领域的话语权将越来加重,中国企业对国际的影响力一步步加大,其中TD-SCDMA技术的提出、研制和建网运营实证了中国的技术实力,打造了中国通信品牌的可信度。同时,TD-SCDMA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和竞争经济潮流中也承担了忍辱负重的角色。寄望以后的通信界保持创造力和责任感、政府以更大的格局观念来掌舵——加大扶持并优化科研和企业管理,使中国早日从移动通信大国进化到移动通信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