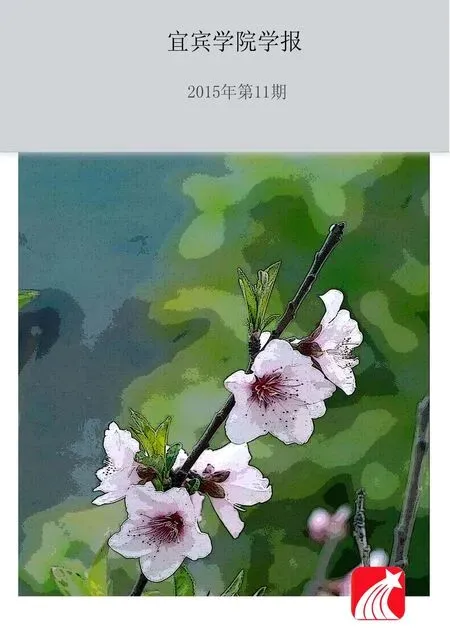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法律适用及其司法技术
朱 政,林 斌
(1.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湖北恩施445000;2.恩施市咸丰县检察院,湖北恩施445600)
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法律适用及其司法技术
朱政1,林斌2
(1.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湖北恩施445000;2.恩施市咸丰县检察院,湖北恩施445600)
摘要:关于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既有研究大多停留在论证基本概念、价值、可能性与限度等基础理论问题上,对司法技术的开发研究较少。在法律推理的理论进路中,少数民族民俗习惯可被认为是一类特殊的法律论述形式,作用在于连接法律推理的链条。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推理(论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形式,另一部分是一组批判性问题。对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推理的司法技术的开发,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民俗习惯;论述形式;法律推理;司法技术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深入,法律学术界与实务界渐渐意识到,西方现代性的法律解决方案无法一揽子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而,法律“地方性知识”的属性得到肯认,法律多元逐渐成为共识。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民俗习惯这类民间规范,人们也不再简单粗暴地弃之如敝履,而是尽力挖掘“本土资源”,试图利用它来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然而,司法实践中适用少数民族民俗习惯,依然高度依赖于法官的取舍,随意性很大。这表明,精致的司法技术才是关键之处,能够促成民间规范转化为个案正义。
一问题的提出:回顾与反思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习惯法、民间法、民俗习惯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众多的研究者运用不同的理论资源,遵循不同的理论径路,不断探索,成果可观。本文将在回顾与反思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为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探寻新的路径。
(一)既有研究及其缺陷
近年来,学界对民间规范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产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但总体上,还停留在论证基本概念、价值、可能性与限度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而深入开发具体适用方法的论著,还不多见。这也反映出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偏好玄思,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作为特殊类型的少数民族民俗习惯问题,则更是受到冷落,无人关注。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习惯法、民间法、民俗习惯等司法适用的概括分析,代表性作品有公丕祥教授主编的《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理论与实践》,张晓萍所著《论民间法的司法运用》,这一类著作大多面面俱到,但遗憾的是在法律方法的运用问题上点到为止,缺乏深入;第二,论证其法源地位,如王林敏所著《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这类研究是该论题域的主体之一,亦即将习惯法、民间法、民俗习惯等作为非正式法源看待,强调其在司法适用中作为正式法源补充地位的重要性;第三,将民间规范的司法适用视为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手段,如贾焕银所著《民间规范的司法运用:基于漏洞补充与民间规范关联性的分析》;第四,讨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习惯权利的著作,有少许内容提及司法保护问题,如高其才所著《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多元司法》,田艳所著《少数民族习惯权利研究》,等等。此外,西方学者对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讨论,多采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进路,如吉尔兹、Frank K. Upham等,从法律方法论角度进行深入探讨的亦很少见。
虽然,既有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的复杂性,但缺陷也很显见。它们都将主要精力放在论证民间规范司法适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上,而很少深入开发具体的司法技术,更缺乏对真实案例的考察。当然,应当承认,民间规范的非正式法源论和漏洞补充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国内学界的普遍共识。但这还不够,尚未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等民间规范在司法适用中的潜力与作用。
(二)理论进路
司法裁判是法律方法的体系化运用,法律推理是其核心内容。诚如美国学者伯顿所言,“法律推理就是在法律争辩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1]1可以将这个过程理解为法律推理链条在法庭辩论中“正向推进”,以及面对裁判结果的“逆向重构”①。因而,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将法律解释、法律修辞和法律论证等具体方法,置于推进或重构法律推理链条的意义上理解,将它们看作不同种类的论述形式(或称论证图示,argument scheme),发挥各自说理或说服的功能。这样,少数民族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类特殊的法律论述形式,其作用在于连接法律推理链条。如此处理,与既有研究,尤其是将其视为非正式法源和漏洞补充方法的相关理论,不但不冲突,而且能够很好地融合。具体来说,本文试图将具有弥散性特点的少数民族民俗习惯(习惯权利)转化为一类或几类特殊的法律论述形式。它的用途在于,作为一种探索工具,连接法律推理链条,完成佩岑尼克所谓的法律论述的“跳跃”(jump)。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强其在司法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大胆设想是否可能针对少数民族民俗习惯这一类特殊的法律论述形式,开发一套简明的“批判性问题”,形成一套标准情势下的问答“指南”,进而防止错误适用,发生“谬误”。
二少数民族民俗习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律论述形式
一如上述,将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运用置于法律推理的视阈下,其意图在于有针对性地进行司法技术的开发。然而,这里仍有两个前提性问题亟需澄清:一是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述形式的关系,二是法律论述形式的内涵与构造。换句话说,只有处理好这两个问题,才有望获得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推理(论证)的具体方法。
(一)法律推理与论述形式的关系
法律推理在纯粹形式方面,例如内部证立的涵摄形式,主要着眼于推理链条的重构。而在动态视角下,所谓推理其实是在每个分歧的“节点”上展开争论,获得局部结论,进而不断推导向前的过程。质言之,推理的重点在于,基本涵摄形式中间所插入的步骤如何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裁判具有论题学取向的(topoi-oriented)维度:“它是一门问题定向的思维技术。”[2]26
在描述性视角下,论述形式(论证图示)就是面向“争点”的论辩方式或技术。在规范性视角下,它的作用是联接、阐明或重构推理链条,完成“跳跃”。因而,诸多我们所熟识的具体方法,都可以如此理解。例如法律修辞,佩雷尔曼在《新修辞学》中最先以法文使用论证图式这一术语(schème argumentatif、schèmes d’arguments),意指各种说服性的论辩技术。《新修辞学》一书大约四分之三的篇幅(第三部分)都在讨论两大类论证技术(论证图式)的问题,亦即:结意法,准逻辑论证方法(quasi-logical arguments)、基于实在结构论证方法(argument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reality)和建立实在结构关系之论证方法(the relations establishing the structure of reality);离析法(the dissociation of concepts)。[3]185再如法律解释,麦考密克和萨默斯在《制定法解释:一个比较研究》中提出的解释论述即为一种论述形式。在阿列克西那里,法律解释是最重要的一组外部证成的论述形式。诚如卢勃列夫斯基使用的“操作解释”(operative interpretation)的概念,“‘操作解释’被嵌入法律论证,而作为一种实践推理的形式,目的是对法律裁决的证立。”[4]21此外,法律论证的方法就更是这样。当代的法律论证理论,不论是阿列克西的程序性论证理论,荷兰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语用论辩术”(pragma-dialectics),还是沃尔顿的“新论辩术”(new dialectic),都在不同侧面阐述了论证形式的功能及其重要性。
上述思路的确拓展了民间规范司法适用研究的视野。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少数民族民俗习惯在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作用很大,它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法源引入;可以与法律解释的方法结合,解释制定法的条款;可以作为正当性理由或地方共识,进行论证和增强裁判的说理,等等。然而,既有研究大多意在阐述这样一个“可能性”的道理,未将重点放在司法技术的开发上。因此,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依然高度依赖基层法官的认知与修养,更多时候并未充分发挥出它的司法功能和潜力。
(二)法律论述形式
显而易见,将少数民族民俗习惯视为一种法律论述形式,事实上就是将其定位为法律推理中遭遇相关“争点”的解决资源。这样,也就要求面对“争点”搭建法律论辩的平台,以容纳更细致的司法技术。
加拿大逻辑学家沃尔顿提出的“新论辩术”(new dialectic)非常成功地刻画了“对话”的交互框架,并在一个“说服型对话”的主体中,区别出其他多种对话类型,容纳了多种论证形式与技术,并针对性地对它们给出运用和评价的方法。“新论辩术”是建立在一种似真推理框架之上的。“似真推理既不同于演绎推理也不同于归纳推理(现代意义上的概率推理)。” 似真论证(plausible argument)是第三种类型的推理。“似真推论的特征是:如果前提真,则结论似然为真。但是似真推论是可废止的,因为大前提中的概括从本质上说是有例外的,而且这种例外是不能事先考虑到的。似真推论是非单调的,这意味着它能被新引入的前提所推翻。”[5]111正是如此,在评估论证上,似真论证与演绎论证、归纳论证也不同。在传统逻辑学中很多谬误的论证形式,在似真论证中却是合理的。在著作《法律论证与证据》(LegalArgumentationandEvidence)中,沃尔顿考察了法律论证的一般形式②(许多形式就是佩雷尔曼和奥尔布莱希特-提泰卡在《新修辞学》中识别和开发出来的)。这些论证的一般形式,被沃尔顿称作论证图式。与本文所称的法律论述形式是同一回事。术语上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本文的理论进路并不限于法律论证,而着眼于法律推理这样一个兼具“适用”与“论证”的动态过程③。每一种论述形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形式,另一部分是一组批判性问题。
诉诸专家意见论证[5]50-52的基本形式是:
大前提:证据来源E是包含命题A的主题领域S里的一名专家。
小前提:E断定命题A为真(假)。
结论:A为真(假)。
六个基本的批判性问题:
专业问题:作为专家证据来源E有多可信?
领域问题:E是A所在领域里的专家吗?
观点问题:E断言了什么意味着A?
可信赖性问题:作为一个证据来源E本身可信赖吗?
一致性问题:A与其他专家所断言的一致吗?
支持证据问题:E的断言是基于证据提出的吗?
也就是说,相对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似真推理不仅关乎推理形式(form)问题,还关乎对话的语境与对话的参与者。由此可知,新论辩术是一种建立在“对话”框架上的论证理论。诚如熊明辉所言,“新论辩术是把论证置于(说服性对话)对话语境,根据对话目的来进行分析与评价的艺术。”[6]201
三增强实践可操作性:司法技术的开发
笔者利用新论辩术、语用论辩术等理论资源,尝试对法律推理中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这一类特殊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发司法技术。当然,这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得出终局性的结论,毋宁说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最终司法技术的完善需要回到司法实践中予以检验。诚如阿列克西所言,“这些分析研究必将通过对司法裁判行为的经验考察来予以补充。”[7]35
(一)基本形式
沃尔顿在著作《法律论证与证据》中开发出多种法律论证的一般形式,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基本形式,例如上文提到的诉诸专家意见论证。但这种基本形式看上去非常简单,与形式逻辑相差甚远。一方面,这些基本形式,不论是解释规准,还是修辞技术,都具备一定的“形式”。“非形式逻辑不是不讲‘形式’的,不是没有‘形式’的,不过这种‘形式’和形式逻辑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8]另一方面,在形式结构上,它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重要的可能是,结合论辩规则开发出面对不同论述形式的批判性问题(目录),增强各类论述形式之运用的可操作性以及为评估论辩是否发生谬误提供指南。阿列克西适切地指出,在论证的规则和形式两者间,前者是更为根本的。“商谈理论可以完全通过规则表述出来,因为这一理论并不包含对个体的特殊规定。出于简化的理由,在规则之外表述论述形式 (Argumentformen)是合乎目的的。将(论述)形式转换为规则(它允许或规定使用特定形式的论据)在技术上不会产生任何困难。”[9]91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司法裁判中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推理(论证),其基本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模仿沃尔顿建构一套结构形式。例如:
大前提: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果情形与民俗习惯R相吻合,那么,在该种情况下应该依据R做出决定。
小前提:这个情形与民俗习惯R相吻合。
结论:(1)在这种情形下应该依据R所规定的来做出决定;
(2)在这种情形下该做出符合R的解释
……
显然,上述基本形式不能解说什么是“特定条件”,可能也无法穷尽民俗习惯与其他具体方法的结合方式。因而,仅有基本形式,还远远不够。
(二)批判性问题
根据沃尔顿的“新论辩术”,可以认为法律论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形式,另一部分是一组批判性问题。这种构想不但不会简化法律推理,反而增加了其复杂程度。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典范”的意义上,对应于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论证的批判性问题还是值得深入研究。这里的“典范”意指,它仅能够形成一套标准情势下的问答“指南”,不应将其设想为一个过于复杂和庞大的体系。但可以初步认为,批判性问题一方面与其基本形式相对应,具有形式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与论辩负担、论辩转换相关联,又具有表达论辩规则的意义。因而,突显其重要性。
关于法律论辩规则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是阿列克西的程序性论证理论和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语用论辩术”。阿列克西在普遍实践论辩的一般理论中和法律论证理论中,提出了一套法律论辩的规则与形式。埃默伦指出,批判性讨论有四个阶段:冲突阶段、开始阶段、论辩阶段和结束阶段。在冲突阶段,论辩双方确定他们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在开始阶段,论辩双方都试图消除意见分歧。他们分配了角色:谁是正方,谁是反方。他们就讨论规则以及讨论的出发点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论辩阶段,正方通过提出论证来应对反方的异议或打消反方的疑虑,为他的立场作辩护。在结束阶段,论辩双方评估意见分歧消除的程度,确定论辩结果支持哪一方。④在这个过程中,论辩规则即论辩者的行为准则。
不难看出,批判性问题既是对基本形式结构的展开,同时又是将论辩规则化约为一份简单的目录。针对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论证,可以设想如下问题:
问题1:(少数民族民俗习惯)R,真实存在吗?
问题2:R,有拘束力吗?是否为当地大多数人认可?
问题3:有制定法的条款,与民俗习惯R相关吗?
问题4:民俗习惯R,与制定法冲突吗?
问题5:R规定了什么,以及是否R需要进一步解释?
问题6:当前情形实际上与R所规定的情形相吻合吗?
问题7:是否根据R对制定法进行解释,能够获得新的意义?
问题8:R与相关规则相竞争,哪一方能更好地适合当下的情形?
……
这份问题目录是不完整的,因为这项具有司法实践意义的课业,需要大量原始素材的积累,需要在司法裁判工作中不断摸索与总结。本文只是提出一个设想。诚如萨尔托尔所言,这是一类大部分未经检验的研究课题:“关注孤立的语言行为的以程序为基础的法律争论图式如何与整体评价相竞争的观点的以融贯为基础的法律推理图式结合在一起。”[10]360
注释:
① 相关论述参见朱政《法律适用的理论重构与中国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另可参见朱政《重述法律推理》,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② 沃尔顿共讨论了十类法律论证的形式:诉诸类比论证、诉诸既定规则论证、诉诸征兆论证和回溯论证、诉诸从位置到知道论证、诉诸言辞分类论证、诉诸承诺论证、实践推理、诉诸人身攻击论证、滑坡论证和其他重要的论证。参见[加]道格拉斯·沃尔顿《法律论证与证据》,梁庆寅、熊明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73页。
③法律论辩的展开极为复杂,它表现为一种事先难以预料的论证链条。因而,它更适于在事后进行理性重构和评价。在这一点上,它表现出“论证”的性格。法律推理的各类前提,既包括法律规范又包括法律事实,正是通过两者的论辩逐渐形成,或者说从各自的主张(诉讼要求)开始,在对方的质疑中不断展开,每一个法律论述的“跳跃”都置于各方(尤其是法官)的检视之下。如此,从前提一步步导向最终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它又表现出“适用”的性格。参见朱政《法律适用的理论重构与中国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参见[荷]弗兰斯·凡·爱默伦、斯诺克·汉克曼斯《论辩:通向批判性思维之路》,熊明辉、赵艺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页。
参考文献:
[1] [美]史蒂夫·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M].解兴权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 [德]菲韦格.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M].舒国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 CH.Perelman and L.Olbrechts-Tyteca, 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M].John Wilkinson and Purcell Weaver (trans.).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
[4] MacCormik,D Neil and Summers,Robert S(eds.). Interpreting Statutes, A Comparative Study[M]. Aldershot: Do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 1991.
[5][加]道格拉斯·沃尔顿.法律论证与证据[M].梁庆寅,熊明辉,等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6]熊明辉.诉讼论证:诉讼博弈的逻辑分析[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7][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M].舒国滢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8]李永成.第三类推理是什么?:沃尔顿假设性推理研究述评[J].政法论丛,2009(5):88.
[9][德]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M].朱光,雷磊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10][意]乔瓦尼·萨尔托尔.法律推理:法律的认知路径[M].汪习根,等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许洁〕
O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Folks and Customs
ZHU Zheng1,LIN Bin2
(1.LawSchool,Hube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Enshi445000,Hubei,China;
2.People’sProcuratorateofXianfengCounty,Enshi445600,Hubei,China)
Abstract:The existing studies on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folks and customs mainly stay in 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fundamental concepts, values, possibilities, limitations and so on. In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legal reasoning,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folks and custom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pecial kind of legal argument scheme, which plays the role of mediator connecting to the legal reasoning. The reasoning and argument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folks and customs contain two parts: one is the basic form, and the other is a set of critical issues. Further, it is able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judicial technology and enhance the operability of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Folks and Customs; argument scheme; legal reasoning; judicial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11-0044-06
作者简介:朱政(1980-),男,江苏南京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法律方法论和法社会学研究;林斌(1970-),男,湖北恩施人,主要从事民法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4 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14HBZ008)
收稿日期:201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