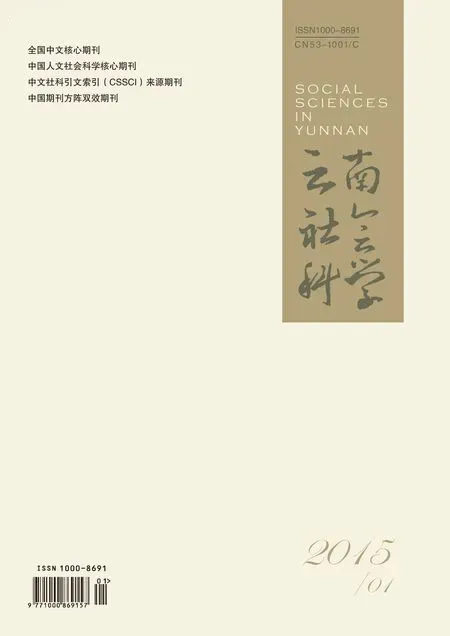明代云南汉文化发展态势与地理格局研究
——以滇人汉文著述为对象的考察
钱秉毅
明代是云南汉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明代,汉文化确立了在云南主导文化的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以汉字书写、运用汉文语法著述的文献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滇人汉文著述比前面任何时代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呈现飞跃发展、繁荣兴盛的局面。但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与区域范围内也存在不同的发展特点。滇人汉文著述在云南发展的过程,正是明代云南汉文化影响不断加大,并最终确立其主导文化地位的过程,其在时间及地域分布方面的变化,是汉文化在云南动态发展的直观体现,反映出明代云南汉文化发展的阶段态势与地域格局变化。
一、明代滇人汉文著述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从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进入云南,到永历十五年(1661)南明永历政权在云南覆亡的280年间,共产生了622部*数据统计依据及来源见拙著《明代滇人著述书目》,载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11》,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由云南籍的文人学士用汉文撰著的典籍文献。 622部滇人汉文著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发展特点。本文以文献作者主要生活的年代作为其著述的产生年代,基本按明代年号50年一断,280年分为6个时段进行统计分析。
第一阶段,从1381~1435年共54年,涵盖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5朝,滇人汉文著述数量为27部。
第二阶段,从1436~1487年共52年,涵盖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4朝,滇人汉文著述数量为59部(包括不知明确修纂年代,只考订出最晚修于正统的方志11部,最晚修于天顺的方志13部)。
第三阶段,从1488~1521年共34年,涵盖弘治、正德2朝,滇人汉文著述数量为72部(包括考订得知最晚修于正德的方志12部)。
第四阶段,从1522~1572年共51年,涵盖嘉靖、隆庆2朝,滇人汉文著述数量为148部,(包括不知明确修纂年代,只知成于嘉靖的文献2部)。
第五阶段,从1573~1619年共47年,即万历1朝,滇人汉文著述数量为115部(包括万历《云南通志》中收录不知确切年代的文献3种,考订最晚修于万历的方志1部)。
第六阶段,从1620~1661年共42年,涵盖泰昌、天启、崇祯、永历4朝,滇人汉文著述数量为181部(包括崇祯前3部,明季遗民著述的文献78部)。
此外,还有时代不明、无法纳入统计的著述20部。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6个时段呈现明显的阶梯状上升趋势,上升最为明显的是正统至成化和嘉庆至隆庆两个阶段,洪武至宣德年间仅有27种滇人著述,其后的正统至成化间上升至59种,弘治、正德间为72种,嘉庆至隆庆间跃升至148种,都实现了翻倍的增长,而泰昌至永历间181种滇人著述则达到了滇人著述数量的最高峰。
明代前期,明军平定云南以后,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在推行流官统治的郡县制度的同时,针对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的实际状况,完善土司制度,精心构建严密的统治体系。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建设开发,如大军驻守屯田,大量迁徙内地汉族进入云南,开发山区等。洪武至宣德间出现的27部滇人汉文著述,正是明朝初期云南文化经营与建设的反映。
明正统朝至成化年间,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历经繁衍生息,正统年间云南的汉族人口数量比之洪武年间增长了近三倍[1](P268),屯军的粮食生产也实现了自给有余[2](P258)。在正统、景泰、成化、弘治、正德朝云南均有府州县儒学设立。总体来说,这一阶段,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保持了一种持续发展的态势。在基本物质条件得到保障,文化教育建设累积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滇人汉文著述增加到了52部,比洪武到宣德的50年间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是明代经济、思想、文化空前兴旺发达的时代。其时的云南,社会相对较安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因水利工程的兴修得到很大改善,嘉靖时期粮食产量增长明显,在自给之余还可略有输出[2](P260)。在基本物质条件得到保障后,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也掀起了高潮。在嘉靖至万历时期,云南各地的儒学不断增设,负责童蒙教育的社学卫学达160余处[1](P431),各地还建立了五华、云峰、凤仪等书院20余所,培养出了大量能熟练运用汉语著书立说的文人学士。从洪武到万历200余年间,通过兴教办学、屯田定居等措施,云南的社会结构、民族构成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多夷少的局面形成,同时士绅阶层兴起,成为引领云南各地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物质、文化与人才储备这些基本条件具备之后,云南汉文化开始飞跃发展,其典型反映便是在嘉靖、隆庆阶段,滇人汉文著述数量飙升到148种,其后在万历年间略有回落。笔者认为,嘉靖、隆庆时期滇人著述大量涌现与当时杨慎长期谪戍云南有很大关系。杨慎以其卓越的学识与巨大的声望,吸引了为数众多的云南学士与其交游唱和,他鼓励云南学者出版著作,多次亲自修订和推荐云南学者的著作,极大地促进了滇人汉文著述的发展。因此嘉靖朝滇人著述集中涌现,并高于万历朝。嘉靖至万历时间不足百年,在整个明代历史中只占到了1/3多一点,而两个阶段共261种著述,却占到了明代所有滇人汉文著述的40%以上。明代滇人汉文著述的发展,在嘉靖、万历时期呈现出兴盛繁荣的局面。
明末云南发生了持续多年的沙普之乱,对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泰昌、天启、崇祯、永历四朝40余年云南的汉文典籍数量却高达176种,似与时局发展相矛盾。但细究却也有其缘由。云南动乱远不及北方、江南惨烈,永历帝驻滇时间虽短,但有大量来自文化发达地区的文人跟从,在云南还举行了科举考试,促进了云南文化的发展。在永历覆亡以后,一大批云南学士不愿仕清,或隐居、或出家。《明季滇南遗民录》[3]所收有93人,而其中很多人著书立说时间实际是在清初。在明末这一阶段的181种滇人汉文著述中,就包含了明遗民的著述78部。相当数量实际成书于清朝初年的滇人汉文著述被纳入明末来统计,因此,明末最后40余年的滇人汉文著述数量才会较高。
明代云南滇人汉文著述表现出的阶梯状发展特点,不同阶段虽然增长幅度不一,但基本是一种上升的势头。反映出汉文化在云南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从明初开始奠定基础,正德至成化年间势头强劲,在嘉靖朝形成了一个高峰,万历年间维持了高水平的发展,而明末的战乱并未能影响汉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趋势,汉文化成为云南主导文化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二、明代滇人汉文著述的地域分布格局
明代滇人汉文著述在云南的不同地区,其地域分布状态存在巨大的差异。622部明代滇人著述中有507部为个人撰著文献,115部为方志。个人撰著文献将根据作者的籍贯进行地域的划分,进而进行文献地域分布的分析。而方志的作者大多署名为当时的地方长官,并不是实际的编纂人,简单依照作者籍贯统计,则难免混乱,失之准确。因此,对115部方志将按其归属地作地域统计。
明代云南省有府19、御夷府2、州40、御夷州3、县30、宣慰司8、宣抚司4、安抚司5、长官司33、御夷长官司2[4](卷46《地理志·云南》,P1171)。507部滇人汉文著述,根据作者的籍贯,其地域分布如下:
云南府有著述143部,约占到507部的28%。其中昆明47部,安宁州27部,晋宁州21部,嵩明州15部,呈贡10部,禄丰10部,广南卫3部*都司卫所辖地不是各府所属区划,本文为准确反映典籍的地域性,将都司卫所人士著录的典籍纳入所在府的地域范围内统计,如广南卫在永乐后驻于昆明东部,因此纳入云南府统计。,云南后卫2部,昆阳州2部,罗次2部,宜良1部,归化1部,云南右卫1部,1部无法细辨属于云南府何地。
大理府有著述90部,所占比例为17%。其中太和33部,云南县22部,浪穹14部,宾川州10部,邓川州5部,赵州1部,剩余5部无法细辨。
临安府有著述87部,所占比例与大理同为17%。建水州31部,石屏州20部,通海11部,宁州6部,蒙自5部,阿迷州4部,临安卫3部,河西3部,剩余4部无法细辨。
永昌府有著述55部,占11%。其中保山28部,腾冲卫6部,腾越州5部,永昌卫3部,金齿司2部,永平1部,剩余10部无法细辨。
鹤庆府有著述30部,占6%。其中剑川州16部,其余13部无法细辨。
楚雄府有著述24部,占5%。其中楚雄12部,定远8部,镇南州3部,南安州1部。
曲靖府有著述23部,与楚雄府同样占5%。其中南宁12部,马龙州6部,陆凉州4部,剩余1部无法细辨。
丽江府有著述14部,占3%。
姚安府有典籍12部,占2%。其中大姚3部、姚州3部,剩余6部无法细辨。
蒙化府有著述12部,占2%。
澂江府有著述9部,其比例也为2%。其中新兴州5部,剩余4部无法细辨。
广西府有著述4部,所占比例为0.8%。弥勒州1部,师宗州1部,剩余2部无法细辨。
北胜州*《明史》卷四十六《地理志·云南》:“北胜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布政司,寻降为州,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正统七年九月直隶布政司。弘治九年徙治澜沧卫城。”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7页。本文将其视为省辖府级政区进行统计。有著述2部,占0.4%。
武定府有著述1部,占0.4%,为和曲州人士所著。
另有地域不明的著述2部,占0.4%。
根据以上不同地区著述的数量和所占的比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等次:
1.云南府为分布密集区,著述数量过百,所占比例为28%,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
2.大理、临安、永昌3府为分布次密集区,著述数量在50~100部之间,所占比例在10~20%之间。其下又可分为两个亚区:其一为大理、临安两府,著述数量接近100,所占比例接近20%;其二为永昌府,著述数量突破50,比例超过10%。
3.鹤庆、楚雄、曲靖、丽江、姚安、蒙化、澂江7府为一般分布区,著述数量在10~30部之间,所占比例处于2~6%之间。也可分为两个亚区,其一为鹤庆、楚雄、曲靖三府,著述在20~30部之间,所占比例突破5%;其二为丽江、姚安、蒙化、澂江四府,著述量在9~20部之间,比例只占2%、3%左右。
4.广西府、北胜州、武定府为分布稀少区,著述数量不足5部,所占比例不到1%。
5.寻甸、永宁、顺宁、广南、元江、景东、镇沅7府及滇南、滇西诸宣抚、宣慰司为分布空白区,无私人著述的汉文典籍。
从以上5个层次可以看出,明代滇人汉文著述中私人撰著文献的地域性分布差异明显,云南府为全省之冠,大理、临安、永昌3府紧随其后。鹤庆、楚雄、曲靖、丽江、姚安、蒙化、澂江稍次一等,而广西府、北胜州、武定府又次之,寻甸、永宁、顺宁、广南、元江、景东、镇沅7府及滇南、滇西诸宣抚、宣慰司为外围地区,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环形分布态势。
方志方面,明代云南共修纂了115部方志,其中省志9部,府志34部,州志40部,县志18部,司甸志12部,按照其所属地域进行划分与统计。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云南府领州4,领县5,共有15部方志,其中府志1,州志10(4)*前为志书数,括号内为涵盖地区数。如此处为:云南府有10部州志,涵盖云南府4个州。下同。,县志4(4)。
临安府领州5,县5,长官司9,有志书15部,其中府志2,州志7(4),县志5(4)。
大理府领州4,县3,长官司1,方志有12部,其中府志4,州志5(3),县志3(2)。
澂江府领州2,县3,有方志7部。其中府志4,州志1,县志2(2)。
曲靖府领州4,领县2,共有6部方志,其中府志1,州志5(4)。
广西府领州3,方志有5部,其中府志2,州志3(3)。
楚雄府领州2,县5,方志有4部。其中府志2,县志2(2)。
姚安府领州1,县1,方志有4部,其中府志2,州志1,县志1。
武定府领州2,县1。方志有4部,其中府志2,州志1,县志1。
永昌府领州1,县2,安抚司4,长官司3。方志有3部,府志1,州志2(1)。
蒙化府无下属州县,方志有2部,俱为府志。
广南府领州1,方志2部,府志1,州志1。
鹤庆府领州2,方志有2部,州志2(2)。
丽江府领州4,有1部府志。
寻甸府,无下属州县,有1部府志。
元江府领州2,有府志1部。
景东府无下属州县,方志有1部,为府志。
镇沅府领长官司1,方志有1部,为府志。
永宁府领长官司4,有1部府志。
北胜州无下属州县,有1部州志。
顺宁府领州1,有1部府志。
孟定御夷府领安抚司1,有1部府志。
从上文可知,在方志的数量方面,云南21个府级政区可分为3类: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3府都有10部以上的方志;曲靖、澂江、广西、楚雄、姚安、武定、鹤庆7府方志数量在4~9部之间;寻甸、北胜州、永宁、广南、丽江、永昌、蒙化、景东、镇沅、元江、顺宁、孟定12府方志有1~3部。
而从志书体系来看,明代云南的21个府级政区均修有府志,州志方面,43个州有27州修有州志,县志方面,明代云南30个县,有16个县修有县志。具体来说,志书体系完整,府及下辖州、县均有志书的有云南、澂江、大理、临安、姚安、武定6府,广西、广南、鹤庆3府领州而有府志、州志,蒙化、寻甸、景东3府没有下辖州县,有府志,北胜州无下属辖区,有州志;志书体系不完整的有永昌、楚雄、曲靖3府,3府有下辖州县,除府志外,或缺州志、或缺县志;有初级的志书体系的丽江、永宁、元江、镇沅、顺宁、孟定6府,有下辖州县,但仅有府志;无志书体系:孟艮府无志。
由此可以看出,以方志分布地域进行分析,明代云南形成了云南、大理、临安3个发达中心区,志书数量多,志书体系完整;曲靖、鹤庆、楚雄、武定、姚安、澂江、广南为次发达区,数量较发达区少,体系不完整;寻甸、永宁、丽江、蒙化、永昌、北胜州、顺宁、孟定、元江、广南、景东、镇沅为边缘区,有志书,但数量较少,不成体系;滇南、滇西大片外围为空白区,无志书出现。
除府、州、县志外,明代云南还有12种修于天顺之前的司甸志,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马龙他郎甸司,干崖、南甸2宣抚司,者乐甸、纽兀甸2长官司,车里、孟养、缅甸、木邦、老挝、八百大甸6军民宣慰使司12地的方志。方国瑜先生曾有论曰:“明初修一统志,诏天下修郡县志。功令所迫,各府州县当修志书,故明一统志引州郡志27种。有他书未著录,亦有提要称创修于天顺以前者。”[5]以上12部志书应该正是这种情况。而据《明史·土司》载:“天顺末,许土官缴呈勘奏,则威柄渐驰。”[4](卷310《土司》,P7982)天顺以后明代云南再无此类司甸志出现,正是明中后期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边疆问题日趋复杂的表现。地域方面,除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外,其余11地均为土司统治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设置、治理与郡县制下的府州县不同。因此,虽然明初各有1部志书,但无后继发展,再无志书出现。在明中后期,这11地中很多叛服无常,更是扼杀了方志发展的可能*对明代方志的地域分布分析详见笔者文《明代云南方志的历史地理考察》,载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10》,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对私人撰著的滇人著述与方志两部分的地域分析结果来看,虽略有差异,但主要特征基本相同。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为滇人著述汉文典籍最为集中的区域,曲靖、澄江、楚雄、姚安、鹤庆、永昌等府为中间的环形过渡地带,滇人汉文著述分布逐渐稀少,而滇西和滇南的大片区域为滇人著述汉文典籍的空白区域。
据此可以得出明代滇人汉文著述的一个三级分布格局:第一层级为云南、大理、临安三府,为滇人汉文著述的发达地区;第二层级有19府,其中又可分为三个亚区:曲靖、澂江、楚雄、姚安、鹤庆、永昌6府为第一亚区。此亚区紧邻中心发达区,滇人汉文著述较为发达。丽江、北胜、蒙化、武定、广西5府为第二亚区,距离第一级三府距离稍远,发达程度稍次之。第三亚区包括永宁、寻甸、广南、元江、镇沅、景东、顺宁、孟定8府,为第二级的外围,滇人汉文著述发展程度较低。第二层级对第一层级形成了逐层递减的环形包裹态势;第三层级包括里麻司、南甸宣抚司、干崖宣府司、陇川宣抚司、芒市司、湾甸州、镇康州、大侯州、勐缅司、威远州、者乐甸司、新化州、钮兀司、车里宣慰司、孟琏司、孟艮府,为滇人汉文著述的空白区,所在区域全部位于滇西和滇南明代云南的边疆地区。
此分布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特征,第一层为核心地带,以此为中心向外扩散,在第二层中,影响力和发展程度逐渐减弱,到第三层就微乎其微。周振鹤先生曾提出“边疆与内地的圈层型关系”,即在政治地理中存在 “核心区—缓冲区—边疆区”的特征的理论[6]。通过对本身即为边疆省份的云南进行考察,以滇人汉文著述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在省级这样相对较小的区域范围内,在文化地理领域,同样存在核心、缓冲和边缘的圈层关系,文化影响和传播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边界逐步减弱的格局。
三、影响滇人汉文著述发展变迁与分布差异的因素
明代滇人汉文著述的时空差异,与明代云南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息息相关。
1.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云南高山深谷相间,山间坝子星罗棋布。坝区内土地平坦肥沃,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河湖水道纵横,直至今日都是云南人口密集、农业生产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滇人汉文著述分布密集的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境内都有自然条件优越、面积较大的坝子。文献数量较少的永宁、寻甸、广南、元江、镇沅、景东、顺宁、孟定8府及滇人汉文著述空白区的滇南、滇西诸宣抚、宣慰司,这些地区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说,俱是高山峻谷、坝区稀少的区域,在这些地方,相对较差的自然环境限制了人类的活动,文化建设也相对滞后。
2.政治统治的影响。明代的不同时期,对云南不同地区统治力度是不同的,这在滇人著述上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在方志的修纂上反映非常明显。如在晋宁州,明朝廷历次下达修纂志书的诏令俱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而40多个宣抚司、长官司、宣慰使司只有11处修有志书,且全部修于天顺前,其后此类地区便再无志书问世,反映出在天顺后,中央修志的诏令并没有能够得到执行,中央的控制力与滇中区域比较明显薄弱。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说,云南府与大理府居明代滇人汉文著述数量的第一、二名,这与云南府与大理府作为不同历史时期云南的政治中心有必然的联系。从元代开始,云南府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所在,各种资源向其倾斜,对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当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明代之前,南诏大理国政权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前后延绵500余年。与云南府一样,历史上政治中心的地位大大促进了大理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明代滇人汉文著述发展良好的基础。而在一府之内,治所所在地也是滇人汉文著述数量最集中的地方。在有著述的14个府中,有7个府治所所在地生产的文献,达到或超过了全府著述数量的1/3,如云南府昆明、大理府太和、永昌府保山三地的著述数量都占到了全府的一半还多,丽江府的滇人汉文著述甚至全部集中于治所所在地。政治中心地所聚集的各类资源,对一地的区域文化发展作用十分明显。
3.经济发展的因素。经过百余年发展,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增长和进步。滇人汉文著述也在嘉靖、万历时期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明代云南各地的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滇人著述在各地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明代滇人汉文著述分布最为密集、次密集的地方,几乎全是经济发达区域,如滇池流域、洱海盆地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是领先的地区,而滇西、滇北、滇南大片典籍的空白区域,也与其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对应。可见经济条件对于区域文化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4.移民的作用。在明代以前,进入云南的汉人数量很有限,而且逐渐融合到各个民族之中,汉人夷化的趋势明显。随着明政府在云南统治的建立,政府有计划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云南的汉族人口数量,逐渐超过了云南境内其他民族的人口总数,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大量的汉族移民,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文化的发展。如明代中后期云南共有131个千户所建制,滇中地区就集中了39个,与之相应,滇中也是滇人汉文著述数量最多的地区。大理府有20个千户所,仅次于云南府,永昌有17个千户所。临安卫虽然只有5个千户所,数量虽少但集中在建水、石屏一带。三府都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汉族移民区[7]。而滇西南大片区域为瘴气肆虐的地区,在当时并无有效治疗和防治技术的情况下,以农业为基础生计的汉族人口很难迁入当地并立足,因此这一区域的民族构成以各少数民族为主。在这些地方,从物质条件、文化交流、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各方面都还不具备汉文化蓬勃发展的条件,因此滇人著述的汉文典籍数量屈指可数。由此可见,明代汉族移民的密集区,也正是汉文著述数量多的地区。而汉族移民进入较少的区域,相应汉文著述的数量也较少。明代汉族移民的分布与汉文著述的发展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5.学校教育的作用。明代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官一直很重视云南的教育发展,将其视为巩固边疆的重要政策。明太祖及明初镇守云南的官员都很重视学校的建设。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应天府乡试还没有云南人参加,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云南有2人中试。永乐九年(1411)朝廷批准云南布政司独立举行乡试,已有28人中举。云南举额不断增多,举类增加,这意味着接受汉文化教育的云南知识分子的不断增多,具有相当学术修养的知识分子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明代滇人著述大量涌现的基础。另一方面,明代云南不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地滇人汉文著述的发展。如明代云南府有儒学12所、社学34所、书院7所,共计学校53所,有明一代共有进士举人762人[8],学校数量与中举人数均为云南省第一,相应云南府汉文著述的数量也为全省之冠。
6.民风民俗的转变。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并分居于各处,经过数代的繁衍生息,最终形成了汉多夷少、汉夷杂居的局面。民族结构的改变直接导致民风民俗的转变,而这成为云南汉文著述发展的契机。“高皇帝既克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二百年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然惟云南、临安、鹤庆、永昌诸郡四民乐业守法度,子弟颖秀,士大夫多材能尚节义。曲靖、楚雄、姚安、澂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义,人文日益兴起”[9](卷4《俗略》)。良好的社会风气、文化氛围是汉文著述赖以产生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如顺宁府“鲜习文字”,元江府“境内皆百夷,性懦气柔……庠序廖落,社读几废”[10](卷3《地理志·风俗》,P111)。顺宁与元江府在明代除各有一部府志外,再无其他滇人汉文著述传世,可见两地文献的稀少与其地的民风有很大的关系。
7.交通的影响。纵观明代滇人汉文著述的分布,与交通道路的发展密切相关。最为明显的是临安府和永昌府。临安府境内的红河自古便是云南通往越南的主要通道,元明时期红河成为云南锡业贸易的主要运输线。永昌两千年来一直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和物资集散地,云南至印度缅甸的交通线都要经过永昌。交通便捷,信息传递灵敏,使得临安与永昌文化传播与发展较快。临安与永昌一偏滇南,一踞滇西,都不在云南发展的腹心地带,历史上也从未成为过云南的政治中心,但临安以87部文献与大理比肩,永昌以55部著述跻身滇人汉文著述分布的次密集区,可见交通对一地文化发展影响之巨大。
蓝勇先生曾指出:“区域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11]汉文典籍正是汉文化最精粹的因子,本文通过复原滇人汉文著述在明代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及在云南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异,进而探讨明代云南汉文化的发展态势与地理格局。滇人汉文著述在明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阶梯状上升的阶段特征,及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也呈现出的“核心—缓冲—边缘”层级递减的地理格局,是明代云南文化格局发生转变、汉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大最为直观而深刻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