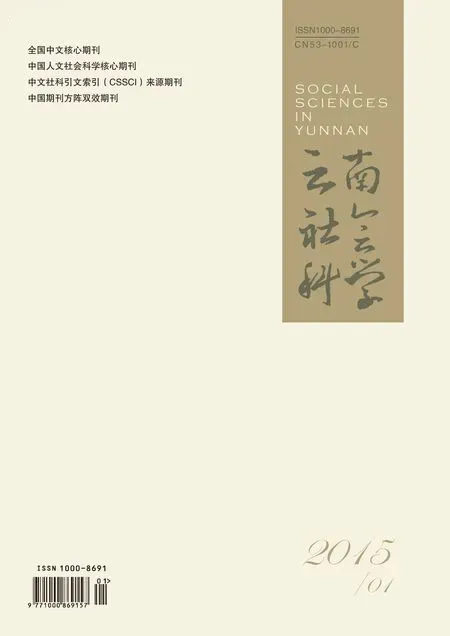现代主体的建构
李东东 赵媛媛
一、现代主体的确立
人作为主体的矗立不是先天确定的,而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不断被怀疑、否定、“掏空”与重构。中世纪,人的主体性开始被神学家推向天国,人作为一个被上帝创造的充实和确定的个体而存在。此时的人类不相信自己的本质力量,认为自身如果离开上帝将是空虚的、无力的,支撑自身存在的东西是灵魂的拯救和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人的自身被认为是不能进行自我决定、自我创造的。但是,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每个人又无需依赖任何外在权威,只要不断向自身内部挖掘,就能使自我成长起来、确立起来,并完成自己所有的目标。应该说,正是这种人的自我的确立给现代主体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准备。正因为这样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这一重要命题中的我思作为认识的确定性根据, 人的自我存在则由知识的确定性来支撑,“这样,‘自我’,人类主体性,就被说明为思想的中心”[1](P876)。因此,自笛卡尔、霍布斯尤其是康德以来,把个体化的人作为理性的依存体,人与主体逐渐统一,并履行主体的职责、承担主体的职能。康德曾经说过:“在全部被造物之中,人所愿欲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东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所以,凭借其自由的自律,他就是道德法则的主体。”[2](P95)作为近代主体的人,剪断了与上帝脐带,摆脱绝对存在的束缚,逐渐自足自立,并以世俗化为首要内容开始建构现代主体。
进入现代社会,“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人作为一种存在者成为全部存在者的中心即主体,必须是在人对于自己的主体身份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主体不可能是真正的主体”[3](P290)。由此可见,现代主体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动地进行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一切人们希望的、美好的东西都聚集到主体这里,由主体承载。真理、知识、规则等相继聚集于现代主体,并作为现代主体的生长物、维系物体现着主体的地位与功能。现代主体完全能够自己主宰自己、拯救自己、解放自己,完全能够把自己做大做强,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它的作用和功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运用,或者说就是理性以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式在生产力中的充分体现。主体的人利用科学技术,不仅开发、控制了自然界的各种资源,而且也间接地控制了一部分人,并且掌握控制权的那部分人自己也没能摆脱这种控制的控制。个体“认真地对待其主体性并希望自己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个体一方面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不断地问自己,在追求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的过程中,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4](P116~117)。事实上,市场化的实践给个体带来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同时,也使得个体自我可以不顾他者,甚至边缘化他者。或者说,个体自我正是在尽情地满足自身希望和要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二、现代主体的困境
主体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伴随着死亡、黄昏等字眼,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在哲学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尽享前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舒适和繁荣。同时,人类也面临着诸多致命的危险,像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臭氧层空洞、物种灭绝、全球温度升高、核战争等。在这种境况下,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也对主体、主体性等有关问题进行了不断地分析、研究和反思。19世纪末,尼采就大胆地对世人宣称“上帝已死”,并且按照“主人道德”的标准,指责主体其实是人类自我欺骗的产物。弗洛伊德则通过对精神分析研究表明,自我意识之下和之前隐藏着分裂的、盲目的心理能量,这个能量对瓦解自我起到决定作用。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揭示出主体或自我作为逻辑和语法的特殊功能的实质。20世纪下半叶,以福柯、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是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启蒙和现代性,导致了对主体性消解的巨大声势。利奥塔认为:“不论是作为最高的价值、创造世界的上帝、绝对的本质还是作为理念、绝对精神、意义或交往的关联系统,或者在现代自然科学中作为一切、改造一切的主体,都只不过是人的精神创造出来,用以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东西而已。”[5](P31)福柯不仅猛烈地批判了西方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体性原则,并且声称要完全、彻底地消亡自笛卡尔以来无所不在的主体,甚至于他用“人的死亡”的口号来宣布主体的消解,以及现代性的终结。
的确,后现代主义者通过批判本质主义、还原主义和绝对主义抓住了现代哲学的根本,切中了哲学自我理解的要害。然而,观念论和还原论倾向恰恰隐藏在这个批判过程中。“其一,以精神的观念特征作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不自觉地将对现代文明的探讨还原为对主体性精神原则的批判和反思;其二,由于批判对象是观念,而不是人现实的存在状况和存在关系,批判的任务就只是改造思想,而不是改造历史。”[6]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观念论批判代替了现代性批判,而超越现代性的出路则被指明为解构主体性,宣布理性主体之终结。在这一思路上,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三个理由反对现代主体:“首先,主体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杜撰)。其次,对于主体的任何关注都假定了后现代主义者不予赞成的某种人道主义哲学。第三,主体自发地需要一个客体,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主客二分。”[7](P46)后现代主义者是否真的就消解了“现代主体”呢?美国哲学家弗莱德·R·多尔迈认为:“主体性观念已在丧失着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的探究所致。然而我们不应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来曲解这种削弱了的条件要求。……事实上,依我之见,再也没有什么比全盘否定主体性的设想更糟糕的了。”[8](P1)无论后现代主义者如何显示个人的非主体性、无中心性和无本质,他们都不能剥夺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这些特性正是现代哲学所要维护和证明的基本特征。因此,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又开始呼唤主体的回归。他们建议用“后现代个体”来取代现代主体的角色。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体是“突现的主体”“过程的主体”“实现和享用生活的主体”,或者是各种不同特殊习性的载体。还有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假如曾经存在着一个主体暂时死亡的阶段,那么这个间隙正在走向终结。[9](P57)事实证明,现代思想的所有观念,比如“外部实在”“因果性”“权利”“人道主义”“解放和自由”等等,都是建立在独立的主体之上的。假如“现代主体”被扔掉,任何标准都不存在了,那么现代社会政治赋予社会地位、集团和阶级的重要性将会失去,决策、设计和管理的理性也不能再控制科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活动方式,现代社会的体制和现代人的生活会坍塌,人类必然会在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中游荡。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主体的消亡,而是什么样子的主体在消亡,或者说是什么样子的新主体在出现。
三、现代主体的建构
从对现代主体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现代性,都是要通过批判的精神特质,实现个人自由。当初,笛卡尔用“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破除“上帝”的束缚,就是为了实现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自由自主。今天,后现代主义批判以理性主义为原则所导致人生活的单调、空虚和人生意义的枯竭,强调人的多面性,强调人非理性的一面,其实质也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但是,为实现人的自由这一目标,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却采取了两种相反的路径,现代性过度夸大理性,而后现代主义过度强调非理性,这必然导致关于主体认识的狭隘、偏颇。邬焜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人是一个多维存在”。他指出,“人是一种在多维的综合中生成、建构和创造着自身本质的存在。人的本质并不简单直接地来源或存在于某一独立的单维之中,而是来源或存在于多维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建构”[10](P306)。而且主体是一个与人本身存在直接关联的范畴,尤其是在近现代,主体几乎被认为与人是同一术语。因此,现代主体的生成、建构和创造也是在多维中进行的。具体来说,现代主体是在物质和信息、延续和超越、主体和客体、理性和非理性等四个维度进行生成、建构和创造。
1.现代主体在物质和信息维度上的建构
在物质维度上,现代主体表现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主体首先是一个现实而独立的存在主体,现实的主体与自然界一样具有无可辩驳的实在性。主体和自然界的物质性存在本身是实践的。主体的存在不能脱离现实的经验世界,只有这个世界能为他提供维持自身存在的生活条件。主体是从自然界中产生并在自然界中生存,从而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不论他发展到何种阶段,具有何种社会特征与知识水平,主体的物质存在形式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直接基础。同时,主体也是一个社会存在。主体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主体,总是与相应客体在时空中发生着历史地变化。应该说,人的主体性发展过程,与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外部环境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黑格尔曾经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11](P11)因此,人的主体性必然带着历史的性质,必然是客观的,必然是物质的。然而传统主体性哲学,把主体作为一个先于认知活动的开端、起点,即无论认知活动是否开始,一个先验主体已经存在。针对这种先验论的主体性假设,萨特强调:“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12](P12)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主体身份和主体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人的不断认识和不断实践中生成的物质本质。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物质世界是传统关于主体的发生、建构和创造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形态的发现,为主体打开了一个一直隐藏在物质维度之后的信息维度。“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13](P45~46)在信息维度上,现代主体表现为不同信息形态的多级中介建构。这个复杂的信息系统中不仅包括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再生信息等三种类型的信息,而且包括信息场、物化工具、人体神经系统、主体先已建构起来的认识结构等四个方面的中介。具体来说,在主体自身建构的过程中,自在信息按照自然原则,通过一种纯自然行为,在信息场和信息体中完成了对主体自身的自然属性的规定。主体通过人体神经系统,按照一一对应的原则,直观把握了自在信息,把自在信息转化为自为信息。并且以形态、图像、颜色等等被主体所记忆和储存。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人体先已建构的认识结构,在自在信息和自为信息的基础上创造了再生信息。这不仅仅是对 “物料”模拟的超越,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主体能动性的规定,而且是对自我和现存状况的超越,是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不断寻求。因此,人自身的社会性和复杂信息体性正是通过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和再生信息的多维综合,以及人实现其目的性信息的实践活动,得到集中的规定。由此可见,从信息维度的多级中介建构的视角来看,主体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直接存在,还是一种信息性的间接存在,是递进的三类信息形态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统一的动态凝结、变化发展、综合多重信息维度的复杂信息体。
2.现代主体在延续和超越维度上的建构
现代主体在延续和超越维度上的生成、建构和创造,主要体现在对自然和人本身的延续和超越。经过近现代的发现、确立、弘扬,主体直接与人相关联、相统一,不仅具有维系自身存在的因素,而且也对主体自身、外在世界进行批判与改造,具有超越的品质。具体来说,作为主体的人的生理、心理,或是行为都体现了决定性与非决定性的同一,是延续与超越的统一。作为主体的人有两大生产,其一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保持种族的繁衍;其二是人的生产劳动,维系自身的存在。个人首先是作为一个现实的、自然的存在,具有自然的机能。根据遗传基因学研究证明,在人体的遗传基因结构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个体发育信息程序,即DNA与RNA。其中,DNA的遗传信息是一种决定式的延续,它确保着个体中最一般的生理、心理和行为活动方式的建构;而RNA的遗传信息则存在着突变,它是对原有的发展模式的打破,是一种非决定式的超越,这是人自然本能层面的延续与超越。基于对人的遗传基因信息有关延续与超越的认识,再从生理结构、心理结构、行为结构方面进行进一步探讨。就生理结构层面而言,经过生理机能的正常发育,个人会形成人最一般的结构,譬如:身体应有的感官器官、四肢、脑以及相应的组织、系统。这些依然保持了遗传基因中自然属性的方面,但是人后天的发展、培养,如人的直立行走以及喉部、声带发育器官的发声训练,还有脑皮质思维和语言的生理性结构,这些都是人对自然存在的超越。就心理结构的层面而言,神经系统包括感官、神经、脑等一般性的心理结构,它是作为心理活动能力的物质基础而存在的。同时,它具有一般性的各类感知、记忆及初级的想象等心理活动能力。而主体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他具有一般高等动物所不具有的能力,尤其是在使用概念信息、符号信息进行抽象思维方面,这些是对原有存在的超越。同时,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所延伸的人的感知、记忆和思维能力等,则是按照一种非决定方式在后天的人的社会环境中建构的。当自在信息通过主体的感知系统,被主体所把握,自在信息就上升为自为信息。自为信息把自在信息的载体——“物料”——变为形态、图像、颜色,或是其他符号储存在大脑中。当主体对于所储存的自为信息进行的不仅仅是保留、模拟,更重要的是改造、创新。再生信息的载体也同自为信息的载体出现了区别,已经不是对“物料”一一对应式的模拟,而成为一种超越,形成了具有指代意义的符号。同时,在这一阶段是作为信息人体内循环和人体外循环的分水岭,这时再生信息的载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储在人机系统的记忆区中,长期地保持起来;二是成为实践的计划、方案被制定下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再生信息的载体承载了实践的目的、意图。当主体发出指令信息时,信息的人体内循环结束,信息开始进入人体外循环,也就是开始实践了。就行为结构的层面而言,按照延续方式存在的人具有维持生命的初级本能性行为活动,如吃饭、喝水、睡眠等等。但是,工具的使用和制造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达到了对自然的超越。
3.现代主体在主体和客体维度上的建构
现代主体在主体和客体维度上的生成、建构和创造,具体表现在以信息凝结为中介的个体认识结构的建构和认识、实践的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个体通过遗传承载了人类种系进化中凝结的遗传信息。这个信息不仅凝结着人类产生的历史信息,而且直接规定人的个体活动、个体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要使主体认识结构实现建构还必须不断同化适宜的环境信息,促使遗传信息和环境信息相互作用,不断改变个体的认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认识主体特征被个体所呈现,主体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信息,并且主体把产生这个环境信息的信源物规定为他所认识的客体。主体认识结构的不断进化,也将进一步加强和改变主体对客体信息进行加工、改造的深度、广度、速度和具体方式。由此产生了认识主体,建构了主体的认识结构。通过操作工具,主体把认识中的目的性、计划性信息转化为客体的结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将输出信息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客体信息不断对主体进行反馈,主体也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控信息,这样就在实践活动内部形成了信息循环运动过程。实践活动不仅实现了主体信息向客体结构的运动,而且也实现了客体信息向主体的运动。然而现代主体性哲学把主体和客体割裂,主体把握的不是外部客体,而是心灵中的现象。建立在主客分离的基础上的主体中心主义,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支配、征服和改造,把主体看成凌驾于外部客体之上的统治者,所有的事物都作为对象被带到主体面前,接受主体的拷问、谋划、设定和支配,突出表现在主体对于自然无限度的开发利用方面。由于对自然的无限扩展,控制自然所造成的恶果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人类生存,用霍克海默的话说就是“自然的反抗”,或说“非理性机巧进行的报复”。
4.现代主体在理性和非理性维度上的建构
现代主体在理性和非理性维度上生成、建构和创造,具体表现在理性与非理性统一于主体的思维中。理性不仅表现为人类对自身有限生命的超越,对必然性、普遍性及永恒无限的能力追求,而且表现为生命的灵性的光辉。非理性则蕴含着对于生命的自然欲望和冲动,体现了人类追求感性、具体、有限性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思想史既是一部理性的自我反思的历史,也是一部非理性的思维跳跃的发展史。在人的认识和行为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总是交织在一起,总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传统主体性哲学,把主体作为认识或者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得到满足的自我或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规范、观念、行动准则等内化到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消弭改造的痕迹,把“人变成主体”的过程变为一种个体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一种理性化过程,从而使现代个体把主体化理解成自我教育,自觉自愿地按照主体标准改造自己,成为标准的现代人。后现代主义认为工具理性膨胀和生活世界殖民化导致了主体是“被异化了的”。因此,福柯宣称“人的死亡”,就是要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人在世界和现实中的地位,重新审视曾经作为万物尺度和中心的人,以及曾经自以为了解的世界。他们认为真实的主体应该表现出人的感性、欲望、本能等非理性的方面,认为这才是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但是人的感性、欲望、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已经不是纯粹动物性的本能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在人的感性、欲望、本能中都有人的理性因素渗透其中,打上了社会性的烙印,都是被意识到了的感性、欲望、本能。并且理性对非理性具有指导和调节作用,能够促使非理性的动机与道德、文化、社会理想的价值和趋向相一致。同时,一定知识理性智慧为非理性中的灵感、直觉、顿悟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因此,“理性离不开非理性的补充,否则历史就不是现实的人的历史,实践也不是现实的人的实践;非理性离不开理性的驾驭,否则历史就会滑出正常的轨道,实践也会脱离科学的里程,人类精神就会引入混乱的、甚至是疯狂的状态。有了理性,人类历史才会循序渐进,人类才能知礼立德;有了非理性,人类的生活才会色彩斑斓、历史才会跌宕起伏”[14]。
由此可见,从多维度建构的视角来看,现代主体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直接存在,还是一种信息性的间接存在。这种存在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随着人类进化,现代主体也在不断地实现决定性与非决定性的同一、延续与超越的统一。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自发演化的特定阶段上创生出来的。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总是对立统一的。如果脱离自然,仅从主体出发,不仅无法找寻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人的社会的问题的答案的原因,而且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破裂、对立,遭受“自然的反抗”。同时,纵观人类发展史,尤其是人类精神史,它始终充盈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它既是一部理性发展史,也是一部包括感性、欲望、本能等在内的非理性发展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体完成了物质和信息、延续和超越、主体和客体、理性和非理性等四个维度上的生成、建构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