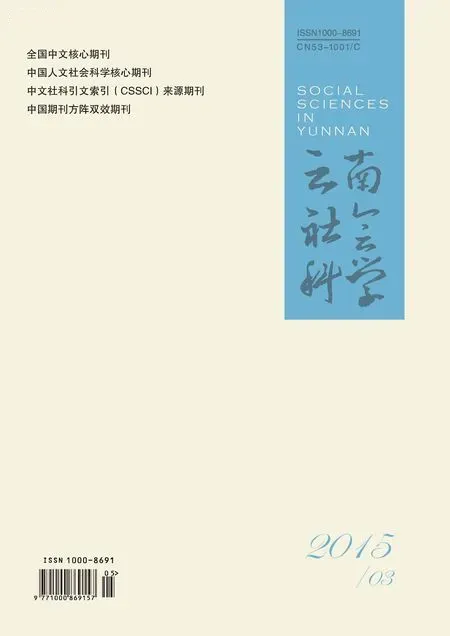新时期中国史学“非中心观”述评
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80年代之后,中国历史研究在观念上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被视为对“西方中心观”的重要突破,它虽引人瞩目,但也发人深省。90年代前后,旨在超越各种“中心观”的“非中心问题”这个更富有历史意义的思考被提了出来,并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进而形成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观念和新取向——“非中心观”。拙文就“非中心观”的理论源流、内涵、提出、方法论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并述说个人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非中心观”的理论源流及其内涵
从理论源流上讲,“非中心观”脱胎于以“非中心化”为本质特征和以“非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母体之中。后现代主义以“解构”(deconstruction)理论为核心思想,以“去中心化”“去自然化”“去等级化”“碎片化”和“不确定性”为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对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理性”与“进步学说”进行猛烈的批判和否定。由此,“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成为对它的特征的一种概括”①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6页。。后现代主义之旨趣就在于从根本上颠覆人们固有的二元对立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和认识框架,并通过对边缘和他者的关注,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破除对理性、主体和本质的迷信,彻底捣毁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根基。②参见拙作:《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以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为中心》,《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顾名思义,“非中心论”就是对“中心论”这一观念的批判和取代。美国学者保罗·韦普纳(Paul Wapner)就曾将“非中心论”定义为“对社会现实的任一要素或部分可以被规定为本质的、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这样一种观念的批判。③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0页。在以德里达为首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他们又根据“非中心论”所批判的具体对象的不同,将其分为“温和的”和“极端的”两种形式。④从批判的对象及其主张上看,后现代主义也可分为温和的和极端的两种形式。温和的后现代主义是建设性的,主张顺势而为,倡导对现代性因素进行发展和改造。而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则是破坏性的,主张逆流而上,倡导对一切现代性因素进行消解和颠覆。“所谓‘温和的非中心论’是指对各种人为定义的中心、主体、特殊的参照系统、本源或有关绝对基础的全部思想的公开摈弃和消解,比如科学、文明、理性等。所谓‘极端的非中心论’则是对‘中心’这个概念本身,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中心进行否定。”①Jacques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 Alan Bass,London:Routledge,1978,P.286.换言之,“非中心论”否认语言之外存在任何独立的先天性结构或内在中心,以及任何不能再分的不变的内核,否认事物拥有终极意义。
在历史研究领域,以“非中心论”思想为理论内核,逐步衍生出了“非中心观”这一历史观念和研究取向,成为批判“中心观”的有力武器。“非中心观”揭露了以往历史研究中各种“中心观”的弊病及其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危害和导致的偏差。其通过对“中心观”的批判和摒弃,又逐渐发展为对“中心”这一提法本身的质疑与否定。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解,可以说,“非中心观”既是温和的,又是极端的。它旨在树立“非中心”意识,培养多元化观点,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既重视具体历史发展的个性和特殊性,又兼顾其共性和普遍性。正如中国学者侯且岸所言:“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把问题全部解决了。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也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②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2-133页。也即是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坚持“非中心观”就是要摆脱传统历史思维模式的束缚,转变历史研究的观念、视野和方法,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查与研究,在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不应拒绝西方的一些有价值并值得借鉴的经验;在关注源自西方经验的一般规律的指导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中国自身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从而建立中国历史研究的新体系。
二、“非中心观”的提出
“非中心观”在20世纪末叶“相对主义中心观”之后被提出。大体说来,它的提出与学术界对当代历史研究观念的反省、史学意识的自觉以及时代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是学界达成的一种普遍共识。
1.“中心观”的流弊使史观的突破成为必然
“西方中心观”的流弊自无需赘述,它对历史多元化和不同特性的遮蔽与抹杀,注定了其无法逃脱被新观念批判甚至取代的命运。在对“西方中心观”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以非西方国家或地域为中心的各种“相对主义中心观”。它针对“西方中心观”的弊病,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主张研究视角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具体化为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中心观”,打破西方经验的束缚,发现各个社会的特质,从内部寻找线索,以揭示其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比如:美国学者保罗·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中心观”,中国台湾学者杜正胜提出的台湾“同心圆史观”③杜正胜在《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载2002年台湾《新史学》第十三卷第三期,第39页)一文中指出,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已经引起了年轻学生的更大的兴趣。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以中国为中心转为以台湾为主体、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等。这些观念的共通之处,就是通过对历史独特性的诉求,表现出了与传统研究模式的巨大差异,对非西方历史研究起到了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相对主义中心观”在抵制“西方中心观”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它一方面打破了旧观念的樊篱,突出强调了西方之外某一地域历史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却又作茧自缚,忽视了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及与其他地域历史的参照和比较,也难以适应以世界历史的整体运动为对象的研究。”④参见拙作:《“中心观”的摒弃与多元化观点的树立——对全球化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思考》,《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因而,从这一层面看,“相对主义中心观”实际上只是一种替换性策略,试图以其他的中心替换“西方”这一中心,本质上并未脱离“中心观”的窠臼,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西方历史研究中超越“西方中心观”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其流弊与局限更加暴露无遗,传统史学中的“中心观”必须彻底摒弃,史观的再次突破成为了必然。
伴随着学界对“相对主义中心观”,尤其是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讨论与反思,更多的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指出,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不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①[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诚哉斯言,在历史研究中,任何一种“中心观”都是我们应极力避免的。“非中心”意识的树立和多元化观点的培养,已成为推进新世纪历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2.全球化进程推动着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发展与创新
各学科领域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也迎来了一场“洗礼”,在学科范型、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历史观和方法论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回应时代的挑战。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西方中心论”这一观念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不仅将西欧视作历史进程的中心,还把西欧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模式上升为普世标准,去定义和改造其他文化与历史,这种塑造及改写必然会存在扭曲真相的可能,同时也包含着人种优越论的成分,否定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学者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②[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同时,“全球化趋向也并非意味着各个民族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消失,只是表明在这一过程中,平衡与不平衡是不断变动的,这才构成了历史过程的动态曲线。……某一时期某一区域的历史发展较快,自然就会成为突出的重点,成为影响世界进程的主导方面”③吴怀祺:《全球化趋势与新世纪史学》,《新视野》2001年第2期。,但它也只能算作世界的“重心”,而非“中心”。因此,我们在对“中心论”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同时,还应注意“中心”与“重心”的区别。也正如中国学者周谷城在论及他对世界史的研究时所指出的:“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等于抹煞世界史上某一个时期欧洲是重点。若没有重点,不仅没有世界史,也将没有历史本身。……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上,确实成了重点,这是事实,不能否认,如实叙述是应该的。……把贯通全部历史的中心与一时突出的重点混为一谈,是错误的。”④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115页。因而,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新史观的提出自然也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可见,全球化进程是推动当代历史观念与方法论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非中心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因此,“非中心观”是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历史观念进行自觉反省的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对历史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的具体要求。
三、“非中心观”的方法论意义
“非中心观”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观念、新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拓展思路,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促进中西史学的交流、对话与融合。在我看来,它的重要价值及其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集中体现在其蕴含的诸多方法论意义之中。以下两个方面或许最应为我们重视。
1.加强中西历史的双向比较和对视
“非中心观”力求消除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以更加公正、客观的立场去观察世界和审视自己,从而克服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因而,在历史研究中,加强对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双向比较和对视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比较的独特价值就在于,通过比较的方法,而不用抹杀任何一方的特点,就能发现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异同、关联及其缘由。对视就意味着从相对的角度出发而进行相互审视,这与换位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不仅要从欧洲的立场看中国,而且也要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通过对视,转换视角,加深理解,促进反思。
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经表明:“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⑤左玉河:《当代世界与文明研究的新动向——世界文明国际论坛第二次国际研讨会综述》,《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值得一提的是,已有不少学者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坚持双向和相互的比较方法,力求突破西方中心的前设。比如,中国学者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中,就通过对中英早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比较,指出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与英国有着不同的道路,其特殊模式是基于“江南经验”这种区域性的独特历史发展经验而形成的。其研究视角的调整与思维方式的更新,对于我们摆脱以往明清经济史研究中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将视野和研究重心转向中国历史自身经验的独特性,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又如,美籍华裔学者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也强烈地质疑和批驳了长期盛行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以及一系列西方优越论的观点。然而,他并未全盘否定西方的理论范畴,而是运用了包括西方理论和方法在内的各种学术理论,在深入比较中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且又多重的轨迹。可以说,王国斌的这种尝试既超越了“欧洲经验的局限”,又避免了“中国中心主义”。可见,历史比较方法是避免偏执与片面,增强结论客观公正性的极为有效的方法。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将其视为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在全球一体化的新时期,历史比较与对视的方法无疑是我们深化认识,消除隔阂,实现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前提,不容小觑。
2.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历史
历史研究“非中心观”所蕴含的内在前提和关键就是历史研究视角的转变。历史研究无论以谁为中心,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狭隘历史观,都不能充分取代世界的眼光和全球的普遍观点。在具体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全球史观”。20世纪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化,促使学界对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史观”应运而生。“全球史观”排斥了以“欧洲中心论”为出发点观察历史的传统,而提出应根据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从宏观的视野、联系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及走向进行考察和分析。同时,“全球史观”作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还具有全球性、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等独特的优点。
当下,全球视野已日渐成为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早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尝试和选择。比如,中国学者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就体现了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路。作者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宏观视野,对19世纪的中国进行考察,指出市场的全球化是18、19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19世纪的中国,通过茶叶和鸦片贸易,也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正是茶叶和鸦片等商品使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经济关联,但最终也导致了中国19世纪的全面危机。该书从全球视野出发,重新解释并揭示了19世纪中国的危机及其内涵,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被称作国内全球史研究的一个范例。
的确,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宽广的情怀,正如论者所言,“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胸中有中国,还要眼中有世界”①徐松巍:《中国史研究应有世界的眼光》,《北方论丛》1999年第3期。。同时,中国史学研究者也应怀着不卑不亢的平等心态,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在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取得平衡,从而实现中国史学的和谐、全面、健康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四、对“非中心观”的反思
举凡一种观念或理论的提出,我们都需对其进行多重考察与反思,探讨研究者在运用这些理论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些理论自身的困境。就“非中心观”而言,这样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这一观念的两种极端的理解上。一种理解认为,它是一个毫无内涵的新概念,如同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是对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全球史观”等史学方法的总体概括。另一种理解认为,“非中心观”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甚至是个伪命题。犹如站在月球观察地球,看起来很美,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试问谁又能真正让自己置身于月球呢?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只是痴人说梦。
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理论或观念的提出或许是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促成下水到渠成之事,但要将这些理论或观念贯彻到具体实践中,却非易事。“非中心观”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观念和取向,仍需要诉诸切实可行的方法才能实现目标,发挥作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全球史观”只是“非中心观”带给我们的两种主要的方法论启示,是其得以付诸实践的两种必要但不充分的方法。从某种角度说,“非中心观”这一提法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些方法及其内涵的总体概括,但反过来,它又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些方法的理解和运用,规避这些方法自身的局限性,甚至赋予其新的内涵,并且随着史学研究实践的发展和深入,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还会催生出更多的新方法。可见,“非中心观”并不是把玩概念的结果,也不是一具用来吸引眼球的理论躯壳,而是历史研究观念和史学意识的自觉与更迭,也是研究方法得以发挥和创新的理论支撑。因此,“非中心观”的提出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也是前文为何要追述它的提出与产生的原因之所在。
至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我们对于“非中心观”这一观念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更不能偏激。就“非中心观”而言,其最终目标当然是要摒弃历史研究中的“中心观”,树立“非中心”意识,尽管这一最终目标还很遥远,实现起来也困难重重,而且或许根本无法实现,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为之所付出的努力。因为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们总会更加接近这一目标。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历史学的终极目标在于探寻历史的真相、发现历史的规律,但至今我们也未能完全获得历史的真相,更不用说发现历史的规律,一些人甚至十分肯定地认为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但是否也可以由此否定我们为之付出的所有努力呢?显然是不能的。否则,历史学将不会存在。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历史学也才有了不断发展前进的动力。同理,对于“非中心观”而言,只要我们在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诉诸于恰当的方法,尽可能地朝着目标努力,或多或少地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非中心观”的诉求。因而,它的实现绝非异想天开,而是取决于我们愿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以及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去实践它。
另外,从理论上讲,“非中心观”是对“西方中心观”和“相对主义中心观”的替代,那么是否意味着它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中心观”的所有流弊?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心观”或许永远不会消失,甚至还会自始至终地伴随着我们的历史研究,但我们却有理由,也有能力将它的影响降到最低。正如柯文所言:“西方史家面临的严重挑战,不是要求他们彻底干净地消除种族中心的歪曲。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求他们把这种歪曲减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要做到这点却是可能的。”①[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其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页。对中国史学工作者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学界对于“非中心观”的定性式的讨论明显多于有针对性的范型的解读。可见,它的提出虽得到了学界大多数同仁在理论上的认同,但就具体实践而言,特别是在其相关理念的最终落实上,还存在诸多困境,也面临不少挑战。这也再次证明,一种新观念、新理论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得到充实、完善和发展,对于“非中心观”亦可作如是观。无论如何,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历史以及非西方历史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正自觉地朝着这一目标不断努力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