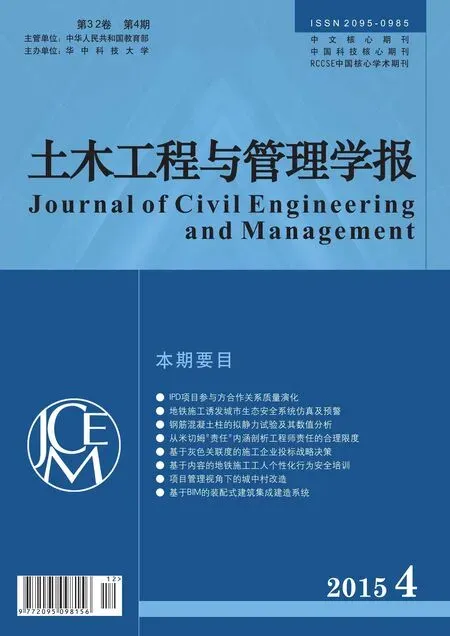从米切姆“责任”内涵剖析工程师责任的合理限度
王进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从米切姆“责任”内涵剖析工程师责任的合理限度
王进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工程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进程,这使得工程师承担责任成为必然之举。米切姆定义“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但随着巨型工程的日益增多,工程技术的日渐复杂,作为人类进步主要力量的“负责任的工程师”是否应当承担扩大化的责任值得商榷。本文认为该定义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工程知识的结构分类极大提升工程师辨识责任的能力;二是工程师力量的复杂多变警醒工程师审慎对待责任;三是知识与力量的不同组合共同助推工程师在合理限度内履责。只有通过辨析米切姆“责任”内涵,充分认识到工程师在知识局限和力量有限上的困境,才能理解其只应当“力所能及”地“当责”,方能期待工程师的道德自觉和伦理自省得以彰显,从而“把好的工程做好”。
责任的合理限度;工程师;工程知识;力量;卡尔·米切姆
1 学界低估了米切姆“责任”内涵之于工程师担责的重要性
卡尔·米切姆(C.Mitcham)认为:“说‘诚实的工程’几乎是画蛇添足——如果工程不是诚实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工程”[1]。现代工程是价值负载的伦理决策过程。所有的伦理课题皆离不开责任[2]。米切姆从语义学考证,责任(responsibility)的词根是拉丁文的“respondere”,意为“允诺一件事作为对另一件事的‘回应’或‘回答’”[3]。
西方学者对于责任内涵的理解有三种代表性观点:责任是人类群体性的必然要求;责任是人内化了的行为规范或倾向;责任通常意味着付出代价[4]。在中国,“责”本意为“求也”,“任”本意为“符也”,责任即为符合要求,其含义与西方观点大致吻合:担当某种职务和职责;做好分内之事;承担不履行应尽之责导致的损失[5]。责任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各行各业伦理水平高低的试金石。“责任仅仅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3]。米切姆的这一论述虽然勾勒出构成责任的两大要素,但对于知识与力量如何协同形成“自我的规定性”,并未详细阐述。研究者历来也认为这一观点简单明了而未加深刻解读,导致其学术价值被严重低估,论述主要集中在两方面:赞同者坚信“责任应当真正与知识和力量成正比”。掌握精深知识或掌控特殊权力使得工程师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理当担负更多的伦理责任,同时亦当制定特殊的伦理规范来约束其职业行为[6]。随着科技进步的飞速发展,工程师在知识增长和能力拓展上的急速变化,使得责任“不仅关乎工程师本人,而且关乎其周围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既然头顶“知识权威”桂冠的工程师期望凭借自我的能力展示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自然应当承担因技术使用不当而产生的任何损失。质疑者认为“责任因为知识和力量受到遮蔽和约束而不易明晰”。巨型工程的日益增多、工程技术的日渐复杂以及组织结构的日趋扁平,既弱化了工程师以专家身份独立承担责任的可能,又削减了工程师对于工程决策方案进行裁决和拍板的掌控力,使其日渐沦为在自由意志和道德行为能力上都广受限制的“边缘人”,只应当承担有限度的工程伦理责任[7]。
随着“责任”从社会“边缘”进入到生活“中心”且工程对世界的影响度与日俱增,对米切姆责任内涵的重新认识将使工程师理解:不负责任是无可救药的恶,但是负责任充其量不过是不充分的善[3]。米切姆认为“工程师的责任已扩展为一种社会责任”[3],工程师在道义上有责任、有义务向用户介绍技术要领和产品细节,凭借其工程知识和专业经验阐释潜在危害。但在“知识”和“力量”两个维度上,现代工程都令工程师常生无所适从之感,难以承担扩大化的责任。一方面,职业倦怠使工程师偏离了“实现项目目标”的正确轨道而陷入“为工作而工作”之歧途,导致获得卓越绩效所必须的有效“知识”被“流放”至配角地位。另一方面,工程师“天经地义”地被视作拥有改造自然、改变社会、改换世界的力量。可现实并非如此:工程师常表现出深重的无力感。米切姆赞同道:“实际上工程师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并没有像莫里森、普鲁特所说的普遍责任,而仅有一些特定的和特殊的责任”[3]。
论文的研究依循如下思路:首先,辨析工程知识的结构分类,以提升工程师辨识责任的能力;其次,探究工程师决策力量的能级分层,论述工程师力量的复杂多变,从而警醒工程师审慎对待责任;再次,厘清知识与力量这两大源头构成责任的内涵机制,以辅佐工程师有限度地合理承担责任;最后,总结知识与力量的相映生辉,助推工程师真正实现兼顾技术标准和伦理规则的“批判性的忠诚”。
2 工程知识的结构分类极大提升工程师辨识责任的能力
工程师若要勇于当责,必须具备工程知识这一重要智力资本。工程知识包含诸多层面,对工程知识加以合理分类和认真辨析,能够增进工程师辨识责任的能力。但是,工程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倘若工程师固步自封,则其工程知识的储量受限,极易导致工程师创造新知的努力受挫和意愿受限。
2.1 工程知识是工程师勇于当责的重要智力资本
知识是认知主体(工程师)对客观事物(人工物)抽象出来的主观影像。米切姆认为:“与科学不同的是,工程所关心的是‘做(make)’,而不是‘知(know)’”[8]。但沃尔特·文森蒂对“工程知识”中“知识”一词给予更宽泛的解释,认为它不仅以科学知识(know-why)为基础,还包括“如何做(know-how)”和“是什么(know-what)”。“如何做”包含“如何设计/建造/运营”以及“如何产生新知识”,“是什么”是有关事实的知识[9]。
工程知识是多元化的知识混合体,是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统一,展现了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的深度交织与融合[10]。工程知识经历了由最初的素朴经验常识到工具主义的工程科学,再到工程“食谱”的演变过程。所谓工程“食谱”是指工程师解决问题之法及结果以参考手册的形式编目记载,并跨领域成为通用知识。约瑟夫C·皮特宣称“一本好的食谱应该可以为任何人准备一顿美餐”。但工程师仅有“食谱知识”远远不够,更得掌握“怎样做菜”的技术知识。
长期以来,工程被片面理解为“应用科学”或“技术应用”,实证主义者更是把工程知识、技术知识均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工程知识服务于工程实践,承担“考虑周全的义务”。它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兼具实践性、中介性、情境性及现场发生性。约瑟夫C·皮特甚至宣称:“工程知识被证明要比科学知识可靠得多。”工程知识增进工程师“化繁为简”的能力,助推工程师激发创造力,且能理性判断并合理抉择,为工程师“当责”消除了智力障碍。
2.2 工程知识的结构分类增进工程师辨识责任的能力
(1)工程师要兼具休谟所分类的事实知识(科学真理)和价值知识(道德准则)。专业背景使工程师更擅长事实知识,而伦理教育的弱化令其轻视价值知识。工程师习惯以价值知识浅陋作为伦理不作为的挡箭牌,但亚里士多德早就批驳过“在无知中行动”的观点:“一个人应该承担双重责任:首先要对自己的无知负责,其次要对自己在无知中做错的事情负责”。对“工程必须接受伦理考量”这一理念缺少认知,既限制工程师形成道德认知,又助长其推卸责任。工程师道德敏感性的缺失不但模糊了伦理审视的焦点,而且强化其“理直气壮”捍卫自身作为“专家权威”的勇气。正如康德所言:“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工程师惟有保证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的齐头并进,才能实现专业表现与道德自觉的并行不悖[11]。
(2)经验知识和直觉知识都源自“拇指规则”(rules-of-thumb),体现工程师的“实践智慧”,决定工程师伦理决断力的强弱。迈克尔·波兰尼将知识分为外显知识和内隐知识。外显知识是指已经过编码可用公式、定律、原则、制度和说明书等类型化的知识,是工程师发挥力量的主要源泉;经验知识和直觉知识都属于内隐知识,具有较强的环境依赖性、模糊性和个体性,需要通过“附加的洞察行为与试验行动”才能获得。经验知识为工程师理解新技术难题和新伦理困惑提供历史透视角度;直觉知识,伊德称之为身体化的“默会”知识,其运用无需通过大脑有意识的思考。工程师借由经验知识和直觉知识提升问题解决速度。缺少“实践智慧”,经验知识会退化为僵化教条;缺乏“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考”,直觉知识乏善可陈。
(3)工程师要打通个体知识与群体知识的界限并实现互融。彼得·德鲁克强调,知识是组织或个人的首要资产。工程师的知识储量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公司聘请专家重在“购买”其专业见识。同时,工程的世界,是一个与他人“共在”的世界。工程共同体各方所拥有的知识各异,沟通协调时群体知识较之个体知识更重要。参与一项重要工程,工程师能获得和同业佼佼者反复商洽的良机,能发掘自有知识,与同事共享知识,并为机构创造新知识。
(4)工程师既要重视成功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失败知识的警醒。成功知识是指在成功项目的实践中累积的高创新性知识,失败知识则形成于工程缺陷和事故等失败经验。因项目成功标准的界定受多元价值的影响,且项目管理成功与项目成功时常背离(如悉尼歌剧院),在成功知识与失败知识的认定上屡有争议。工程师该如何区分两者呢?若为了推卸责任而肆意颠倒黑白,是否会恶化工程师伦理缺失的境况?此外,工程师易患“项目健忘症”,即项目结束时根本不予反思和总结,任由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流失和遗忘。惟有“知识化”后,才能使“需要的人”能在“需要的时候”以“需要的形式”得到“需要的内容”。
工程师常被赋予更多期待:他们被要求成为科普专家,教育民众理解工程,帮助公众加深对工程师职业的认同。若工程师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不足以胜任这一职责,就算工程师极力希望在公众心中树立“权威”和“当责”形象,也是无异于缘木求鱼。
2.3 工程知识储量易导致工程师创造新知的努力受挫和意愿受限
当知识拒绝审视自我、停止发展时,主观或教条就会占据上风,工程师易陷入封闭心态和狭隘姿态而变成武断之人。工程是科学和技术的集成性创新,是创新的主战场。但在风险偏高、事故频发的工程领域(如土木工程),资深工程师宁愿选择成熟技术,而将“试错”推给他人。依常理而论,“多知”比“少知”更能审慎决断。但悖论是:人越“有知”,越对“所不知”感到畏惧,反倒不够自信和果敢。处于知识成长期或成熟期的年轻工程师常有“惊世骇俗”之作,部分即源于“无知者无畏”的心理暗示。很多处于知识衰退期的“老工程师”深怕“越雷池半步”,甚至为顾全面子而滥用行政权力和专业权威扼杀年轻人的知识创造力。这印证了马尔库塞所描述的技术悲观主义论断:“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
工程师懂得“适宜知识”有助于责任意识的增强。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知道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太多东西的人,是聪明的。”工程师若不能将知识转换为助推责任担当的驱动力,知识就会遭遇“降格”或“贬值”的危险。
3 工程师力量的复杂多变警醒工程师审慎对待责任
工程师对于工程知识的掌握和使用,最终体现在工程师对工程决策及工程共同体能够施加多大的影响力上,这恰恰是工程师力量的本质体现。力量多寡决定着工程师责任承担的范围,但当责意愿的大小同样不容忽视。工程师只有同时在意愿、能力和机遇三方面都满足条件时,才能变身为积极履行责任的道德主体。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工程师会根据项目成功与否而有“偏好性”地选择邀功或是推诿,此类做法会严重损害公众对工程师职业角色的正向期待。
3.1 力量的本质体现为工程师对工程决策及工程共同体的影响力
长久以来工程师都被认为具有改天换地的超级力量。早期的军事工程家亨利·加士利·普鲁特就相信“工程师,而不是其他人,将指引人类前进。”[3]莫里森是这一观点的忠实信徒,他说:“我们是掌握物质进步的牧师,是能够使别人享受自然界伟大力量源泉的牧师,是拥有用头脑控制物质力量的牧师。我们是新时代的牧师,却又绝不迷信”[12]。技术的力量使“责任”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成为伦理学的新焦点。但工程师对于力量的错误认知歪曲了伦理自由,进而导致责任承担长期处于能级不匹配的状态。
工程师的力量,表现为其影响力的大小。影响是强者对弱者的“提携”。影响力包括两部分:一是组织赋予工程师的权力及因权力而衍生的强制性影响力;二是工程师借助知识、名望、同理心等要素练就的自然性影响力。权力源自工程师所在职位及其附属的资源控制力,使得工程师拥有能影响其他工程参与者之行为的能力;强制性影响力派生自权力所携带的“权力束”,包括强制权、奖赏权、合法权等;自然性影响力体现的是工程师在“责任簇”上的综合表现,各构成要素对于担责能力贡献不一。D.E.苏泊尔和P.B.巴赫拉赫描述“工程师善于处置事物而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就是对工程师在自然性影响力方面动力不足、能力不济的直接批评。至少在面对工程引发的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等环境伦理和社会伦理问题时,工程师意见的分量与他们被赋予的权力不成正比。
3.2 力量多寡和意愿大小决定着工程师责任承担的范围
权力及其强制性影响力体现“权”的实力,自然性影响力彰显“威”的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工程师的力量之源。当源头遭遇枯竭危机时,工程师会陷入如下三种困境。
(1)工程师缺乏工程决定权使其无“力”可言。无“力”体现为:一是典型的工程决定(proper engineering decision)让位于典型的管理决定(propermanagement decision),管理者逾越角色边界而拍板本该由工程师做出的决定。约瑟夫·雷林说:“因为教育背景、社会环境、价值观、职业利益、工作习惯和见解的不同,管理层与职业层存在着自然的冲突。”这种“对抗关系”甚至会导致雇主或管理者出于公司利益而强迫工程师行败德之事。倘若工程师胆敢举报,将被企业视为挖组织墙角的“叛徒”或“异端分子”而加以报复。二是技术力量集中于工程共同体金字塔上部,一线工程师的工程决定权少之又少,沦为“事务性”工作的“看门人”。C.S.路易斯尖锐批评道:“人们常说技术发展是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增长,其实这种力量不是付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而只是把自然当作中介来使一部分人相对于另一部分人的力量的增长。”这种“少数人在力量上优于多数人”的现象,在工程共同体内更为突出:塔尖处的业主、投资人和权威专家手握重权谋得暴利,却将失败风险丢给塔底的无“力”者。
(2)工程决策的“集体政治”姿态决定了工程师的“力不从心”。一则虽然工程师常被称作“有产者的仆人”,但现代公司中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权力配置过度,而是很多人的权力太小或太少。工程师常常处于“权力萎缩”的焦虑之中。在忠于雇主和公司利益的义务与履行对公众安全的道德责任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工程师在管理、就业等方面的弱势地位,加剧了这种伦理冲突带来的道德强度。在米切姆看来,“公众希望人们不要为恶,鼓励人们去做英勇的善事。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律令,它最终只会产生极权主义或压抑的政治体制。”企业只希望工程师成为“温顺的羔羊”,而非公众利益代言人。相较于工程所负载的巨大使命,很多工程师被赋予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这就是谢帕德为何将工程师称为“边缘人(marginalmen)”的原因,也契合莱顿“工程师既是科学家又是商人”,“科学和商业有时要将工程师拉向对立的方向”的观点。二则因为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高,工程师个人在整体工程活动中只能起到细微作用。现代工程活动采用流水线施工,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加大了将集体责任归咎到个人的难度。这就是汉斯·约纳斯所描述的:“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与整个社会的行为整体相比,可以说是零,谁也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本质性的作用。……‘我’将被‘我们’、整体以及作为整体的高级行为主体所取代,决策与行为将‘成为集体政治的事情’”。
(3)工程师功利主义的算计使其“不愿出力”。纳尔逊和彼特森说:“工程师之所以是功利论者的一个真正原因,正是因为事后他们不必负道德上的责任”[13]。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解决技术难题的“力出多头”减弱了工程师们主动担责的意愿。当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和工作关系的互赖性过高时,各方利益诉求的冲突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的勾心斗角和本位主义的互不相让。压力重重极易使“有道德者做出不道德的决策”,而工程师共同体的存在更是剧增责任分担和集体懈怠的道德风险。二是工程师们与经理层之间的观念分歧对其当责造成困难。施泰因曼将工程师的伦理行为分为四种:履责却不关心伦理的“艾希曼式”;懂得善恶之分却非伦理地谋私利的“理查三世式”;为实现自我价值而采取卑鄙手段的“浮士德式”;专业与伦理兼备的“组织公民式”[14]。大多数工程师希望变成为企业谋利、为上司分忧的忠诚雇员;工程师与缺少工程教育背景和现场经验的经理存在交流障碍;工程师对仕途抱有期待而不愿与上司发生正面冲突,上述情况共同决定了采取“组织公民式”伦理行为的工程师少之又少。
3.3 工程师力量的“偏好性选择”损害了公众对工程师职业角色的正向期待
工程失败后的责任推诿,会彻底葬送公众对工程师的职业期待,使其从令人尊敬的“社会仆人”滑落为“勤勉的破坏者”。工程师是涉及专业知识、自我管理与公共利益的“专门职业”(profession)。乔治·伯纳德·肖指出:“对于外行来说,所有的专业人员都是合谋者”。工程师若想欺瞒公众,凭借其独占的专业知识和执业时的自主权,易如反掌。米切姆认为:“角色的变化使得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仅要承担职业责任,还要额外承担对公众的责任”[15]。正因如此,有时“工程师往往被赋予了太多权力,并代替公众独立做出了决策”。工程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以公众为实验对象的社会性试验,这决定了工程师成为“社会变化的催化剂”,必须符合“遵守社会规范的游戏者”这一角色的规制。但米切姆却坚称:公众讨论使得“工程责任……看起来像是缩小而不是增大的”[3]。这导致工程师“偏好”根据项目成功与否选择性地抢功或卸责。正如小布鲁默所说:“为了赢得公众和社会对工程事业的信任和支持,工程师声称工程是科学。一旦发生技术事故或者灾难,工程师又辩解说工程不是科学,在工程中出现风险和失败是难免的”。为摆脱这一责任困境,一是要引入查尔斯·佩罗称为“正常事故”(由复杂工程设计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紧密结合性”和“复杂相关性”而引发的无法归咎责任主体的事故)的概念以帮助工程师洗脱“污名”;另一方面,米切姆强调“考虑工程的伦理问题不再是专家们的事情,而是这个时代所有人的事情”[15]。应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使公众参与到科学技术事务中,从“专家统治”向“公众参与”转变,在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之间倡导“合作责任”(Co-responsibility),即积极倡导公众讨论和技术评估[16]。
4 知识与力量共同助推工程师依循合理限度履责
工程师仅仅承担技术责任远远无法满足公众期望,但扩大化“普遍责任”对工程师又过于沉重。这使得米切姆“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这一定义,既能升格为工程师当责的重要依据,也能变身为工程师推诿的借口。这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要合理设定工程师的责任限度,必须建立基于知识与力量的不同组合,以确保其真正实现言行一致;二是部分工程师之所以只能“力所能及”地承担责任,恰好是因其知识局限和力量有限所致;三是每一伦理问题的解决,既是对工程师履责意识的强化,更是对其知识创造和力量升级的共同促进;四是某些工程师愿意“道德自觉”地承担责任,既决定于道德敏感度与所处知识周期的契合度,又取决于道德发展历程与力量能级的相关度。
4.1 知识与力量的不同组合是合理设定工程师责任限度的重要依据
“工程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存在争议。反对之声如塞缪尔·佛洛曼的观点“工程师的基本职责只是把工程干好”[3],工程师因其掌握的知识和掌控的力量有限,无需承担责任。赞同之声如斯蒂芬·安格的主张“工程要致力于公共福利义务,社会就要给工程以学术自由的环境,工程师则必须拥有开展道德讨论、不断提出争议甚至拒绝承担他不赞成的项目的自由”[3]。民众常因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及其客观性和中立性,将其视作权威。一旦工程有难,公众就认定工程师难辞其咎,必须接受伦理审判。K.D.阿尔伯恩甚至高调宣扬:“工程师有责任做出个人牺牲,来唤起公众对有缺陷的设计、有疑问的实验、有危险的产品等的注意……工程师(必须)乐于做出比常人所通常要求的更大的个人牺牲,这使得工程师是一定意义上的道德英雄”。
随着人类对责任范围认识的不断加深,工程师应当承担扩大化“普遍责任”的呼声日渐高涨。例如,汉斯·尤纳斯就坚持“把责任的范围扩大到对全体人类特别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包括物种在内的整个自然界”。对此米切姆却不敢苟同。他认为:“工程师个体只是假定对其行为的直接后果负责,不能对大量技术行动后果负责”。这意味着工程师只能根据其知识多少和职位高低决定其“是否出力”、“出多少力”以及“向何方出力”,却保障不了“行为善”必然能导致“结果善”。
责任范围扩大并非好事,由此衍生的责任界定模糊、互相推诿以及难以胜任可能削弱责任主体的职业责任感。正如哈耶克所说:“在现代社会中,责任感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责任的范围被过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对其行动的实际后果却不需要负责”。从米切姆的责任内涵可知,与其强迫工程师承担扩大化“普遍责任”,不如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知识与力量的不同组合,合理设定责任限度。
4.2 工程师解决伦理问题的过程伴随着知识创造和力量升级
工程师履行责任的过程中,会促进知识创造,激发力量升级。知识创造的成效取决于“知识共享”的程度。经过知识螺旋模型(SECI)的群化(socialization)、外化(externalization)、融合(combinat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四个阶段,知识转化机制使得新知识从小到大、由浅到深地扩散,形成知识资产。“在每一个组织中都有‘知识市场’在运行,这些知识市场中有知识的买家、卖家和经纪商”。如果企业设立基于利他主义原则的知识转移形式,如“师徒制”,将使工程师代际间更易实现工程知识互通。任何伦理冲突的消解,都有赖于冲突各方充分沟通与彼此坦诚造就的知识共享。只有充分了解达成利益均衡所必需的各项知识,才能摆脱伦理困境。借助用沟通理性代替以往的工具理性,知识分享催生出价值共识。随着各种不同伦理难题的一次次化解,工程师面临两难抉择时的判断力和解决力都会同步上升。责任的承担会带来组织对工程师的角色信任以及公众对工程师的职业认同,这会继续强化工程师创造知识和积聚力量的自信和激情。
4.3 知识局限和力量有限限定工程师“力所能及”地承担责任
工程师属于用脑多于用手的知识型员工,知识展示工程师履行职业责任的智力资本。知识固然是力量,但知识能够组织、选择、学习和判断的力量,不仅来自于信息和逻辑,更重要的是源自价值观和信仰。只有“价值多元、信仰坚定”的工程师,才能将知识真正转换为力量。
工程师对工程控制权的大小及其所处岗位的差异,决定其担责能级。在雇主控制的“他治”市场中,“主仆”地位决定了工程师基本无“话语权”。防止失职的职务责任和嘉奖尽职的责任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从事具体工程活动的“基本行为主体”是企业[17],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工程师显然不具有合理性。“对于超过他们能力和控制之外的政策与决定,他们不负道德责任”[18]。责任的承担需要两个前提:行动主体对道德规则以及行为后果拥有起码的认知力;具备自由意志力。工程师认知力的局限阻碍其自由意志力的增长。多数工程师囿于知识局限和力量有限,担负法律和专业伦理准则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底线责任已属不易。让其承担符合“公众认为正常而慎重的理性标准”之合理关注的道德责任,殊为不易。至于关照超出职责要求之上的符合善举的“普遍责任”,更是强人所难。承担有限度的责任,才是实现工程师伦理自由的必经之路。
4.4 知识周期和力量能级助推工程师“道德自觉”地承担责任
工程知识的多元化特点决定了工程师“当责之力”的获得必须循序渐进。工程知识的多元化体现在:第一,工程形态的日益复杂化决定了工程知识必须具备多元走向才能与之匹配;第二,工程实践是由不同利益主体广泛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参与各方拥有的差异化知识使得工程知识多姿多彩;第三,知识本身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化左右着工程知识的多元化趋势。工程师的道德敏感度与其所处知识周期(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阶段关联甚大。对重要信息的无知会明显阻碍负责任行为的出现。
工程师的道德发展历程决定其力量的能级。哈里斯说:“当人们有意识地做某事,或者使它存在或发生时,那么他们就应该对它承担道德上的责任”。米切姆认为工程师的责任观有三:一是强调对公司忠诚;二是强调技术专家领导;三是强调社会责任[19],工程师的责任向着公众和社会领域拓展。若工程师了解伦理行动更能获得职业认同和公众嘉许,那么道德自觉就会升级为工程师当责的主要驱动力。工程师是否具备道德敏感并依规行事,与其所处个人道德发展阶段相关。理查德将专业人员个人道德发展总结为三层次六阶段,充分论述了工程师在道德发展阶段上达到的层级越高,就越倾向采取符合道德的行为。当然,能进行道德推理和做出道德判断并不表明道德行为的必然出现。只有将道德认知转换为真正的道德执行力,工程师才称得上真正履责。
5 结论
工程师是有着广泛责任以确保技术改革最终造福人类的人,这使得工程师如何担责成为重要议题。米切姆定义“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寓意拥有职业技能和专业权威的工程师可以不卓越,但不能缺少责任心。囿于伦理知识的匮乏,工程师意识不到工程问题的伦理意蕴,单纯以技术思维寻找解决方案只会一再陷入伦理困境;限于力量的弱小和分散,工程师即使愿意直面工程所涉的伦理议题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上述两块短板使得工程师常受人诟病“不愿担责,明知有害而为之”。知识是道德的基础和来源,能破除扰乱人心的假象。作为最重要的智力资本,工程知识的结构分类极大提升了工程师辨识责任的能力。“知识就是力量”表明工程师获取知识的同时也赢得控制自然的理性力量。工程师力量的复杂多变警醒工程师审慎对待责任。知识与力量的不同组合,共同助推工程师“道德自觉”且“力所能及”地履责:一方面,工程师负责以某种方式实现“工程善”,并驱使其在知识更新、共享、创造等方面不甘人后,体现责任的前瞻性;另一方面,工程师应当依其行为获得“赏善罚恶”的合理对待,并鼓励其在力量增长、聚合、效用等方面审慎决断,契合责任的后视性。更重要的是,工程师解决伦理问题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知识创造和力量升级,二者形成互促互助的良性循环。当知识与力量相映生辉,“能够作为一种途径达到技术与工程的更好的自我理解”时,工程师才能真正做到兼顾技术标准和伦理规则的“批判性的忠诚”。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可以分为四类:必须承担的直接责任、选择担当的共同责任、采取行动的见证责任以及表达关切的未来责任。工程师可依其物、我、人、天四重人生境界选择承担何种伦理责任,以达到合理限度履责的目的。其合理路径为:“物”向,应顺习而行,技术祛魅;“物我”双向,要抉择义利,寻求功名;“物我人”三向,需尽伦尽职,穷理尽性;“物我人天”四向,能天人合一,求真求实。最终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将承担伦理责任视为工程师职业追求的自我关照[20]。
[1]Mitcham C,Shannon R D.Engineer’s Toolkit——A First Course in Engineering[M].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9.
[2]查尔斯·E·哈里斯,迈克尔·S·普理查德,迈克尔·J·雷宾斯.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第三版)[M].丛杭青,沈琪,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3]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等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4]况志华,叶浩生.责任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5]罗竹风.汉语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曹南燕.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J].哲学研究,2000,(1):45-51.
[7]秦婧.面向技术风险的工程师责任伦理探析[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6-21.
[8]Mitham C.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9]Vincenti W G.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10]邓波,罗丽.工程知识的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31(4):35-42.
[11]王进.论工程与伦理的融合[J].工程管理学报,2015,29(1):23-27.
[12]田鹏颖.从技术的思想到技术的伦理学转向——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思想述评[J].哲学动态,2005,(4):26-30.
[13]Nelson C,Peterson S R.A moral appraisal of costbenefit analysis[J].Issues in Engineering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Activities,1982,108(1):21-25.
[14]霍尔斯特·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M].李兆雄,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5]Mitcham C.Co-responsibility for research integrity[J].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03,9(2): 273-290.
[16]Mitcham C.Why the Public Should Participate in Technical Decision Making[C]//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Hennebach Lectures and Papers(1995-1996).Colorado: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Press,1997:29-38.
[17]李伯聪.微观、中观和宏观工程伦理问题——五谈工程伦理学[J].伦理学研究,2010,(4):25-30.
[18]Vesilind PA,Alastair SG.工程、技术与环境[M].吴晓东,翁端,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9]Mitcham C.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M].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7.
[20]王进.境域关注下工程师伦理责任归咎限度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29(10):38-43.
Reasonable Lim it of Engineer’s Responsibility from M itcham’s Responsibility
WANG Ji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4,China)
Engineering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and changed the course of human society,which makes the engineer’s undertaking responsibility an inevitable necessity.Carl Mitcham defined responsibility as a function of knowledge and power.With the increasing of complexity ofmega-projec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whether Responsible Engineer as amajor force forhuman progress should undertake the enlarged responsibility remains to be considered.The definition includes three meanings:(1)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of engineering knowledge greatly enhances the engineer’s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responsibilities.(2)The complexity of engineer forcesmakes the engineer alert to the responsibilities.(3)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knowledge and force jointly boost the engineer to fulfill responsibility within reasonable limits.Only through discriminate the connotation of Mitcham’s responsibility,fully aware of engineer’s knowledge and power limitations can we understand the responsibility within one’s ability.And then we can look forward to engineer’smoral and ethical conscious introspection.Thus good engineering can be well done.
reasonable limit of responsibility;engineer;engineering knowledge;power;carl Mitcham
B822.98
A
2095-0985(2015)04-0020-07
2015-05-24
2015-07-20
王进(1972-),男,贵州湄潭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工程伦理(Email:csruwangjin2@126.com)
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2013-X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