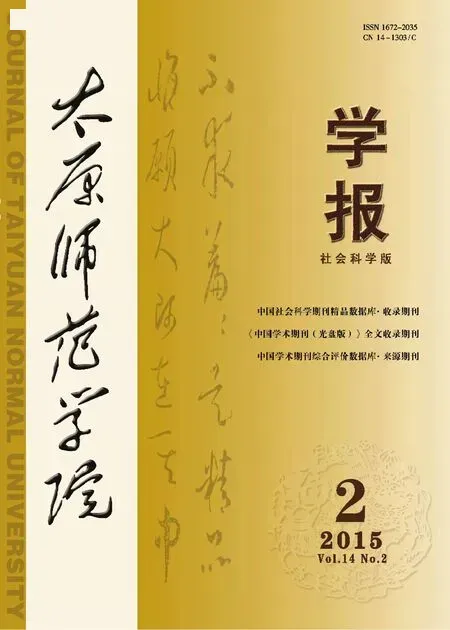重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何建朝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以其浓厚情意、质朴天然的艺术魅力千古传诵不绝。我们知道,并不存在通向任何一首伟大诗歌的唯一真实的道路,在其多种多样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从某一角度看来都可能是一条歧途,在对待此诗的阐释上,亦复如是。“阿尔都塞将通过斯宾诺莎这个参照来理解马克思的过程称为绕弯。……直接阅读是无法达及其思想本质的,只能通过将第三者的著作与所阅读著作进行交叉阅读才能有可能。”[1]108我们可以试着运用这种“征候阅读法”来阅读。笔者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再重复此一诗篇所表现的兄弟之情谊、亲人之思念,也不是将重心放在其结构如何巧妙、构思如何精致上,而是在新的视野下发掘文本的“新信息”,这种发掘,可能会让人有牵强附会、无中生有的过度阐释之感,但是,我们从新的“参照系”扩展出去的不仅是诗作本身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与时代文化的重新“映射”。以王摩诘这首被认为是抒情诗的其早期作品为例,我们可以按照奥古斯丁的“历史、词源、类比、寓言”或阿奎那的“字面、寓言、道德、奥秘”等解释层面重新解读该诗,然而,对字、句的揣测,细微已甚,更关键的乃是如何接通整体以寻找如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
一、寻找“家园”
王维此诗作于开元五年(717),时年十七岁,此时,距其来长安已两年之久,在开元三年其十五岁时就离家赴长安,《旧唐书》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2]5052可见,王维精通诗画、音乐,天赋才高,所以在京城成为王公贵族争相交际的宠儿,到开元九年其二十一岁时,便擢进士第。在离开蒲州后对家乡、亲人、兄弟的思念不可避免地引发在“重阳”的节日庆典中,借用其擅长的手段表达此情感,以“忆”为基石,由兄弟→亲人→家乡,此一层思念可从文中“显”见,虽题为“忆山东兄弟”,但此“亲”不仅是“兄弟”,而是象征着更广泛的“亲”,甚至推至对故土家乡的“亲”。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年十七)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3]1306
但如若我们只停留在此一阶段,而不对那在感觉中稍纵即逝的“理性”之光做出片刻的回应,那我们将会错过“上升”至另一“家乡”的机会,这里的“家乡”是切近本源的地方,“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4]15。游子思乡在诗歌中是一个永恒的、常见的主题,而其之所以有此艺术魅力和精神吸引的原因可能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明白的,然而,窃以为中国传统的安土重迁情节背后除开经济、政治或文化等因素外有一种潜藏的家园归属感,这种感受是被上述因素包裹的,但如果剥开层层外衣,核心的应该是心灵对精神“家园”的眷恋,这种依恋实则涵盖了其相反的一面,即流浪,即使对一个喜爱流浪的人或民族来说,这种对“家园”的“背弃”无论是被动抑或是主动皆源于其对立面,也就是说统率这种行为的仍然是“家园”责任感,对“家园”的背离或逃避是一种异变了的依赖,就像我们常说的,离家越远心却离家越近,这种流浪是处在不断寻找新的家园与不断抛弃家园的过程中,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纯粹理想的“自由”,但人们却不经意地陷入了“消极的自由”而不是在“积极的自由”中寻找归属,所以,尽其一生或整个民族在前进的路上步入无休止的循环歧途。“‘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即‘自由地发展’之自由并不是一回事,人脱离大自然独立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赖以发生的世界连为一体,仍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他赖以生存的大地、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动物及血缘群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24也就是说一味地将逃离“家园”作为“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的途径,最终虽然从“始发纽带”中抽离出来,却无益于到达“积极的自由”领地。由此可见,真正的对“家园”的背离或依恋都是基于那种对“家园归属”的认同感,无论是安土重迁还是浪迹天涯。
诗中从始至尾都充斥着一股对本己家园“存在”的寻求,从诗题中的“忆”为起始,由“忆”的对象扩展到对对象存在空间的“忆”,再由所忆对象返回自身的生存状态——“独”,这一“独”却正是“此在”的表现,同时,“此在”并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而是就在“异乡”的大地上展现为“异客”的身份,这种身份不由自主地在九月九日时重回到对家园“亲人”的思念,是以时间属性为契机的,其实,整首诗也是以此为源泉的。在此“思亲”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与此“异乡”大地相对应的“遥远”的大地,此处,大地表现为“高处”,此“高处”是相对于“大地”而言的,是矗立在大地之上的高山,并指向“天空”,因此“高处”在这里是连接“天空”与“大地”的中点,其是一种冲突和抗争与融合和妥协的显现。“高处”一词蕴含一种自身对立和冲突的矛盾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并非无意识地藏于篇中,此关系是整体的枢纽核心所在,“异乡”与“家乡”,“自我之思”与“对象之思”,“客”和“主”,“身”与“异身”,“心”与“归心”之间的对立,皆发源于此。回到“遥知兄弟登高处”一句,在那异地遥远的“高处”图景中行为的主体是“兄弟”,而其行为乃是“遍插茱萸”,插茱萸何为?《尔雅翼》引“风土记曰:‘俗尚九月九日,谓为上九,茱萸至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6]260茱萸具有驱虫除湿的药用价值和避恶辟邪的文化价值,除这两点外,“折其房以插头”这一“插茱萸”仪式化的风俗作为诗作的结尾,不但是承接上一句兄弟所存在的“高处”,而且“茱萸”在此处是“家园”的象征,茱萸这一植物生长于大地之上,人们需要寻找这样一种“继发纽带”来实现其与“家园”联系的安全感。插于头上的“茱萸”同矗立于“大地”上的“高处”一样具有沟通功能,作为天、地、神、人的连接点。站在“高处”的兄弟是连接“天空”和“大地”的“人”,承载兄弟的“高处”是连接“人”和“天空”的“大地”,头插“茱萸”的乡人是连接“大地”和“神”的“人”,插在头顶的“茱萸”是连接“神”和“人”的“大地”。“于是就有四种声音在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地自为地持立和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若没有其他三方,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它们无限地相互保持,成为它们之所是,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4]210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天空”、“大地”、“神”、“人”概念皆是指向“家园”的某一属性,从此一参照来看,“天空”指“高处”所表现的“家园”属性——隐性;“大地”指“异乡”所变现出的“家园”属性——本源性;“神”指“茱萸”所指向的“家园”属性——象征性;“人”指“兄弟”或“亲人”所表征的“家园”属性——实在性。
二、变异“庆典”
作为汉族民间传统节日,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又称“重九节”、“茱萸节”、“登高节”、“菊花节”、“老人节”。据说重阳节源于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流放汉北,他的学生宋玉为他送别的日子,至西汉已成固定节日,魏晋以后更加盛行,到唐代得到官方认可。“重阳”之说来自《易》,《易》中“九”为“阳数”,两九相重,故名“重九”或“重阳”,且“九”与“久”谐音,有长久、长寿之意。
“重阳节”插茱萸的习俗,在西汉时就出现了,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载戚夫人伺女贾佩兰回忆宫中往事时提及“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7]20之风俗,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茱萸”术说:“井上宜种茱萸:茱萸叶落井中,饮此水者,无温病。”[8]279茱萸,具有食用与药用双重作用,具有驱虫除湿、辟邪保平安的功用。可见茱萸在民间传统中具有重要价值,故“重阳节”又被称为“茱萸节”。“重阳”天朗气清、秋高气爽,人们常常邀友结伴郊游登山欣赏山川风光,李白有《九日登巴陵望洞庭水军》云:“九九天气清,登高无秋云。造化辟川岳,了然楚汉分。”[9]1246因此,“重阳节”也称“登高节”。重阳时节正是菊花盛开之时,所以“重阳节”赏菊饮酒吟诗也成为风俗延续下来,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有“更待菊黄佳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10]2604的诗句。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11]463由于赏菊也是“重阳节”的主要习俗,因此,“重阳节”也叫“菊花节”。1989年我国政府把每年的“重阳日”定名为“老人节”,于是“重阳节”在新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了一个尊老、爱老、敬老的节日,一方面突出了重阳节中“九”与“久”的祈求长寿的含义,另一方面将我国传统尊长重孝的美德与现实国情重视老人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应对之举相结合。此外,由于各地风俗习惯的差异,还有一些独特的重阳习俗,如放风筝、吃花糕等。
“重阳节”这一节日从其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风俗仪式的扩展与充实,意义的变化与丰富,如茱萸与重阳,登高与重阳,菊花与重阳,老人与重阳。在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中我们能看到“插茱萸”、“登高处”,甚至其中也已经有了尊老的表现,忆兄弟、思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自己由于不能在家尽孝悌之道的悔恨,通过诗歌的艺术形式以减轻、冲淡由此所造成的哀伤。在此诗中与重阳相关的众多事物中缺少了菊花这一重要形式的出场,那么,这种缺失意味着什么?作者对所缺失的原归属于重阳的范畴是不表达还是不可表达我们无从窥测,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此也只能将其抛掷出来而未能找到合适的理解途径。
“九月九日”表明了整个诗作的背景所在,那就是重阳日的到来,我们可以将这一节日看作“庆典”,且其中暗含了群体的狂欢情节,从“重阳日”众多的习俗和活动可以看出,又登高,又插茱萸,又赏菊花,又饮酒,又思亲,又吃菊花糕,等等,人们将其当作是一次集体的狂欢。我们拈出第二句诗中的“每”字来寻求另一种解释空间:“每”字表现出“重阳”这一庆典的重复性,“庆典”形式和内容都可能会随着历史的迁移而发生变更,而只有在这一“重复性”中才能看出此“庆典”的本质规定,“每”在这里展现的不是一次庆典活动中的“此在”的境域,而是扩展为不止一次的节日庆典活动。我们与作品的接触其实是与自我的接触,类似于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这样,我们在不同的视界中作出不同的评估,而不同的视界也是随着“庆典”的演变而转移的。“节日庆典活动是一次次地演变着的,因为与它同时并存的总是一些异样的东西,某个同样遭受到这种演变的节日庆典活动,依然是处于这样的历史存在体中的。节日庆典活动本来就是这样的,并这样被进行的,以后它就演变为变化了的活动,然后继续演变为再变化了的活动。”[12]179由此可见,作为这种“庆典”活动一旦从其原初的起源中脱离出来后就处在不断的流变中,这不仅为“重阳”这一“庆典”本身内容的嬗变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为重新看待《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寻找到一个支撑点。
[1] 庞晓明.结构与认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彭定求,等.全唐诗[G].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
[5]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6] 王维(撰),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7] 葛洪.西京杂记(古小说丛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9] 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8.
[12]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文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