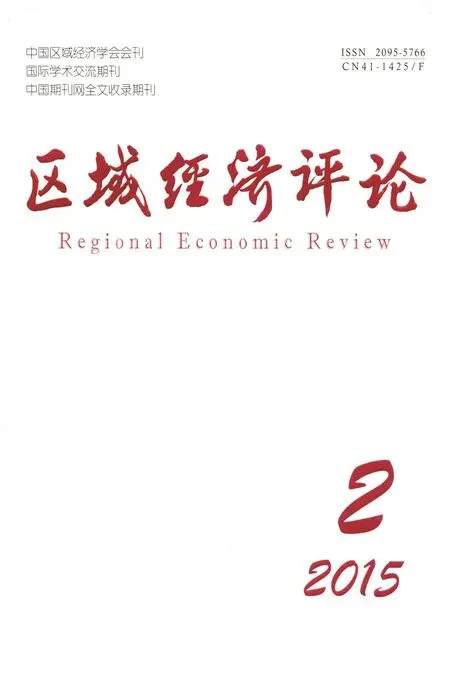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概念辨析、构成要素与判断标准
孙根紧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国家纵向投资和高速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1],这一现实困境促使学术界对诱使地区发展差距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路径进行不断探索,其中一部分学者就将研究焦点放到了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之上。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文献多关注如何培育和构建西部特定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而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内涵以及水平判断研究尚有不足。鉴于此,本文在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内涵进行辨析后,从不同视角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并归纳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特征,进而探讨一个地区在不同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的发展表征,以此对“什么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一个地区实现了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等问题做出回答。
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辨析
国内外诸多学者基于对“自我发展”的理解,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尝试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内涵进行深层次阐释。但时至今日,学术界仍未就这些内容达成共识,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与内涵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已有界定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在国外区域发展研究领域,虽有“自我发展”(Cornelia Flora et al.,1991)[2]和“自我发展战略”(Gary P.Green et al.,1990)[3]等词汇,却无“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与的相对应的是“地方化能力”(Peter Maskell,1998)[4]和“自我振兴能力”(Toni Saarivirta,2007;Kati-Jasmin Kosonen,2008)[5][6]。Jan L.Flora et al.(1992)[7]将自我发展定义为一个地方项目的实施或一个公司(或几个公司)的创新,但更能让我们接受的概念是“一种主要依靠创业精神和本地资源的内源性发展”(Jeff S.Sharp et al.,2002)[8]。Peter Maskell(1998)[4]认为“地方化能力”包含制度禀赋、现有结构、自然资源和知识与技能等四种要素。Toni Saarivirta(2007)[5]认为一个地区的自我振兴能力源于个人层面的学习过程,在企业、组织、机构和区域层面上具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而开发、勘探、吸收、整合、领导力以及社会资本则构成了自我振兴能力的合理内核。
在国内学术界,唐奇甜(1990)[9]首先尝试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界定,他基于生产力发展角度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定义为“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是一种“在任何灾害的情况下能保持自治、自理、自强的能力”。这一概念虽不严谨,但却给后续的研究者以重要启示。之后,诸多学者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概念进行界定,按区域发展与“外围力量”的关系大致可以将它们分为两大类。第一种观点强调区域发展的内源性,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定义为区域主体在没有外部扶持情况下,依靠区域自身力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10-12]。第二种观点强调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明确表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与外围力量之间并非互斥关系,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外围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13-15]。
从学术界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到,学者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内源性达成了共识,但他们只是揭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概念内涵的部分内容,并没有完全触及其本质内涵。
2.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再界定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不仅要体现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一般性内涵,还要体现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空间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概念中应该体现出“自我”二字的特殊含义。基于此,本文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区域主体基于自身条件,依靠区域内部系统发展机制,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通过对区域内外部稀缺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
第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针对推动区域发展的“外力”提出来的,关键在于其独特的发展机制——自我发展,即它是一种充分依靠和挖掘区域系统内在潜能来实现发展的能力。
第二,虽然区域自我发展是指区域依靠系统内部力量推动的自身发展,但是并不意味着区域发展是在封闭环境条件下实现的。由此以来,在自我发展能力驱动下的区域发展过程中,对稀缺性资源的利用是开放性的,既有内部资源的有效安排和外部资源的大量集聚,又有对区域内外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是一种必然选择。
第三,虽然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区域内部家庭、企业、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微观主体能力水平的综合体现,但是这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并非单是这些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央政府和其他关联地区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强调“自我”的发展机制并不意味着否认或摒弃外部力量的推动作用。在更多情况下,特定地区只有形成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外部推动力的预期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区域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而外部推动力决定着这一过程速度的快慢。
3.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
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们就利用各种资源来进行生产,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多样性的生活需求。由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这种资源配置问题不仅存在于经济部门之间,也反映在不同地理范围之间[16],这就是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一个地区对稀缺性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因此,区域发展过程也是区域发展主体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过程。
区域层面的稀缺性资源配置存在着竞争性。由于大多数稀缺性资源具有可流动性,因而,即使是分布均匀的稀缺性资源,在区位效应作用下也会向某些地区集聚[17]。一般来说,稀缺性资源从低配置效率地区流向高配置效率的地区,因而那些能够聚集资源的地区往往是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这样就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一个地区为了实现自身发展,就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吸引、集聚、利用区域内外部的稀缺性资源。
无论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通过地方政府调控使得区域占有和利用更多的稀缺性资源,并实现其合理配置,所实现的区域发展都可以称为自我发展。中央政府出于某种战略考虑实施宏观调控,或者是其他区域出于人道主义实施援助,以投入大量发展要素来推动某一地区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就是外源性发展。与地区自我发展相比,虽然中央政府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来进行稀缺性资源配置确实会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效果,但由于国家不可能永远通过倾斜性政策来推动某一地区实现高速发展,因此这一机制缺乏持久性。进一步讲,对某一特定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来说,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缩小其与发达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关键,仍在于依靠自身力量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对稀缺性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看来,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就是特定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部稀缺性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
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
区域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复合体,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从而导致特定地区所具有的自我发展能力也是一个复杂系统,由诸多要素构成。这些构成要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有机整体。下面本文分别从发展主体、发展内容和实现状况等角度来阐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
1.发展主体
区域主体可以从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来区分,从宏观层面上讲,一个地区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独立主体的行为特征;从微观层面讲,区域行为主体包括家庭、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某一特定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也可以区分为宏观层面上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微观层面上的家庭自我发展能力、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和非政府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宏观意义上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一般性概念,指的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行为主体基于自身现实条件,依靠系统内部发展机制,通过有价值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而实现的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的各种组合和可能性。
从微观意义上看,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家庭成员作为社会生产劳动力的供给者,所具备的人力资本状况,它包括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预期寿命和道德素质水平,等等。
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完全可以通过林毅夫教授的企业“自生能力”来理解。他根据某一特定产业部门或某一特定企业在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的预期获利能力——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如果在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很显然,如果一个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18]。在这里,“自生”不仅有生存之意,还包含成长、发展、壮大之意。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理解为企业在实现基本生存基础上,不断实现规模扩大,竞争力增强的能力,具体包括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产品竞争能力。
政府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各级政府自觉地履行其职能的能力,它在执政过程中得以体现,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基本保障。具体说来,政府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地方政府为区域自我发展提供所需要的硬件设施和法律制度、文化软环境、区域财政和公共品的能力。
非政府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地方非政府组织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发挥作用以规避市场和政府“双失灵”风险,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在维持区域内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发挥着关键作用。
2.发展内容
发展经济学认为,区域发展过程就是区域发展主体对区域内外资源的创造、集聚和利用,以及协调各种发展活动的过程。这里的发展活动不仅包括社会生产领域的组织活动,也包括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其他环节的组织活动,还包括区域主体为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内容之间相互关系的活动。鉴于区域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划分为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
创新开发能力不仅指区域主体在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新的原材料供应地和新市场的开发等方面的能力,也包括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以区位条件和生存环境,以及适应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而进行制度和体制改革的能力。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创新开发,不单单指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还包括基础理论的推进和市场开拓。
要素集聚能力就是吸引、凝聚生产要素的能力。这里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力,还包括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知识、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这里所说的生产要素集聚,不仅指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向某一特定的次级地域空间集聚,形成区域内部的集聚经济区,也包括吸引区域外部的生产要素不断流入区域内部,增强区域内部的生产要素密度,形成这一地区的集聚优势。
资源利用能力是指区域发展主体所具有的,由区域创生或集聚在区域内部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并最有效率地将其转换为社会财富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和产出水平两个方面。
协调发展能力不仅包括区域发展主体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与消费、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区域差异等问题的协调能力,以及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差异性问题的协调能力,还包括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等协调发展的能力。
3.实现状况
从实现状况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分为现实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现实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某一特定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发展能力,体现为区域系统立足自身条件,使得区域内部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资本积累能力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效率日益提高,实现经济发展内生化。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现实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作用的发挥程度,往往由区域内部经济社会运行的现实状况来体现。
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某一特定区域具备某种特定优势,或者某些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区域系统内部某些环节出了问题,使这种优势不能得以发挥,或这些有利条件不能有效地得以利用,以促进区域发展,因此这种优势或有利条件就仅仅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而没有转换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一个具备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往往具备了实现自我发展的多数基本要素,但是缺少某种能够使得这些要素相互作用以生成自我发展能力的机制,这一地区便不具备或者逐渐丧失由区域内部力量推动的“自我式”发展。如果通过外力或者内部的自组织力量实现了能够使这些基本要素相互作用产生自我发展能力的机制,那么这个地区就会逐渐形成或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水平的高低往往由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要素来决定,而它往往又决定着区域未来的自我发展趋势。
在构成要素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综合性。从发展主体上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家庭、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四类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而成;从发展内容上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综合而成。因此,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第二,系统性。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构成的能力集。第三,阶段性。按照能力水平高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发育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尚无自我发展能力阶段、较低水平的自我发展能力阶段、较高水平的自我发展能力阶段和完全具备自我发展能力阶段。第四,动态性。随着构成要素匹配效率的不断变化,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也会不断变化,从而导致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出动态性特征。第五,空间一般性。任何地域空间都会面临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问题,而且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来说,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问题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第六,可塑性。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可塑性指的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区域主体的努力和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地区的援助来获得。正是由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可塑性特征的存在,所谓的区域开发实践活动才具有现实意义。
上述基本特征体现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特殊性质,使其表现出一些独特征象和标志,从而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区域发展能力。
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判断标准
在发展过程中,特定地区在不同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都会因为具有不同的自我发展能力构成要素,而表现出独特的自我发展特征,这些特征就成了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及其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高低的标准。
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特定地区几乎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经济发展缓慢或处于停滞状态。在中央政府倾斜性政策的支持或其他地区的援助下,区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供给状况虽然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是如果外部推动没能使这一地区形成一定水平的自我发展能力,仍不具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也就很难实现,那么这一地区的发展就不具备持续性。一旦外部推动力量消失,这一地区仍会重返“无发展”状态。总之,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要么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状态,要么在外力推动下缓慢发展,即使出现了短暂的经济复苏迹象,也很难实现持续性发展。更重要的是,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即使在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的援助下获得了暂时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但没有可持续性,而且是没有“效率”的增长,也势必会造成援助资源的浪费,其原因在于这种外援式推动发展很难通过自我发展能力这一内因发挥作用。
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或是自身发展条件的改变,区域系统内部开始形成资源集聚与创生能力。其中更多时候是立足于本地区内部资源,尤其是依托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等特色产业不断发展,资本积累能力逐步增强,区域积极参与产业分工和对外开放,经济结构逐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日益提升,由此以来,这一地区就进入到了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具备较低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科技教育文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产业结构开始踏上转型升级的路程。虽然技术创新能力水平仍然较低,但区域系统内部已经产生了发展冲动,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不断涌现。此时,这一地区就能够较好地利用外部援助为区域发展所用,也就是说,能够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实现较快发展。即使没有这些倾斜性政策支持与援助,区域经济系统也能够依靠内部力量实现内生化发展,但是发展速度会大大放慢,甚至有再次陷入发展停滞状态的危险,这些地区仍然属于“问题区域”,需要国家实施倾斜性区域政策来给予大力支持。
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或者通过自身发展的不断积累,特定地区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形成了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这时该地区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水平的地区,区域系统能够吸引区域内外各种资源流入区域内部,并且实现了较高水平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具有较强的资本积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区域经济的较快发展,成为新兴“崛起地带”。这些经济发展“新星”已经具有较高水平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它会积极寻求各种发展资源为其所用,不再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也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
在内生发展力量推动下,区域内部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对区域外部的各类资源也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区域内部技术和组织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由此以来,该地区就形成了完备的自我发展能力。此时,区域系统能够对区域内外资源实现最优配置,并且能够自动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具备完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往往是一国或某一较大地域空间范围的增长极,它不仅具有较强的内聚功能,能够依靠自身力量集聚大量资源,而且具有较强的扩散功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来带动周围腹地的较快发展。
对处于不同水平阶段的地区来讲,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发展的重点、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和可能采取的发展手段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过程中,就处于同一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的不同类型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构成要素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同一地区在不同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的自我发展能力要素构成进行历史演进角度考察,对这些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提升抑或维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1]孙久文,夏文清.区域差距与亟待解决的问题[J].改革,2011,(6):48-53.
[2]Cornelia Flora,Jan L.Flora,Gary P.Green,et al.Schmidt.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Local Self-Development Strategies[J].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Summer,1991,19-24.
[3]Gary P.Greena,Jan L.Florab,Cornelia Florac,et al.Local Self-Development Strategies:National Survey Results [J].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 Journal,1990,21(2):55-73.
[4]Peter Maskell.Low-Tec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the Role of Proximity:The Danish Wooden Furniture Industry.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1998,(5):99-118.
[5]Toni Saarivirta.In Search of Self-Renewal Capacity—Defining Concept and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University of Tampere Research Unit for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Sente Working Papers,2007,(10):1-11.
[6]Kati-Jasmin Kosonen.Strengthening Self-Renewal Capacity in the Inno Steel Platform in Hämeenlinna, Finland.University of Tampere Research Unit for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SENTE Working Papers,20/2008.
[7]Jan L.Flora,Gary P.Green, Edward A.Gale,et al. Self-Development: A Viable Rural Development Option[J].Policy Studies Journal,1992,20(2):276-288.
[8]Jeff S.Sharp,Kerry Agnitsch,Vern Ryan,et al.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Case of Self-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cruitment in Rural Iowa[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2,(18):405-417.
[9]唐奇甜.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若干思考[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1-6.
[10]周亚成,兰彩萍.新疆牧区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浅析[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72-75.
[11]徐君.四川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6):41-46.
[12]郑长德.中国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J].民族研究,2011,(4):15-24.
[13]鱼小强.对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思考[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9):11-14.
[14]王科.中国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解构与培育[J].甘肃社会科学,2008,(3):100-103.
[15]杜青华,窦国林.青海东部干旱山区扶贫对策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11,(1):47-50.
[16]徐康宁.产业聚集形成的源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18]林毅夫,刘培林.能力和国企改革[J].经济研究,2001,(9):6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