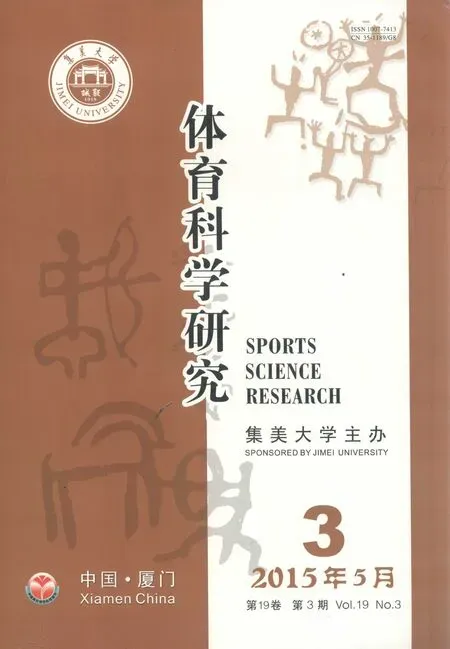后现代课程语境下体育课程的文化思考
牛建军,王枫林
(泰山医学院体育教研室,山东 泰安 271016)
后现代课程语境下体育课程的文化思考
牛建军,王枫林
(泰山医学院体育教研室,山东 泰安 271016)
在充分认识后现代课程观理论基础上,分析传统体育课程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困惑:传统文化驱控下体育课程钟摆现象;工具性逻辑导致体育课程的文化之性缺失;“礼”“忍”文化秉性与体育教学权威的形成。从后现代课程观视角出发,构建新型体育课程文化观:体育课程内容体现多元性和动态性;回归体育课程文化逻辑;追求体育课程文化自觉。
体育课程;文化冲突;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是西方世界兴起的一股文化思潮,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批判与反思各学术领域也成为一种必然,这其中也离不开教育领域。[1]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便是在这一文化思潮背景下,利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思潮对现代主义课程观批判与反思的结果,“是自社会改造主义文化观以来的文化不断拓展,深化的结果,是批判与反思性课程文化观的‘集大成者’或最新发展”。[2]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虽没有形成系统的、规范的理论体系,但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树,对于构建新型体育课程文化观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 后现代主义课程文化观
后现代主义课程文化观是在对现代主义课程文化观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从解构与建构两个维度发展而来。它主要是针对封闭化的、认同主义的、决定论的课程文化观,转变课程的文化逻辑,从而使后现代主义课程文化观完全突破那种把只认同而不求异、只掌握而不建构的课程文化作为文化传承工具的逻辑。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课程是实现社会及文化变革的工具,为文化的发展及创新提供核心机制,它不仅可使学生掌握单一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有利于学生了解更为广泛的知识,增进学识,激发和改造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强调课程知识的多样性、非系统性、文化性、开放性、动态性和过程性,要求从学生的发展、对话、探究、转化的角度来重新厘定认识课程本质,强调张扬学生主体意识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尊重学生个体间差异,促进学生有差异、自由地发展;对教师来说要改变角色,教学过程中的学习和理解来自对话和反思,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的过程中互相影响,教师和学生一起达成共识,教师的作用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师的权威转入情境之中,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
2 我国体育课程发展历程的文化透视
从世界课程改革历程来看,课程改革运动的背后蕴育着文化矛盾和冲突。一般观点认为,文化对课程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影响课程内容;二是文化影响课程类型。体育课程发展也离不开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为作为体育课程的母体,文化不仅决定着体育课程的品性,而且设定了体育课程的逻辑规则和范畴来源,文化变迁必然促使体育课程的发展与变革。建国初期,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和足够认识,加上中苏在当时特殊的关系和凯洛夫教育思想影响,中国学校体育文化主要是效仿前苏联。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和对照搬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反思,中国学校体育开始积极寻求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体育课程体系,将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正式列入教材,凸显了中国学校体育文化独立意识的初步形成。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下“体育课程乌托邦”的伤痛之后,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体育课程也进入学校体育文化的拨乱反正时期。针对当时体育教学大纲提出的“以有利于增强学生体质为基本准则”为指导思想,出现了多种学术观点并存并趋于多元化的局面,各种国外的体育思想和文化开始在中国学校体育这片土壤广泛传播和实验,中西体育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进入新世纪,面对多元化文化的挑战,我国启动了第八次体育课程改革,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级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稿)》,这一体育课程标准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学生为本,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出了“以人为本”的文化选择。[3]以人为本的文化选择伴随着新体育与健康课程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多年中,我们不但没有放弃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体育课程的建设,而且加强了对体育课程建设的文化学研究,这是一种建构新课程理论形态的积极尝试,对于我国体育课程开发和建设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体育课程的文化困惑
在课程与文化关系上,课程即产生之日到几经飘摇的历史时期,一直作为文化的传承工具被理解和运用。历史演绎出课程传承文化的逻辑,而实践又强化了这种认识,于是便形成了体育课程作为文化传承工具这样约定俗成的定论。体育课程自身文化缺失和消解,课程与文化之间形成了工具与目的的关系,体育课程发展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困惑。
3.1 文化驱控下体育课程的钟摆困境
从文化的本性来看,任何一种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后,都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品质。文化所体现出保守的秉性昭示着它最终将被另一种新型文化所取代。任何一种文化范式都将经历产生、完善和没落的历程。文化变迁历程表现出清一色的茧式化理路、机制与逻辑。“茧式文化必将赋予课程茧式框套的约束。”[2]不同主流文化交替更迭为体育课程的发展设置了迥然相异的“文化场域”。体育课程钟摆困境的产生便是不断的、肤浅的适应不同主流文化的使然。文化决定体育课程的品性、逻辑规则和规范来源,不同社会文化形态将赋予体育课程不同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和传输内容。这也使得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研究视角一直都在不同“中心论”之间游移、摇摆,结果是体育课程发展的“钟摆现象”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受文化位移的驱控,使本来不具备文化选择权的体育课程,只能被迫于不同“文化场”之间的“奔波”,像钟摆一样在不同的极点摇来摆去。
3.2 工具性逻辑导致体育课程的文化之性缺失
在后现代课程观看来,传统的课程文化观把体育课程作为传承文化的工具。工具性的体育课程文化观仅是对既定的文化传承与复制,不能积极主动地去更新和创造文化,失去了拥有文化主体性地位。“在文化意义上,课程仅是一个虚概念,不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文化形态而存在,不具备任何文化的品性。”[2]体育课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逃脱对文化的依附,没有脱离文化藩篱,始终秉承“课程家族”的传统——以传承文化作为使命,并将这一历史使命演变成为自己的基本逻辑和立论依据。作为传承文化工具这一发展逻辑,体育课程所包含的文化只能是某种特定文化的外在形态,体育课程体现的仅是一个虚概念,而自身应有的文化品性及内在的、独立的价值标准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殆尽。有时虽被赋予了文化的某些功能和特征,但仍不具备文化所持有的文化基频和本质,体育课程的性质依然就范于某种特定社会文化霸权式话语与规范。传承文化只能使体育课程成为一个失去自身价值存在的文化传递工具,使得由来已久的体育课程,承袭社会文化适应论的工具主义化逻辑和机制,体育课程徒具文化之表,而无文化之性。
3.3 “礼”“忍”文化秉性与体育教学权威的形成
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凝固性、绝对性和控制性品质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文化具有绝对权威和统治力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控制性的伦理文化体系。由这种文化演绎而来的“官本位”、“官至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营造了一种强烈的上尊下卑,归属从安和安分守己的文化氛围和理念。在这种文化理念驱控下,中国体育文化表现出略显保守、重“礼”擅“忍”的文化特质,并长期以来为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保驾护航”,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礼”、“忍”的传统教学观念虽赋予学生尊师重教和师道尊严的优良传统,但对于师长的尊重,教师的权威,已经在传统的教育中达到顶峰。由此造成教师高高在上,学生毕恭毕敬,体育教学看似井然有序,学生的动作整体划一,而实际上学生却苦不堪言。因为在教师的权威下,沉闷、默许成为学生的唯一选择,而看似整齐划一的教学只是养成了学生服从的意识,对于掌握的一些动作技能,不可能激发他们创造的欲望,学生沉闷、默许、服从的意识慢慢形成,教学权威的意识形态已经固若金汤。
4 新型体育课程文化观的构建
体育课程的改革注定要以冲破原有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为契机,寻求一种恰切性的新方法和视角,才能超越试图以定势的戒律演绎未来逻辑的做法。“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是对各种传统课程理论尤其是对被视为现代主义课程典范的‘泰勒原理’进行系统的批判和反思”。[4]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结合我国现代体育课程的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新型体育课程文化观。
4.1 体育课程内容体现多元性和动态性
后现代主义主张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倡不同文化间的共存与发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文化都在积极寻求认同的基础和得到发展与尊重的权力,文化价值观发生着猛烈的撞击。文化差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特征,也是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基础。面对多种异质文化冲突的复杂形势,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以固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来同化外来体育文化的异质因素,保持民族体育文化的原有形态;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培养全球意识和时代感,在重视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提升自身的文化魅力。这里的融合不能理解为简单的结合(那种一拍即合的只能算是完美的结合,最终必然不欢而散),而是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不断创新和融合贯通的过程,体现了在互补和互惠关系中寻求平衡的结合,其结果不是形成单一的他文化,而是赋予原有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互动过程。
4.2 回归体育课程文化逻辑
作为传承社会文化工具性存在,体育课程传承文化实际上是通过传承文化外在化的、技艺化的、形体化的符号形式进行的,没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此时体育课程难免只能在表层结构上“游荡”,其所持有的文化品质消失殆尽。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课程不只是传递知识的工具,也是创造和重新创造我们和我们的文化的工具”。[5]体育课程除了作为传承社会文化的工具外,还具有生成和创新文化的功能。探究体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源自西方的近代学校体育,携带着西方人独立自主和对未知世界不断开拓进取的求真精神;高尔夫球运动展现了英国的“绅士文化”;武术折射出中国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天德合一”思想;瑜伽折射出提倡出世、精神修炼的佛教文化,等等。可见,各种运动项目背后蕴涵着形态各异的文化特质,而作为以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程更应是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对文化的一种表达,是文化逻辑的理性回归。文化逻辑的回归意味着体育课程从过去对文化的占有与传递转变为现在对文化的发生与创造,从作为传承社会文化的工具转变为社会文化的本质存在,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因而以文化的形式出现的体育课程,关注的是体育课程本身的文化意义,凸显出体育课程的文化内涵与文化魅力。[6]
4.3 追求体育课程文化自觉
从文化发展来看,整体性的文化具有自由自觉的特征,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他文化的一种态势。体育课程文化自觉是人们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想态度和思维,是对体育课程文化发展的深度领悟与整体的把握,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思考,是一种执着的文化追求,也是为适应新历史做出的自身文化调整。[7]长期以来的文化工具性逻辑和角色,加上以传统经验、习俗和道德思想等为代表的自在文化排斥和阻挠着体育课程改革的进程,使得体育课程陷入停滞和徘徊状态(文化自在状态)。从力学原理角度考虑,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要改变体育课程的文化自在状态,需要借助于力的作用才行。力从何而来呢?需要一种或多种自觉文化形态向自在文化形态的不断渗入,由于各文化本质和属性的不同,在它们之间便形成一种张力,推动体育课程克服和超越由自在文化引发的惰性,实现由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的跃迁。自觉文化体现了体育课程文化内涵提升,是一种动态发展形态。若要保持体育课程发展的活力,就需要不断地从外界积极吸收优秀的文化因子,与自身文化形成张力,以保障体育课程拥有长久的发展动力,否则,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和更替,体育课程文化将再次陷入自在文化状态。
5 后现代体育课程观的思辨
后现代体育课程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引入体育教育研究而产生的理论,是对现代体育课程价值观的批判与反思。它崇尚体育课程多元价值观,追求体育课程的“过程性”和“流动性”,是现代体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理想目标。后现代主义课程已经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研究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在课程建设上卓有成效。例如,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下出现的课程“三级管理”、“三自主”和“俱乐部”等课程模式,反映了我们对体育教育本质更深层次的认识,寓意着体育课程地位进一步的实质性提升;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对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关注,突出表现了后现代体育课程观以“人的发展”为基点,对知识权威的消解和对人的全面关怀上;他们追求知识的多元融合性,体现了教学由静态、封闭的体系结构转向动态、开放的生成,由关注知识技能的掌握到关注终身体育意识和体育能力的提升;他们更强调一种微化与活化的体育教育,关注焦虑、绝望、行为异常等边缘性道德,引导我们更加注重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这些理念对体育课程与教学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后现代主义思想下形成的体育课程观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和超越的局限性。很多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是一种反对理性的思潮,而对于“以直觉思维见长,习惯于权利崇拜的中国人而言,理性的思维不是多余,而是不足。”正如有体育学者认为,中国学校体育课程的发展更需要理性的洗礼。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学校体育课程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现代性的“洗礼”,“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在中国都没有很好的成长,更没有形成自己在教育上的相对独立力量”;而现代体育课程所提倡增强体质和促进健康的教学目标也离不开工具理性的支撑,理性的科学精神还远没有在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中扎根发芽,“真义体育的现代性理论,对当前体育课程改革仍具有科学指导意义”。[8]也确实,面对一个人文精神失范、科技还不够发达、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的国度环境,中国学校体育课程还没有经历本土化和校本化的理性思辨,在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还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化批判,中国学校体育课程离不开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建设,需要培植理性的精神。
多元文化并存导致的文化价值冲突,使我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和建设面临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争论,更是深刻影响着我国体育课程观的确立以及体育课程领域诸多问题的回答。后现代主义质疑和批判现代性思维方式有其合理性与深切的现实基础,但把后现代主义视为医治现代性痼疾的唯一手段显然不可能。对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我们不能不考虑其生存的环境和不顾我们本国国情而简单移植和随意剪裁,也不能拿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做简单的比附,谈论孰优孰劣,只有运用辩证的思维,系统地认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能对体育课程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刘旻航.无序中的有序——现代体育课程改革的文化审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李平,高成强.体育课程文化选择[J].体育文化导刊,2009(3):106.
[4]崔伟.后现代课程语境下的体育课程改革思考[J].体育学刊,2007(7):76-79.
[5]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6]田菁,石鸿儒,郑颐乐.体育课程价值新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8(6):101-105.
[7]张晓东.课程文化自觉:实现课程改革的文化转向[J].当代教育科学,2004(18):16-18.
[8]何劲鹏,吴畏,姜立嘉.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我国体育课程研究的现代性焦虑与应答[J].体育学刊,2010(10):67-70.
[责任编辑 江国平]
Cultural Think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under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NIU Jian-jun,WANG Feng-l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shan Medical College, Taian 271016, China)
In this paper,in the full knowledge of the postmodern curriculum the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cultural confusion aris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the sports curriculum pendulum phenomenon,instrumental logic leading to lack of culture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Li”,“Ren” culture temperament and the sports teaching authority form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 modern curriculum view,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ports curriculum culture values:sports curriculum content reflects the diverse and dynamic,return to sports curriculum culture logic,the pursuit of sport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ur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culture conflict;Postmodernism
2014-09-02
:泰山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牛建军(1978—),男,山东东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G807.0
A
1007-7413(2015)03-007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