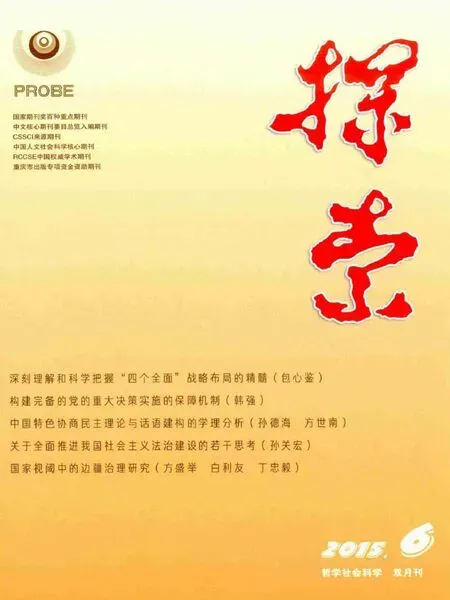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学科形态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1 加强从“学科形态”层面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言,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新阶段》报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及其基本逻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658他在延安整风时期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准确地阐释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2]796,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体。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虽然没有重复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突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式、新途径、新气派,创立“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体,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直接重拾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3]270。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列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10条“宝贵经验”之首,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自世纪之交以来率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不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或者偏重于哲学范畴、(中国传统)文化范畴,或者偏重于“基本经验”层面,或者偏重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基本层面”之间、“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之间的“区分”,而弱于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学科形态”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出的新成果作整体的学理凝练,因而人们对作为“顶层”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等印象深刻,而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学科形态”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所抵达的学术“制高点”有点若明若暗。这种情形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具体理论成果变成“一阵风”或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事”,既不利于它们自身的持续拓展,也不利于它们合乎其理(科学)地持续向下层延伸,特别是向广大民众传播。
应该从“学科形态”层面去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当然,在这种“学科形态”的研究过程中,决不能学院式地来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因为作为“中国化”过程之“矢”——“马克思主义”原初不是以“学科形态”“分批”“分次”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整体地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形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人们在对这一过程的阐释上不妨把它解读成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或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解读它。
2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概念集中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哲学”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词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出现过,而首次出现于列宁的著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中。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从“哲学”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提出了“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延续了这些概念,中国哲学界也续用了这些概念,但他们没有当“传声筒”,而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创造性工作,创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概念。
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中再一次完整地阐明了这个概念。这条以“实事求是”为硬核的“思想路线”被历史性地载入了中共党章,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都对它作了阐释和高度评价。中共十六大报告在它们的基础上侧重强调“与时俱进”,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在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侧重强调“求真务实”,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4]6这一新论断。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概念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简单“翻译”,而是一个富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因为“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一个本体论和认识论“构架”,带着浓厚的学术或哲学气息,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就属于这样的学术性哲学著作,它们的“落点”都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必居其一的(本体论)“决斗”现象。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概念不属于纯“学术品”或“哲学品”,而是一个围绕着党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或历史使命而让“理论”服务于“实际”的真理性“意义”,是一个融“理论”与“实践”或“学术”与“政治”于一体的“结晶体”或“结合部”。“理论只是用来研究实践的一种工具……科学不是一团知识——它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它的理论就是它的方法。”[5]391所以,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基本层面”或“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做法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客观情形或本真形态“变形”了,属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划分。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任何没有理论引领的“实践”都属于“盲的”实践或“伪实践”,任何超脱实际或实践的“理论”或“学术”(成果)都属于某种“空的”理论或“伪理论”,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境界格格不入、与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境界格格不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显然不属于那样的“理论”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确取得了诸多新成就,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概念无疑是其中含金量最重的成果,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上的“学科形态”,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品之作。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引领或潜移默化下,当代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代中国人不仅比之从前更“胆”大,而且比之从前更理性、更虔诚。不难预见,美国昔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通过它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一务实精神经过近140年时间成就为全球超霸,中国通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熏陶,经过若干年一定会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将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集中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经济学”形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词也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出现过,但马克思恩格斯有“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6]596,“《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7]34、“社会主义的圣经”[7]900、“共产主义的圣经”[7]901等论断,列宁提出过“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8]312、“马克思的经济理论”[8]314等论断,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9]573概念。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延续了这一概念。邓小平称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也沿用了这一概念,胡钧、裴小革等学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命题[10]。
尽管邓小平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但他实际上提出了构建这一概念的逻辑思路与关键环节。他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挑明了他对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逻辑关系的态度: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阐明了这一概念得以确立的决定性观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中共十四大正是根据邓小平这些思想观点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这一概念予以系统化、制度化。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出了“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的号令,中共十八大报告具体阐明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与举措,提出“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思路。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学界也提出要加强对包括“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资本市场问题、城乡一体化问题等重大问题的深度研究,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趋向丰富、完善。
显然,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并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简单应用,而是一个富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崭新范畴。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无疑是《资本论》及其手稿。那么,其要旨是什么呢?《资本论》及其手稿从“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研究了这一“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一方面,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历史性功绩与地位: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资本家……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7]683。“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1]927-928“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2]90-91另一方面,马克思论证了这个生产方式早期的“原罪”与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7]743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13]405,以至于“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871。马克思由此在逻辑上推断:随着资本竞争会带来资本集中或积聚,“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7]87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创造性运用。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本”形式、“市场”形式在促进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能量与潜力,强调管理方法、科学技术“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14]765,“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5]373;另一方面守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质的区别性,坚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明的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思想,用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方向驾驭、管控“资本”、“市场”本身所具有的逐利性甚至掠夺性方面。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无疑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济学形态:它通过“体制”形式汇聚、凝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方面的许多成果如社会主义的“本质”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论、社会主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论等成果以及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关于“企业主体”、股份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城乡一体化(即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等学术成果,并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上真正收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红利”。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取得了诸多新成果或创新了多种经济形式、经济举措,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无疑是其中含金量最重的成果,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学上的“学科形态”。正是在这一经济体制及其内在逻辑的驱动下,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高度。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在实践中也出现了新问题,但当年中国若不勇敢地走这步“险棋”而因袭原有的路子,将不可避免地重尝鸦片战争“落后挨打”之苦。不难预见,少数欧美发达国家凭借“资本”力量、“市场”威力在近现代文明史上出尽风头,我们中国通过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发优势”定律,经过一定的奋斗期必定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集中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社会主义”形态
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社会主义”一词早先出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6]131和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6]576中。不过,他们当时是把“社会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而使用的。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开始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概念[17]700;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开始使用“科学社会主义”[17]298,并在其他著述中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尽管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延续了这一概念,中国学界赓续了这一概念,但他们没有“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而是对此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工作,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说:我们不能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他挑明中国人“需要”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正是基于紧紧扣住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实情所作的科学“诊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确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只能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6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确并非直接始出邓小平之口,但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关键内涵或科学所指是由他揭明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15]225;“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15]252;并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5]379-380。中共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特征及其具体运行的“基本路线”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提出“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18]12,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18]13。中共十五大报告由此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十八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进而依凭这个“总依据”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作为一个内容相对独立的、标明社会发展特定水准的“社会形态”范畴,并非是对由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简单重申,而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形态”。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共产党宣言》中被明确阐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422;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则被这样表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364-36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则摒弃了过去那种超越历史阶段即脱离中国国情的穷“共产主义”模式,摒弃了本土曾经有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定势与源自西方那种超时空“人道主义”的抽象玄论,实事求是地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合格”性,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蛋糕”不够大的实情,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进行循序渐进的经济建设工作,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所必要的社会“条件”而脚踏实地地进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
的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有许许多多,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是一个极富中国智慧、极富时空分寸感的科学范畴,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并把它们相互贯通的“基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所须臾不可脱离的“基石”,堪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飞跃在政治智慧、哲学智慧、社会学智慧方面一个地标性“符号”,集中代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飞跃成果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学科形态”。正是在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即“总依据”启示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蓝图既亲近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的根基,又使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融入并影响了世界现代性主流,“收获”了让世人惊异的巨大成就。可以相信,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向即共产主义方向,那么,只要我们中国坚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这一科学思路,“以进一步理解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增强道路自信”[21],坚持不懈,终将达致理想的社会境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J].求是,2012(22).
[5]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胡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和中国化[J].经济学动态,2008(4);裴小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J].学术月刊,2008(3).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1]张远新.党的道路自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J].求索,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