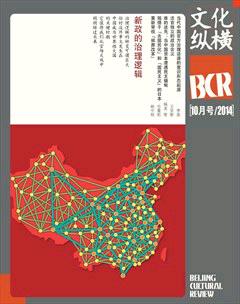困境与出路:中国草根NGO现状调查
木怀琴
过去二十年,中国非政府组织(NGO)数量呈现井喷状况,由1980年的四千余家增长到2013年的五十多万家。而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相称,尤其缺乏对近十年来大量涌现的草根NGO的关注。为补此阙,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安文杰(Anthony J.Spires)、陶林(LinTao)、陈健民(Kin-man Chan)在《中国研究》(TheChinaJournal)2014年第71期发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支持》(societal Support for ChinasGrass-Roots NGOs)一文,选取北京、云南、广东三地263家草根NGO(其中60%在艾滋病、劳动权利、教育、环保领域中开展活动),探讨其法律地位、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获取人力资源和财力支持的重要问题。
NGO的行动能力与自主性有赖于是否能够获得财力支持,而对NGO的海外资金支持总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特别考虑到在20世纪末期持续发酵的“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往往被指认为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与资助,这就使得草根NGO的合法化成为棘手问题。根据相关法律,NGO的三类常见法人形式——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和严格的活动范围限制,而且要想在民政部门获得登记,必须找到一家政府机关作为其主管单位。尤其最后一点,成为很多草根NGO难以跨越的障碍。为了规避登记规则,它们要么选择企业法人的形式,要么选择在香港注册,或者挂靠在其他机构下面,甚至干脆不进行任何注册。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违法风险是极高的。从而,是否能够在法律授权之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草根NGO获取正当性的关键问题。
草根NGO的人员通常由三部分构成:全职员工、兼职员工和志愿者。统计数据显示,拥有全职员工的组织仅占到调查总数的三分之一,(出于如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需要)雇佣兼职员工的也没有达到一半,而所有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志愿者群体。这就意味着,在没有物质报酬的情况下,它们完全靠自身的使命设定和发展愿景吸引志同道合者。这一状况,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却也隐含着高度不稳定的风险。此外,NGO组织非常重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组织当中往往会有同时或曾经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成员。这些成员即便无法帮助组织获得正式的法律地位,至少也能协助组织拓展活动空间、降低违法风险。
事实上,全职员工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草根NGO的资金问题。尽管2005-2012年问,对NGO的各项资金投入总额增长了6倍,但在资金流向上的倾向性明显受到了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根据调查,国外和国内基金会倾向投入艾滋病领域、注册地在北京的以及合法注册的组织,企业资助则很少流向劳动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和教育领域,而国内个人资助则恰恰与前二者相反。这种在机构和个人资助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似乎在短时期内也不会得到改变。
作者认为,中国公民社会尚在襁褓之中。虽然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放宽,草根NGO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但必须认识到,草根NGO的规模仍然不大,相关资源也相对匮乏。因此,它们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所能主张的社会权益也就十分有限。即便在组织数量上能够维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外在环境若不发生实质变化,面对巨大的、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就只能是杯水车薪。因而,不难看出,草根NGO要想突破瓶颈、走向成熟,必须超越相对狭隘的使命设定,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就其自身发展而言,这才是实质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