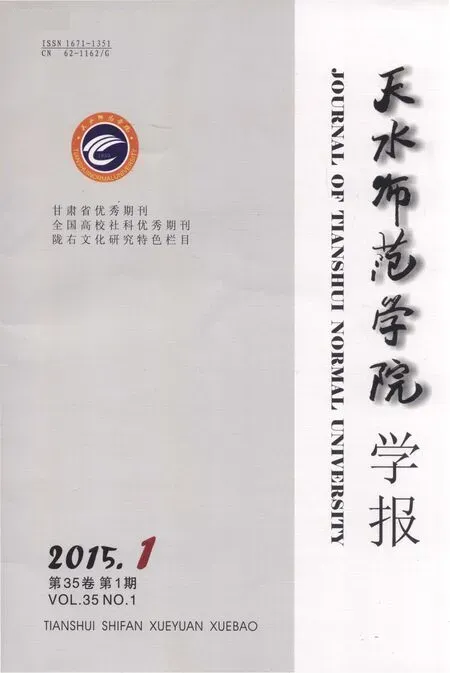后殖民主义视阈下的《肉体伤害》
石 静
(兰州商学院 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1)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1]481它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冷战与后冷战时期推行的一种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围剿和渗透的侵略方式,在理论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简言之,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其他文明从自己角度所做的合理化解释。依据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只有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楷模和中心,而其他地区的文化则被贬斥为边缘文化和愚昧文化。
加勒比海地区原为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故乡,也是帝国主义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领域。从15世纪末开始,它相继沦为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和美国的殖民地。《肉体伤害》便是素有“加拿大文学女王”,“加拿大当代文坛旗手”之称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依其为背景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虽然这个地区的不少国家在二战前后已经获得独立,但是殖民主义者多年统治所带来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文中的主人公杂志社记者蕾妮来到岛国圣安托万,本想在美丽的热带风光中忘却、摆脱肉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肉体上因罹患乳癌被切除了左乳房,心灵上同居男友杰克对她始乱终弃。然而,她万没料到,自己在无意中却陷身于岛国的政治风波中:暗杀、政变、暴力事件频发不断;异国之旅中结识的一些身份不明,行踪不定的游客;身陷囹圄后所见证的狱中种种的暴行和丑恶,幸运的是,最终她被使馆施救返国。本文将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基础,深入剖析文中所蕴含的殖民话语及白人中心论等后殖民思想。
一
在殖民主义理论所划分的“统治”(dominant)和“霸权”(hegemonic)两个不同的阶段中,“统治”阶段殖民者直接依赖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迫使殖民地人民就范,这一时期起作用的主要是物质和制度的力量,而当殖民地人民已经部分或是全部地接受殖民者的价值体系之后,“霸权”阶段殖民话语的力量便凸显出来,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殖民地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对宗主国的依赖,客观上使其人民心灵深处和文化根源上留下了臣属的标签。
圣安托万原属英国殖民地,政治上刚刚获得独立,各方面都处于飘摇动荡中。帝国主义剥削模式在岛上大行其道,造成了这一地区的落后局面。在这里,人们没有多少生活设施,有时甚至没有垃圾袋或是厕所用纸;出租车上是20世纪50年代早过时的软糖一样的座位,百废待兴。在圣安托万独立之前,英国不仅掌管着该国的军事大权,设立了军事驻地,还操纵着此地的经济命脉,占有大量土地并雇工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香蕉,致使经济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英国殖民统治撤离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经济大权,难怪保罗向雷妮抱怨,他的职责是告诉这里的人,这里除了香蕉,还能种红芸豆,“却发现人们希望这里的人只种香蕉”。[2]38可见,英国表面上虽然已经放弃了与此地的政治、经济瓜葛,但它的霸权力量却依然渗透在殖民地生活的各个方面。
圣安托万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美国也一直对圣安托万虎视眈眈。“圣安托万的南面是圣阿加莎,圣阿加莎的南边是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美国的第三大进口国。我们的北边有古巴,我们是链条中的一个缺口,谁控制了我们,就可以控制输往美国的石油。”[2]126圣安托万拥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和自然资源,受到美国垂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小说中的保罗是美国殖民统治的代表人物,表面上他是美国农业部派来的顾问,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他密切关注殖民地局势并辅助美国政府进行经济殖民,把目光投向可以产生巨大利润的毒品市场,圣安托万于是成了毒品加工基地,加工后的毒品再由保罗等人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此外,保罗还帮助美国政府向当地政府提供武器,从中攫取巨额利润。
此外,加拿大对加勒比海国家的新殖民统治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加拿大派来的特使刚去参加过他在巴巴多斯的基地”,“加拿大资助圣安托万为捕龙虾的渔民开办潜水培训班”;[2]129当圣安托万受到飓风灾害之时“可爱的加拿大人送钱来了”,[2]12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加国采取的是一种比较隐蔽、间接的方法,以经济渗透的办法,打着“援助”的幌子进行国家资本输出,以此控制受援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用在先进科技上的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继续控制和掠夺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赤裸裸的经济殖民不同,加拿大采取的是糖衣炮弹式的殖民手段。
二
寓言在后殖民话语中被作为帝国主义统治象征的讽喻,以寓言的形式来使异质文化的接受变为无形,而相当于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则作为它的载体。著名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家法伦的“善恶对立寓言”(Manichean Allegory)构成了殖民话语的一个基本模式,即文明与野蛮,高尚与低贱,强大与弱小,理性与感性,中心与边缘,普遍与个别等。在对峙的双方中,殖民者永远代表着善,而殖民地民族则永远代表着恶。[3]8在这种“善恶对立寓言”的话语关系背后,是一种西方与东方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
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圣安托万被描绘成一个遭受肉体与心灵双重折磨的人间炼狱。岛国警匪勾结,集凶残、贪婪、蛮横于一身:蕾妮刚下飞机就遭到了岛国警察的勒索,她也观察到警察在大街上对残疾人的暴力相向;当蕾妮身陷监狱之时,她亲眼目睹到警察对服刑人员滥施酷刑,对女嫌犯猥亵、侵犯。在圣安托万,岛国民众是一群愚昧无知、凶狠残暴的受众,他们兼具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双重身份,面对西方殖民侵扰敢怒不敢言,卑躬屈膝,对本国同胞却肆意残害,无所顾忌。岛国的领导者俨然是一群炼狱的魔王,首相埃利斯经年未现身政坛,代替他行使权力的是国家行政司法部长。部长暗地里从事一些不正当的毒品交易,假赈灾之名欺骗与勒索民众,搜刮民脂民膏,在大选活动中贿选,同时采取极端手段打压、迫害其他党派人士。岛国唯一的正义之士就是米诺博士。他曾经在加拿大受过教育,具有亲英倾向,主张在圣安托万推行西式民主,主张在国内推行西方国家的管理模式,发展旅游业,推进经济发展,但最终却被无辜暗杀。
在权利——话语结构中,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应与边缘国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在这种对立的权利话语模式中,较之宗主国而言,边缘国往往是一种虚弱的陪衬,一种在文化霸权语境下的自我贬损。蕾妮来到加勒比海采风,虽然不想被牵涉到岛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但她却总在不自觉中流露出“白人文化话语”,在她的观照下,圣安托万成了被看的东西,成为了白人眼中的“他者”。蕾妮被保罗利用运送枪支,却拒绝承认破坏了圣安托万的法律,归根结底是她并没有把岛国的法律放在心上,对另一种文化的否定也是“白人”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这种否定和忽视就是种族中心主义对“他者”的一种偏见。蕾妮眼里的圣安托万肮脏、酷热,目光所及,均令人不快:“装饰毫无特色,活脱脱一个土里土气的英国乡下旅馆”,[2]42“它狭窄,满是砂砾,还沾了一块块油污,软乎乎的,像口香糖,像柏油……鱼泡像是用过的安全套,散布在沙滩上”。[2]79蕾妮眼里的岛民蒙昧不开化,在岛国内战爆发时,她无视保罗CIA特工的身份,仍希望他解决争端,在蕾妮的潜意识当中,“白人文化”中的“白人精英”才是解决岛国命运的唯一主导。
三
在后殖民理论中,殖民宗主国的妇女与被殖民国家的妇女,实际上都成为对抗的男性间斗争的牺牲品与象征性中介,也是他们共同利用的对象。妇女遭受殖民文化的压抑“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丧失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利,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1]499
除了身处第三世纪的女性遭受的“他者”伤害外,宗主国的女性在男性至上现实环境中也不能摆脱被伤害的命运。岛国的女孩洛拉青少年时期住在地下室里,遭到继父的虐待,还险些被奸污,而当她被关到圣安托万的监狱里后,就没那么幸运了,狱卒诱奸她,事情暴露后又毒打她至昏迷。在圣安托万三股势力政治夺权的较量中,蕾妮被卷入了几乎丧命的牢狱之灾。故事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前男友杰克,与蕾妮婚外恋的医生丹尼尔、岛国的走私犯保罗,他们与蕾妮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女主角先后游走在错综复杂感情的纠葛和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伤害也暗示着女性受伤害命运的必然性,不论是在安逸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貌似风平浪静的殖民岛国,女性都难逃被伤害的宿命。
阿特伍德还使用了闪回的方式,不时将杰克与丹尼尔的形象进行了对比:杰克年轻、热情、富有活力,用性爱来维系与蕾妮之间的感情,蕾妮则喜欢穿杰克赠送的情趣内衣,甚至不惜假装性高潮来愉悦情人;与杰克相比,丹尼尔则代表了另一种男人的形象:优雅、稳重的成熟男人,雷妮像只呆头鹅一样爱上了这个有妇之夫。在普世的观念中,年轻的女性渴望能够得到像丹尼尔这样成熟男人思想上的引导和教化,而成熟的女性却渴望杰克般活力四溢的身体。这种对女性本身的不敬观念,影射着普遍意义上“女性弱者”观:女性是被动的承受者。男性的第三类角色特质体现在圣安托万岛上的保罗身上,他对蕾妮温柔、体贴,让她能以此重新找回因失去乳房而产生的对自身女性身份的缺失感。加之保罗身上潜移默化不经意流露出的切·格瓦拉一般的革命气质,使蕾妮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保罗与她的一夜情其实是探查她身份的手段,她所经历的一幕幕度假艳遇范本背后却是阴谋,政治的阴谋、爱情的陷阱、统统逃不过利用二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特伍德打破了传统男女关系之间的平衡状态,她真正要揭露的并不单纯是肉体或精神的残酷,也不仅仅局限在殖民地弱势的女性身上,而是更进一步将其推进到整个社会道德层面。在阿特伍德的笔下,丹尼尔中产阶级的形象,杰克玩世不恭的嬉皮形象,保罗游走在危险与浪漫之间的形象,都是阴暗且不可信任和依托的。即便是女主人公蕾妮,也是时常游离在浅薄和幼稚之间,在她的潜意识中,“她永远不会得救,她已经得救,她没有幸免。相反,她是幸运的,突然地,最终地,她幸运无比,正是这幸运托起了她”,[2]294幸运才是自己能安全回家的原因。作为一个生命体,蕾妮幸免于难得救了,但作为本体的、精神性的蕾妮,她并未得救,没有被幸免。
四
究其本质,蕾妮和洛拉所遭受的“肉体伤害”是女性所面对的无处不在的暴力,不论是杰克、丹尼尔对其身体及精神施加的软暴力,还是洛拉和蕾妮在监狱里所遭受的硬暴力,它们的伤害是全方位的,作为女性,无一幸免。小说中对蕾妮的遭际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与刻画,以此来掩盖其温柔表象背后的暴力伤害;对洛拉经历的描绘则是粗野的暴力摧残,她们互为表里,立体地展示了西方女性的社会生存状况。在后殖民主义作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对话策略”这一背景下,我们应该尊重女性话语域内出现的多元化趋向,清除主流文化所持有的种族偏见,重新创造和建构东西方女性话语。
[1]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肉体伤害[M].刘玉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 萨义德.东方主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