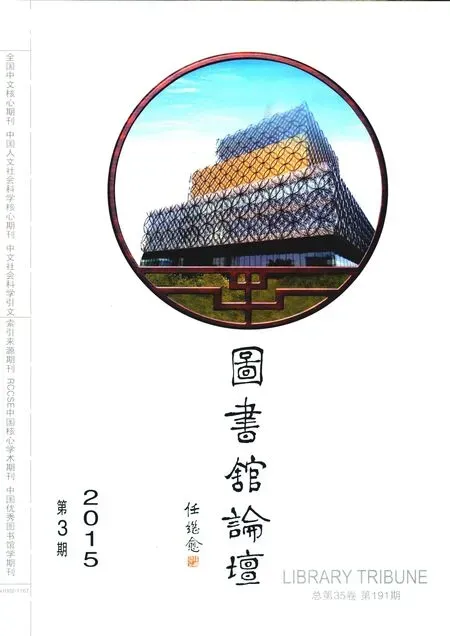风尚与渠径:明代江南“书香门第”的构建及启示*
王安功
风尚与渠径:明代江南“书香门第”的构建及启示*
王安功
在中国文化史中,具有读书、治学、入世传统并传之久远的书香门第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明代江南书香门第形成的社会氛围有两个方面:发达的编纂刊刻事业和普遍存在的图书藏抄风尚,书香门第的形成以修齐治平理念为内生动力。梳理书香门第的发展经验,使书香规避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引导,让书香融化功利的家庭教育的缺失。
书香门第 藏书文化 江南 明代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具有诗礼传家、文化学术内涵丰富、社会地位尊崇等特征的望族、世家凭借丰厚的读书底蕴积淀与承继,经历前辈后代的共同努力,形成读书、治学、入世的传统并传之久远,是为“书香门第”。书香门第丰富的意涵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书香家族“依靠自己家庭教育的力量,连续几代甚至几十代为社会培养出许多杰出的人才”[1]。这种情形在明代江南表现尤著。当时的江南人文荟萃,携唐宋以来之文脉流韵,书香门第如雨后草原,遍地花开,用学界时髦术语言之即为“泛在”。本文从书香门第泛在的社会氛围、内生动力等方面分析书香门第的产生发展,以期对古代藏书进路的现代转化和当今书香门第建设提供参考,祈请方家指正。
1 明代江南“书香门第”形成的社会氛围
1.1 文献基础:江南发达的编纂刊刻事业
首先,繁荣的出版业促进了图书流通的市场化。明代江南“私家刻书十分繁盛,文化世族是其中的主力军。文化世族成员具有强烈的家族文化传承意识,通过刻书活动延续家族文化传统,甚至使刻书也成为家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因为文化世族具有人力、财力优势,刻书活动持续时间长、规模大”[2]。书香家族的图书出版活动不仅丰富了书香门第所需之质料,而且对官刻有相当影响,即“公家亦闻风兴起,广延学士大夫,设局刊书,与私家事业并行不悖。各地书贾亦竞翻旧籍,刊印新书,由是学者皆得人手一编,潜心考索”[3]。明代江南官营出版业在出版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来自南京国子监、司礼监、经厂、行人司等机构的官刻本、私家刻本、坊刻本并行充盈文化市场。李伯重考察明代江南的商业出版活动后指出:明初,政治性和教化性读物在江南出版产品中占有很高比重;中期以后,以牟利为目的、面向中下层民众的商业化出版业日益发展,导致明代江南出版业的发展出现外向型趋势,即生产所需的原料要依赖外地供应源,生产出来的产品(印刷品)则依赖外地市场[4]。各种图书的市场化使民众有机会通过购买得以共享文献资源。
其次,发达的印刷术使高质量图书印刷快捷化。明代江南出版业出现两个重要的技术进步,一是活字印刷的推广,二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5]。明代藏书家胡应麟说:“活板始宋毕升,以药泥为之,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6]木活字本在万历年间有很多,藩府、书院、书坊、私家都曾采用木活字印书。清代文献广泛记载了明人用木活字板印刷书籍的情况,木活字本达一百多种,流播地区极广,苏州、杭州、南京、福建等一带以及四川、云南等地都有[7]。成熟的传统雕版技艺,加上木活字印刷术的进步,令图书质量大大提高,也使图书印刷快捷化。
再次,丰富的出版内容满足民众需求的多样化。明朝“右文成化”,出版产品的教化和宣传功能特别浓。明初政治性和教化性读物是江南出版业中的大宗产品,如《御制大诰》、宝训、鉴戒等政治性书籍,及洪武《大藏》、永乐《北藏》《道藏》等宗教出版物。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出版业兴起,大量印制适销对路的大众读物,包括通俗文艺作品、通俗实用读物、童蒙课本、时文选本、年画、日历及祭祀用品。以坊刻书为例,大致包括有医书、科举、翰林院馆课、八股文、小说戏曲等,囊括了民间日用参考实用书、科举应试书、通俗文学书等类别[8]。出版物的商业性生产,使大量图书在市场上流通,满足了从官员、商人到普通士绅、农耕者等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从政治出版物作主导到大众通俗读物的流行,编纂刊刻事业的发展丰富了书香门第建设的文献基础。
1.2 技术渠径:江南普遍以图书藏抄为风尚
就社会外部环境而言,明代江南普遍存在家族嗜书、争相藏书之雅尚。由于江南“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9],而且这种藏书之风渐而“被及商贩,刊上豪门,广中洋贾,间亦挥霍多金,购藏典籍,开馆延宾,属以校刊。其用意虽为附庸风雅,自跻士林,然其保存传布之功,固不可没也”[10]。可见文人有志藏书的连锁效应。书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读书人嗜书如命,并从中获得乐趣。发达的出版业直接促进“藏书之家,插架亦因之愈富”[11]。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之人比比皆是,有些读书人甚至如痴如疯,构成了中国阅读史上的动感篇章。苏州人杨循吉成化年间曾任礼部主事,身体欠佳,但读书成癖。《尧山堂外纪》记叙他读至兴时,常常手舞足蹈,被人称为“颠主事”,其书室积书达十余万卷。明代祁承爜也说:“余每遇嗜书之癖发不可遏,即取《通考》翻阅一过,亦觉快然。庶几所谓过屠门而大嚼者乎。”[12]清代藏书家孙从添总结前代藏书之趣说:“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13]从古到今的文人与书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关系,他们读书、买书、著书、藏书,书是陋室孤窗下心灵的慰藉,是可以倾心的伙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从未失落的家园。明代常熟人杨仪喜好藏书,在他看来,藏书不是目的,不是为了装潢门面,而是心灵的寄托。他日以读书、著述为事,收藏之富,堪称雅博[14]。太仓人王世贞筑“小酉馆”藏书三万卷,又建“尔雅堂”专藏宋版书,“藏经阁”专贮佛教和道教经籍。以苏州府常熟县为例,藏书在明代晚期蔚为风尚,一直波及清代。明末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两处藏书所更是知名全国,对当时及后世藏书风气有推波助澜的功效。《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三十二更专门设置“藏书家”类目[15],收录元明清三代常熟县藏书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常熟县藏书社会风气之浓郁。
从实际效用看,图书传抄起到了珍品备份、互通有无、丰富品种的作用。袁同礼撰文揭示:“明人好钞书,颇重手钞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16]明宣宗朱瞻基时,官府藏书仍以抄本为主。据《明史·艺文志》载:“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17]吴晗说:在明代“好学敏求之士往往跋陟千里,登门借读,或则辗转请托,渔录副本,甚或节衣缩食,恣意置书,每有室如悬磬而奔书充栋者;亦有毕生以钞诵秘籍为事,蔚成藏家者。”[18]一直以来,文人就好抄书,抄书成为读书与学习的重要方法。杨仪亦爱好抄书,并抄出了名堂。《藏书纪要》“钞录”篇在介绍到明人钞本时,“杨钞”即是其中地位十分重要的一种[19]。所以说精心抄录秘籍是明清以来藏书家所普遍看重的增益藏本的方式。昆山人叶盛,在英宗、宪宗时任官数十年,所到之处总是带着抄书吏,访书抄书,并亲加校勘,藏书数万卷,其《菉竹堂书目》尽载私藏精华,奇书秘本仅次于宫中所藏。明代大多数藏书家都曾参与抄书,且抄书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从数卷以至数万卷的都有[20]。在吴地甚至出现结社传抄交流书籍的组织,如范钦“与吴门王凤洲家,岁以书目取较,各钞所未见相易”[21]。梅鼎祚“尝与焦弱侯、冯开之,暨虞山赵元度订约搜访,期三年一会于金陵,各书其所得异书遗典,互相雠写”[22]。明末浙江《宁海县志》卷九“文籍”载:宁海人陈舜时曾专著《抄书臆见》一书[23],对抄书之法进行详细总结。足见当时抄书热情之高、风尚之盛。
从不断优化的藏书环境看,形成了以藏书楼营建为代表的家族藏书楼文化。明代藏书家以“万卷楼”命名其藏书楼者非常多,如项笃寿、丰坊、杨仪、吴自新、范钦等。这些藏书家往往“插架至富”“牙签万轴(图书数量很多)”。至于芸编(书籍)、芸帐(书卷)、芸阁(藏书阁)、芸署(藏书室)、芸香吏(校书郎)等专有名称则频繁出现在时人诗文集中,构成了江南藏书文化的核心词汇。其他著名的藏书楼还有很多,如明初童伯礼“石镜精舍”、胡万阳“南国书院”、袁忠彻“瞻衮堂”、张瑞“甬州书庄”、范钦“天一阁”、陈朝辅“四香居”、陆宝“南轩”、余有丁“五柳庄”、朱勋“五岳轩”、朱献臣“小五岳轩”、诸来聘“昌古斋”。这些藏书楼无不打上家族式烙印,历时而传承;不少藏书楼还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重新组合,融入到醇厚的文化积淀中去。可以说,藏书楼成为明代书香门第的重要标志。
2 明代江南“书香门第”建设的内生动力
明代江南人文荟萃,崇尚书香。每个世家、望族莫不以读书以修身,修身而科举齐家,齐家乃求入世治国、平天下。可以说当时处处充满着读书上进、光耀门楣、报效国家的风气。
2.1 普遍存在开卷修身的读书风气和阅读心态
对读书的倡导,历代有之。究竟何书可读,无论官私,皆有弘论。嘉靖时期黄佐撰《南雍志》大倡读书:“孔门谓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则学在于读书亦可见矣。删述以来,天之牖民,翳书是赖,其可废邪。”[24]无独有偶,明末安徽学者吴与箕著《读书止观录》,辑录中国先秦以来读书古训和读书掌故,尤其对明人读书故事发明甚多。该书卷三载:“周文安尝著《经书辨疑录》,每曰:‘吾为此录,发经书之蕴,正先儒之失,破千载之疑,虽三公之尊,黄阁之荣,不与易也。’读书者当观此。”[25]吴与箕还列举很多身处逆境仍然苦读书的人物,如著名政治家、“三杨”之一的杨溥,“在狱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数绝粮,又上命叵测,日与死邻,愈励志读书不辍。同难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读书何为?’答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述及此,吴与箕点评道:“古人著书读书,每发愤于穷苦患难之际,今人平时先自废弃,况患难时乎!若必待患难来而发愤,此其所以终身废弃也,此其所以终世偷生也。朝闻夕死,吾深有慕于杨公。”[26]最后他指出,读书的人应当从这里得到启迪。于今人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古人常说士必以诗书为性命,富不肯读书,贵不肯积德,必然走向衰落。家中纵使贫寒,也必须留下读书种子。习读书之业,便当知读书之乐。明代万历年间福建人徐孛力,其“红雨楼”不但藏书7万卷,而且著述颇丰。他在《笔精》“观书三益”条中对读书之益有很深的体会:“客来观书,病懒时颇厌其烦。然有三益,不可以厌烦而废:贱性善忘,经目辄忽,独对客搜寻之事,虽阅年能记,一益也。览所不及,庋床便蠧,因客披,二益也。习懒成病,偶因客至,整书忘疲,亦古人运甓之意,三益也。夫学求益也,一益尚可,况三益乎?”[27]他还说:“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踰其快也。六一公有云: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余友陈履吉云:居常无事,饱暖读古人书,即人间三岛皆旨哉言也。”[28]这种读书有益并以此作为人生一大乐事的心态,在明代非常典型,读书问学,坦坦荡荡,非常值得今人学习。清代读书人王永彬就用浅显白话总结了前代读书的经验:“读《论语·公子荆》一章,富者可以为法;读《论语·齐景公》一章,贫者可以自兴;读书无论资性高低,但能勤学好问,凡事思一个所以然,自有义理贯通之日。……清贫,乃读书人顺境。……读书不下苦功,妄想显荣,岂有此理?为人全无好处,欲邀福庆,从何得来……”[29]。富延、贫兴皆从书中得,正与北宋真宗“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六经勤向窗前读”的诗句异曲同工。明代金圣叹评点《西厢记》说:“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名山、大河、奇树、妙花者,其胸中所读之万卷之书之副本也。于读书之时,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对奇树,如拈妙花焉。于如名山、泛大河、对奇树、拈妙花之时,如又读其胸中之书焉。”[30]这就是“阅读欣赏与自然欣赏的互渗”[31],不同形式的阅读风气汇成了书香社会的阅读正能量,而且“阅读风气的形成是一个时期政治、学术的综合体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时代而变迁,“又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与继承”。[32]风清则气正,良好的阅读传统,成为催生书香门第的重要推手。
2.2 官僚世家与文人家庭讲究家学渊源的氛围熏陶与读书引导
关于古代的家族门风及其内在的精神动力,钱穆指出:“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33]的确,古代世家大族世代累积并一贯遵守了一整套“道德标准、价值准则、处事原则及期望目标,能集中体现一个家族特有的精神风貌,直接关系到家族的荣辱兴衰”[34]。明代有很多读书氛围引导方面的典型事例,祁承爜为教育子孙继承爱书读书的习惯,“亲手撰写了《澹生堂藏书约》,制定了《读书训》《聚书训》《购书训》和《鉴书训》,教育子孙如何鉴别图书、如何购买图书、如何收藏图书,以及如何阅读图书。”[35]并对如何读书、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进行指导:“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便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殆为是耳。”[36]他认为要加强子女教育,并以古训去感染他们:“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37]祁承爜还以梁朝贵族子弟腐朽的生活方式为例,劝导多读书,读书以致用,其言凿凿,如雷贯耳。他说,梁朝盛世,贵族子弟不爱读书,把衣服薰得香香的,把脸刮得白白净净的,擦粉涂红,坐长辕车,穿高跟鞋,座位上垫着软垫子,背上靠着舒适的“斑丝隐囊”,手边放有很多宠物。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文则提不动笔杆,武则耍不得刀枪,衣冠依然楚楚;但如果他们有知识,怎么会被人耻笑万世呢?所以说积财千万不如一技在身。
2.3 科举入仕成为各个家族鼓励读书的首要目标
明代非科举无以为官,家族要振兴,跻身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就是科第成功。这就离不开家族教育,而且科举成功之后,延续家族社会地位的关键还在于教育,所以一般的家族都将家族教育的首要目标锁定在科举入仕。为了科举就必须读经,“凡读书须识货,方不错用功夫。如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当终身诵读也;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亦要一一寻究,得其要领。于子史百家,不过观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记诵,便是玩物丧志。”“经义之外,视己才力所近,专习一事似为易造,其有才力者,自当务为全学。求放心然后可以读书,读书正所以求放心,盖交相养互相发。”[38]明代大多数的“望族都遵循着‘读书—科举—光宗耀祖’的共同模式来规划着家族教育”,这些家族,“除了重视科举之外,还注重文学、史学、艺术等其它方面的素质教育”,逐渐形成了“以科举中试为目标,以其它素质教育为辅助的家族教育体系”,这样既保证家族世代科甲,也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就,成为维系文化望族社会地位的重要动力源泉。所以说,科第成功、文化素养的家族式沉淀,“奠定了久负盛名的江南乃至全国文化型望族的社会地位”[39]。
3 明清以来江南书香门第现象的历史影响
3.1 促进了对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机制的反思
通过书香门第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到古人对书香的尊崇和挚爱。如何认识传统中国社会中绵延两千余年的书香门第的传统,并从中汲取益世的营养?首先要对传统社会结构有清醒的认识和洞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制度,而家又是整个社会的核心,“它是‘紧紧结合的团体’,并且是建构化了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化’作用以传递个人。……在传统中国,家不只是一个生殖的单元,并且还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政治的乃至宗教、娱乐的单元。它是维系整个社会凝结的基本力量。”[40]现在看来,传统“家国同构”社会较为形态下,较为单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表现出了逻辑脱节、过于理想化等缺陷,传统观点强调道德素养的评价固然无可厚非,而时代要求的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则未能充分表达。因此,借用“家国同构”的外壳形式,突出家庭单元的独立地位,实现两者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既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活力,又能加强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积极和现实的意义[41]。当前,众多的书香家庭,脱离了旧式家族式培养的土壤,借助“家国同构”机制,全面推动家庭书香文化涵育,进而为书香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
3.2 推动对历代藏书文化现代性因素的挖掘
要深入挖掘古代藏书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贵流通、倡捐赠的新思想。明末清初藏书家曹溶的《流通古书约》是藏书文化划时代的总结性作品,它提出了“互借”主张,对后世藏书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再看捐赠思想的发展,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把书籍捐给书院之事:“应天书院,宋大中祥符三年,邑士曹诚建,聚书千五百卷。”[42]南宋时期叶适也记载了一则藏书捐赠的事例:“东阳郭君钦正作书院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书以实之。”[43]晚清以后,倡导捐赠的现象更多。咸丰年间岳麓书院藏书尽毁于太平军攻打长沙一役。战后院长丁善庆着手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典籍862卷,随后士绅学士纷纷捐献,曾国荃、李翰章、李恒等捐赠大批典籍,到了同治十七年,私人典籍捐公比例达到65.9%[44],促进了湖湘文化发展,对于开启民智、助长学风影响深远。相较之下,固有的藏书在各个家族间的私相授受现象虽可以存文脉、正学风,形成多个书香维系的家族和家庭,然而这种偏狭的藏书私用、吝借风气不可能产生普惠众生的社会效用,对读书的推广缺乏深层推动力,更无助于普通民众的知识获取。对流习已久的书香门第传统“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45]详细搜求历代江南书香门第之故实,不但可以据此窥视江南社会与文化的互动脉络,亦对当今书香家庭建设不无启发意义。
3.3 为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的“江南因素”提供了纵深空间
江南书香门第发展的历史经验不断丰富和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后起的重要文化现象,江南书香门第已经具备了众所公认的“文化隐喻”资格,成为理解传统文化的一种认知手段,为开展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以近代江南出现的无锡钱氏望族为例,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鏐到清代的钱大昕,到近代的钱玄同、钱钟书、钱穆,再到当代的钱伟长、钱学森、钱永健,无不为中国学术文化、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钱氏家族得以成功延续的重要因素就是其重视藏书、重视读书、重视教育的门风。无论是从历史视野中的门第,还是从文化视野下的书香,都可以找到学术研究的灵感。在魏晋六朝就有“士族门阀”,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明清以后可以说过渡到了“书香门第”,从“文化隐喻”的思维方式出发,这是一种向文化本真状态的回归。从“士族门阀”到“书香门第”,这涉及到中国文化认知模式的转变,可以丰富我们对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江南因素”的分析和评价的视野。这已经超越了本课题所倡导的藏书文化研究之本意,它也许是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进一步认真梳理和研究的基础课题。
当前中国社会的家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革,延续了数千年的书香门第这一美好传统出现断层,因此,“书香家庭”重建命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只有当作为现代社会之细胞的家庭真正营造出一种浓郁书香氛围的时候,让每一个家庭都认识到所谓‘藏金藏银不如藏书,花香酒香不如书香’的时候,让每一个家庭都自觉意识到文化传承之重大意义的时候,建构书香中国的国家战略构想才有了一个可靠的基地。”[46]从书香门第到书香家庭,这看似惊人的历史一跃,实则借助传统家族式的聚书、读书等方式,以回应现实对历史的诉求。展望未来书香门第的建设,只有寄希望于个体家庭书香氛围的营造和家庭阅读的健康、良性发展,为家庭书香建设注入灵魂和动力,使书香规避社会价值观空洞、泛化的恶性引导,让书香融化冷漠、功利的家庭教育之缺失。惟其如此,书香中国的建设才有几分实在的意义。
[1]育心累积法.书香门第成功教育的启示[J].琴童,2013(1):58-59.
[2]姚蓉.明清江南文化世族刻书活动研究[J].思想战线,2011(1):121-124.
[3][9][10][11][18][45]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史学论著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8-209.
[4][5]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3):94-107,146.
[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60.
[7]奚椿年.中国书源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01.
[8]萧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J].F.文献,1985(1):236-250.
[12][36][37]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13][19]孙从添.藏书纪要[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96,100.
[14]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224.
[15]庞鸿文,等.(光绪)重修常昭合志[M]郑钟祥,等,修.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2210-2239.
[16]袁同礼.袁同礼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84.
[17]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3.
[20]赵林平.明代苏州藏书家抄书活动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0:9.
[21]胡文学.甬上耆旧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2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27.
[23]宋奎光.宁海县志:卷九[M].崇祯五年刻本.
[24]黄佐.南雍志·经籍考[M]//太学文献大成:卷十七.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
[25][26]吴与箕.读书止观录[M].合肥:黄山书社,1990:31.
[29]王永彬.围炉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0]金圣叹.金圣叹全集: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8-9.
[31]曾祥芹,张维坤,黄果泉.古代阅读论[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8.
[32]王余光.关于阅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图书情报知识,2001(3):7-11.
[3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10.
[34][39]王晓洋.明清江南文化望族研究——以吴江汾湖叶氏为中心[D].苏州:苏州大学,2004.
[35]桑良至.愿光芒永放:名家书趣[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52-53.
[38]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四[M].同治正谊堂本.
[40]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9-30.
[41]舒敏华.“家国同构”观念的形成、实质及其影响[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2-35.
[42]查岐昌.归德府志:卷十一[M]//乾隆十九年刊本.
[43]叶适.水心集[M]//石洞书院记: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36.
[44]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6:124.
[46]余小茅.书香中国畅想曲[J].教育研究,2012(1):134-137.
Fashion and Path:Constructing Scholarly Families in South Yangtze River Area of Ming Dynasty and Its Implication
WANG An-gong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scholarly families,as a cultural symbol,have the traditions of reading,learning and engaging in mundane life.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forming of scholarly families in south Yangtze River area of Ming Dynasty:well-developed compiling and printing industry,prevailing private book libraries and book-copying.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scholarly families,indicating that scholarship should avoid empty social values and utilitarian family education.
scholarly family;library culture;south Yangtze River area;Ming Dynasty
格式化 王安功.风尚与渠径:明代江南“书香门第”的构建及启示[J].图书馆论坛,2015(3):41-47.
王安功(1978-),男,硕士,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4-07—20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以来藏书文化嬗变研究——以典籍捐公为中心”(项目编号:14YJC870020)、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近现代藏书文化嬗变视野下的典籍捐公研究”(项目编号:2014CZH00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近代以来藏书家典籍捐公的社会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14—GH—565)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