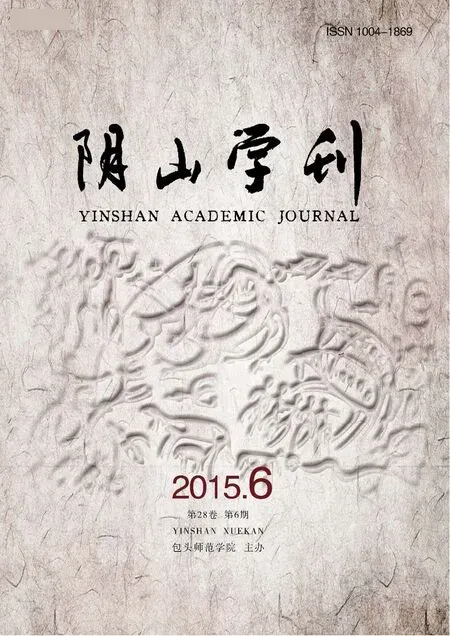庐山会议与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魏 明 康,万 高 潮
(1.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庐山会议与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魏 明 康1,万 高 潮2
(1.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要:由于自早年求学所接受的即是中国传统义理之学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且之后在苏俄哲学教科书的影响下不断强化,毛泽东从来指历史规律为社会本体并指对此之认知为普遍真理而指社会主义的实现即历史规律与普遍真理的实现,故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他就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本土化,所谓纠“左”亦仅限于纠正在推行“三面红旗”过程中发生的具体层面错误如共产风、浮夸风之类。而对于质疑“三面红旗”本身的彭德怀,他指其为政治思维上的经验主义,政治路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
关键词:中国政治;政治思维;三面红旗;庐山会议;毛泽东
本文旨在讨论在推行“三面红旗”过程中尤其在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的政治思维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笔者曾析政治思维为宽容取向的经验理性思维和专制取向的先验理性思维。与此有别,经杨昌济五年耳提面命,毛泽东自早年求学,接受的却是中国传统义理之学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后经研读苏俄哲学教科书,他还将此改造成为了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维模式,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P74~84)虽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比较王明等不仅在本体层面,而且在具体层面为一以贯之的教条主义者,其政治思维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比较彭德怀等不仅在具体层面,而且在本体层面为一以贯之的经验主义者,其政治思维的消极影响同样显而易见。
一、“用最高速度发展我国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
自1952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十到十五年完成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政治作为就集中在两件事:一是进行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推行“三大改造”并以反右捍卫之,二是进行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即推行“三面红旗”并以“文革”捍卫之。由于指历史规律为社会本体并指对此之认知为普遍真理而指社会主义的实现即历史规律与普遍真理的实现,他于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不过是年初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喜忧参半:“我们的主动一天天多起来了,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2](P236,469)后经1957年反右,他自认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已经取得主动。那么在工业方面能否也取得主动呢?他称:“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3](P216)因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4](P1)。当然,依其既定政治思维,必然规律果然要能够起作用,就还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他又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才实现这种结合。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P506)那么这条道路何所指?就是指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所谓总路线,因不满国务院《国民经济远景规划》的“保守主义”,1956年初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出台。其中设想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一万亿斤,竟比国务院规划高70%。国民经济各部门急忙跟进,以致当年全国基建总投资比上年骤增60%。为了遏制“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冒进局面,6月周恩来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8月在“八大”上刘少奇也主张“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于是毛泽东开始了“反‘反冒进’”。当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即称:“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平衡、静止是相对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根本还是促进。”1957年在三中全会上他亦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3](P314,474)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又称:“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一种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二、三年搞完。哪种好?”当然“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好。“这么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主张俄国革命热情与美国求实精神的统一。”[5](P283,315)虽然以学理计,“美国求实精神”是为本体层面之“求实”与具体层面之“求实”的统一,故不可与本体层面之“俄国革命热情”统一。不过毛泽东无暇顾及学理。而他的党内同事,既然“促退”是国民党,“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也就只好表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如此即后者之所谓:“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可是若反对者持相同的逻辑呢?也许就是估计到此,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报告中加写了一句话:“有些人还没有得到教训,他们说:‘到秋后再找你们算账。’他们总是要输的。”[6](P157,223,273)
毛泽东无疑咄咄逼人,可他自称“我的目的不是整人”[6](P108),“目的在大家有共同语言。”[5](P284)那么共同语言何来?“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共同语言。”[6](P197)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之为共同语言,指的就不是具体而是本体——“为什么从这谈起,因为历来讲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而“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主观唯心论”,“是经验主义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7](P24~25)毛泽东所论未免玄,倒是周恩来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的检讨,说明了何以“冒进”与“反冒进”的对立,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经验主义世界观的对立:其一,“反冒进是不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其二,“反冒进是把个别夸大为一般”。所谓“不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在“三大改造”的完成“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因而“多快好省”是一种“客观存在”,可是“反冒进派”不仅漠视这种“客观存在”,而且抗拒这种客观“必然”,他们的作为就当然是“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他们的世界观就当然是“经验主义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了。至于“把个别夸大为一般”,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冒进’的共同语言”,表达的还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即是其本体:本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具体则失误难免;倘若因为在“冒进”中出现了具体失误就全盘否定“冒进”本身,岂不就是“把个别夸大为一般”吗?如此即毛泽东本人之斥“反冒进”:模糊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大局与小局、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使用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方法,1957年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用的就是这种方法”[6](P59~60)。
必须指出,正是经“反‘反冒进’”,关于毛泽东思想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关于毛泽东本人即真理化身,关于服从他即等于服从真理,关于这种服从即使与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冲突亦当义无反顾等,毛泽东和他的大多数党内同事从此达成了默契,而始作俑者即他本人。即以前述《人民日报》社论为例,他指“这篇东西”为“尖锐地针对我”[6](P32~35)。当然“我”非不可以被“针对”,关键“我”之“冒进”不仅在本体层面完全正确,在具体层面亦无懈可击:“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形找势改变计划。”[8](P196)于是乎对此“针对”他就完全不能容忍了。在南宁会议上他称:之所以会发生“反冒进”,是“有人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6](P28),企图在党内“反个人崇拜”。“有人”者何?他直言不讳:“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言及此,他重提1953年周恩来因新税制事件而被其指为分散主义的历史故事:“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2](P768~769)“这八句歌诀,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想出来的。”[6](P57)自“那时”起,“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9](P72)可是刘少奇、周恩来均为“政治局、书记处、常委”成员,他们之于本职有些不同意见,何以就成了“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呢?毛泽东于是称“只能有一个核心”是指“以一个人为核心”。可是在说明“歌诀”时他明明称:“大权独揽习惯上指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党委集体。”既指“集体”,何言“个人”?他接着从两方面作解释:一是将民主集中制由寡头制解释为独裁制,即将党委中“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的统一”亦即书记与委员的统一,解释为军队中“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亦即上级指挥与下级服从的统一。二是将党委委员间“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关系,解释为谬误服从真理的认识关系,所谓“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即使在党委中居少数,也“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6](P28,57,30)而正是屈从于此种以真理为名的强硬逻辑,周恩来、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反冒进”,“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因此就是“错误”的。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嘛,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个人崇拜,而在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行。”那么“不正确的崇拜”有何表现呢?他举了两“怕”:一是“怕马克思”,二是“怕教授”。说到“怕马克思”,他尚含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镇压住了。”[2](P774,793,797)说到“怕教授”,则他不客气:“对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6](P118)至于崇拜何人为“正确”,他重提延安整风:当年“我”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代表,王明则理论脱离实际,全党在“我”和王明之间就得作选择:“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9](P197)闻听此语,与会者均会心一“笑”,接着便纷纷表态:“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2](P802),“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9](P259)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不正确的崇拜”:一是“怕马克思”。他称:“不要怕嘛!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6](P206)二是“怕教授”。他称:“对科学家不要迷信,对其科学要半信半疑。”[9](P267)历史上“科技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相反“名家是最无学问的”,所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明乎此,“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新老干部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对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赶上美国,必然有重大帮助。”[6](P236,194)三是“怕内行”。他称:“政治家是管人与人关系的”,并不做业务,所以“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6](P200)。能“又红又专”当然好,而这并不难。“搞工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信。”[9](P72)至于崇拜何人为“正确”,他点睛:“谁有真理我们就服从谁。”[2](P818)如“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恐怕只有几百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6](P114~115)但既然“总路线正确”,既然“多快好省”反映了客观真理,那么就应该是“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服从这“正确”的、掌握了真理的“几百人”而不是相反。于是接下来的会议发言就颇有些“正确的崇拜”的意味了:“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而是崇拜真理。”“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经验,加以分析,化为理论,指导现代人,教育后代人,像圣人一样,但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圣人。”[5](P331)
1957年11月13日,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社论称:“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958年6月21日社论又称:“用最高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毛泽东何以如此在意新中国建设的速度呢?原因一是为了和美国作敌对式竞争,二是为了和苏联作同志式竞赛。关于美国,他开始还有些保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他称:“我们六亿人口的大国,杜勒斯不看在眼里,总有一天我们赶上美国,他才知道有这个国家。”[5](P311)关于苏联,则自斯大林去世,他就有了争夺国际共运第一把交椅的雄心。无奈实力悬殊,1957年在莫斯科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他只能称:“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10](P626)然而回国后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他却称:“中国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口第一个多嘛!人多总要做事,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因此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其实岂止“可能”,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他就称:“美国那点东西,一亿吨钢,几百颗氢弹,中国要超过它。”[9](P293,34)8月在“八大”上他又称:“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三万万吨钢呀?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4](P88~89)后待大跃进果然成为全民狂热,他的“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也就“一天等于二十年”地不断前移了: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他称“十五年赶上英国”[6](P45),3月在成都会议上他称“二十年赶上美国”[2](P793),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成了“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2](P815),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更是口气大得吓人:“今年争取产钢1 100万吨,明年增加2 000万,后年再搞2 000万,苦战三年,接近苏联。到六二年,接近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6](P394)
二、“公社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
毛泽东何以对新中国“七年”即可“变成天下第一”如此自信呢?原因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在中国创立了人民公社制度。1958年成都会议后他即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研机关,有商店和服务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2](P826~827)以上经“八大”二次会议广为传播后,各地闻风而动。当年8月他即赴河北等地视察,一路称:“人民公社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5](P388)在北戴河会议上又称:“公社的特点一为大,二为公。人多,几万户,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些就是大。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取消掉。”“搞公共食堂,养猪都归公,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公社。如鞍钢叫鞍钢公社,政社合一。”[2](P831~837)
为什么“搞公社”就可以促成大跃进呢?毛泽东称原因在先进生产关系对落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他即称:“初级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要求改变,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转变的时间,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11](P515)然而到了1958年,他又不以“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为满足了。在北戴河会议上他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成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了,我国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6](P360)历史果然如此吗?当然不。相反,正是由于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与“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合作社相比,公社制度就更彻底地消解了农民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而其不仅未能促成经济大跃进,反而造成了“经济大倒退”。而因财产权利的缺失导致公民权利的缺失,公社制度还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此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所感慨:“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奴隶了,使他们失去了生产自主权、产品支配权。1992年我主持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第一步改革划上了句号。”[12](P1)
毛泽东之认定公社可以促成大跃进,还在他指政社合一有利于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并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1958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即称:“以前因为有一部分干部是在做官,有些工人就不那么积极,不为共产主义奋斗,是为自行车、手表、钢笔、收音机、缝纫机五大件奋斗。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这一干的结果,今年粮食大概可以差不多增长一倍,钢铁可能翻一番。”[6](P379~380)那么事实呢?历史已经证明,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纯属自欺欺人。那么公社是否有利于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呢?回答亦是不。所以不,理论上,“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研机关,有商店和服务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需要使用何种强力手段,才能让这些本身就已经自给自足的“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呢?何况每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更大的公社”还须围绕某种政治经济存在,组成一个“天下第一”的共产主义国家!毋庸置疑,依马克思当年关于旧俄公社与沙皇专制之内在关系的分析,这种强力手段就只能是“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13](P761~775)。而实践中,公社实行的不仅是计划经济,而且是“专政”经济。1958年在北戴河会议上,为了集举国之力实现当年钢产量翻番,毛泽东曾声色俱厉:“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上来。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马克思和秦始皇要结合起来。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那还得了。省委书记回去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逐级搞平衡,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做社会主义秩序。”[5](P358~360)尤有甚者,如此还意味着经济的军事化:“一个工厂就等于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我们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就建立了脱离了小生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农业产业军。”毛泽东尤其欣赏河北徐水:“这里的劳动组织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6](P573,523)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即将之隆重推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公社三化很好。是无产阶级军事化,互相关系是同志关系。”[5](P363~366,448)至于“三化”是否果然为“同志关系”,因各地均发生了对社员“一捆、二打、三骂、四斗”的现象,“动不动就‘辩你一家伙’”[2](P894),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曾不得不正式通告全党:“在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了,干部作风好坏对群众的影响更大了,必须严格禁止和纠正假借军事化而打骂捆绑群众和任意处罚群众的现象。”[6](P518)
毛泽东之认定公社可以促成大跃进,还在他指公社可以通过调整分配方式,像在战争年代调动民众的革命积极性那样,在和平年代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即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5](P363~367,47~452)会后参观安徽舒城舒茶公社,得知该社已实行吃饭不要钱,他即称:“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社也能办到。”[6](P432~433)问题是一大二公与政社合一已经从所有制和人与人关系方面消解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倘若连按劳分配都必须破除,岂非所有的激励机制都将不复存在?毛泽东称不然。他称只要像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那样坚持政治挂帅,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就将像“原子核释放热能”[6](P42)一样。事实果然吗?当然不。因为农民当年之所以投身革命,在“打土豪”可以“分田地”,而非空洞的政治挂帅。历史也已经证明,无视个人利益的经济建设根本就不可能带来什么大跃进。尤有甚者,在大跃进中推行政治挂帅不仅经济后果严重,中国的政治生态亦因而更加毒化。1956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承认:“四中全会以来,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慎小心,莫谈国事。”[4](P50)1958年3月中宣部亦报告:“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尤其党外知识分子“谨小慎微,不敢说话”。[6](P133~134)然而四中全会所造成的还只是党内的“谨慎小心,莫谈国事”,反右所造成的也主要是党外知识分子的“谨小慎微,不敢说话”,而在大跃进中坚持政治挂帅所造成的恶果,却是党内党外、全国上下争先恐后地说假话、大话、空话。众所周知,苏俄之刺激劳动者的手段在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例斯达汉诺夫运动。对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亦羡慕:“苏联有一个工人,人家五年才能做完的事情他一年就可以做完。”[14](P325)问题是自“三大改造”完成,他所期望的大跃进已经不是一年等于五年而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乎他就以自己的政治挂帅取代了斯大林的物质刺激。至于如何挂帅,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称:“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或其他人插灰旗。现在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连队、学校、企业,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2](P818)不过,尽管他自信“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起来了”[6](P50),甘居中游的插“灰旗”者仍有人在。例中国铁道科学院某研究员向组织交心:“我把中间路线分成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善与人同。第二,不争上游,不甘下游,安于中游。第三,运动中不带头不落后,运动在前进,我也在前进。”毛泽东阅后,称其“第一”为“反阶级斗争”,“第二”为“折中主义”,“第三”为“中庸是伪装”,总评价为“这种人是右派后备军”。[6](P292~295)不言而喻,既然下游即等于右派,中游即等于右派后备军,在如此政治挂帅实则政治高压下,全党全民就确实不能不争先恐后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即使这种“鼓足”与“力争”明明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也罢!
三、两次郑州会议与纠“左”
1958年9月毛泽东到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讲到粮食问题时他喜气洋洋:“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6](P380)然而此数实为3800亿斤。由于当年征购是以“七千几百亿斤”为基数并被定为1200亿斤,加之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自当年秋冬,他即先后接报:安徽“灵璧冯庙乡、杨町乡、伊集乡由于自然风灾、谎报亩产等原因,到目前已饿死不下五百余人”,“各地为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要求轻工业让路,许多日用品和食品已脱销”,“云南因肿病、痢疾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6](P436,492,585),全国“十五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8](P209)。以上噩耗接踵而至,对于此前一直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毛泽东形成了强烈震撼,于是他试图抑制其时正在甚嚣尘上的共产风与浮夸风。
1958年11月,作为八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称:“公社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针对超英赶美的浮夸风,他亦称:“今年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400亿斤,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4](P434~441)问题是他坚持“三面红旗”本身正确,错误仅出在本体与具体的结合层面。故此后半个月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他又称:“我就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公共食堂、公社垮台。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15](P162)由是他坚持:“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甚至在批阅湖北省委“关于随县弄虚作假,搞六万斤卫星试验田情况的报告”的当日,他依然鼓动与会者:“共产党人总是将藐视一切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每件工作,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4](P445,612)然而,尽管毛泽东自诩“藐视一切”,由于农村“肿病死人”的惨象愈演愈烈,他内中也是忐忑的。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他袒露:“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4](P445,612)不过囿于既定的政治思维,关于究竟应该如何“避免破坏”,他的对策就依然只是“讲步骤”,即并非放弃“三面红旗”之为政治本体,而只是放缓人民公社走向全民所有制的具体步骤。他承认:“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后,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公社成立了,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制。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干部讲清道理。公社在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以队的核算为基础。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8](P87,61~75)
自两次郑州会议召开,依其化政治学为认识论的思维定势,毛泽东一直不情愿承认,以上制度调整是他本人理想中的社会利益格局与农民的现实利益诉求之间博弈的结果,反而称经一年实践,他已经“认识”到了公社发展的“客观真理”,现只要予以贯彻,就“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他加快了在具体层面抑制共产风与浮夸风的节奏。1959年3月他给各省委第一书记写信:“河南、湖南均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同意。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月底又在七中全会上称:“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如果群众确实同意也是可以的;如果群众不同意就要改变。要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8](P111,185)那么如此再四,他果然从此就“要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了吗?回答是不。虽然为了“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他可以允许公社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退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退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又可以从公社集体所有制退到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再退到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因为这一切“后退”都不过是在共产主义大道上“讲步骤”而已,即是在具体层面坚持实事求是。倘若要求继续“后退”,如不满足包产到队而是要求包产到户,不满足恢复自留地而是要求分田单干,那么即使这些确实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在他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此已经脱离了共产主义康庄大道,背叛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
在从具体层面加快抑制共产风的同时,毛泽东也加快了抑制浮夸风的节奏。其时他给省以下各级干部写信称:“包产一定要落实。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200斤,也就很好了。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加200、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并称对他信中所说,“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8](P235~237)那么该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以上反省呢?首先从方法论角度看,他依然是一以贯之地混淆政治学与认识论。在认识论意义上,所谓自由确实基于人类对必然的认识。故人类中的真理在握者确实可以指望愚夫愚妇的追随与服从,就如同科学大师之于科普受众。然而在政治学意义上,由于政见不一源自人与人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政治自由就并非指人们对某种客观必然或自称反映了某种客观必然的主观意志的追随与服从,而是指每一人类个体的自行其思与自行其是,只要此自行其思与自行其是不妨害彼自行其思与自行其是。其次从政治操作角度看,正是由于混淆了政治自由与认识自由,从“反‘反冒进’”到大跃进,毛泽东就始终以真理化身自居并以此诱迫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自己的追随与服从。虽然在1959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他承认:“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可他依然将“打败仗”归因为“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2](P948~949)此后一个月庐山会议召开,由于自认已经弥补了这个“不足”,他就再次以真理化身自居并以此诱迫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自己的追随与服从。再次从就事论事角度看,毛泽东对浮夸风的抑制也是根本不到位的,因为将1959年钢产量和粮食产量分别确定为1300万吨和4800亿斤,本身就还是在浮夸。尤其当年6月青黄不接,当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向他汇报:“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他居然又盲目乐观起来:“但是已经开始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8](P320)
四、“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当然毛泽东并非全然盲目。因为据各地报告,在农村通过“粮食问题大辩论”,“紧张情况已得到解决”[8](P606,480);在城市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凡是采取这一办法的单位,粮食问题都解决了”[16](P402)。既如此,他忙里偷闲,于1959年6月回到了湖南湘潭韶山老家。此前时任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亦曾回该县乌石老家。后者称:“我到了乌石、韶山两公社,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没有公布的那样多。”[17](P266)而毛泽东眼中的家乡大不同。其《到韶山》诗云:“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8](P324)7月2日,史称庐山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相继召开。会议前期毛泽东轻松愉快,他美其名“神仙会”,缘由即在对形势乐观。会议第一天他讲话:“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于是他提出:“今年钢产量是否定1300万吨?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明年钢增加多少?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可即使形势乐观,远水解不了近渴,仍在蔓延中的大春荒怎么办?对此他还是有些紧张的。他交待:“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了。”那么如何“安排”才“好”呢?他出主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18](P76~84)然而他的乐观并无感染力。不仅与会者们对“千万人饿肚子的问题”议论纷纷,就连自诩从来“只左不右”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亦指1958年的本省形势:“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而曾多次陪毛泽东到两湖视察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承认:“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已死1500人。”[19](P26~29)会外则有中宣部报告:“天津部分党员干部否定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有总政治部报告:“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紧张不满,否定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有统战部报告:各民主党派对大跃进不满。“罗隆基说物资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龙云说解放后只是人整人,人心丧尽。”“于学忠说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有国务院秘书厅报告:“我厅议论很多,认为公社所有制与目前生产力水平不适应,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原则。认为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钢指标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地规定的。”有江西省委报告:“省委党校有近半数学员认为公社没有优越性。”[8](P342~387)于是7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大会讲话。他首先为以上种种强辩:“从局部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其次化政治学问题为认识论问题:“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算是出了学费。”再次警告:“要党内团结,首先思想要统一。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1800万吨钢不行,搞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30%左右是有的。”[2](P971~974)
其实关于“三面红旗”之可能引发“团结问题”,自始毛泽东就不曾有片刻释怀。1958年成都会议他即称:“今年干劲这么大,如果不丰收,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出来说话。”[9](P264)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他又称:“观潮派、算账派会出来讥笑我们。”[8](P74)此刻在庐山,为其所一直耿耿的“党内团结”就果然发生问题了:7月14日彭德怀呈毛泽东一封信,16日此信被后者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交会议讨论,21日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就此信发言表示同情,23日毛泽东即发表了他的第三次大会讲话,他指《意见书》为党内外一切反“三面红旗”的右派言论的代表。可此信果然有什么偏激之语吗?没有。信开篇即称:“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才批评:“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过急过多了一些。”谈到人民公社,信亦称:“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虽然在所有制上曾有一段混乱,但经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谈到大炼钢铁,信亦非全盘否定:“全民炼钢铁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但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普查,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不过信未止于就事论事:“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已影响到工农、城市各阶层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信还试图从“思想方法”上分析问题的成因:“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也同样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17](P281~287)若平心静气,此信实为折衷之论,但毛泽东不这么看。他指责彭德怀:“你挂帅,组织派别。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彭德怀称自己认同“三面红旗”,只是“强调了部分缺点”时,他居然连自己此前承认过的“一个指头”也不再承认了:“他们提出的批评,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现在是一个太平世界,形势很好。否则我们为什么在庐山开神仙会?”他尤其不满彭德怀称炼钢铁为“有失有得”:“有一点损失,我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接着他为共产风强辩:“群众不满主要是一平二调,无非想早点进入共产主义。”既如此,就没什么了不起:“刮共产风是容易改的。有人分散资财,也不要紧,物质不灭嘛!”至于浮夸风,他称:“放了许多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对彭德怀批评经济比例失调引起政治关系紧张,他更不以为然:“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就是两三个月,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而对彭德怀指“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全盘否定:“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左’倾机会主义要在民主革命阶段消灭资产阶级”,所以才叫做“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办公社,办食堂”,不正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于是8月1日与彭德怀谈话时,他声色俱厉:“共产风、浮夸风都已经解决。现在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9](P132~136,182~225,294~338)
毛泽东清楚,若就事论事,他对彭德怀的定性难以服众:“彭黄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8](P452)所谓“复杂”,他指彭德怀与自己的历史关系为“合作不合作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是合作的,解放战争是合作的,抗美援朝是合作的,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之所以称八年抗战为“不合作”,在政治上,是因为彭德怀在太行根据地时发表过一个访谈,毛泽东当年即曾批评:“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20](P26~27)8月1日他即旧事重提:“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而所以称八年抗战为“不合作”,在军事上,7月31日谈话时他批评:“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以致彭德怀不得不当场就百团大战作检讨:“这一仗帮了蒋介石的忙。”连林彪亦不能不当场撇清自己:“平型关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19](P185~222)问题是彭德怀错不止此。毛泽东称,此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主革命同路人”,“同路人不可能不犯错误”[8](P522~523),如“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这次对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2](P986,1007)“民主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对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命,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于是就闹翻了。”[19](P334,291~294)
五、“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
对彭德怀作以上政治定性后,毛泽东接着便剖析其政治思维。《东方红》唱毛泽东“爱人民”,其实其之爱实为柏拉图之爱,即其所爱为人民这个概念,而非作为人民之具体组成的普天下匹夫匹妇。所以“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10](P66),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21](P646~647),即使已经因此而出现了“千万人饿肚子”甚至“肿病死人”的人间惨象,他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视之为历史进步的必要牺牲及为探求历史规律所必付的“学费”,甚至可以轻描淡写为“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乃至“鸡毛蒜皮”!而彭德怀无此高妙境界。在“文革”冤狱的交待材料里他回忆自己童年乞讨的悲惨细节:“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15](P2)关键是漫长的革命生涯并没有铸成他的铁石心肠。赴庐山途中他茶饭不思,居然是看到车站外饥寒交迫的难民而感同身受:“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此前在农村考察,一位在乡老红军递条:“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他就真的在庐山上挺身而出。所以当毛泽东面责:“你出身劳动人民,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彭德怀竟坦承:“经验主义肯定,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是被动地跟着干社会主义。”意识到其人并不觉悟经验主义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继续深入:“你这个同志,经验主义,承认的?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另一种世界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对体系。你的经验主义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要修正总路线,你想另搞一个。”之后又在大会上称:“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问题。他们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唯我主义。无客观标准,不是从感觉到理性。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主义。”[19](P95~98,190~210,290~291)考虑因缺乏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理性思维能力,而在本体层面沉溺于个人素朴经验,从而背弃历史规律者,在党内大有人在,并非限于彭德怀,毛泽东向全党亮出了“批判经验主义”的理论旗帜:“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我们现在必须作战,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8](P446)所谓“作战”,对外,其时赫鲁晓夫曾借斯大林在苏共“十七大”上的讲话批评中国的公社化:“劳动组合只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公社把社员的生活资料也公有化了。公社为了避免垮台,就不得不放弃生活公共化,开始按劳动日计工,把谷物分给各户,允许社员私有家禽、小家畜、奶牛等。”[22](P556~560)可毛泽东不仅不引为鉴,反提出:“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公社会不会垮台。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而由于以历史规律的“先知先觉者”自命并自认超过斯大林,他声称:“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而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对内,除了彭德怀、黄克诚,他下大气力对付的是自己心目中的彭黄的盟友张闻天。在他看来,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后者就是一个只会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者,可今天居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只知斤斤计较在推行“三面红旗”过程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具体失误,而罔顾“三面红旗”本身是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本土化。于是他怒斥:“闻天同志: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8](P390,410,399)同样招致他强烈不满的还有他在延安时期的秘书、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上山之初他曾向周小舟表示,拟以纠“左”为会议主题,后者指其“很像斯大林晚年”。其时与会者穷追不舍:“斯大林晚年指什么?”周小舟坦然:“就是180度大转弯,从反‘左’到反右。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毛泽东闻之大怒:“苏联鞭死尸,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并大不以为然:“哟!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吗?我没有,怎么叫转180度啊?”[19](P143,282~299)当然此非虚言。因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他就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本土化;而他之纠“左”,又仅限于纠正在推行“三面红旗”过程中发生的具体层面错误如共产风、浮夸风之类,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庐山会议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经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的以漠视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又经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的以漠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为特征的经验主义,所谓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作为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所惯用并因其左右逢源因而战无不胜的思想利器,终于通过既与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又与资产阶级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而最终为党内高层所全盘接受;同时他本人作为如此左右逢源、如此唯一正确的政治思维模式的人格化身,也因而变得完全神圣不可侵犯。虽然自“反‘反冒进’”,关于毛泽东思想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关于毛泽东本人即真理化身,关于服从他即等于服从真理,关于此种服从即使与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冲突亦当义无反顾等,毛泽东和他的大多数党内同事达成了默契,但彭德怀不以为然。在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他就质疑:“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即使参加由毛泽东本人主持的常委会,他亦称:“全民炼钢,补贴五十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当主持人冷对:“不会有这样高。”他居然脱口而出:“那就矮一点吧!”当然,对彭德怀的不满毛泽东心知肚明,因为前者本来就是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问题是他的不满不能见容于毛泽东。庐山会议前三个月,后者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曾口口声声:“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P280,99,73)综观四十余天庐山会议,他对彭德怀之最为凛然决绝的一段话,也正是这十六个字。可是为什么“我”就不能为彭所“犯”呢?毛泽东的理由有三:一是在他看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是上下关系,“犯我”等于“犯上”。为了维持“抗日的民主”的国内政治局面,毛泽东曾将民主集中制差强人意地解释为政治民主制加行政集中制。不过自1953年周恩来因新税制事件被其指为分散主义,总理负责制即名存实亡。后经“反‘反冒进’”,1958年毛泽东又自谓:“南宁会议后,承认我挂帅。”[19](P202)1959年他更是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宣布:“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8](P196)至迟自此,曾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所遵奉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委员合议制,就变成了上令下行、令行禁止的首长负责制,而所谓首长即发号施令之“帅”为毛泽东本人。所以庐山会议后期,就不仅有众多与会者指彭德怀“好犯上”,尤其出离愤怒的还有身为“主席”而居然被“驳”的毛泽东本人:“说我是主席不能驳,事实上纷纷在驳。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第二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19](P139~142)二是在毛泽东看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类似君臣关系,“犯我”等于“造反”。所谓“造反”,七中全会前他曾与彭德怀半开玩笑:“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23](P316)所谓君臣,在全会上讲话时他又以嘉靖与海瑞比之自己与彭德怀:“海瑞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看了。’)”[2](P941)此后三个月在庐山,周恩来固然是“吸取教训”了,可彭德怀像“海瑞那样勇敢”,却成了大逆不道的“造反”!既要人“别造反”,又要人学海瑞,如此诱人以罪,岂非在党内重演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的故事?毛泽东毫不掩饰:“你讲我阴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道理。我叫你们放,你说我钓大鱼。确实,就是要大鱼小鱼一起钓!”[19](P297)然而海瑞之说何以自圆?他居然振振有词:“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2](P1007~1008)庐山会议与会者多讲不出如许大道理,他们于是直接以三国君臣故事演绎彭德怀:“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他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当彭德怀分辩:“‘张飞’这个绰号是主席取的。”毛泽东竟称识人有误:“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内有二心,外似张飞。”[19](P149,217,187,198,206)三是在毛泽东看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是真理与谬误的关系,“犯我”等于冒犯真理。并且就是因为在历史上彭德怀只能“三七开”而“我”却一贯正确,在现实中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8](P522),他才会如此理直气壮:“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既如此,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们就只好异口同声:“毛泽东三个字已经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名字了,它是党的化身,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并谴责彭德怀大不敬:“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而毛泽东之能心安理得地瓦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合议制,同样因为他以真理化身自命。他斥彭德怀:“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19](P64,134~135,352,330295)理由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并且是“我”在推行而“你”在反对这个“真理”。进而他之能心安理得地以嘉靖自居,亦在他自诩“秦始皇加马克思”。即他之得行“独裁”并非简单如旧式帝王那样依据历史唯心论的奉天承运,而是依据历史唯物论的客观真理。所以在以汉光武帝刘秀、魏武帝曹操不计前嫌、招降纳叛的历史故事向周小舟并通过周小舟做黄克诚的招降工作时,他所摆出的政治姿态,就绝非仅在宣示旧式的君臣之义,而是同时要求后者“迷途知返,不远而复”[8](P397),即由右倾机会主义“迷途”,“复返”马克思主义真理。
参考文献〔〕
[1]魏明康,万高潮.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维——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J].阴山学刊,2015,(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邱实.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7]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参考研究资料(第三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2]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J].新华月报,1998,(7).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毛泽东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李锐诗文自选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7]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0]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2]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3]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韩芳〕
Lushan Meeting and the Political Thinking Mode of Mao Zedong
WEI Ming-kang1, WAN Gao-chao2
(1.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Institute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From the early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eo-Confucianism and receiving its political thinking mode to combine the transcendental metaphysical ontology and experience physics specific, then strengthened constan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viet philosophy,Mao Zedong refers the historical law as the social ontology and refers the cognition for the historical law as the universal truth and refers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a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law and the universal truth,therefore,since the first meeting of Zhengzhou rectifying the “left”,he always adhere to the “three red banners” is for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Leninism loc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so-called rectifying the “left” is limited to correct the specific error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ree red banners”,like anti-communization,fanfares. For the question of Peng Dehuai to “three red banners”,he accused as empiricism in the political thinking mode and the right opportunism in the political line.
Key words:Chinese politics; political thinking mode; “three red banners”; Lushan meeting; Mao Zedong
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5)06-0073-11
作者简介:魏明康(1958-),男,江苏南京人,硕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