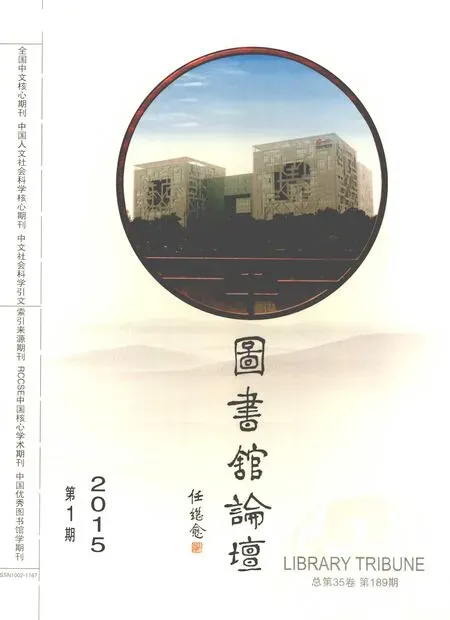智慧服务背景下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推演与重构
——以后现代构建主义知识观为视角
许正兴
智慧服务背景下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推演与重构
——以后现代构建主义知识观为视角
许正兴
从后现代构建主义知识观的视角阐释图书馆智慧服务下图书馆学五定律的新内涵,在对阮氏五定律进行解构、推演、整合的基础上构建图书馆智慧服务新定律。
图书馆学五定律 智慧服务 构建主义 转知成慧
0 导言
众所周知,服务是图书馆的永恒主题。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正是由于深入分析并高度概括了图书馆服务的基本原则,而一直被学界奉为经典。尽管服务作为图书馆的天职不会改变,但图书馆作为“生长的有机体”,其服务模式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革。伴随人类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步入知识社会,图书馆也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走进了知识服务阶段。“这一路径反映了图书馆的发展从依赖资源、技术到越来越依赖于图书馆人的智慧”[1]。同时,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实践的不断进步,作为上层建筑的传统认识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20世纪以来,基于人主体实践的交互、相对、生成性的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知识观逐步取代传统静止、绝对、单向性的客观主义知识观[2],它通过强调人在知识生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突出知识的个体性,进而彰显了作为人“主体能力”的智慧的价值。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指出作为客观知识本体的图书馆学既是知识之学,也是智慧之学[3],应该以“智慧”作为当代和未来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方向[4]。相应地,图书馆服务也应从一般性知识服务上升到以提高人类智慧为核心的创造性知识服务即智慧服务。
作为知识服务的深化和升华,智慧服务已成为图书馆界热门话题,相关论文呈逐年上升趋势。然而相对于智慧服务理念这一重大变革,作为图书馆服务理论经典的阮氏五定律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却没有得到相应拓展。图书馆学五定律作为学科原理和职业精神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普适性,但作为实践方法与指导原则却需要结合具体实际不断发展与更新。笔者以构建主义知识论为依据,对图书馆智慧服务下的阮氏五定律进行解构、推演与整合,进而重构并全新阐释图书馆智慧服务新定律。
1 第一定律:知识在创造性运用中转为智慧
1.1 知识变迁彰显智慧力量
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客观知识作为图书馆的活动基础和存在根本,在读者心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然而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等新理论对经典“牛顿—笛卡尔”绝对理性范式的冲击,传统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化危机”[5]——以单一标准来决定所有差异,进而统一所有论述的“后设叙述”被瓦解[6],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知识都具有不确定性[7]。基于此,人类的认知由以理性为中心的无身认知(disembodied)向以人为中心的具身认知(embodied)推演,知识的范式也发生了从普遍、一元的客观主义向境域、多元的建构主义演变的巨大变迁。因此,“即使知识也不能使我们安全,真正的安全是依靠我们辨别力和所遵照的那些维持、滋润我们生命的永恒原则”[8]。所以,正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以不确定性和不断变革为本质的知识社会,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掌握知识更重要。而智慧正是人开发、利用、创新信息的能力[9],它源于知识又高于知识——知识无非是感性的抽象[10],是被动认知层次上对暂时性事物的局部把握和有限理解;而智慧则是理性的升华,是人主观思维层次上对事物整体的永恒推理和无限反思。因此,如果说知识服务只能解决既得知识的搜索和获取,那么智慧服务则能激发人创造未知的智慧和潜能——智慧就是把握不断变革的知识社会的“永恒原则”,是推动人类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智慧就是力量”。
1.2 运用知识手段以达到提升智慧的目的
阮氏五定律中的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实际上强调了知识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借以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随着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知识在进化过程中不断被“商品化与权力化”所异化——知识的工具理性达到极致,而作为价值理性的人的内涵却被削弱,知识成为与提升人自身能力无关的单向度追求目标。这不仅违背“书是为了用的”的宗旨,也与“以人为本”的理念背道而驰。而智慧既是运用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也是运用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过程[11],它不仅完全体现构建主义所提出的“知识的人的主体性”,还通过突出人的主观创造力而充分反映“以人为本”关照下人的自我构建、自我完善、自我进化的价值理性升华。因此,“暂时性”的知识只是人类实现其发展的前提和手段,而人类求索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获得至上智慧[12]。这既是图书馆知识服务向智慧服务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向“以人为本”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认为,“人们基于知识的认识世界是为了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13],而改造世界的关键取决于人类的智慧运用与知识创造,因此被动的知识认知仅仅表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主动的智慧实践才代表着人类改造世界的水平。如果说传统图书馆只是服务于认知层次上的知识获取以认识世界,那么智慧服务则强调更高实践层次上提升人的智慧创造力以改造世界。所以开展图书馆智慧服务就是要帮助读者对知识由“用”提升到“创造性运用”,就是要促使人的个性主体由“知识的人”转向“智慧的人”,从而最终达到“转知成慧”的目标。
2 第二定律:读者在智慧性实践中创新知识
2.1 读者在实践中“转知成慧”
阮氏五定律中的第二、三、四定律即“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时间”共同指出了图书馆服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知识获取中对“有”的需要,这对于解决当时书籍匮乏与读者需求不断增多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这种单向、授受式的“有”无疑是以客观、绝对的传统知识论为导向,将间接获取知识与掌握知识等同,忽略了人的实践在检验真理标准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构建主义强调知识的建构性,认为“知识就是社会场域(Field)与主体思维互动交流的结果”[14]。因此,“如果不分析知识的建构,也就不能理解知识本身”[15],“惟有亲身实践才会领悟到这些境域性知识的本质内涵[16]”。同时,构建主义反对“知识决定论”,认为知识都具有个体性和情境性——不同的个体在面对同一知识亦或同一知识置于不同的情境中,其认知结果并不相同,而正是这种“差异性认知”推动着知识的进化和增殖。因此,正如“尽信书不如无书”,读者在“有”了对知识客观绝对性无条件信任的同时也“无”了对知识主观性验证批判的实践可能,从而最终与“真理必须是证伪的”建构主义知识进化论背道而驰。这种对已有知识机械性复制的“有”非但不利于知识的进化和读者智慧能力的提升,还极易使“智慧湮没在过多的知识中”[17]。因此,智慧服务不但要提倡知识“学以致用”(第一定律),还要积极引导读者“用以致学”——即读者在主体性知识运用的“意义建构”实践中通过还原知识的建构情景(Context)来重拾其发生过程,从而使认知从判断知识本质的“知识为何”(What)转向体验知识生成的“知识何为”(How),进而使读者在“用”中“学”,“行”中“知”,达到“知其所以然而知其然”的彻悟。同时,如前所述,书籍不但包含知识,还是作者智慧创造力的结晶,读者在验证和体验知识建构的过程中不仅会领悟到知识的真谛,还能通过感知作者的智慧而引发共鸣,进而使自身的智慧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激发和释放。
2.2 以智慧实践推动知识创新
建构主义否定普遍、永恒的知识,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一种暂时的理论,都是对现有问题的猜测性解释,因而必将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化而不断变革,并随之出现新的解释和假设”[18]。因此,认知的目标不是终其于结果,而是运其于过程;知识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既有,而在于提供人们籍以不断创新的“起点”。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向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智慧经济时代[19]过渡,促进知识的转化和创新已成为图书馆工作重点。依据Nonaka[20]SECI理论揭示的知识创新四阶段即知识的同化(Socialization)、外化(Externalization)、合化(Combin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创新必须与基于个体知识社会化、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知识流动”紧密结合,如果只强调静态“有”的知识获取,而没有通过智慧的实践转化使其流动更新,知识就会因失掉创新所赋予的生命力而变得毫无价值。所以,知识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江激流,人智慧的实践创新为其注入了流淌的生命和奔腾的动力。因此,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关键就是促使读者从传统以“有”为目标的被动性学习转向以“创新”为目标的“创造性学习”——在“主动建构”的创新实践中学习知识,使创新成为学习手段和目标的统一。而相应地,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也应从以知识存取为目标的“读者有其书”转变为以启迪智慧创造为目标的“读者创新书”:读者通过作为场域的图书馆知识共享交流平台在“转知成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基于智慧创新的“转慧成知”,进而以客观知识主观化、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创新螺旋”不断打破旧的认知结构、重构新的知识体系,使读者在创新实践的过程中不但掌控知识和提升智慧,而且还在掌控知识和提升智慧的同时创新知识。
综上所述,读者不仅要有“书”,还要有其“智”;读者不仅要有“智”,还要以“智”创新“书”——读者基于实践的智慧创新不但使知识在重构中进化,还使智慧在实践中升华;不但使读者在超越知识的同时超越自我,还为图书馆引领全社会“知识协作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场域和不竭的智慧动力,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以知识创新为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发展。
3 第三定律:图书馆在人与知识的交融中不断发展
图书馆活动必须同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知识,二是人[21]。本文提出的以“知识”为出发点的第一定律和以“读者”为出发点的第二定律不仅充分概括了这两个辩证统一的图书馆学活动范畴,还突出了阮氏第五定律“图书馆是生长的有机体”中图书馆“生长”的发展革新性和“有机体”的内在统一性。
首先,第一定律强调知识是基于人的知识。构建主义提出“知识的人的主体性”,认为一切知识都深深地打上人的烙印。诚然,智慧源于知识,知识又源于人的实践,必须也惟有经过人的创造性运用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在知识折旧率加快、裂变整合加速的今天,知识尤其需要不断更新和创新,否则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其次,第二定律凸显了人是基于知识的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就在于其智慧创造性。因此,人既做为知识的受众显示其自在客体性,又做为知识的创造者突出其自为主体性。人是客观知识的动物[22],没了知识,其“类本质”就会丧失。
综上所述,知识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知识。知识作为人自为意义的根本手段造就了人,大大促进了人的实践发展和智慧提升;而人作为知识存在的必要前提也运用智慧创造着知识,其实践发展又必然推动进一步的知识创新。这样,基于知识的人和基于人的知识既相互依存整合,构成图书馆统一的“有机体”,又不断交融转化,使图书馆智慧服务朝着“转知成慧”的目标持续“生长”:其全过程就是一个以人和知识的矛盾转化为核心,形式上表现为新知对已知“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内容上体现了从“知识转化”的量变到“转知成慧”的质变的永恒发展过程。
4 结论
本文以后现代构建主义知识论为依据提出的“图书馆智慧服务新定律”是智慧服务下阮氏五定律的演化和升级,具有完整的逻辑性:第一定律从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出发,引出了类似哲学意义上“世界观”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第二定律作为第一定律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中的应用,阐述了通过智慧服务到达图书馆学逻辑终点“人”的“方法论”途径。第三定律则整合前两定律,既论证了人与知识辩证统一的图书馆本质,又揭示了其“转知成慧”的实质性运动发展过程,是智慧服务下图书馆的“本体论”。
新定律在系统构建图书馆智慧服务理论框架的同时深入阐释智慧服务的基本理念,为智慧经济时代图书馆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我们应以“知识在创造性运用中转为智慧”为宗旨,不断推进“读者在智慧性实践中创新知识”的智慧服务,积极建设“书书转人智,人人创新书”的智慧创新型图书馆,从而在引领图书馆在智慧经济时代发展中以智慧的无穷力量推动创新型知识社会的进步,最终使图书馆作为“社会发展动力之源[23]”名正实归。
[1]柯平.当代图书馆服务的创新趋势[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8(2):1-7,18.
[2]袁维新.从授受到建构——论知识观的转变与科学教学范式的重建[J].全球教育展望,2005(2):18-23.
[3]傅荣贤.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的反思—从知识之学走向智慧之学的取向[J].情报资料工作,2009(1):6-10.
[4][12]熊伟.建立面向与通往“智慧”的普通图书馆学科体系[J].图书与情报,2012(1):4-9.
[5]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5.
[6]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6.
[7]阮新邦.批判诠籍与知识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52-153.
[8]AlleeV.知识的进化[M].刘民慧,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2.
[9]沈俏梅.论图书馆“有智慧的服务”[J].前沿,2002(3):86-87.
[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6.
[11]梁光德.智慧服务—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服务新理念[J].图书馆学研究,2011(6):88-92.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9.
[14]杨晓农.试论当代知识社会学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J].图书馆论坛,2014(2):1-6.
[15]Delanty.G.Social Science: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M].New York: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7:125.
[16]姚文峰.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教育探索,2004(7):70-72.
[17]T.S.Eliot.传统与个人才能[M].卞之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24.
[18]K.R.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ism[M].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30.
[19]刘向荣.智慧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下一个经济形态[J].商业时代,2010(31):14-15,20.
[20]Nonaka I,Toyama R.SECI,Ba and Leadership:A Unifi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G]// Managing industrial knowledge:Creation、transfer and utilization.London:Sage,2001:43.
[21]蒋永福,张红艳.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哲学四定律[J].图书馆建设,2002(5):20-23,26.
[22]蒋永福.客观知识·图书馆·人—兼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5):11-15.
[23]郭丽英.知识社会:图书馆职能的超越与整合[J].现代情报,2001(2):7-8.
De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Constructivism Views on Knowledge
XU Zheng-xing
After analyzing the new meaning of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in libr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Constructivism Views on Knowledge,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builds the new libr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law on the basis of deconstruction,ded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laws,in order to provide a prospectively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librar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isdom economic times.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intelligence service;constructivism;transform knowledge into intelligence
格式 许正兴.智慧服务背景下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推演与重构——以后现代构建主义知识观为视角[J].图书馆论坛,2015(1):25-29.
许正兴,硕士,任职于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014-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