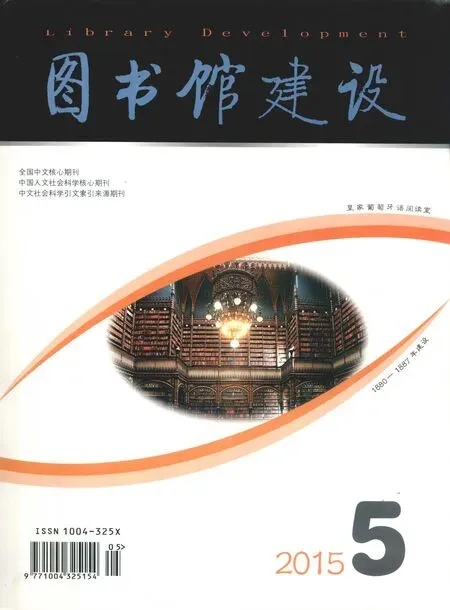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
张书美(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江西 南昌 33002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
张书美(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江西南昌33002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教育经费紧张,民教机关数量有限,无法满足民众教育飞速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势下,图书馆界有识之士发出“将学校图书馆公开”的倡议;国民政府也多次颁布相关法规,倡令学校图书馆公开,以增加社会教育功效。面对时代呼唤,各级学校图书馆积极响应,通过开放阅览、举办图书展览、兼办民众图书馆等路径,将本校图书馆公之于众,收效良好。
学校图书馆社会公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实施以“唤起民众,训练民众”为目的的民众教育①。民众图书馆因具有“全民共享、开化民智、民众参与”等特征,而迅速成为民众教育的重要机关。但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经费紧张,民众图书馆数量有限,无法满足民众教育飞速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势下,图书馆界有识之士发出将“书可尽其利,人可厌其欲的教育机关——学校图书馆公开”[1]88的倡议;民国各级政府也多次颁布相关法规,倡令学校图书馆公开,以增加社会教育功效。面对时代呼唤,学校图书馆积极响应,通过开放阅览、举办图书展览、兼办民众图书馆等路径,将本校图书馆公之于众。此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众图书馆太少的矛盾,促进了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其经验对当代学校图书馆的公开亦不无借鉴价值。
1 原 因
学校图书馆本是为一个学校所附设、所独有,专供校内师生阅读图书、参考材料、研究学问之用的机构。但因种种原因,学校图书馆亦有对社会民众公开的实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校图书馆就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面向社会公开。
1.1学校兼办社会教育需要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虽然在当局的推动下,民众教育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因社会教育经费紧张,民众教育机关数量有限,无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教育部为推进民众教育事业的发展,曾命令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目的在使“社会受学校之益,而除旧布新;学校受社会之益,而扫其迂腐,益趋精富。社会学校互相受益,互相策勉”[2]。在当时教育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若各学校都要另起炉灶来兼办社会教育事业,不但客观形势所不容,而且亦不符合教育当局提倡原旨。教育当局鼓励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乃是希望学校将原有的教育工具,如教室、体育场、图书馆等设施酌量公开,这样在不影响学校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民众也得以享受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民众教育事业发展。而在学校可供开放的几项教育工具中,教室、体育场的公开有时间限制,只有图书馆可以随时随地迎接民众。所以,将图书馆向社会公开,无疑是于学校本身最稳妥、最轻而易举、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学校通过图书馆的公开,也算是兼办了社会教育,走上了与社会教育合作的途径。
1.2图书馆界积极呼吁
如果说学校兼办社会教育需要是学校图书馆社会公开的外在动因,那么图书馆界的积极呼吁,则是学校图书馆社会公开的内在驱力。1933年,在民国时期图书馆界影响力最大的职业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上,上海民立中学图书馆提出“酌量公开学校图书馆俾学校图书馆与社会合成一气补助成人教育”案。此提案经大会修正议决通过,并议出“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函请各校图书馆酌量开放,供给校外人阅览”的实施办法[3]。上海民立中学图书馆之所以提倡学校图书馆公开,原因在于,“学校图书馆大都专供一校自己之师生阅览,不肯公开给校外人借阅,在公共图书馆多的地方,原非必要,而在少的地方,或竟然尚未有的地方,如学校图书馆不公开,凡离校以后之青年成人,而在业余时间再欲自学,势所不能矣。如是,社会进步亦难免横生阻力。故使学校图书馆公开,并可教育成人,儿童与成人均有充分教育,社会斯有进步,国家方能强盛”[3]。上海民立中学图书馆的提案,代表了当时图书馆界的认知,折射出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一种社会担当。
1.3国民政府大力倡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图书馆向社会公开,除了以上两个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民国各级政府大力倡行。在这其中,又以教育部致力尤多。对于此点,《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0卷第3期上曾有专文介绍,“教育部以值兹提倡普及教育及体育运动之际,对于各种民众教育极为注意。除已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调查各地图书馆及民众教育状况外,兹又谋普及与便利民众阅报起见,决定由该部社会教育司起草计划,令全国各级学校当局将各该校之图书馆及体育场一律开放,任民众参阅书报及运动,该项计划,刻草拟中,一俟审核完毕,即行通令各省市施行”[4]。
此后,教育部于1941年2月24日公布《普及全国图书教育办法》,其中第6条规定:“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附设之图书馆应一律开放,供民众阅览,开放办法另订之。”[5]331941年6月3日教育部又公布了《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设置图书馆(室)供应民众阅览办法》(共9条)。对学校等机关团体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开放办法、工作内容、工作职责等都有明确规定。例如,在开放时间上,规定“各图书馆(室)除有特殊情形得另订民众阅览时间外,应于每日开放时间,允许民众入内阅览”[5]28;在开放办法上,规定“各图书馆(室)如规模较大或具专门性质者,应将普通参考书籍供社会人士阅览外(借阅办法由各图书室自行规定),并应将通俗书刊及日报提出1部,专辟民众书报阅览室,供民众阅览”[5]28;在工作内容上,规定“各图书馆(室)应将每日规定开放时间或民众阅览时间,通告周知,广事宣传劝导,并应举办民众读书会读书竞赛等,以提高民众读书兴趣”[5]28;在工作职责上,要求“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应轮派职员协助图书馆(室)主管人员办理及指导民众书报阅览事宜”、“各图书馆(室)应备民众阅览登记簿及各种表册,以备查考”、“各图书馆(室)应于每年度终了时,将本年度开放民众阅览工作,编具报告,送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备案”[5]29。
除国民政府倡令学校图书馆社会公开外,地方政府也积极倡行。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广东省教育厅于1939年颁布的《令各学校办理图书公开,以增加战时社教功效》,广西省政府于1940年颁布的《广西省普设民众图书馆计划》。如果说在教育部等政府相关法规颁布之前,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是一种自主性行为;那么在相关法规颁布之后,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就变成了一种政府主导性行为。也正是有这层法律约束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才会全面展开,收效良好。
2 意 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于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朝野意见一致,可谓不谋而合。先是图书馆界积极提案,发出倡议;继而教育部连发数文,明令“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附设图书馆(室),应一律开放,供应民众阅览”[5]28。朝野如此默契,实因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有着重要意义。
2.1有利于发展学校教育
虽然国民政府竭力提倡学校教育要与社会教育合作发展,但事实上众多学校,都只是打着与社会打成一片的幌子,依然故我地与社会隔绝着。以致学校培养的人才不符合社会的需要,甚至与社会格格不入。同时,由于学校与社会难通声气,也易导致社会民众对学校的误解。凡此种种,皆不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如果学校公开图书馆,则不但可使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一层隔膜除去,使学校认识社会,依之可以在管理上、教育上尽量改进,以实现社会化的目标;而且可以使民众有目共睹,有耳共闻,学校的确在改良教材,改善教学方法,为国家造有用之材。到那时,民众对学校的质疑和误解自会消除,学校教育自会得到社会民众的支持。
此外,学校公开图书馆也促使学校图书馆进行改良,从而间接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过去学校图书馆不公开,图书馆管理人于学问上不知求上进,于方法上不知求改善,而只是将图书分类编目、流通阅览,就算尽其能事。但若是学校图书馆一公开,工作人员就不得不努力去做读书指导的工作,不可能再如往昔一样消极地供人需求。如此,学校图书馆的改良及学校教育的发展,自在不言中。
2.2有利于激励学生学习
民国时期学校教育还不普及,很多人因为经济及时间因素不能到校求学,只有部分幸运儿可享受在校的幸福生活。可是这批幸运儿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明白学校幸福生活的来自不易。不论校规如何严,教师如何紧,大半学生还是做他们所想做的,将宝贵的光阴浪费于谈笑嬉戏之中,殊为可惜。这些学生之所以会虚掷光阴,主要是他们没有体验到社会民众生活的疾苦所致。如果将学校图书馆公开,就可以使在校学生受到社会上那些边谋生边利用余暇来学校图书馆自修者的感化,自警自励,努力求学。此外,学校图书馆的公开,也使得学生有了常与外来民众共读的机会,学生俨如过着真正的社会生活一样,因此能洞察社会之需要,明白解决民间问题的方法,而来求切合实用的学问。此于学生未来置身社会,亦是大有益处。
2.3有利于推动民众教育
民国时期不在学校受教育的民众,之所以养成坐茶馆、进酒肆的习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地方上没有正当的娱乐,没有高雅的地方可去。现在若将“学校重地,闲人莫入”的禁牌取消,将学校图书馆公之于众,无疑可使民众得到一个优质的教育环境,可以享受正当的消遣时光。此举对于民众智能上的长进,对于民众沉静、和平、守秩序等美德的养成都将有所裨益。这是因为环境与读书兴趣有着莫大关系。例如,任职图书馆事业者天天在书海里遨游,对于图书终是要翻翻看看,这是环境使然。而民众对于读书兴趣不浓厚,原因是少与图书为友。如果将学校图书馆公开,允许民众入内,与图书为侣、学生为友,则此良好的读书环境自然可以提高他们的求知兴趣,而且因学生参考研阅图书的影响,也会使民众自己觉得知识浅薄,相形见拙,继而见贤思齐,奋以求知[1]90。此情此景下,发展民众教育自是水到渠成之事。
综上看来,若将学校图书馆向社会公开,一则可以打破民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隔阂,二则可以使学校学生和社会民众均受其利。所以,在国民政府欲改进学校教育和推行民众教育的紧要时刻,将学校图书馆向社会公开,真是一举而数得。
3 路 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民众教育快速发展的情势下,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也显得格外迫切。但学校图书馆究竟如何公开,以达“便利民众,促进社会进步”的初衷,各级学校可谓是各显神通。
3.1开放阅览
开放阅览应该算是学校图书馆社会公开中最简单易行的一种方法。因为学校无须多费思量,只需将图书馆大门打开,欢迎民众前来阅览即可。据笔者查考,民国时期最早实施学校图书馆开放阅览的是成立于1910年的武昌文华公书林。该公书林由美国人韦棣华女士筹办,韦女士将文华大学的中西文图书,采用开架形式,公开陈列,“凡武汉三镇各机关、各界人士皆可应用,自由阅览”[6]。文华公书林的开放精神从此传承下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亦在战时公开,供民众阅览。1938年,国立中山大学西迁至广东罗定,图书馆特设民众阅览室,陈列普通图书两千余种。“当地民众有谓生平从未见有如许图书者,馆内悉挂,各种抗战图画,由馆员对民众讲评,乡中男妇老幼无不齐集”[2]。据该馆工作报告,平时到馆阅览者,1940年度48 521人,1941年度65 551人,1942年度100 781人,可谓盛况空前[2]。
如果说文华公书林和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是大学图书馆公开的范例,那么私立长沙妙高峰中学南轩图书馆及吴兴县立后林二礼小学图书馆则是中小学图书馆公开的楷模。妙高峰中学南轩图书馆成立于1926 年 10月,发展至1936年时,藏书已达近 3万册左右,期刊 400 余种[7]。南轩图书馆除了对本校师生开放外,还兼对社会人士开放,影响盛于一时[7]。由戴季陶创办的吴兴县立后林二礼小学,该校原有图书八九百册;1934年2月,戴季陶又慨助图书500多册;“现闻该校不欲私之于一校,略加整顿,即定开放借阅办法,以期普及一般民众云”[8]。
学校图书馆开放阅览可能会对学校治安及本校师生利用图书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如果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提前干预,这些问题都将会迎刃而解。例如,将民众常阅书报置于一室,与师生分开阅览等都是可行的解决方法,且社会成效显著。
3.2举办图书展览
学校图书馆开放阅览虽然能带给民众甚大方便,但它并不能满足特殊时期、特殊节日图书宣传的需要,如抗战时期抗战救国方针的宣传等。因而,学校图书馆除在正常开放阅览外,还需举办有针对性的图书展览,以应时需。民国时期学校图书馆在举办图书展览、服务社会的实践中,做得比较成功的首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该校图书馆最早于1929年就将图书公开展览,内容丰富,成绩斐然,大为社会人士所赞许[9]。时至1937年抗战军兴,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即感到宣扬战时文化及推行战时教育的重要,故即在馆内举办“战时图书展览”,陈列各种有关抗战的读物,编造各项抗战材料索引和统计,以供众览。又为普及民众起见,曾在中山大学附中及省立民众教育馆分别举行,阅者八千余人[9]。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迁坪石后,校址甫定,图书馆民众阅览室即设于镇中心,每周编贴壁报,介绍新书及新闻摘要、科学常识、时事短论,并举办关于全国总动员、我们的领袖、国际名人传、战时经济、中山文库、抗战史料等专题图书展览。
在抗战军兴时刻,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战时图书展览不仅“便利了广州文化工作者工作上的参考和普遍提高民众对于抗战认识的水准”[2],而且在民众因战事影响,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无着,精神粮食陷入饥荒的状态下,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适时进行图书展览,也给民众带去了精神上的慰藉。因而,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战时图书展览得到社会广泛好评。例如,1938年5月10日《广州日报》如是评价,“我们希望广州的公私文化机关,都动员起来,搜索战时图籍,不断的举行展览”[2]。
3.3兼办民众图书馆
因民众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学校图书馆在采取开放阅览、举办图书展览等社会公开形式外,还兼办民众图书馆,以应时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该馆在1929年4月商承当局暨研究实验部之意,于无锡城北江阴巷设立民众图书馆;由于经费较充裕,得尽量添购新书[10]。到1932年度终,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所藏图书已达17 100余册,价值2 400余元;又得赵叔愚先生遗书两千余种,张景琨先生遗书一百八十余种,另架庋藏,以志纪念[10]。由于该馆图书丰富,按月到馆之刊物亦不下五六百种,而且又实行开架式服务,所以流通率日益增加,“当时来馆读书阅报听讲或参加民众组织及教育活动之民众,不仅及于全城四门,更及于乡间,天下市刘谭桥等处”[10], “每日到馆阅览人数计平均为一百二三十人”[11],社会影响盛极一时。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除做好日常流通阅览工作外,还积极编辑“教育论文索引”,按期发表于《教育与民众月刊》上,对读者嘉惠多多。同时,为谋各实验区及实验机关之需要起见,该馆意欲实行巡回文库及谋建新馆,“尽量搜集相当图书,以备对外绝对公开,使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打成一片”[10]。可谓法美意良。
此外,广西省政府为“加强国民基础学校成人教育”[12]、“推广文化运动使普遍深入乡村”[12]起见,于1940年5月颁布了《广西省普设民众图书馆计划》。其要求本年度“每中心国民基础学校设置民众图书馆一所,计全省应设置2 302所。每所配备基本图书一套,并另按乡镇校每乡镇各发一套,均存放于各该乡镇中心校之民众图书馆,以后仍须逐年扩充”[12]。广西各级学校民众图书馆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广西省国民教育运动的进行。
4 成 效
4.1推进了民众教育发展
民众教育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项重要施政方针。围绕这个主旨,国民政府采取种种举措,其中包括倡令学校图书馆的公开。虽然现在还统计不出究竟有多少民众曾受惠于学校图书馆,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民众教育机关数量很有限是确确实实的事。据教育部1931年公布的《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显示:1930年,我国共有各类图书馆2 935所,其中民众图书馆为575所[13]。如果加上与民众图书馆性质相似的社教机关附设图书馆331所,民众图书馆总数也仅为906所[13],还远远不能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
在此情势下,要使社会上的民众不论贫、富、贵、贱,程度高低、深浅,都可以到合适的地方去自学自习,“使在受学校教育者,获得辅助其智能之生长力;使未受学校教育者,得启发其智能之生长力;使曾受学校教育者,得继续其智能之生长力”[1]88。这个使命的完成,确是“有待于全国各级学校图书馆的公开,来共负其责的”[1]88。因为“大学图书馆公开,则可以展览图书;中学校图书馆公开,则可以指导读书;小学校图书馆公开,则可以联络家长;使各种人来阅览、参考、研究,此不啻天天在干识字运动的工作,也就是天天在施全民的教育”[1]88。 所以,学校图书馆的公开对于民众教育的推进是不言而喻的。民众图书馆学家徐旭先生不禁慨言,“若能将全国大、中、小,各级十四万四千余的学校图书馆或阅书报处公开,则不啻于短时期内,骤添设了这么多的民众图书馆,此予民众教育之助力,是何等地大啊!”[1]88
4.2增加了战时社教功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加剧了侵华的步伐。为了保家卫国,中华大地掀起了抗战热潮。文教界积极声援,开展起本位救国行动。1939年,广东省教育厅为了增加战时社教功效,曾命各学校办理图书公开。令称,“广东省教育厅以抗战期间,战时教育关系全面抗战甚巨,该省内大中小学校,虽属遍设,但以文化水准低落,教育不能普及之我国情形观之,实不足供应社会需要。从前学校所有图书,及一切之科学参考实验品等,均为供应校内学生所用,对于校外民众,完全隔绝,为推行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重期间,特饬该省内各大、中、小学校对于校内所藏图书仪器等校品开放,准许民众参观,并于可能范围内准予借用,以期校外民众得有参阅之机会,而增加战时社会教育之效”[14]。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在杜定友先生的主持下,亦以兼办社会教育事务为己任。特别在抗战军兴后,为及时宣扬战时文化及推行战时教育,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在馆内持久举办“战时图书展览”,收效良好。对此,“中大乡导学术新潮社版”曾有报道:“前不久,教育部通令各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直到现在,还不见有什么成绩表现,而中大图书馆对于社会教育的顾及,是很可注意的;抗战发生后,该馆先后举办了战时图书展览,编印战时书目及地名索引,举行职业教育化运动,在南岐江有战时图书阅览室,现在坪石又成立民众阅览室,这种教育作用很大,而且也是很深入的。”[2]
5 结 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情势下,将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视为当务之急。为了扩大社会教育途径,时人发出将学校图书馆向社会公开的倡议;国民政府也颁布相关法规,予以倡导。各级学校肩负时代使命,积极采取措施,面向社会开放,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民众教育的发展,以及战时社教功效的增加。事实上,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问题,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重要议题,也是我们当今社会需要认真思考的时代命题。教育部虽于2002 年、2003年分别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 修订 )》和《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修订)》,鼓励各地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图书馆尽可能地向社会读者开放。但由于管理体制及长期形成的封闭式服务等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学校图书馆还处在一种与公共文化服务绝缘的状态,社会民众很难享受到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15]。其实,无论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还是技术设备的先进性来说,我国当今学校图书馆的社会公开条件已趋成熟。只不过是万事俱备,只欠“学校图书馆人的服务理念转变”这个“东风”罢了。
注释:
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二词基本上是通用的。因此,在本文行文中,有“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用词的替换现象。
[1]徐旭. 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M]. 上海:中华书局, 1935.
[2]杜定友. 社会教育与民众图书馆[J]. 社会教育辅导, 1944(3):16-19.
[3]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 酌量公开学校图书馆俾学校图书馆与社会合成一气补助成人教育案[R]. 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报告, 1933:56.
[4]教育部. 教部通令各学校开放图书馆[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10(3):12-13.
[5]河北大学图书馆学系. 图书馆法规文件汇编[G]. 石家庄:河北大学图书馆, 1985.
[6]邹华亭, 施金炎.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17.
[7]沈小丁. 民国视野下的湖南地方图书馆事业[J]. 图书馆, 2009(1):129-132.
[8]中华图书馆协会. 吴兴县立小学图书馆公开[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4,9(5):29.
[9]中华图书馆协会. 中山大学图书馆展览图书[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3,9(3):35.
[10]中华图书馆协会.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4,9(6):17-18.
[11]姜和, 胡耐秋, 朱秉国. 本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半年实习计划[J]. 教育与民众, 1931,2(3):1-14.
[12]广西省政府. 广西省普设民众图书馆计划[J]. 广西省政府公报,1940(795):3-4.
[13]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十九年度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M]. 南京:[出版者不详],1931:前言.
[14]粤教厅. 令各校办理图书公开以增加战时社教功效[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14(2/3):19.
[15]倪晓建. 学校图书馆应对公众开放[J]. 北京观察, 2012(2):43.
张书美女,现工作于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Social Publicity of the School Library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ocial education fund was relatively tight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quantity of the mass education organ was limited, and could't meet the nee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education. In this situation, experts in the library circle issued an initiative of opening the school librar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lso issue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make the school library ope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ocial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the face of the times' call, all levels of the school library made a positive response.They opened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open reading, holding the book exhibition, helping to operate the popular library, which had good results.
School library; Social publicity;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G259.29
B
2014-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