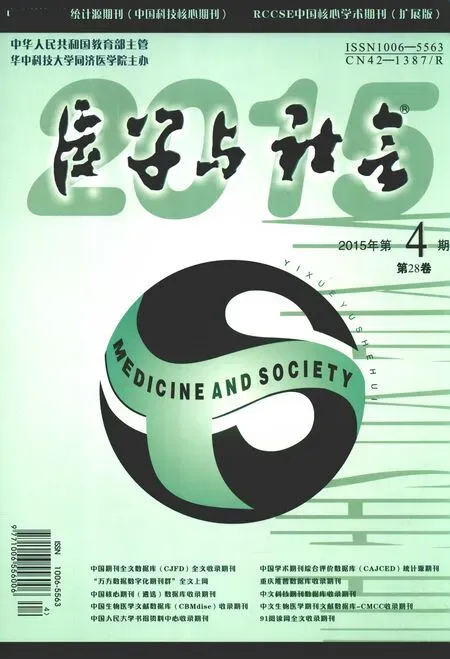我国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研究
何 心 张 雪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81
对于大多数的医疗纠纷而言,由于医疗侵权而造成的医疗损害居于多数,而造成的损害往往是由于医护人员存在过失。在罗马法中,过失指“行为人怠于注意,即行为人本应注意、又能够注意因而造成的不良后果”[1]。我国学者将“过失”定义为行为人应注意且能注意的,而未注意的,或是无法达到普通的、正常的有理性之人所应达到的谨慎程度[2]。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将医疗过失责任细化为医疗技术过失责任、医疗产品过失责任和医疗伦理过失责任。笔者认为,医疗技术过失是指医护人员在对患方的诊疗过程中(包括问诊、选择和实施诊疗方案、追踪病情以及术后护理等),不符合医疗领域内当时的技术水准,或是在此过程中存在技术或专业知识的懈怠或疏忽,医疗技术过失在医疗损害案例中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对于医疗过失的研究和解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 我国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
1.1 抽象标准阐释的缺失
在学者提出医疗技术过失研究标准这个概念以前,我国的医疗技术过失认定都未确立统一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首次将医疗水平作为认定医师注意义务的标准,即医疗事故发生当时业内所能够达到的、一般的医疗技术水平,既不是以最顶端的医学水平为标准,也不是以技术最低的医护人员水平为标准。此立法中将时间作为抽象标准的影响因素考虑到了条文中,实则是一大进步。但是,还有其他很多额外因素,如由于地域差异引发的医疗技术水平差异;经济发展不均衡引发的医疗条件差异;不同专科医院之间、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的差异,以及一些紧急状况(如医疗资源十分紧张而导致医生分身乏术,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一位病人的病情上而造成医疗过失的情况)等,都会对医疗过失的认定产生影响。该法条在起草的过程中曾经考虑到了地域因素对于诊疗义务的影响,具体表述为:对于医护人员的注意义务标准,应当适当将地域因素、医疗机构级别、医护人员自身素质等因素列入考虑范围之内,但该表述在审议时却将其删除,只将“当时的医疗水平”所保留,单独成条[3]。
1.2 具体标准缺乏系统性及规范性
判断医护人员是否违反医疗技术过失的具体标准是指医护人员在对患方的诊疗过程中(包括问诊、选择和实施诊疗方案、追踪病情以及术后护理等),根据类型而划分的不同的具体义务内容,如手术、麻醉、用药、护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将判定医疗技术过失的具体标准范围规定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有关诊疗规范中,违反以上文件内容致患者发生损害结果的,即视为存有过错。事实上,医疗法律法规和规章一般并不规定医方在诊疗过程中的具体义务,而更多体现在“其他诊疗规范中”,而医生即使遵守诊疗规范,也不一定就未违反注意义务。对于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大多都零散在各个医疗指南中缺乏整理。由于没有规范化、系统化的具体标准。加之,法官医学知识有限,对于医疗纠纷,尤其是医疗技术过失的认定也就无法依据规范的、系统的具体标准进行裁决,从而不得不依赖于其他鉴定部门的认定意见,这有失司法的独立性。
1.3 实践中法官过度依赖医疗技术过失的认定意见
认定意见又称鉴定意见,法官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过程中对于法律专业的问题自然不在话下,但对于医疗技术过失认定这个医学方面的专业问题,法官则显得无从下手。因无法律层面的具体化、规范化标准,加之,法官对于医学专业术语一知半解,无法对认定意见内容是否正确进行审查,只能对认定意见的法律逻辑进行形式上的大致审查。而鉴定机构的良莠不齐,以及其资质的不确定性,极大影响了当事人对于认定意见的认可度,从而严重影响司法系统在百姓心中的公正性与权威性。认定意见对于医疗损害案件结果的影响十分巨大,地位十分重要,本来脆弱的医患关系及复杂的医疗纠纷,因患方对于认定意见的质疑显得更为紧张。
2 国外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
国外医疗纠纷一般大都以侵权的维度进行调解,医疗过失认定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因侵权法发展而逐渐被关注。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问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棘手的复杂问题,国外学者对于医疗过失的认定标准问题研究较早,已经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相对完善的医疗过失认定标准和规则,并在自己的法域内发挥其作用。国外立法主旨大同小异,但立法的细致性、严谨性、逻辑性及规范性方面都十分值得我们思考及研究。
2.1 英美法系
英国作为典型的判例国家,其注意义务标准的规则同其他规则相同,都是通过大量的判例来确立的。1957年的 Bolam v.Frie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案是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的里程碑案例,奠定了英国最早期的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基础。Bolam Test标准的认定原则包括几方面。①一般性。医护人员的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是其在提供诊疗服务过程中,所处于的专业领域中一般性的医护人员所具有的普通性的技术、知识和注意水准,即,既不是该领域中最优秀的医护人员的技术、知识和注意水准,也不是该领域中最没有经验的医护人员的技术、知识和注意水准。②存在性。医学科学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理论及实践的百家争鸣,很难有统一或一成不变的观点。若医护人员所提供的诊疗服务行为得到其中任何一种理论或实践观点的支持,很有可能证明其无过失;同理,若医护人员所提供的诊疗服务行为不符合各学说的其中任何一种理论或实践的观点,其很可能被证明违反了注意义务,即存在过失。③特殊性。医护人员提供的诊疗服务行为即使符合业内普遍的理论或实践观点,因医疗行为涉及至高无上的人的生命及健康,具有特殊性,所以不能因此作为该医护人员行为不构成过失的绝对证据而判定被告无过失[4]。
英国对于初级医师因欠缺经验所犯错误时,与德国法基本类似,也以同样严格的标准评价。经典判例 Wilsher v.Essex Area Health Authority中,一名初级护士对于一名婴儿的血氧含量的检测失误,使其血氧过度饱和,最终导致失明。法官的判决阐明:对于法律来说,无论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医生,都应以同一标准对待。否则,在此类诉讼中,经验的欠缺会被援引成抗辩事由。英国法对于抽象标准考虑到了地域因素与医院类型因素,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些许差别,这是被法律所容许的。英国法对于“紧急”要素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在Wilsher案中,法官论述:若医院资源有限,医生同时着手多个患者的多件病情,其中一件稍有差池则不被认定为过失[5]。
同属于英美法系的美国法,对于医疗技术过失标准的认定与处理同英国法相类似,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美国法律没有专门的医疗过失单行成文法,法院对于医疗诉讼的审理大多以侵权行为法为依据,尤其是“过失侵权”的相关规则。①可接受的做法(The Accepted Practice),还是习惯做法(The Customary Practice):美国学者对于医护人员的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是以可接受的做法为准,还是以习惯做法为准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医护人员在提供诊疗服务过程中的注意义务标准以可接受的做法为准[6]。可接受的做法是指:以医疗领域内的合乎理性的、获得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A reasonably competent Member)所期望的可接受的做法为准。②尊重少数派学者观点的规则(“Respectable Minority”Rule):医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具有复杂性及多样性,因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诊疗方案才是最合适的诊疗方案或方法较难抉择[7]。对于法官来说,对于各个互相冲突的观点进行抉择时,他们很难做出评判。对于医学科学的百家争鸣,尊重少数派学者观点的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应用。
临床路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随后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先后应用临床路径诊治患者,目前临床路径已在全球得到广泛认可与重视。美国在2004年发起一项名为“挽救10万人”活动,该活动通过以科学的标准和程序降低在医院中,病人因不合理的措施造成的死亡率。该活动提出一系列方案,包括“呼吸机组合措施”,预防肺部感染;为急性心梗病人提供循证医学诊疗服务,预防因心脏病突发造成的死亡;“中心导管措施”,预防血液感染。该活动持续的两年时间内挽救了超过12万人的生命,也掀起了医院应用临床路径提高病人安全保障的高潮[8]。
英美法系对于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的研究讨论主要集中在怎样阐释和认定“合理”二字,并以此为核心进行不断的改进与丰满,直至形成强大的逻辑体系。围绕“合理”二字的核心通过Bolam标准和“可接受做法”进行基础性的阐释,形成内核;在此基础上的其他特殊因素认定标准,如地域、医院级别类型、紧急要素等,并对某种因素是否能成为认定标准被援引为抗辩事由做出衡量,如医护人员经验等,以丰满内核,弥补内核的漏洞与不足之处。
2.2 大陆法系
在日本,“医疗水准”理论作为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风靡日本学界。1961年的“东大输血感染梅毒案”引发了日本学者对医师注意义务标准采用“医学水准”的强烈不满。在该案中,因供血者出示血液介绍所的证件及合格证书,依据当时的临床普遍惯例,采血医生未向供血者询问及确认是否有感染梅毒的可能性。然而,该供血者已经感染梅毒。事实上该供血者是在检查之后,即报告未出来之前感染的梅毒。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医学作为救死扶伤的科学,医护人员的诊疗行为是管理最为至高无上的人的生命和健康,所以应当承担也必须承担防止损害结果发生的最大注意义务”[9]。该案首次提出,医疗水准不一定与平均医师的医疗习惯一致,不能认为其符合医疗惯例就不违背医疗水平的注意义务。而在1974年早产儿视网膜病案中,法庭的判决提出最大注意义务的观点:即使某种医疗方法尚未得到医疗界的普遍认同,医护人员为了患方的健康,也应当实施,此谓医护人员应尽的最大注意义务。此判决立即引发日本学界的轩然大波。学者松仓丰治教授首先提出,“医学水准”不应该作为医护人员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认定标准,而应以“医疗水准”取而代之,即“医护人员实行诊疗行为当时的普遍的医疗水平是其注意义务的内容”[10]。该学说立即得到各方人士的一致赞同,并在“1982年高山红十字会医院案”中被法庭所采纳。目前,医疗水准说被日本学界普遍接受与赞同,并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广泛应用,且该认定标准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有着专门处理医疗过失诉讼的第六法庭,该法庭已经积累了在此领域内的处理一系列纷繁复杂案例的经验。对于抽象注意义务标准,德国的要求更为严苛,出发点在于《民法典》第二七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必须尽到“社会所要求的注意水平”。医生须证明自己尽到了“一个值得尊重的、勤奋不苟的,具备相关领域平均技能的医疗职业人士”的注意标准[11]。所以,作为救死扶伤的特殊职业者,医务人员须努力掌握新技术,了解新文献,以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一个初级医生应当意识到患者有可能因为他的经验缺乏而面临风险损害,其应当果断停止治疗,请求高级别医生进行诊疗,其个人的技术缺陷不能成为免责事由;且对于高级医生,其技术级别越高,所受的注意义务标准就越高,若在诊疗活动中未能充分使用其技能,则判定有过失。德国法兼顾了医务人员的级别、年龄等特点,使得抽象标准更加严谨细致,但某些细节问题上也体现了德国法较其他法律更加严苛。
大陆法系的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有较为规范的体系化。一方面,对于认定标准的内涵进行了细致合理的阐释,如日本确定为“医疗水准”,德国为“社会所要求的注意水平”,并通过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探讨,对其他可能影响医疗技术过失的认定因素尽可能的列举,进而逐一分析。另一方面,在程序上通过设立专门的处理医疗过失类案件的部门或法庭,足以体现大陆法系国家对此方面的重视程度,也表明了医疗过失类案件确实较为复杂和棘手,需要专业人士进行专门处理。
3 完善我国医疗技术过失认定标准的对策
3.1 规范医疗技术过失抽象认定标准
明确“当时医疗水平”概念,采取“合理的专家的标准”,也即“合理的医师”,医护人员在诊断和治疗时以当时普遍的、合理的、社会所要求的,并值得肯定的医疗水平为标准。医务人员的诊疗注意义务不仅要有基础的标准,即达到整个社会普通的医疗水平,还要体现差异化标准。对于诊疗注意义务达到普通水平标准而言,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国家医院分级等级制度、国家诊疗常规体系,都是以国家标准而严格实行准入制度,这对于抽象标准达到了基础的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医事行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对于医学技术创新和提高,医护人员诊疗义务还应该体现一定的差异性,尽量多方位、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即对于抽象标准要考虑时间的紧迫性、地域的差异性、医疗的专门性以及医学理论的多元性[12]。因此,医护人员应不断学习、追踪新文献,保持知识技术水平的先进性,从提高自身素质做起,从而推动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
3.2 整理和完善医疗技术过失具体标准
医疗行为之过程可分为对疾病认识过程及基于对疾病认识所采取的对应措施。与之对应的具体医疗注意义务是指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包括问诊、选择和实施诊疗方案、追踪病情以及术后护理等)所实施的具体医疗行为,如问诊、输血、麻醉等,应符合医学指南、规范或准则等所要求的必须遵守及必须注意的义务。医疗技术过失具体认定标准进行整理和完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建立临床路径。临床路径是指卫生部或医学权威机构部门专门为特定的疾病整理归纳出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系统化的治疗流程,以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为指导来促进治疗、管控疾病的方法,最终起到规范医护人员诊疗行为、减少副作用、将时间成本及经济成本降至最低并提高诊疗质量的作用。临床路径的实施使得针对某种疾病医疗技术过失的认定标准类型化,一方面,医护人员可以就此路径科学地实施诊疗行为,患方对于自己疾病所接受到的诊疗行为经过临床路径的比对也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亦可以通过临床路径直接明了地审查医护人员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目前我国已制定上百种临床路径,为医护人员的诊疗行为提供规范化的诊疗模式。
3.3 专家辅助人制度和专业法庭对医疗技术过失认定的辅佐
法官在面临专业问题时,一般需要专家证据。目前对于医疗损害纠纷案件的专家证据大多是由鉴定机构出具一份认定意见,无专家到庭接受双方质询。这不仅使当事人双方无法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询,而且对于不擅长的医学知识法官来说也无法当面质询,只能对意见进行逻辑问题排查。司法实践中的专家提供鉴定意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聘请专家在法庭上对某些问题发表意见,二是由专家(机构)就某个事实进行认定。可见,出具纸质认定意见并不是法院借助外力对医疗技术过失判断的唯一方式。专家辅助人制度可以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有效补充甚至替代,让专家当庭接受当事双方的质询,不仅使法院最大可能公正、公平、专业地对待认定意见,还可弥补集体做出认定意见难以追责的弊端。对于法庭则有利于法官简单明了地认定医疗技术过失,大大提高效率,节约了当事人双方及司法系统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无疑是维护了各方利益的。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设置了专门处理医疗过失诉讼的第六法庭,日本东京和大阪地方法院也新增了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类案件的处理部。在我国,地方法院的法官专业人才较为缺乏,其医学知识的欠缺,使其不得不依赖医疗鉴定结果,所以法院应当选拔培训具有医学专业和法学背景的法官组建专业合议庭,对医事案件进行审理。鉴于我国这方面人才较少,如今已加大了培养一批具有医学和法学学历背景的跨学科人才的力度,但与迅猛突发的医事侵权案件还相差甚远。因此,相关机构应加紧培养更多的医学法学人才,为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专业的后备力量迫在眉睫。
[1]Tony Weir.A Casebook on Tort(10 thedn)[M].London:Sweet& Maxwell,2008.
[2]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3]马辉.论医疗水准的确定[J].法学杂志,2010,3(3):25-28.
[4]Peter Vanezis.Medical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M].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2013.
[5]John Weir.Street on Torts(10thed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6]Hongjie Man.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M].Berlin:Heidelberg,2013.
[7]Jackson.Professional negligence:first supplement to the fourth edition:up-to-date until December 19,1997[M]London:Sweet& Maxwell,1998.
[8]Lars Noah.Medicine's Epistemology:Mapping the Haphazar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the Biomedical Community[J].Ariz L Rev,2002,44(2):373 -466.
[9]夏芸.医疗事故赔偿法——来自日本法的启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0]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改革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成功与不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10-13.
[11]松仓丰治.怎样处理医疗纠纷[M].郑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12]Marc Stauch.The Law of Medical Negligence in England and Germany[M].London:Hart Publishing,2008.
[13]张雪,尹梅.医疗过失认定标准之比较与借鉴[J].学术交流,2013,7(7):57 -59.